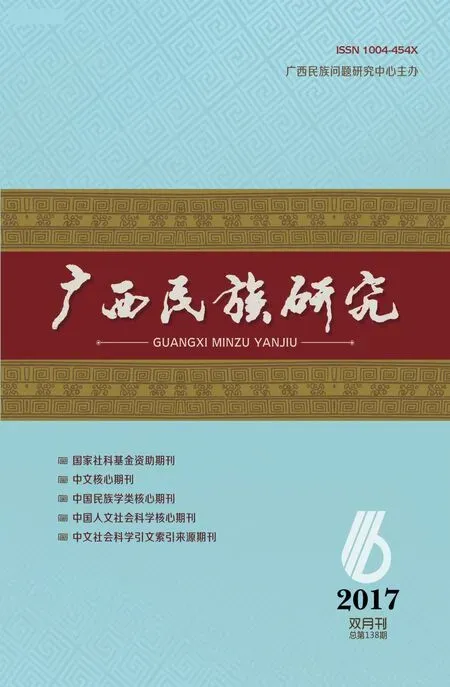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实现保障研究*
许锋华 徐 洁 刘军豪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实现保障研究*
许锋华 徐 洁 刘军豪
职业教育的生产性特征、大众教育倾向、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及在“投入—产出”方面的优势性价比,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适龄学生具有更为实际的吸引力。这些功能与优势赋予职业教育参与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以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时代使命。作为一项根本性与长远性的精准扶贫方式,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制体现为转变片区贫困群体的价值观念,提升片区贫困群体的知识文化水平,丰富片区贫困群体的成人成才途径,以及推进贫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的特色化发展。做好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顶层设计、倡导实施职业教育定向培养模式、推进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是保障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生产性导向;扶贫脱困
为了有效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帮助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民众脱贫致富,习近平在全国第三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此外,教育部等六部门在其协同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也明确提出:“加快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围绕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高职业教育扶贫的精准度。”由此可见,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推进贫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业已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是,拥有“顶层信任”只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功能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职业教育与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仍然需要拥有充分的理论论证与事实说明。唯有如此,才能为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反贫困功能的有效释放构筑坚实保障。
一、职业教育承担着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时代使命
教育是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为根本的扶贫举措,遏制贫困的区域化蔓延以及阻断贫困的代际性传递都需要教育的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是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的关键举措,它因促进就业脱贫与服务区域发展的价值功能而担负着片区反贫困的时代使命。
(一)教育在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主要涉指的是我国境内在地理位置上相连或相近且存在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如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等。一般而言,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致贫因素复杂多样,集中表现为自然环境较差、地域偏远、人力资源匮乏、政策支持有限、基本公共服务滞后等等。故而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扶贫方式的选择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态势,如发展特色产业、加大中央财政支持、移民搬迁……诚然,上述扶贫方式对于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途径并没有从实质上、从长远方面改变片区的贫困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片区的一些贫困人员不愿意摘掉“贫困的帽子”,逐渐滋生出以“等、靠、要”为主要特征的惰性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国家扶贫工作的初衷和成效。即使片区一些贫困户通过外力资助暂时摆脱了贫困,但是由于自身生存与生产能力的不足而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返回到贫困的生存境遇之中,由此而产生贫困“常态化”。[1]因此,可以说,贫困不仅仅是由资源匮乏、地域落后等外在因素造成的,从实质上来讲,贫困的根本生成要素在于人,在于人思想观念的落后与知识能力的不足。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的贫困都是与个人的知识、能力与素养紧密相关的。因为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一切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都渗透着人的价值理想与思维痕迹。正是由于人在认知、思维、能力等方面的不断提升,社会才能得以不断进步。因此,我们认为,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解决片区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也必须从最根本处着手进行批判与反思,亦即需要对人知识素养与技术能力进行全方位提升。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只有经过教育的洗礼才能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才能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求,适应与超越社会发展对人所提出的各类要求。因此,要提升片区贫困人员的知识素养与技术能力,解决片区的贫困问题,就需要诉诸教育实践的伟大力量。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就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因此,教育扶贫是从根本上扶贫。“扶贫先扶智”决定了教育扶贫的基础性地位,“治贫先治愚”决定了教育扶贫的先导性功能,“脱贫防返贫”决定了教育扶贫的根本性作用。[2]概而言之,教育在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扶贫脱困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与先导性的作用。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联合声明所言:“教育和培训有助于人的个性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和培训还可以传授增加收益及创收的技能,帮助人们扶贫脱困。”[3]
(二)职业教育是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的关键举措
作为与经济产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服务最为贴近、贡献最为直接有效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职业教育是一种具有旨在提升受教育者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的智力扶贫方式,它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与高技能专业人才为主要任务。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它瞄准扶贫对象,聚焦重点人群,支持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增强其脱贫致富的能力,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贫。[4]
当前,很多国际组织高度重视对职业教育的反贫困功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发布的《修订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第2条就明确提出:应将技术和职业教育视为“有助于减轻贫困”的一种方法。1974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教育工作文件》特别强调,通过职业教育提供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反贫困的最有效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理应作为增强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而优先得到世界银行的重视与资助。[5]66另外,在国内,我国政府历来就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反贫困功能。1996年修订通过的《职业教育法》第七条就明文提出:“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妇女接受职业教育,组织失业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扶持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发展。” 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把职业教育发展“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当前全社会倡导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更是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可见,无论是从国际社会的理论探索抑或是国内的发展经验来看,职业教育在扶贫脱困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差,自然环境恶劣,更需要职业教育的积极参与。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分布广、扎根深、见效快、后续力长的扶贫特点。分布广,是指职业教育作为片区政府层面出力的教育类型,分布在片区所有的贫困县、乡、村发光发热;扎根深,是指职业教育在物质与精神上,深入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民众的内心,可以得到广大群众力量的支持;见效快,是指职业教育培养人才助力当地产业,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好帮手;后续力长,是指职业教育厚积薄发,培养人才反贫困的力量不仅眼前见效,今后也可成为片区反贫困的核心力量,继续推进反贫困工作。故而,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在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上,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生产性特征、大众教育倾向、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及在“投入—产出”方面的优势性价比,对贫困地区适龄学生具有着实际吸引力。这些功能与优势赋予了职业教育参与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扶贫脱困以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时代使命。
二、职业教育促进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作用机制
习近平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作为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一项根本性与长远性的反贫困方式,职业教育能够纠正片区群体关于贫困的错误观念,提升片区贫困群体的知识文化水平,传授片区贫困群体以谋生致富的技术技能,以及丰富片区贫困群体成人成才途径,继而打破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常态化的窘状。
(一)转变贫困观念,引导片区民众树立积极的脱贫致富观
阿瑟·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指出:贫困现象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更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心理与精神现象,经济贫困总是与文化贫困缠绕在一起,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6]贫困人群在心理态度、思维惯性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已经习惯于贫困的生活方式,甚至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贫困的圈子里。这就是落后的、消极的、不自觉的贫困文化观念。并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越是顽固,他们往往认为贫困是一种常态化存在的客观现象,就算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扭转贫困的问题,因而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阶级鸿沟。这是深层次的贫困问题,也是“精神贫困”的体现。
职业教育是变革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民众精神贫困观念的有力武器,它致力于通过深入片区贫困群体腹地,由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主导部门统筹规划,职业院校努力配合,民众积极参与,校企深度支持,形成农事教育、技术培训、群众科普教育等多种形式并举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采取夜班、集中培训、广播电台等宣传手段,使片区民众全面认识与理解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与作用,继而形成积极的思想观念。换句话说,职业教育能够通过对知识塑造、技能培养、文化濡染的教育宣传遏止片区“甘心守贫”的落后观念,激发其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涵养其脱贫致富的精神动力,特别是对其青少年的脱贫思想教育,尤其重要。[7]总而言之,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关系到当地民众的脱贫致富,关系到成千上万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关系到贫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与稳定发展,为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在片区民众观念转变中的作用。
(二)培育知识文化,打破片区贫困代际传递常态化的窘状
导致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群体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贫困群体本身的知识占有量奇缺与文化认知水平较低,他们往往缺乏获取知识、分享知识以及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与选择权利。在知识与文化支持下日益发展的21世纪,知识与文化早已成为创造财富的重要工具,获取、分享与交流知识途径与机会的匮乏与经济贫困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内在关联性。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低关系密切,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了21.3%;而中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贫困发生率只有7%—8%;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有一半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中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仅有20%左右处于1000元以下”。[8]令人担忧的是,知识文化的匮乏不仅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家庭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也为其后代继承与延续经济贫困埋下了伏笔,由此而产生了贫困的常态化传递与“上代贫、下代贫,代代都贫困”的恶性循环。以职业教育方式参与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过程,一方面即是通过短期培训与继续教育的方式传授下岗片区失业人员、贫困农民等成年经济贫困群体相应的道德文化知识、科技创新知识、产业发展知识等,进而改变其不合理的文化认知偏见,提升其文化认知水平;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通过对接受过初中与高中教育的片区毕业生进行专门化的职业学校教育,进一步深化他们对基础文化知识与职业技能知识的学习,帮助其逐渐成长为具有较高理论知识文化素养的新时代高素质劳动者;再一方面,可以适当跳出地理视域而关注一些特别群体的技能教育,比如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子女职业教育问题,使特困民族地区的骨干发展力量更有提高空间。[9]可以说,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培育贫困群体的知识文化,不仅能够为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民众家庭的脱贫致富创造出路,同时也提升了贫困个体的综合能力与人格素养,继而为阻滞片区贫困的代际传递提供了可能。
(三)丰富人才培养渠道,优化片区贫困学子成才路径
受考试招生体制以及社会偏见的影响,职业教育往往不被人们所关注,甚至被认为是“没有前途、低人一等的教育”,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亦是如此。但是,对于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很多贫困学子来说,职业教育却有着更为实际的吸引力。因为,职业教育是一项准入门槛低、面向社会大众的“人人教育”,它对受教育者的教育背景不做严格要求。也就是说,在我国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别的教育相比,它的包容性更强,是一种准入条件较低的教育。[10]根据教育部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人数为674.44万人。当普通高中与大学将许多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学子拒之于门外的状况下,职业教育则毫无偏见地为片区贫困学子提供了继续学习知识与技能的机会与途径。同时,党和政府逐渐提出并实施了中等职业教育免费的政策,从而为就读职业教育的贫困学子免除了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这一惠民举措大大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此意义上,越来越多的片区贫困学子可以通过入读职业教育成人成才,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家庭的经济状况。例如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巴马职业技术学校,通过短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电焊、电工、五金、酒店服务等,每年将1500名贫困人口培训为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等同于助力约1500个贫困家庭具备脱贫能力;再如武陵山区多个中等职业学校采取与企业、工厂联合办学或开展“订单式”培养,如富士康、长虹集团等,学生就业后月收入大约在3000元以上。[11]78由此可见,虽然普通升学教育在制度与经济等方面对贫困学子形成了限制,但是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足以成为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学子成才与脱贫的优先选择。
(四)传承民族文化技能,推进片区经济特色化发展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与民族技能受到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冲击,正濒临“消亡”的困境,许多反映着民族生命力的传统民族技艺逐渐弱化、凋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技能,而且对于促进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职业教育适宜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与技艺的性质特征。与普通教育不同,职业教是培养民族文化艺术与工艺技能人才的重要渠道,它在办学目标上能够有效地将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与产业经济结合起来。为此,《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要求:“重点支持旅游、民族文化和现代农业等专业性职业院校”“大力培养‘双师型’职业教师师资和民族文化艺术人才、民间工艺技能人才”;另外,《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也要求:“加强民间文化、民族手工业、民族建筑等特色专业建设,培养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人才。”
可以说,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培养民族文化艺术、民间工艺技能人才提供了场地,有利于通过人才支撑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例如,在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由于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县域经济薄弱,贫困面广且程度深,在此基础上发展传统种植型经济难以改变贫困面貌,而发展特色文化与特色技能则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迅速发展。以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当地职校开发了矿泉水产业、香猪养殖业、瑶族特色火麻食品产业等与之特色相关的专业体系,充分发挥了民族地区特色,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良序转型;又如在武陵山片区,生态环境脆弱,承载能力有限,加之山区地貌,无法实现大面积种植,当地职校将培养重心放在林业技术类与畜牧兽医类专业培养人才之上,开发了高山茶叶、烟叶种植培训专业,最终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特色化发展。
三、保障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策略思考
职业教育肩负着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教育责任和时代使命,它能够从观念变革、知识培养、技能提升等多个层面帮助片区贫困群体与个人超越贫困对生活的桎梏。虽然近些年片区政府逐步认识到职业教育在片区扶贫脱困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依然处于较大劣势,这对于职业教育扶贫效能的充分释放十分不利。为了有效保障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亟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做好对片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
加强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即是要求强化片区政府职教扶贫战略引领,完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制度与法律法规体系,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组织管理机构、实施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工作协调与任务合理分配,最终实现片区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扶贫对象之间利益的共生发展。片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功能的释放之所以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是因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内部的要素诸多且整体复杂关联、相互钳制。例如,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招生制度不仅影响职业院校扶贫对象的精准锁定,影响有限教育扶贫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也影响着行业、企业等其他相关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积极性。当前,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扶贫政策制度体系不够系统和完善,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程度低,管理机构不健全、专业设置重复率较高、扶贫对象与扶贫主体之间利益共生性不强……概言之,即是缺乏对职业教育扶贫的顶层设计。[12]在此境遇下,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一方面需要继续坚持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引导,不断完善片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制度与法律法规体系,充分论证并出台有利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与法规,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组织机构、实施机构、经费资助体系、招生制度、人才培养与办学机制以及相关主体的责任边界进行规划与界定;另一方面,各个片区要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管理机构,负责整合与优化片区内部的职业教育资源,同时负责监督与指导片区内职业院校与培训机构有效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二)倡导片区实施职业教育定向培养模式
长期以来,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致贫原因之一在于本地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流向外地,造成人力资本的外流,致使人力资本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建构职业教育定向人才培养模式是一项针对性强、效果可持续的反贫困措施。因为定向培养就是解决人才“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有效途径。由于定向培养的人才质量规格是为片区当地条件艰苦或人才急需的行业订制的,因而职业教育定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实施就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反贫困方式。可以认为,实施面向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定向培养模式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本地工作待遇、增强本地就业吸引力、阻断贫困恶性循环、保障人才有效供给。
具体到实施层面,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定向培养模式主要涵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三个方面,其从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保障了人才的培养切实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定向招生的计划安排和专业设置有助于从源头保障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更好地服务区域发展。相比于传统的人才培养,定向招生生源在入学初即签订三方协议,保证毕业后到片区内的定向单位或部门就业,且定向招生的专业设置紧密围绕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突出片区区域特点,凸显特色优势农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及相关现代服务业,因此可在毕业后在片区内部及时找到满意对口的工作。其次,定向培养的方案制定和教学管理有助于从过程上把控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升服务区域发展的精准度。鉴于定向生的培养有明确的培养方向和目标,即为本地区特定行业或特殊产业培养专门的技能型人才,因此,定向生的方案制定应基于岗位的技能特点和实践需要展开。同时,定向单位或企业可通过提供实习机会、共建实训基地、捐赠教学设备及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以切实提升定向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最后,定向就业的政策落实和待遇提升有助于从出口保障定向生能真正留在当地,并为片区发展切实贡献力量。定向就业是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定向培养的重要目标,其通过将定向生留在片区内,进而实现为片区切实培养人才的目标。人才具有外部流动性,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因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滞后的发展水平而很难吸引到外部人才流入,因此,通过定向就业减缓本地人才的外流是实现人才补给的有效措施。
(三)推进信息技术与片区职业教育反贫困深度融合
随着以计算机、互联网、通信技术等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逐渐渗透,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对信息技术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必将为片区职业教育反贫困支撑起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首先,信息技术能够大幅度提升片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舆论宣传效果。中国职业教育技术网、中国扶贫网,以及各个片区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等诸多网络在线媒体为贫困人员了解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源,实现了职业教育扶贫由面上宣传向点对点的个性化宣传转变。其次,信息技术能够为片区贫困人员提供在线申报服务机制。以片区所推广实施的“雨露计划”为例,贫困人员可通过下载并登陆“雨露计划”APP即可在线申报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的精准扶贫名额,从而免去了复杂的申报程序。再次,信息技术能够扩大片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推进同一片区不同省域内、同一省区不同片区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并且贫困人员也可以通过注册与登录下载实用技术网络教育课件。除此之外,信息技术还能够优化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管理过程与教学过程,支持与专业课程配套的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开发与运用,增加贫困人员与扶贫主体之间的网络互动等等。
由上可见,信息技术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促进作用是基础性的、全方位的,为此,我们亟须为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信息技术与片区职业教育反贫困深度融合。一方面,要加大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薄弱,部分片区数字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缺乏凸显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信息平台,“校校通”工程与“数字化”校园建设缓慢。[13]另一方面,提升运用信息技术服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意识与能力。信息技术能否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深度融合,归根结底取决于广大师生员工使用信息技术的意识与能力。为此,各个片区内的职业院校要积极宣传使用信息技术的理念,通过培训提升职校教师与管理人员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同时,广大贫困学生也要积极学习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自己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与技能的能力,帮助自己最终摆脱贫困。
[1]王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2]刘传铁.教育是最根本的精准扶贫[N].人民日报,2016-01-27.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Z].2001-11-02.
[4]朱爱国,李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策略探究[J].职教论坛,2016(1).
[5]沈亚芳,谢童伟,张锦华.中国农村的教育贫困与教育补偿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6]方清云.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7]韦吉锋.少数民族地区未成年思德建设的原则、方法和途径[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8]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贫困:知识贫困[J].中国社会科学,2001(3).
[9]王晓慧,刘燕舞.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设计的利益主体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10]李延平.论职业教育公平[J].教育研究,2009(11).
[11]李刚.中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游明伦,侯长林.职业教育扶贫机制:制度框架与发展思考[J].职教论坛,2013(30).
[13]王杰,许锋华.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意义、问题与对策——以武陵山区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2(34).
A STUDY TO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ANTI-POVERT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UARANTEE SOLUTIONS IN PARTICULARY POOR MINORITY AREAS
Xu Fenghua,Xu Jie,Liu Junhao
To students of the right age in particularly poor minority areas,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bears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on,public education,value orientation in serv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pparent advantage in input and out-put is more attractive.These functions and advantages bestow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commitment of the era in participating anti-poverty campaign in particularly poor minority areas.Served as an essential and long-term way in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in anti-poverty alleviation of particularly poor minority areas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values of the poor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the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level of the affected population,enrichmentofwaysin talenttrainingand the promotion developmentoffeatured industrial economy of these areas.Important solutions to guarante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anti-poverty vocational education rely on top-level designation and directional training pattern of anti-poverty vocational education,intensive reconcili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particularly poor minority area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duction orientation;poverty alleviation
陈家柳﹞
【作 者】许锋华,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武汉,430074;徐洁,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刘军豪,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武汉。430079
D633【文献识别码】A
1004-454X(2017) 06-0151-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定向培养模式研究”(12CMZ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