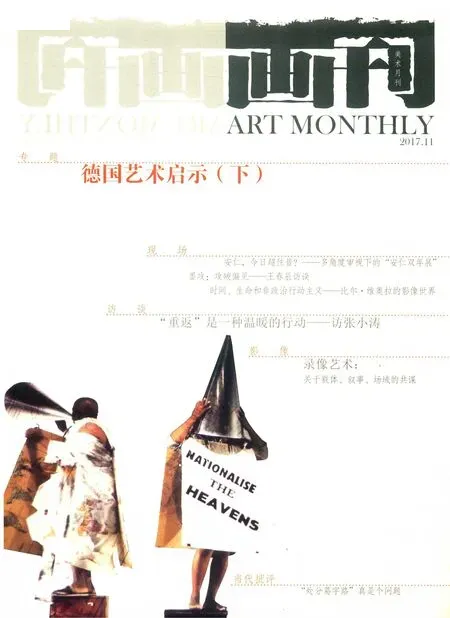砍下的首级与理想的肖像:上世纪30年代巴西图像志中的真实与典型
[巴西]拉斐尔·卡多索(Rafael Cardoso)/文 左夏露/译 金莉/校
按: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最先列出的12个主题都是从不同角度叙述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与解释的差异性。都是讨论艺术在各自文化的生成过程中造成的差异以及其间的区别。这种差异,分为“艺术内部”和“艺术外部”的问题。艺术外部的问题,侧重艺术与其社会、历史及其他因素(政治、经济、宗教、思想、科学技术等)之间的关系。艺术内部的问题,侧重艺术与审美和形式创造及其对艺术在文明和文化中位置和作用的理解,及其与自我的艺术传统之间的关系。
第十四分会的主题:他者与陌生,针对如何看待和评价一个外来的和陌生的艺术的问题。讨论侧重于发生交流和传播的行为发生之前,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每一个文化都遭遇到一个外来的陌生的艺术,甚至在一个文化内部也有对于不在文化中心和不在传统体制内的“外来”和陌生的艺术。
“他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化问题是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使然,对于艺术史而言,“他者”代表着一种新近的文化学角度,被引入艺术史领域不到半个世纪。然而,对“他者”的目光也同样可以投向历史,投向曾经被西方和男权所主导的美术史研究忽略的地方。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本分会发言的学人,拓宽了“他者”的意指范围,将其运用到更为开阔的文化维度和历史维度中,从而让殖民主义的色彩有所淡化,更加强调了交流的创造性。
拉斐尔·卡多索(Rafael Cardoso)的论文阐述了,在1930年代的巴西,政府试图建立一套巴西风格的视觉秩序。他认为,打造这种臆想的“自我”对于巴西社会中的“他者”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场暴力的压迫。
“他者”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代艺术界,随着世界各地汗牛充栋的艺博会、双年展、三年展的出现,探讨他者的问题就更显得意味深重,甚至是矛盾重重。按照当今艺术的市场逻辑,身份政治的浪潮在很多地区都尚未退却,“他者”的身份总是被策略性地彰显。因此“他者”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是:它一方面历史地带有一些殖民化色彩,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主动建构。从被建构、到去建构、再到主动建构,“他者”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变化?也许一时间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距离,还无从定论。但对于艺术史研究来说,具有创造性的交往方式却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具全球化的角度,以此来观照艺术的创造、历史接受及当代解读等问题。(粱舒涵 朱青生)
砍下的首级与理想的肖像:上世纪30年代巴西图像志中的真实与典型
[巴西]拉斐尔·卡多索(Rafael Cardoso)/文 左夏露/译 金莉/校
巴西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前提是混合与杂合这两个概念;巴西人倾向于认为本国人口的多样性是其最大的优势之一。然而,“杂合性”一词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矛盾冲突。与其他诞生于殖民情境的国家一样,拉丁美洲各国面临着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立。这是一条中心线索,贯穿了这些国家历史的始终——从摆脱欧洲列强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到构成了这些国家人口现状的移民潮,再到目前关于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的讨论。巴西经验在民族转换与交流方面极具流变性,本土与外来、自我与他者这些概念几乎一直在被重塑,同时也被战略性地加以运用,以建立起一种秩序——颇为吊诡的是,这种秩序一直以来都很稳定。
尽管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人试图定义典型的巴西特性,眼下盛行的文化成见却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巴西特性(Brasilidade)这一概念——即什么是巴西的、什么是非巴西的——在上世纪30年代占据了主流思想。围绕着所谓异族通婚及其潜在后果展开了一场中心辩论。人们普遍认为巴西是一个主要由三个种族不断融合而成的国家——这三个种族即葡萄牙人、非洲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因此,巴西特性如何在历史的熔炉中生成就成了一个突出问题,让人欲罢不能。种族融合会导致人种衰退的旧观念依然在有些社会人群中驱之不去——虽然这些观念越来越被一个新的混血种族的胜利远景所取代。
本文力求探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视觉话语,其时一种代表巴西民族类型的形象出现在讨论前沿,成了一个思想讨论,甚至施行政府政策的场域。以19世纪自然人类学优生学假说下的种族划分为前提,瓦加斯(Getú lio Dornelles Vargas,1882-1954年)独裁政府力求构建一种“巴西人”的理想化的形象。伴随世界范围内种族和国籍观点的两极分化,一种巴西身份认同的规范化概念被构建出来,并被激进地强加于一个已有的社会和文化秩序——这种社会和文化秩序远不具备这么强的同质性。反讽的是,一些致力于构建新的巴西特性的人本身有移民背景,这使得本已很纠结的讨论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其时人们试图界定巴西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概念上的界限,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构成了“外来者”和“他者”。
这幅摄影作品(图1)拍摄的是传奇侠盗头目兰比昂(Lampião)以及他的10个同伙被砍下来的头颅,这是巴西视觉艺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作品之一。图片故意歪曲了祭坛画,意在亵渎对照片中死者的记忆。构图围绕着一个颠倒的金字塔形,左上角和右上角有两台缝纫机,用来确定基底,向上直指兰比昂伤痕累累的脸。他的头颅被单独置于最底层,两边是一对长刀和两个有纹饰的帽子——这种帽子是“强盗”的一个典型特征,而兰比昂是他们中被高度颂扬的代表人物。这些头颅上的眼睛全都闭着,头发凌乱,有些人嘴巴大张。清晰的伤痕和变形的五官说明他们最近经历的战斗很激烈。围绕着它们,并支撑起构图的中心部分,前景和头颅的两侧放满了强盗生涯所需的随身物品,包括步枪、子弹夹、刀具、皮帽、刺绣袋子以及成串的金币——从死去的战败者身上掠夺来的丰厚战利品。乍看上去,堆积的意象或许让人感到困惑,但是其对对称感、视角和光影明暗对比的有心利用最终使得被枭首的亡命徒的形象被推进到了画面和想象中最显著的位置。
1938年7月28日,这伙强盗死于一支军队之手,终结了长达7年的抓捕。几天之内,这张照片就开始出现在报纸上——这些头颅被描写成“惊悚的战利品”和“死亡活生生的形象”。一周多过后,内务部下令禁止人们复制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埃莉斯·贾思敏(Élise Jasmin)所描述的“意象的战争”的典型,也是其核心作品——她用这个词来定义1936至1938年间媒体对兰比昂劫掠行为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些报道很多都是这个亡命徒自己精心安排的,事实证明他在塑造自己的形象方面很精明。到了他死的时候,兰比昂成了巴西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人们一眼便可认出来;论到臭名昭著,恐怕只有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才能与之匹敌。他的劫掠行径被定期报道,在巴西甚至国际上都成了新闻头条。

图1 兰比昂团伙的头颅
兰比昂于1926年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一个在巴西东北部让人闻风丧胆的强盗,这个亡命徒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期间他扩张了自己的团伙,使之慢慢形成了一支小的军队。他还对组织进行重组,其中包括诸如接收妇女加入和生活奢侈无度这样的激进举措。在接下来的几年,他的传奇影响越来越大,他很快被冠以“匪首”的名号——人们传说他极其富有,记者们好奇地想要知道他用的是什么香水、喝的是什么牌子的威士忌。1930年,巴伊亚州政府重金悬赏来抓捕他。同年的晚些时候,《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1931年,一首名为《我要抓住兰比昂》的通俗歌曲流行起来。1933年,在巴西的首都,一个极为成功的滑稽音乐剧也是以他主题演出的。到了1934年,关于这个强盗头目的两本传记已经出版发行了,他的事迹还被拍摄成了一部正片长度的电影,其未经授权的肖像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商业广告中。
经营他自己的名人形象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兰比昂对此很重视。上世纪30年代早期,这个团伙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一次大的整改,引进了新潮的服装和色彩多样的饰品,以为了公开的炫耀和对自我进行夸饰。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浮夸的土匪成了举国痴迷的对象,一位名叫本杰明·亚伯拉罕(Abrahão)的精明的业余摄影师兼电影制作人追踪到了他们,他的目的是拍摄纪录片。他不但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得到了兰比昂的授权来独家发行他的形象。以策略性地售卖给国家媒体的方式,亚伯拉罕的妙计让早已大热的报道锦上添花。1937年年初,以新闻摄影闻名的全国最大的杂志《O Cruzeiro》大篇幅地刊登了亚伯拉罕获取的图像,其他报纸的头条也把这个亡命徒捧为“明星”。
兰比昂声名大噪之时在巴西历史上绝非普通时刻。在一次共产党的起义失败后,瓦加斯政府强化了镇压手段,并迫害政敌,最终于1937年11月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独裁政府——“新国家”(The Estado Novo),这个政权直到1945年才宣告结束。联邦政府对兰比昂的镇压符合政府以对抗、颠覆极端势力为名来消除地方权力结构和消灭反对派的大策略。把信仰超自然力量的古老神话与现代宣传机制最复杂的手段相结合,兰比昂的传奇成了独裁政府的眼中刺、肉中钉,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镇压的力度。这种政治冲突的大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抓捕这些亡命徒的过程中所使用手段的残酷性,以及亵渎他们的尸首所采取的轻蔑态度。政府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证明不仅这些歹徒已经死了,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反叛和自治势力已经被彻底击败了——在公众迷信的层面上,这些歹徒是否已经死了还是非常不确定的一件事。
既是民间“英雄”,又是媒体的名人,兰比昂在上世纪30年代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一种巴西的文化身份认同。在一个以民族和区域的多样性为特色的国度——其中还存在极端的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要找到能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公众人物很难。当然,瓦加斯总统自身尝试着承担这种代表性的角色,得力的宣传机器帮助树立他作为“人民之父”的形象。然而,对瓦加斯个人的狂热崇拜直到1939年后才真的初具形态,其时这个政权臭名昭著的国家新闻与宣传部成立了,负责强化这位领导人对广大公众的号召力。考虑到1938年以前兰比昂的形象在公众想象中的魅力,以下事实就具有了重要意义:他死在一个节骨眼上,即瓦加斯政府正力图通过艺术作品来塑造一个巴西身份认同的官方形象。

图2 《混血儿》 波提纳里 1934年
瓦加斯时代的建筑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卡帕内马宫(Palácio Capanema)。宫殿的设计者为包括卢西奥·科斯塔(Lúc i o Costa)和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在内的6名建筑师,根据的是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绘制的蓝图。该建筑被公认为现代主义建筑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它的修建是为了容纳其时的教育与卫生部,由部长古斯塔·卡帕内(Gustavo Capanema)下令修建——他也指导并密切监管了曲折的修建过程。修建从1936年开始,直到1945年完成,即在“新国家”出现之前开始,贯穿了这个独裁政权的整个统治时期。在最初的建筑设计中,有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因为没有被落实而经常被人忽视,那就是一座主题为“巴西人”的纪念性雕塑。本来打算放在建筑前面的庭院里,这座雕塑按计划该高11-12米,是一个坐着的裸身男子的形象。这是卡帕内自己的构思。在1937年写给瓦加斯总统的一封信中,这位部长把它比作罗丹的《思想者》以及孟农巨像和卡纳克巨像。这象征了这位部长塑造巴西国民性的使命。据现存的信件和文件来判断,这座雕像是要在花岗岩上雕刻出“这个种族的最佳典范”所拥有的代表性特征。卡帕内非常严肃地对待这项任务,所以他求助于一个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定那些代表性特征在将来或许会是什么样——因为他认识到一种统一的类型当时还不存在。
这个纪念雕像是这个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复出现在柯布西耶的前期手稿中,也成了历时很久的一项研究的焦点。把巴西身份认同这样一个复杂又抽象的概念凝聚成一个形象化的象征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便说这个任务并非不可能完成。最后,这个项目被放弃了——卡帕内苛求完美而提出的反对意见使得计划破产,同时项目也在理论讨论中陷入了困境。政府和它委托的艺术家没有能力建构一个令人信服的巴西身份认同的形象以抗衡兰比昂这个人物形象的巨大力量——这个形象融合了古代与现代、本土性和异域性、男人气概和风度。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项目的失败值得注意。确定人体测量标准将会使种族类型的理想形象植根于科学真理,部长显然对此很感兴趣,这能说明其中隐含的问题的本质。

图3 波西·劳尔为《Tipos e aspectos do Brasil》所绘的插图 1966年
在对于是什么构成巴西特性的种族主义讨论的大背景下,画家波提纳里(Cândido Portinari)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作品值得特别关注。波提纳里后来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画家。1936年后,他受到瓦加斯政府的器重,被其对手说成是政府的“御用”画家。毫无疑问,他和教育与卫生部的紧密合作使其成为了卡帕内通过艺术与文化塑造巴西身份认同这一教育使命中的核心人物。他擅长各种迥异的风格,甚至有时候把它们杂糅在一起,这使得他拥有不同的观众群体,最终几乎获得一致好评。人们普遍认为他取得了现代艺术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平衡;甚至连他得以成名的对生理特征的畸形描绘——比如手脚过大的人物——都被保守的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对现代性所作的让步,是可以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波提纳里受到批评界关注的作品都是对种族和族群的表现。1933-1934年间,他开始创作其他题材的作品,涉及劳作、贫困、族群性和社会正义等主题。当中有两件作品特别受到赞誉:《混血儿》(Mestizo)(图2)和《带着锄头的黑人》(Negro with a hoe)。评论家们称赞这些人物形象的宏大和表现力,以及它们为观众所感知到的、对巴西社会的深层潜流的描绘。以艺术为对象从事写作的主要的现代主义作家Mário de Andrade称赞《混血儿》是一幅杰作,尤其指出了其中人物形象的雕像般的特征,并将其比作德国的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因为这幅画没有避开描绘人物的脏指甲。在争取引领现代主义潮流的过程中,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其时加入了巴西共产党的奥斯瓦德·德·安德瓦德(Oswald de Andrad)。安德瓦德热情地谈到这两幅作品的潜能,并称赞波提纳里站到了当时革命艺术家的阵营里。他坚持认为,作为黑人和劳动者,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代表阶级斗争的最好的素材”。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解读,在政治倾向上,甚至在遵从盛行的现代艺术观念的做法上,波提纳里的作品都远非是一目了然的。在这些意象中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对人物形象的特殊性和细节的过分关注,甚至对身体上的瑕疵和体毛都不放过;另一方面是自觉地赋予风景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般的特征。这些作品一以贯之地刻画种族类型,其静态的背景表露了一种刻意回归秩序的倾向,所以它们让人想起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艺术潮流——这位艺术家造访过意大利,在1931年和1932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曾热情地赞扬过意大利的政治体制。正如评论家法布里斯(Annateresa Fabris)所指出的,刻画工人形象和讨论社会艺术在那时并不是左翼人士的特权,而是涵盖了其令人不安的、经常混乱躁动的意识形态的多个层面。
抛开这些意象为人所感知到的政治不说,值得注意的是,将近10年后,社会学家费尔南多·阿泽维多(Fernando de Azevedo)在他的划时代著作《巴西人的文化》(A Cultura Brasileira)中采用了它们——这本书在“新国家”政权的鼎盛时期出版。这本广泛研究巴西文化的著作源自一项政府任命,即为1940年的人口普查写一个简介——这次人口普查是由经过重组的统计局发起的。作为圣保罗大学的教授和巴西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之一,阿泽维多把这项任命看作是一个机会,用以推行他的教育理念和它在构建统一的民族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这本书带有418幅插图,波提纳里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得到了特别展现,选用了他8幅作品。一幅《混血儿》的复制品紧挨着讲述巴西人种构成的部分。采用波提纳里的画作来图解文化融合的概念赋予了它们一种学术上的地位,这区别于以前把它们作为赞同“社会艺术”的表现来加以接受的做法。以黑白复制品的形式出现在书中,这些画作没有了原来赋予它们图画意义的色彩张力,变成了所谓的巴西“种族性”的赤裸裸的表达。
在阿泽维多的书中,“混血儿”和“黑人”形象的出现更是对文化上的老生常谈的具体化,而非表达了一个特定的教义或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作用非常类似于波西·劳尔(Percy Lau)为《Tipos e aspectos do Brasil》所绘的插图(图3)——这本书是巴西地理统计局在1943年出版的。这些用墨水绘制的素描以精细的笔触表现了特定区域的人物类型,比如亚马逊的割胶工人和巴西南部的高乔人。正如波提纳里的画作,劳尔笔下的人物十分鲜活而细致,足以让人联想到特定区域的人物肖像画,然而它们的标题和文字说明又把它们归于一般性和典型性的范畴。在这两组绘画中,艺术家的描绘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抽象提供了可能的面貌特征。在上世纪40年代的大背景下,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是要求诸于绘画和素描,而不是可以被广泛取用的照片呢?确实,这个决定的效果之一是使表现体系摆脱了摄影肖像指涉特殊性的功能,从而转向与传统的艺术观念相联系的永恒性和普遍性。
建构想象的人物类型来表现一般类别和概念化的抽象成了“新国家”政权所支持推动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波提纳里为教育与卫生部所绘的壁画全都遵循这个寓言化的过程——每幅壁画都代表了巴西经济史的一个片段,在程式化的背景中将工人形象与他们的劳动对象并置起来。大部分人物都没有个人的面貌特征,或被样式化为卡通似的陈腐形象——这是对一种社会状况的非特殊化的表现。与他早期的油画作品不同,在这些壁画中,寓言和肖像画的表现体系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随着这位艺术家年岁日长和事业的成功,他似乎越来越不想跨越现实和非现实的界限,而在早期作品中,他却非常精明地运用了这种手法。奇怪的是,他运用这种手法的一个例证是在一个表现“强盗”主题的系列作品中,这距离兰比昂的鼎盛之时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部分是为了给1952年发表在《O Cruzeiro》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插画。在这个作品所依据的约100张已知的图像中——这些图像出现在1947-1958年之间——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说是肖像,尽管这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虚构的理想化的种族原型的脸与兰比昂及其同伙被砍下的头颅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头颅非常真实,但又几乎难以辨认;这种反差暗示了巴西文化中内在的一种吊诡。一方面对精英人士的赞助极端顺从(那是来自上层的权力),另一方面对民众抵抗持深刻的怀疑态度(那是来自底层的力量),巴西社会因而倾向于表现得难以面对其自身碎片化的形象。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个在地域、民族、语言、宗教以及其他方面如此多样化的国家,一个对巴西特性的标准看法居然得以生根发芽,并且在20世纪激烈动荡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繁荣发展。为这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对差异性的暴力压制。在建构民族性理念的名义下,这个国家中不受欢迎的部分必须被剔除出去。埃莉斯·贾思敏把兰比昂与其同伙的头颅作为战利品被展示的场面比作是“一个镇压的奇观”,把它联系到几个世纪以来巴西的悲剧历史,其中充斥着斩首、暴行、酷刑和对神的亵渎。在对此作解释时,弗里德里柯·德·梅洛(Frederico Pernambucano de Mello)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是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期间欧洲的价值观和习俗被反复强加于处于文化底层的大众——他们被看作是古老过时而野蛮的。然而,近乎吊诡的是,这个追捕并杀害了兰比昂的政府却又认为必须限制这些死去的亡命徒的照片流传。
1938年,兰比昂及其同伙的头颅被交给了位于萨尔瓦多的巴伊亚州法医学研究所,用来对导致人类退化的潜在原因进行犯罪学研究,其根据是当时盛行的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的人体测量学理论。这些头颅被陈列在这个研究所的医学博物馆中,直到1969年才被取出来埋葬了。在它们被锁起来的这30年间——虽然它们同时也还在公众视野中——这个传奇的力量不断增长。这个“强盗”的形象唤起了一种近乎色情的痴迷,直到今天都是巴西文化中的一种强大力量。如下事实或许不会令人吃惊:经由影视作品、平面设计和通俗文学,这个形象已经被抬举到了与美国人想象中的牛仔类似的神话般的高度。当然,这些神话般的描写与那些头颅的“悲惨现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者依然能够动摇或颠覆现有的视觉秩序。在天平的另一端,瓦加斯政权试图建构的巴西特性的虚构原型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无法兑现它们所声称的审美的永恒性和人体测量的准确性。尽管它们的目的是要界定巴西的理想“自我”,但是对于巴西现实中的多样性来说,它们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它们在艺术调整方面僵硬不化,对统一性的追求大而无当;这些在巴西文化的日常经验中很少能找到共鸣,毕竟这是一个由多种声音和碎片化的欲望构成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