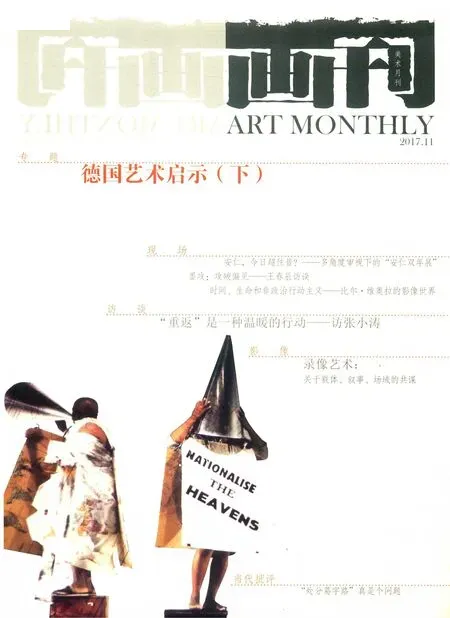此声、此时、此地
——孙啟栋谈“生声不息”展
本 刊
此声、此时、此地
——孙啟栋谈“生声不息”展
本 刊

《雾》 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现场定制装置 混合媒介 2017年
《画刊》:“生声不息: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展近日正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作为策展人,你最初是由于什么原因想把塞莱斯特(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这个艺术家带到中国来的?
孙啟栋:我以前对他的作品就有了解,不过2015年又看到他两个展览,对他才有了颠覆性的认知。一个是巴黎东京宫他的个展“涨潮”(Acquaalta),一个是当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梦的演进》(Rêvolutions)。他特别善于让既有的作品与空间对话,在空间、物理和心理层面,给观众以冲击,进而与建筑空间属性产生交流。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也与我这几年的思考暗合,即我们应该如何去更有效地讨论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去想象和思考未来的图景。
因此我就萌生了邀请他来上海做个展的想法,为此我做了一些详细的研究工作,给他写了一封长邮件。邮件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我对他所有作品的理解。二是我对他代理画廊的理解。有三个国际画廊代理他——巴黎的西帕斯(Galerie Xippas)、柏林的马佐利(Galerie Mazzoli)和纽约的保拉·库珀(Paula Cooper Gallery)。我主要谈的是保拉·库珀画廊,这个画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推动美国极简艺术的发展,他们2009年代理塞莱斯特,是把他作为美国极简艺术精神在当代、在声音艺术领域的一个传承。三是谈了上海以及民生现代美术馆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个人对这个个展的设想。
他回复说很愿意来考察一下。在去年4月份来了上海,我们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对我来说,这个展览完全是一个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合作项目。我们经常一起带着图纸骑着摩托车就出去了,聊关于展览的各种设想和计划。
《画刊》:以声音为主的艺术创作在国内并不算多,观众对这个领域也缺乏了解。那么具体在策展环节,你是怎样考虑从哪个点切入的?
孙啟栋:我构思展览的时候并没有从声音、从媒介角度出发。塞莱斯特是作曲家出身,他选择声音作为创作媒介和方法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训练已经内化到他的血液里,成为他的身体记忆。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当代艺术领域,声音也需要视觉化。所以我不会刻意强调所谓声音艺术,我就把塞莱斯特当作一个视觉艺术家。而且相比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这样更纯粹的以声音为媒介的艺术家,塞莱斯特要更为开放,更注重实验性。
塞莱斯特做过很多个展,策展人们有的从声音角度去梳理,有的讲究互动性。而我主要是进行了一次非常文学化的梳理,把作品分了几个层次,做一个流动性的展览。我当时在看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宫二说过,习武之人有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三个境界是递进的,又回归到本源。落实到展览中,也体现了这三个层次的递进与回归。《编舞》《雾》是见自己的过程,观众穿行在石头上,肢体动作都受到了编排和控制,重新感性地感受自己的身体;《雾》中视觉暂时被剥夺,靠隐隐约约的声音引导进去,耳朵为眼睛服务。《此地入耳》《示踪器》是见天地。《此地入耳》用草、鸟等构建了一个生态;而《示踪器》中,我觉得气球也是一个“活”物,被风扇带动着“活动”。在布展过程中,有时候气球会慢慢靠近你,悄无声息地,像个人一样,慢慢又走了。有时候会飘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想去拿出来,塞莱斯特就跟我说,你别去,再给它10分钟。这种“活”物的呈现,其实无关生命的形式,而是呈现了生命的质感。最后是见众生——《趋势》,虽然我们总是说众生平等,但这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美好想象。不过回到原子层面来说,众生就是平等的。
《画刊》:展览从作品《编舞》开始,感受这件作品是一个需要付诸体力的过程,但是接下来的《雾》营造了一个轻盈的氛围。空间的变化很明显,身体上的感受和观者的情绪立刻就不一样了。整个观展过程基本是由声音牵涉到全身的感受,是一个比较“轻”的展览。
孙啟栋:“轻”这个词比较到位,尤其在像塞莱斯特、菲利普·帕雷诺、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这一代法国艺术家身上,“轻”是一种可以称作法国气质的东西。这种法国当代艺术的气质,其实从杜尚开始就有了。这是他们的艺术体制训练出来的,如果不这样,在他们的体制里就出不来,也不能走到国际舞台上。
《画刊》:这次展出的都是塞莱斯特以前的作品,因为场馆的变化,有没有为此做一些相应的改动?
孙啟栋:有很多,塞莱斯特基本上都会根据场地为作品设计一些新的元素。《编舞》以前在法国的画廊做过,但那是个很小的版本,被他放置在画廊室内的阶梯上,这次则是外移至户外的手扶电梯上;《雾》2010年在路易威登艺术基金会做过,当时是一个盒子空间,这次改为长条的,还组合了东京宫展览上的“嗡嗡僵尸”(zombie-drone)实时投影的效果;《示踪器》原本只有一个风扇、一个气球,现在增加到五个,声音和视觉效果也增加了一些;《此地入耳》的声音每一个音轨都做了编辑,电吉他电贝司的音乐,加上鸟鸣声,声音效果更富有变化。

左·《编舞》 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雕塑 2017年

右·《趋势》 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现场定制装置 混合媒介 2017年
可以说,塞莱斯特这个展是我们馆开馆以来对美术馆空间利用得最好的一个案例。我当然也可以为塞莱斯特改造一些白盒子似的展厅去呈现,但这跟场馆的关系就不大了。本来我还考虑过要不要做一件作品放进黄浦江,一件完全不可见、能引发遐想的作品,不过想想还是太刻意,没有必要。

上下·《此地入耳》 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现场定制装置 混合媒介 2017年
《画刊》:在你们做因地制宜的调整过程中,声音的特性跟以往相比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啟栋:声音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操作中需要达到艺术家对作品效果专业度上的要求。比如《示踪器》,气球充满氦气之后飘上去就不动了,一定要靠风扇吸下来吹出去;气球飞行过程中,麦克风收集空间里面的声音,继而传送到电脑里进行编辑。所以如果飞行轨迹不对就出不来他想要的旋律。整个展览的声音都是这样设计过的,有着从和缓到激烈再到和缓的变化。
情绪也是如此。从《编舞》开始,观众的情绪就被裹挟着,被声音引导和推动着。直到最后,《趋势》让所有的情绪一下子打开了、释放了。

《画刊》:《示踪器》之后是《此地入耳》,中间有一个金属链条的帘幕,从媒材来说有着轻重的区分,暗示了观展节奏的变化。
孙啟栋:这个帘幕不光是为了艺术效果,还有实用性的考
虑。一方面它阻挡了小鸟飞出去;一方面保证空气的流
通,不至于发闷;另外,链条也暗合了摇滚乐。
《画刊》: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来源主要是什么?
孙啟栋:基本来源于日常生活,是对日常生活的转化。他创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上世纪90年代就做鸟,20多年了还在做。用的一直是同一种鸟,斑胸草雀,原产澳大利亚,中国也有。选这种鸟,一是因为外观比较漂亮;二是它喜欢群居;三是这种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沙漠,对严寒和酷暑的耐受性比较强;四是这种鸟是吃小米的,嘴比吃虫子的鸟硬,碰到琴弦就会发出声音。
《画刊》:这些作品的呈现完全是视听交合、轻重衔接、节奏分明的,非常有东方审美中游历般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声音促进了视觉化的有效性。比如《趋势》里碗和水池的色彩、材质以及整体的几何结构本身就有视觉的美感,水的流速控制着瓷碗相碰的声效。这种清脆的碰撞声,把瓷碗材质的特效又放大了。
孙啟栋:之前我们馆也做过池田亮司的展览,他是搜集不同的声音信号来进行编辑,用数理逻辑来生成几何图像,并在色彩上产生黑白的变化。他的视觉是为声音服务的,这和塞莱斯特完全不一样。塞莱斯特的视觉和声音融为一体,视听效果是平衡的。
《画刊》:展览同时又有一种随机跟控制之间的平衡,比如《趋势》里碗跟碗具体怎么碰上是没法控制的,但可以控制它碰的强度。
孙啟栋:所谓的随机是以控制为基础的,控制非常重要,如果作品没有完成控制和把握,谈的随机都是扯淡。我愿意给观众呈现一个随机的状态,但之前的控制一定要做好。
《画刊》:从观展角度来说,这个展览给人的启发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文学性,也不是观念,而是它让人觉知自己,觉知触觉、听觉、视觉,觉知身体的感受力。
孙啟栋:观众也有这种需求。为什么现在相较电影和文学作品来说,当代艺术的观众是最少的?就是因为很多当代艺术的展览一进来就让人觉得是在被教育。一个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上班至少5天的人,他有多少精力和意愿想再去被教育?观众来了很重要,他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就好。

上·《示踪器》 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装置 混合媒介、尺寸可变 2017年

下·《此地入耳》 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现场定制装置 混合媒介 2017年
注:
展览名称:生声不息: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展览时间:2017年9月2日-11月12日
展览地点: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