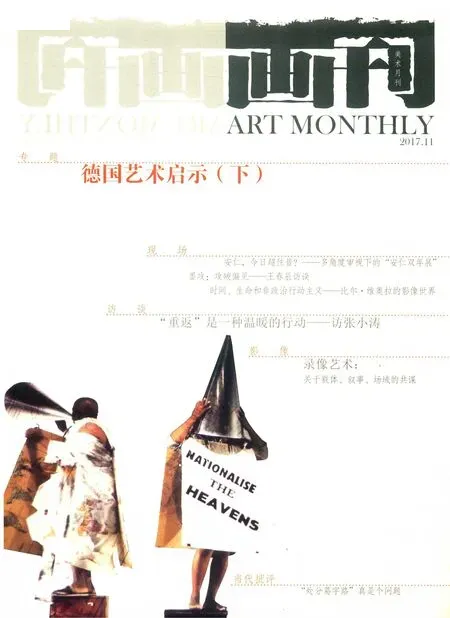墨攻:攻破偏见
——王春辰访谈
本 刊
编者按:2017年,首届武汉国际水墨双年展以“墨攻”为题,在武汉美术馆举办。多年来,有关水墨问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边界和效用、本土性和国际化、传统与当代等诸多宏观层面,但屡被提及而不得其解。此次武汉国际水墨双年展分“起”、“承”、“转”、“合”四个单元展,纵向地呈现水墨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本刊对“合”单元的策展人王春辰进行了一次专访。这是他首次参与策划大型水墨展览,本刊与其就当下水墨的创作方法、理论架构和展制等问题展开讨论。
墨攻:攻破偏见
——王春辰访谈
本 刊
《画刊》:首先从水墨实践谈起。当代艺术领域所谈到的水墨,大概有两个方向:一方面在继承传统技法的情况下融合当下的体验、情境,包含结合西方图式、表现手法的创作;另外一个方向是放弃笔墨、放弃水墨画的基本属性,只把水墨当成一个因子、一个工具。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合”分为7个单元,那各单元之间的分界就会比较含混。
王春辰:这7个单元本身是交叉的网状结构,而不是截然分开的。我既想作一些细分,又不想给水墨再增加那么多负重。现在大家谈了很多水墨概念——现代水墨、当代水墨、实验水墨、表现水墨、抽象水墨,包括新水墨,让人不堪重负。当然命名者都有自己的意图,但这个命名能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新水墨概念并不是因为前些年苏富比的拍卖才出现的。新水墨指不同于传统、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别人的水墨。上世纪中叶,中国不是没有“新”水墨,宋文治画《南京长江大桥》、画造船厂炼油厂,虽然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但不能不承认那也是新水墨。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新文人画”,更有个人趣味。
当然前些年,这个概念的流行有着极强的市场操作性,但为什么短短几年大家一下子又不感兴趣了?本来市场操作是学术介入的一个很好契机,应该抓住新水墨真正的学术内核。在今天,一个新艺术的出现,必须要通过推广使人所知。很多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基弗等,除了学院和美术馆系统的讨论之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画廊、是市场。这并不矛盾,市场认可也是对艺术内在历史、学术价值和时代关系的充分肯定。
再说新水墨。历史是有自我意志的,这个自我意志是由各种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共同体是一个多方面、整体趣味的倾向。所以在这个框架里,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不断产生新的面貌、新的艺术家,也包括新水墨。但我们对新水墨的理解不应狭隘,不应固定在几个人的影响下,画点小动物、小情景、青年小形象,处理得稍微怪异点,或者墨稍微淡一点,就是“新水墨”?如果这样,时间长了就会没人喜欢。格局太小、气度太小,深度不够、广度不够,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大的艺术抱负。伟大的文学家之所以伟大,即在于他能感知社会、感知世界、感知时代的命运。我们对新水墨艺术家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如果审美很低、趣味也低,就想着画些迎合一般审美要求的,肯定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画刊》:水墨有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简单的材料属性。笔墨也好、心性也好,是一个心手相应的系统。那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抛弃水墨特性的水墨实践,要怎么谈?
王春辰:这类艺术家中很多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控制。他们以为换个题材、用点流行的图式就叫新水墨了,实际是对水墨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从其他艺术门类里找一些“灵感”过来,但并没有跟水墨自身结合起来,还不如一些实验性、破坏性的做法。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水墨创作的难度,也要开放、积极地学习,不要满足于简单的市场效果,重复作品,这是自毁。
《画刊》:展览中的“20世纪以来的水墨批评谱系考”板块,其中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发表于《江苏画刊》1985年第7期)引发的“中国画穷途末路”大论战是你们考察脉络的一个重点。你的陈述,跟李小山批判当时的中国画界陈陈相因、重法轻理的状况其实是有呼应关系的。王春辰:以为图像变了一下就是当代了,这和“文革”时期中国画画工地、卡车、火车有什么区别?这样做就是“皇帝的新衣”。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的水墨探索有一大批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现在为什么大家不谈那些概念了?因为没能构成一个学术有效性。当然我们从历史角度看,研究特定时间发生的艺术活动和变化,是可以留下一笔的。但后推50年、100年,多少流行一时的画家,能留下来的有多少?留下来的还是在语言上有创造的。
在这一点上,水墨画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不是说我们不开放,非要回归传统,而是这个系统有它自身的逻辑。就如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一样,如果不了解它的逻辑,是无法做到绘画的发展和改变的。一出手就是天才的艺术家不是没有,但是极少。当然,只知道学,学得一脑袋糨糊也不行。受老师的影响、没有自己的面貌,陈陈相因,这是致命的弱点。所以我觉得新水墨也好,别的艺术也好,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作品,画画就要画好一张画。有人觉得画不好,或者画下去没有意义,又转向别的,这是他自己的判断,都是可以的。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也好、宗教也好、自己的情感体验也好,都可以放进来,但需要一步一步地探索。《画刊》:你的观点还是从水墨画出发,重视的是其基本属性。
王春辰:让水墨回到水墨,就跟让人回到人一样。但人总是会忘掉自己,受外部的影响,看这个好做一做,那个有意思也做一做,认为是水墨的出路,其实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在今天思考和关心的还是人的问题。基弗反思历史是人的问题,从印象派到立体派思考的还是人的问题。我们总是看到表象,以为是形式的问题。水墨和其他媒介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和人、和社会、和历史结合。
我们总觉得水墨是特殊的,因为它源于中国,题材和内容都和中国古典哲学有密切的联系,它“独”属于中国;事实上如今也不“独属”了,日本叫日本画,韩国有韩国水墨画。这种民族情结,我们也需要放下。艺术上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盲目自信也是不可取的。我们既不能自认水墨至高无上,否认其他艺术的价值;也不能认为水墨落后、传统、不当代。回归水墨的绘画属性是水墨发展的正途。
《画刊》:这次展览有一个单元叫“北宗再造”,这个提法是存疑的。因为董其昌提“南北宗”,依据的是禅宗南宗顿悟、北宗渐悟的思想,而非地理因素。那么你提“北宗再造”,这是哪个北宗?又怎样再造?

左·《桃源仙境图》 黄敏 纸本水墨设色 80cm×150cm 2008年

右·《Nomad 24》 申暎浩 纸本水墨 138cm×237cm 2016年
王春辰:其实我是给北宗下了一个新的定义,附加了更多今天的意义,董其昌可没有这么说。所以我这也可以说是“新北宗”,展示的是中国文化追求的天、地、人的关系。我借用了一种地理上的意象,南方湿润、润泽,景致优美,而北方凛冽,张扬出人面对恶劣状态时所激发的最强大的生命力,呼应了古人对阳刚之气、豪迈之气的追求,从美学来说,就是崇高和悲壮。艺术跳开语言,还需要强大的思想支撑。过去100多年来,中国人是很压抑的,我们的文化也是压抑的。外来的因素、自我的压抑、历史的累积,需要强大意志的对抗。
其实,我做这次展览及研讨会的题目是讨论“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和思想之变”,不过大家讨论得更多的是脉系之变而非思想之变。但语言背后是思想,郝青松谈水墨世界观的问题,要开放,说得对,可惜没有足够时间展开。高从宜谈饶宗颐的“西北宗”论,佛教传入是经过西域;老子出函谷关,是西方;儒家在东方,但孔子周游天下还是往西去的。当然寻根关键不在地理,而是当时的思想能对今天产生的启示。

《轻折慢展慢折轻》 姜吉安 现成品绘画(绢本) 119cm×42cm、13cm×42cm 2016年
《画刊》:接着研讨会来说,保罗·格拉斯顿(Paul Gladston)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争论,可惜由于时间有限,没能展开讨论。格拉斯顿先生用古希腊哲学“Khora”[1]来阐释“气”,这就涉及一些问题,将这些西方的哲学、美学概念运用在中国画系统,国内一直有评论家在做,但这当中存在很多理解的偏差和含混。
王春辰:我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尊重所有的说法。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跟你辩论。但总体而言,不管说什么,我都是比较鼓励的,希望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术系统的人,不管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能进入中国的艺术现场来讨论。其实格拉斯顿的文章写得不错,有学理的上下文、有论证。而中国很多文章做不到这些,会比较偏感性地陈述。历史建构、学术研究是要踏踏实实做事的,画画也要规规矩矩画好。
《画刊》:回到展制的问题。水墨大展我们可以作一个纵横比,国内是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国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何慕文(Maxwell K. Hearn)策划的“Ink Art:Past as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以西方策展人和观众的视角选择作品,在国内引起了很多争议,争议的核心即是水墨的定义和边界问题。你自己最近也有发言说:“当年,纽约大都会做了中国水墨大展,国内一片反弹声,但国内做了几个这样的回应大展呢?”这句话是不是说明,你策划这期“合:融汇与变通”也算是一次回应?
王春辰:武汉美术馆做水墨双年展是在延续原有的品牌项目“水墨文章”基础上,从更大层面去推动水墨发展。当然,他们邀请我策划这一期水墨双年展之时,我潜意识里确实希望对大都会的展览作一个回应。对那个展览,大家有不同看法,因为何慕文把水墨仅当成一个概念、一个因子,展出的除了水墨,还有装置、摄影、行为、油画、雕塑等作品,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水墨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做一个展览就是一次艺术史的写作。大都会做水墨大展,包括古根海姆最近做“世界剧场”,都是以他们的眼光作出的判断和选择来进行展览策划与写作的。
我则是集中在水墨媒介这个层面,以水墨绘画为主,考虑有一定历史延续性和突破的作品。作为一个网状的结构,水墨既是媒介,也是思想。我并不想像大都会那样外化到什么都包涵,而是想强调在语言脉系里,什么是真正的水墨。这还是一个绘画系统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国内外都不断地在讨论和反思绘画,谈绘画在今天新的作用和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并没有被评论、理论系统所限定。今天的语境存在很多偏见,艺术家真要根据评论家的指导去创作,永远也超越不了。艺术靠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和直觉支撑,同时也离不开不断地学习。特别是对经典的中国艺术哲学,如“气韵生动”之类,如何具有新的理解、新的判断,赋予新的内涵,都是可以借鉴现代艺术的,但它们并不应该混同。如现代主义绘画讲“纯粹性”、“平面性”,这是基于西方对消除绘画的透视关系、叙事性等具象特征而作出的实践与理论回应,那么,类似于“气韵生动”这样的概念也可以赋予现代含义,打通水墨绘画的古今之变,但水墨的实质依然在。现代绘画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和有思考的智力,同样对于水墨绘画也需要真正的看得懂的眼睛和敏锐的思考力,因为我们看在今天,这双眼睛经常走偏,很多时候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水墨的韵致了——看到僵化的水墨,反而说生动;真遇到独创、有表现的水墨,却视而不见,完全木然,仅仅以图像的可解读性来判断水墨。这是今天的水墨绘画的大患。

《发光体》 冰逸 纸本水墨 49cm×49cm 2013-2015年
《画刊》:其实这是双向的,艺术家靠直觉,但也离不开学习和理性的认知;学者知识系统之外,面对作品,也需要感受力。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水墨大展。它线索明确,有内在逻辑,讨论并梳理了水墨存在的诸多问题。那么,武汉这次国际水墨双年展是首届,其实面对的是同样的资源、同样的艺术家,如何进行组配,并提出新的问题?

《水+墨=?》 张羽 行为装置 亚克力箱、亚克力镜面、宣纸、墨汁、水、水壶 2017年
王春辰: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我也在关注,它们对水墨作出了系列的观察和展示。虽然这次武汉的展览是我策划的第一个水墨大展,但我一直在关注水墨,甚至早于参与当代艺术研究,我一直在看、在思考。深圳水墨展的主办方、策展人、艺术家都是亲历者,书写的是自己所参与的几十年来的水墨活动经历和历史。对这几十年的水墨状态,我既有赞同的地方,也有觉得需要反思的地方。比如水墨装置,装置是一个很开放的艺术,把墨、宣纸什么的组合起来做成水墨装置,已经不是水墨画了,应该放到装置的系统里去,如果硬说成是水墨艺术,则会造成逻辑的混乱。大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做法不是水墨发展的方向,而仅是水墨的拓展和外延。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水墨真正的方向还是一张画。所以我既吸收了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一些优秀的东西,甚至我邀请的几位艺术家也参加过深圳展,但可能我们关注的点不同。我强调的是:在水墨这个绘画系统里要有由来、有去处。
《画刊》:有由来,来历清楚;但是有去处,去处是哪里?
王春辰:去处在于绘画可预见的未来。绘画是一代一代可以走下去的艺术。
装置没有历史,它跟现场和空间有关,重新建构一个独立的世界;绘画是一定要回到历史的,一定会和历史发生关联。今天的艺术是开放的,很多门类可以用;但每个门类还是有各自的线索。录像艺术古代没有,所以艺术史需要为其独立书写;装置艺术,历史上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现代主义以来,装置艺术的概念成立,那也需要独立书写。没有说把装置、把录像归到绘画里的,为什么偏偏要把它们归到水墨里边呢?我觉得这就是水墨的不自信,或者说对水墨没有真正的认同和认知。
注释:
[1] Khora,古希腊哲学概念,代指场域之外的地域。柏拉图引用此概念,表示一种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的状态。德里达用其表示存在与非存在发生区分的场所,用于表达区分的可能性,而又同时抗拒对事物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格拉斯顿在论文中提到“气是‘存在’与‘非存在’之间超出理性范围的相互作用,它同时两者皆是又两者都不是”,并将其与Khora进行类比。
注:
展览名称:“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合:融汇与变通
展览时间:2017年10月20日-12月10日
展览地点:武汉美术馆

左·《和风晓月》 姬子 纸本水墨 145cm×184cm 2009年

右·《岛系列》之二 瓦伦西亚 墨、综合材料、手工宣纸 145cm×76cm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