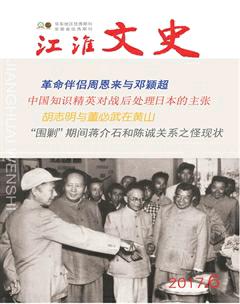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王光宇同志
吴昭仁
2017年8月23日,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决策者、推动者、执行者之一王光宇同志驾鹤西去,我无比悲痛。我在光宇同志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5年时间担任他的专职秘书。光宇同志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一生牢记党的宗旨、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以及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影响至深。今天,我想讲讲在他身边的日子里,感受最深的几件事。
一
1977年6月,万里同志主政安徽,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来到安徽以后首先处理政治上的问题:先是欢送支左的十二军的同志回到军营;接着清理省地(市)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开展揭批查,解放了一大批老同志,让他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在政治形势和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之后,万里同志把大部分工作交由顾卓新和赵守一同志,说安徽是农业大省,他自己主要抓农业。他多次微服私访,不通知任何人,带着秘书、警卫员、司机一车4人,直接进村入户,在田间地头,在打谷场上,在夏日树荫下蹲地吃饭的农民身旁,与互不相识的群众亲切交谈。直到那个时候,万里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要严重。
早在1954年,光宇同志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十多年来他一直都是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的负责人。这一年的秋后,万里与光宇同志一道对全省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长时间调查研究。这次调研先后持续了20多天,去了近20个县,主要是接触最基层的农村干部群众。当时安徽农村多数比较贫困,尤其是沿淮的行蓄洪地区和大別山区的水库淹没区,农民生活相当贫困。许多人家吃不饱肚子,外流讨饭的多。尤其让人难以启齿的是有些人家还衣不蔽体,少数人家妇女在夏天打赤膊没有褂子穿,有的人家母亲和女儿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谁穿。万里同志到金寨县水库淹没区的一户人家走访,他走进这户人家以后,这一家的主妇吓得往灶台底下躲。什么原因呢?就是赶紧用柴禾盖住自己的身体。万里同志当时触动很大,眼睛也湿润了。路上,他就对随行人员说,想不到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还有这样穷困的地方。
在此之前,万里与光宇同志是分乘两辆小轿车,从那以后,他就让光宇同志坐到他的车上,工作人员坐另一辆车,以便在行车途中多听一听光宇同志介绍安徽农村的情况。光宇同志向他汇报说,我们国家这些年不仅在政治上极左,在农村经济政策上同样极左。比如说,有些地方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不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取缔集市贸易,认为农民搞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就增加了私心,就影响集体生产,集体经济就搞不好。一个老百姓家养了两头老母猪就要杀掉一头,说杀掉一头母猪相当于杀掉一个修正主义分子。经常搞斗资批修,搞大批判私字一闪念。尤其荒唐的是,一个公社一年种多少亩棉花、多少亩水稻、多少亩小麦,都要计划委员会下达任务书,再由公社层层向下分解。甚至一个生产队开始种稻子时,一亩田什么时候泡稻子,什么时候开秧门,一亩田种多少棵,棵与棵、行与行之间有多少距离,都要领导同志开会布置,生产队没有自主权。所以农民说,种田的人没有权,有权的人不会种田,瞎指挥。万里同志听后气愤地说,有的人只会瞎指挥,这也管,那也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农民最关心的是工分计算和口粮分配。当时工分怎么记呢?一个生产队几十上百人吹哨上工,晚上开评工记分会就吵,吵到大半夜也吵不出名堂,最后只好都一样,搞平均主义——男人10分工,妇女8分工,老人和未成年人5分工,这就是大呼隆。
在口粮分配上,农民基本上只能靠杂粮。国家征购任务只收大米和小麦,而淮北平原2000万人口地区土壤不适宜种水稻,出产的主粮就是小麦。小麦因为产量比较少,交了征购任务后,人均口粮小麦一般的只有25斤,多的也只有四五十斤,只够一个月的口粮标准,另外那11个月只能吃杂粮,主要靠山芋。所以,淮北的农民说:“红芋面、红芋馍,离开了红芋就不能活。”又说:“红芋是儿子,小麦是女儿,儿子是自己的,女儿是人家的。”这样的情况,人们哪有种麦积极性呢?万里同志说:“种田的人吃不饱肚子,所有的中国人就别想吃饱肚子。不让种麦人吃小麦,城里人就不可能吃到白面。”
万里和光宇同志在调研途中就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从现在开始告诉各地,农村一切工作都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安徽暂时停止“学大寨”,解散省“学大寨”办公室,暂停各级干部去大寨学习,已经联系好火车的都要停止。
回到合肥后,万里同志交待王光宇,你暂时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集中研究一下农村究竟有哪些方面阻碍着农民的积极性,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你组织一个小班子,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再进一步调研,征求基层干群意见,重新制订一些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
根据万里的指示,光宇同志以省农委调研处(后称农委政研室)为基础,由周曰礼牵头,组织一个小班子8个人,开始进一步调研。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调研结果出来了,送给万里同志看。万里同志看得非常仔细,反复审改,随后决定由他自己和其他3位书记,分别在4个点,带着意见稿与基层同志,特别是基层第一线的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和农民代表座谈,看看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还有什么建议提出来。这样又讨论了一次,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1977年11月中下旬形成了文件《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这份文件发布以后,各个地方非常轰动。不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各个地方向农民传达的时候,没有一户缺席。听一遍还不过瘾,要听第二遍、第三遍,简直是欢呼雀跃。文件送到中央以后,首先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
这份文件大概是11月下旬上报的,邓小平同志年底去四川考察,带了一份交给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他说:“万里在安徽搞出来的,你们看看。”此后,《人民日版》在头版登载了资深记者、长期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姚立文写的长篇通讯报道,题目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从此,安徽的这份“省委六条”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十几个省份给安徽发来电报或是打来电话,要求我们把这个文件给他们一份作为学习参考。endprint
这份文件的中心内容就是农村的一切工作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加强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实行生产责任制,有些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的事由生产队自己做主;鼓励农民在参加集体劳动的同时,经营家庭副业,经营自留地,参与集市贸易,增加农民收入;减轻集体和农民负担,落实按劳分配;粮食分配一定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最后一条是,基层各级干部要参加集体劳动。现在普遍认为,这份文件是对多年来农村经济极左政策一次比较全面的拨乱反正,宣告安徽省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二
1978年,安徽省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據各地市县当时向省委汇报,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说,在他们一生当中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大旱。从谷雨后到8月底召开全省抗旱秋种会议时,全省没有下过一次透雨。按气象部门的术语,就是没有一次形成地表径流的降水。全国四大河流之一的淮河,那年收麦子以后直到十月霜降,从蚌埠闸以上几乎是一潭死水。江淮之间淠史杭灌区是全国最大的灌区,有1000多万亩,5大水库常年的积蓄量是60多亿立方米,这一年5月,正是种稻子最需要水的时候,这几个水库的水位已在死库容以下,放不出水了。皖南四条主要河流青弋江、水阳江、秋浦河、新安江,有的地段时常断流,人们可以打着赤脚过河。
在江淮分水岭地区,定远、凤阳、嘉山(今明光市)、肥东、六安、肥西的一部分,有400多万人没有水吃。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只好请省军区的汽车连和驻安徽的陆军第六十军汽车团,出动几百辆汽车从巢湖运水给农民吃。万里当过北京市委书记,他专门要求北京市调来20多支打井队到安徽,帮助各地找水、打井。在省委机关大院打了一口60多米深的机井,要求洗衣服用井水,以节约自来水。
到8月底,省委召开全省抗旱秋种会议时,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汇报,肥西县(时属六安地区管辖)到现在还有70万亩稻坂田不能耕翻,连拖拉机都犁不动。这种情况怎么办?此前安徽几乎每年都会有春荒,如果现在秋种再搞不下去,明年夏荒又在所难免。领导同志们都非常着急。
在这种情况下,光宇同志回想起1954年发大水的情况。1954年的大水来得早,正是插秧的时候,5月初沿江就成为一片泽国,所以很多地方栽不下去。水灾与旱灾不同,水来得快退得也快。退水的时候,人们就抢着栽种晚茬稻。但是退水晚的地方,就没法插秧了,因为耽误了育秧的时间,没有秧苗。农民当时还是一家一户,他们就自发地互相借,退水晚的地方向退水早的地方借,借几块田来育秧,对借出田的一方也不影响,还给一定报酬,大家都不影响栽秧时间,这就叫借田育秧的办法。
光宇同志想到这个办法后,向万里作了汇报,说我们现在的土地都是集体的,农民家里没有地,我们能不能从集体耕地里借一点给农民,调动千家万户积极性,自种自收自吃,种点保命粮,到明年收麦以后,土地再归还集体,这样夏荒要好一些。万里同志说,这个办法好,可以!我们借出土地,小麦收获后,马上收回来,这不是分田,这是短期的帮助抗灾的办法,不会犯原则性错误。
当时借的地有多少呢?起先一个人借2分地,后来万里同志决定借3分。当时假设,一个人借3分,五口之家就有一亩五分地,一亩五分地搞得好就能收获一两百斤甚至三四百斤粮食。为此,省委给全省发了电报。除了借地种麦外,还鼓励大家开荒种地,都是自种自有,不交征购。谁收的多,谁吃得多,调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把洗锅水、刷碗水、洗脸洗脚水都用起来了,有的从远处挑水种田,各种办法都用上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肥西县山南公社(当时称山南区柿树公社,后合并到山南公社)黄花大队乘机把集体耕地全部都分到户了,区委书记汤茂林和公社书记王立恒同意,并要求对外保密。这个事情省里不是一点不知道,周曰礼所在的省农委政研室有位同志叫沈章余,是肥西人,他告诉了周。周曰礼原是曾希圣同志的秘书。1961年,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的时候,就让周曰礼和陆德生(当时是省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两个人在合肥大蜀山下一个生产队搞试点,具体研究一下怎么搞,制订具体办法。他知道包产到户的好处,农民欢迎包产到户,告诉沈章余不要再讲,装着不知道此事。为什么呢?如果说你知道了,不去制止,那就犯错误了;也不能向领导汇报,否则领导为难。不知者无罪,让农民搞下去。大家都装作糊涂,心照不宣。
三
1978年12月中下旬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万里、王光宇、任质斌、杨永良4位中央委员前往参加。全会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两个文件。文件总体上是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加快发展农业生产,但明确写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两句话。万里同志在华东大组上发言时表示:“不要写不许包产到户了,就保留一句不许分田单干吧,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是一回事”。万里同志的这个意见登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简报,但是文件起草组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979年1月中旬这两份文件发下来,全省组织干部到基层宣讲,贯彻落实。光宇同志告诉了周曰礼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情况,周知道了万里同志的态度,于是在他率队下去宣讲时,有意去了肥西山南,并把肥西县委农工部长魏忠、施道周也一同约了去,想乘机把山南包产到户捅开,把偷着干变成正大光明公开干。
2月4日,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八,在山南黄花大队召开干群大会,宣读中央两份农业文件。听众炸开了锅,最经典的是一句话:“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周曰礼连夜赶回合肥,次日上午与光宇同志一道向万里汇报。万里同志思考了一下,说这是大事情,我个人不好做主,通知省委办公厅,明天开常委会,集体讨论。事后光宇同志告诉我,可能万里意识到这次常委会的意见不会很统一,会有争论,所以这次常委会开会的地点定在稻香楼的西苑会议室,不在省委办公厅内。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省委常委之外,我记得还有省委办公厅主任于廉同志和长期做常委会议记录的李迈力同志,另外还有就是1975年跟着万里同志在铁道部搞整顿报道的记者张广友同志。endprint
会上,周曰礼汇报了山南公社的事情。在会上发言中,有的同志提出,包产到户不能搞呀,毛主席批了那么多,七千人大会上批,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单干风,“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那么多人受批判,有的人还在全省游斗,我们怎么能搞呢?也有的同志说,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都是老党员,不能走回头路。还有的人说,包产到户确实能战胜灾荒,确实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欢迎包产到户,但是现在中央文件明确讲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们是不是再给中央写个报告,请示一下,请中央表个态。不过大家也知道,既然中央全会讨论过的文件都写不许了,你写报告有什么用呢?哪位领导会批!
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同志说话了,他说光宇同志自从1950年代中期就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是老资格的省委农业书记,请他讲讲他的意见吧。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工作人员推门进来,说现在已经12点多了,餐厅准备好了午餐,请各位领导到餐厅就餐。万里同志说,先吃饭,吃完饭后再开会,光宇同志第一个发言。
吃饭以后复会,光宇同志发言。他首先回顾了安徽1961年搞责任田的情况。他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有不少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饿、病、逃、荒、死,农民受到了很多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被迫搞责任田,结果当年就翻身。秋收以后,安徽农民不仅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我们的邻省,苏北和鲁西南,好多与安徽毗邻的县的农民,骑着自行车、牵着小毛驴或者挑着担子到安徽来购买粮食。好多是以物易物,带着家里的东西来到我们这里换粮食。尤其是河南省,这一年冬天,郑州经常开来闷罐子车、铁皮车,到我们淮北来收山芋干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联名打电报给安徽省委,感谢安徽的支援,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责任田确实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责任田确实能够战胜困难,农民非常怀念责任田。至今农民还说“责任田就是救命田”,如果不搞责任田,安徽当时死的人可能还要多。现在山南搞包产到户,小麦生长得很好,苗情很旺,丰收有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制止山南这样做,要让他们搞下去。而且我还向省委建议,是否可以在其他贫困的地方,经济不发达生产落后的地方,尤其是边远山区的贫困社队,也允许他们搞一点包产到户。但是一定要经过批准,有组织有领导地搞,不能撒手不管,否则会出乱子,出现后遗症。
他的话刚落音,万里同志立即说:“刚才光宇同志的发言对大家很有启发。”(这句话已印入《万里文选》)万里同志接着又说,包产到户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能够战胜灾荒,农民又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为什么不允许?我认为并不是干部不允许,而是多年来的极左政策,批批批、斗斗斗,把人搞怕了,不敢同意。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同樣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在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万里同志讲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句话,非常了不起,振聋发聩。他接着说,我提议,把山南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验点。现时不登报、不宣传、不推广,干起来再说。到年底再做总结,好就坚持下去,不好就改回来。其他常委纷纷表态,同意万里同志的意见。这样就一致通过,形成省委常委决议:批准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验点。
散会以后,万里同志又专门交代王光宇和周曰礼,宣讲队就是驻点工作队,继续驻地观察和指导,有问题及时汇报,直接向省委汇报,向我万里直接汇报。一定要告诉当地党委要加强领导,做细致工作,保护好集体财产不受损失,保护好水利设施;照顾好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把这些问题研究好、解决好,不要授人以柄。
周曰礼同志连夜回到山南公社报告大家喜讯。会后第三天,光宇同志就带着我们到山南了,向汤茂林、王立恒同志反复交代,省委支持你们搞包产到户试验,你们不要怕,这是省委的决定,如果出了问题也是省委负责、万里同志负责、我王光宇负责、全体常委都负责。你们一定要把工作做细,不要给人家找茬子。接着他又去县里传达省委决定和万里同志的指示。
四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张浩来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营制度,安徽搞包产到组,是搞三级半所有制,是直接违背了我们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是错误的,应当改变。《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支持写信者,直接点名要安徽纠正错误做法。
那一天,我和光宇同志出差在定远县,早上我俩在散步的时候,从手提收音机里面听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报道的这条消息,光宇同志马上就回到招待所,赶紧打电话给万里同志,万里同志说他也听到了。他们两人商议,立即让省委办公厅通知各个地方,现在是大忙时节,各种类型的生产责任制,不论是包产到组,还是个别已经责任到户;不论是联系产量,还是不联系产量的,一律都不要改变,不要动摇,不受报刊舆论干扰。万里要求光宇同志继续在北方地县检查指导工作,他自己则去皖东来安、全椒等地。光宇同志比其他地方提前2个小时对定远县传达了这个指示。我电话通知了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和革委会主任吉诏宏,要求他们赶快到定远与凤阳交界的黄泥公社碰面,光宇同志在那里传达了万里的指示。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1978年5月搞了包干到组,五六户、七八户为一组,因为还顶着个集体,不是到户,所以县委支持。9月初省委下达抗灾借地种麦指示后,普及到全县。“张浩来信”矛头直接所指的就是他们,说这是搞三级半所有制,是错误的。光宇同志传达万里的指示,叫他们不要理睬,大胆坚持,只要群众拥护,能多打粮食,自己吃饱肚子,又能对国家有贡献,不仅是三级半所有,哪怕是四级所有又有何妨?两位县领导人听光宇同志这么一说,都十分高兴,吃了定心丸,不怕那些干扰了,一致表示要坚定信心,争取今年大丰收。吉诏宏又乘势说,农民更希望包产到户。陈庭元立即打断他:“只能到组,谁搞到户开除谁的党籍。”我想,这不是他的内心话,而是因为1959年他作为严重右倾受到批判,心有余悸,在光宇同志面前讲此狠话,是一种政治表态。我们在黄泥公社吃了午饭后,就朝五河、泗县一路去了,过淮河,上淮北。endprint
万里同志3月16日上午到了来安。来安与凤阳一样,全县搞了包产到组,魏郢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是县委书记王业美同志批准的试验点。万里同志告诉他们不要理睬“张浩来信”,你们该干什么干你们的。有的同志说,邻居江苏拉大横幅“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万里同志不屑一顾地说,不要理他,“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的同志表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头版头条我们确实害怕。万里同志讲,《人民日报》是公共汽车,别人能上,你们也能上。他们能写人民来信,你们也可以写人民来信。他能上头条,你怎么不能上头条?他还对地委、县委同志说,不要像“文革”时期,一见北京来电就不得了。农民饿肚子是找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报纸能给你饭吃吗?要自己当家!
当时,周曰礼同志正在北京参加国家农委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他得知这个信息后,就打电话让手下两个笔杆子辛生和卢家丰两人去北京住在安徽驻京办事处,写人民来信反驳“张浩来信”。《人民日报》不登,说“张浩来信”登在头版头条并加“编者按”,我们是报国务院审查的,一位领导同志同意的,现在你们起码要报到他那里,最好是更高的领导。这时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同意周曰礼在会上不限时发言,汇报安徽推行农村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情况。周曰礼在会上讲了2个多小时,各种责任制形式都讲了,包括山南公社的试点。那天,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都到了会。会上各省发言分歧争论很大,王任重离会打电话询问万里,你们安徽来了一个周曰礼同志,他发言内容你可知道?万里同志回答,周曰礼同志我们提拔他当安徽省农委副主任,他去北京我知道,发言内容向我汇报过,是我派他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发生了转机,《人民日报》3月30日刊登了也是头版头条加“编者按”的读者来信,还自我批评3月15日“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注意改正。
五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安徽省军区有位副司令员,到山南公社视察,当面批评汤茂林、王立恒,说他接到好几个部队战士的来信,说家里搞包产到户,我们参军后家里没有劳动力怎么办?我们要回家。指责他们动摇军心,毁我长城,你们赶快收回来。而且他又直接打电话给县委。当时县委书记在党校学习,县长接电话后很害怕,作出县委决定,限定10天改回来,列出包产到户12条“罪状”,还办干部学习班,对思想不通,不收回包出土地者就不让回家。
对这个大波折,周曰礼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安徽日报》驻六安地区记者汪言海和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郭崇毅两位同志写了内参,万里都看了,并作了肯定性批示,于1979年8月3日再次召开专题省委常委会进行研究处理。
省委常委再次统一思想,坚持山南试点不动摇。尽管此时包产到户已扩大到山南全区6个公社777個生产队近8万农业人口,比当初的试验点大大增加了,万里同志仍坚定地支持群众:“让他们搞,先吃饱肚子再说。”万里同志坚定地支持群众,常委们共同担当,会议批评肥西县委错误做法,责成收回错误决定,并由光宇同志亲自去肥西县处理。
1979年,万里同志两次去山南视察指导工作。第一次是5月21日,主要是看麦子长势,群众情绪,指示区社党委一定要加强领导,处理好相关问题,鼓励汤茂林、王立恒大胆工作,不要怕,省委批准的试验,如有问题由省委负责,由我万里负责。快年终时,他得知中央即将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他将调京工作,于是又于12月13日再去山南,要汤茂林详细汇报各项配套规定落实情况,社会各阶层的反映,要有具体事例。汤茂林讲全区今年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加近两倍,征购任务超额43%完成,军工烈属和五保户、困难户的照顾逐户列表,有具体粮款数字,农民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社会治安从未有过如此祥和景象。万里同志高兴地说:“这根本不存在毁我长城,穷的穷富的富、哭的哭笑的笑的问题”;“外界传的,有的根本不是问题,有些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关键在领导”。他赞扬区社工作扎实,接着又就近走访了小井庄生产队几户人家,亲眼所见户户存粮满仓,这下更加放心了。面对闻风而来的农民,他在一位老奶奶家的堂屋里与群众座谈,当大家都问“明年还能不能再这样干”时,万里同志笑容满面地说:“家家都增产增收的好政策,怎么会变呢?你们放心地干,祝今后的日子越来越好。”回程途中他对秘书许守和说,要把农村的这些新气象、好消息,带回北京,报告中央。
根据万里的指示安排,光宇同志2次到县城,5次去社队,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去县里参加2次常委会,传达省委指示,要他们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省委决定的。县委有位同志当面说,下级服从上级是党的原则,全党服从中央也是党的原则,中央文件写了不允许包产到户;再说中央是有红头文件的,省委指示只是口头传达。光宇同志说,这不是我们偷着干的,省委派周曰礼在国家农委会议上作了汇报,中央几位领导都参会听了。我们讲是做试验,到年底再做结论。好就坚持,不好就改回来。而且包产到户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包产到户不改变所有制,是实实在在的按劳分配,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决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要怕,有问题由省委负责,由万里同志负责,由省委全体常委负责,由我王光宇负责,没有你的责任。光宇同志又与他个别谈心,对他的疑问作了耐心解释,在这样情况下,这位同志表示服从省委决定。县委成员统一了认识,增进了团结,收回成命,终使包产到户在肥西山南结出了硕果,为全省、全国的农村改革带了个好头。
山南公社包产到户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考察、调研的络绎不绝,邓小平同志给予肯定。这里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农村改革的成功范例,是党的领导和群众意愿相结合搞改革的成功范例。这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他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山南的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己先搞起来的。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中,光宇同志在关键时刻、关键会议上,做了一个观点鲜明又有极强说服力的发言,对促进万里同志下定决心,促进各位常委统一思想取得共识,形成决议,起了重要作用。endprint
六
光宇同志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在淮河岸边放牛、种田、读书,一直到18岁投身革命。他了解农村,关心农民的疾苦。在我当秘书的那几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生产严重破坏,加之连续的旱涝灾害,农民生活很苦。特别是江淮地区,有不少农民长期外出逃荒要饭。当时安徽的盲流在全国是很出名的,影响不好。所以那几年冬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光宇同志几乎都是在那些穷困地区农村度过的,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安排和检查灾民的生活,特别要求各地领导干部,起码要让农民群众在过春节那几天不至于外出讨饭。
他知道沿淮地区群众有个习惯,希望大年初一能吃上一顿饺子。如果新年第一天连饺子都吃不上,就会认为新的一整年都会不吉利。因此,他与救灾和扶贫部门商定,年关给这些地区的困难户每人发5斤面粉、一斤猪肉。
记得1980年2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天上下着大雪,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凤阳县小溪河车站。我们看见许多人从火车站走出来,基本上都是从南来北往的运煤车上爬下来的,一个个灰头土脸,混身黑乎乎的,背着个化肥袋子,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在狂风暴雪中艰难行进。此情此景,我们心中都不是滋味。光宇同志马上想到,昨晚听县委、县政府汇报,今年春节期间群众生活安排已经落实了,而这些人今天刚回来,也许明天,甚至后天大年三十,还有讨饭回来的,他们家里是否有做年夜饭的米?显然没有检查到,因为这些人当时尚未到家。
于是,光宇同志让司机把车子开进火车站附近的梨园公社,也就是小岗村所属的公社。到了公社后,光宇同志让我打电话把县委书记陈庭元和革委会主任吉诏宏都请了过来。但开会时,有的公社干部讲话很有点不着边调,说:王书记,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很穷,其实他们并不穷。凤阳人自从出了朱元璋,就有个“身背花鼓走四方”的习惯,不少人每年种罢麦,门一锁,举家外出,打花鼓,耍猴子,吃百家饭;中间回来过几天年,初七前后又会出去,直到割麦时才回来。有的人温饱有余,套上了新上海表;有的人背上了半导体收音机;还有人发了财,回家盖新瓦房,娶新媳妇。光宇同志是位忠厚的长者,我几乎从未见过他发脾气,这次他却很生气,非常严肃地批评:群众生活如此困难,你们不是很好检查自己工作做得如何,反而这样信口开河。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在家得以温饱,谁愿意在这寒冬腊月,冒着风雪严寒,离乡背井,拖兒带女,在外面挨门乞讨,对人低三下四!不信你们自己去体验体验,如果讨饭真能发财、发家致富,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庭为什么不参加到这个行列?一席话把这些人讲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后来还是陈庭元同志打圆场:快别这样乱扯了,赶快下去重新检查,看看这些人有无做年夜饭的米,还有没有人尚未到家?我们也赶快回去,通知各社队重新检查群众生活,特别是各地粮站要保证年关有人值班,留出一定救灾备用粮。
第二天上午,我们往五河方向检查工作,中午到了县城对岸小庄子农户家时,发现穷困户面粉发了,但是没有肉。一位老奶奶说:“今年大年初一吃不上饺子啰!”光宇同志吩咐我们立即过河到县委。在县委办公室值班的祝副书记说,五河全县的食品站都没有肉了。光宇同志批评道:“怎么早不汇报?现在外调也来不及了!”他拉着祝副书记一同去县食品公司,又与经理一道去食品公司仓库,好不容易找到一点腌肉,光宇同志说:既然大年初一吃不上饺子,那也要让群众明天年夜饭桌上有一样荤菜。他让县里连夜把腌肉送到农户家里。
次日是大年三十,我们一大早又沿着泗县、灵璧、固镇这条线走,没有到县城,直接进村入户。这一带外出人口少一些,基本上都回来了。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固镇县磨盘张公社,省人大原副主任陈瑞鼎当时就是这个公社的书记,他汇报说群众生活安排落实了,与我们在路上检查的情况相符,光宇同志思想上安定了些。陈瑞鼎说,固镇的风俗是中午过年,留我们在那里吃年夜饭。于是我们一行4人,与12位公社干部一起,在公社食堂开了2桌,两荤(猪肉和野兔肉)三素一汤。下午3时许,我们上车返回合肥。在车上,光宇同志深情地说:“什么时候我能看到全省农民都能常年吃上饱饭,我就安心了!”驾驶员唐义明和警卫员桑潮水不约而同地说:“全省都搞包产到户,肯定天天吃饱饭!”我也乘势讲了句:“大好河山怎会吃不饱肚子?关键是看政策!”
在我的手头上,还保留着一份光宇同志在1981年2月14日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记录稿,是光宇同志亲笔修改后,让我誊抄一份,把誊清稿送给办公厅归档,原稿就留下来了。光宇同志在发言中先批评了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对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不正确态度,接着反复检查自己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错误。他说: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村出现了饿病逃荒死,我当时是省委领导成员之一,“这个罪责我终身不忘”。记得我抄到这里时,停下了笔,去向光宇同志进言。我说,对于那三年的问题,你也不知检讨过多少遍了,几乎是逢会必讲。其实那三年的错误,不仅是安徽,全国各个省区都有,有好几个省比安徽更严重,非正常死亡的人比安徽还要多,在那种情况下,你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即便是第一书记,也是无力回天的。我的意思是,这主要不是你的责任,你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不要用“罪责”这样的词。光宇同志说,你的这些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从总体上看是不正确的。正是因为当时错误严重,错误的面又那么广泛,那就决不是少数主要领导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在有关岗位担任一定职务的负责人,都应该深刻检查自己有什么错误,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只有全党都进行深刻反省,牢记血的教训,今后才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他接着又说,我当时确实有很多错误,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观主义,不实事求是,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都喊过。让农民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每次想起来都非常内疚,深感对不起农民……光宇同志当时对我说的这些话,他多次检讨中也都是这样写的。
我认为,正是因为光宇同志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高度尊重,无限敬畏,所以他才能在1978年那个时候,当时极左思潮尚未得到彻底清算,“两个凡是”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根基还很牢固,而他能甘冒相当的政治风险,置个人荣辱得失于不顾,果敢地、公开地表明自己支持包产到户。endprint
七
离休后,光宇同志每天第一要务就是学习党的文件,看书学习。《人民日报》《安徽日报》他是每天必看。直到九十高龄时,每天仍是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报纸,重要文章不止读一遍,有的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下来。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发表时,他硬是戴着老花镜,每天用毛笔抄录1000多字,共用7天时间,把全文抄了下来。他崇拜陶行知先生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也不知抄写过多少幅,挂在他的卧室,放在他的书案,当作他的座右铭。
许多老同志离退休后都出版了回忆录,发表专著。省人大原秘书长陆德生同志曾把我们这些当过他秘书的人找到一起,商量整理他的传记。当时钱正(光宇同志任省人大主任时的秘书)就说:“这得问他自己,他不愿搞咋办?”果不其然,他不同意。后来陆德生同志又让我们自己写点有关他的文章,适当时候发表。我和袁大振(从淮海战役到阜阳地委书记时期秘书)、金玉言(农业合作化至三年困难时期秘书)各写了一篇,光宇同志知道后又不让发,把稿子扣了下来。有次他与我专门谈及此事,谈得很深,总之是认为当前社会上这类书“有点滥”,“不干这些为个人树碑立传的事”。后来,《往事回顾——王光宇口述》之所以成书,主要是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聂皖辉和资料信息处处长汪智敏等同志,多次上门向他解释,说这是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安排,经省委批准,为了记录、保存一份安徽党史资料,他才勉强同意的,说“服从组织决定”。断断续续经过8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同志采访、录音56次,整理修改,最后上报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经过他们审核肯定,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上将亲自作序,肯定他“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严谨认真,所讲内容很朴实,很谦虚,读后令人觉得亲切、实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
他住的宿舍是1952年盖的,已住了一个甲子。房改后省行管部门告诉他,这处住所在办公大楼旁边,所以不能出售,省里在另外两处盖了省级干部宿舍,按照规定他可以买一套,享有一份福利房。但他坚持不买,说他的孩子们都在各自单位分了房,有房住,他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这产权房干嘛。有人曾劝他:“你最关心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了,现在陶研会经费困难,你买了福利房,将来卖了把增益的钱捐给陶研会。”他说:“用公家钱捐赠,这不是沽名钓誉嘛!”
这些年,他的工资收入除了用于家庭开支外,主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捐赠。汶川大地震时,他先在省人大老同志所在的党支部捐了1万元,后来从电视上看到当地灾情那么重,灾民生活那么苦,恢复家园那么需要钱,决定再捐3万元。当时他手头钱不够,还是司机霍荣幸垫了1万元,发工资后归还的。这些年,他先后支持了5名穷困家庭孩子上大学,有的从小学帮扶到大学,有的从大一管到大学毕业,平均一人在3万元左右。
有一年9月初,我在他家看到绩溪县的一位小姑娘,是省人大老同志所在党支部为他联络的扶贫助学对象,在上海海运大学读二年级,开学了来他家拿学费。光宇同志一次就给了她8000多元,让家人为她买了些学习用品,还买了些食品。去年这孩子来拿学费时,在光宇同志家住了一夜,老人与她谈心,问长问短,鼓励她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这次她说学校已经开学,她一下汽车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光宇同志留她吃过午饭就走了。小姑娘对我说:“多亏了王爷爷,如果不是王爷爷,我哪能上大学呢!”
还有一件事,我非常感动,过去从未公开讲过。1982年6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七中全会,为党的十二大做准备。会议期间,胡耀邦同志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意见,每省参加2人,安徽是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周子健同志和王光宇同志参加的。会上中央人事安排小组通报了对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名单。安徽在册的有4人,其中就有光宇同志,名册上是这样讲的:“王光宇,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继续当中央委员。”讨论时,光宇同志站了起来,说:“某某某同志,中央建议名单上是候补委员,我提議他当中央委员。如果中央因为名额限制,不好调整,我愿意与他调换,他当中央委员,我当候补委员。”后来还是胡耀邦亲自表态:“不变了,王光宇同志继续当中央委员,某某某同志中央另作安排。”那天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对我连讲了两遍:“今天光宇同志的发言,太让人感动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光宇同志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他一心只想着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从1956年1月起就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85年离开省委,到省人大工作为止,当了30年的书记处书记,其间第一书记换了8位,真心实意给予支持,实实在在当好助手。他的这种坚强的组织观念,这种共产党人的高度党性原则,这种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确实令人钦佩!
[作者曾任王光宇同志秘书,原安徽省农经委副主任,省政府咨询委咨询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