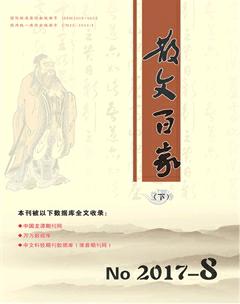过年五忆
冬至过后,“年”便如一场长途比赛的终点,慢慢地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了。关于小时候过年的记忆便如那挂在终点的晃动的红绸,永远那么鲜艳。
杀年猪
记忆中的过年,是从一 阵又一阵“嗷嗷嗷”的杀年猪的嚎叫声开始的。
腊月以后,“嗷嗷嗷”的此起彼伏的嚎叫便响起在村庄。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了。
民谚:“养鸡为换盐,养猪为过年。”平常日子过得好不好要看鸡屁股,过年过得好不好要看猪屁股。年猪的重量决定了过年的质量。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要养几条鸡,养几头猪的。养鸡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下蛋,换盐;养猪不是为了卖,而是为着等过年杀。过年时杀猪不叫“杀猪”而叫“杀年猪”,就是这个意思。一条年猪,绝大部分都要烘成腊肉,过年的那几天要吃它,正月来了待客要靠它,开春以后肚子闷了解馋要靠它。没年猪杀的人家,男人没笑容,女人唉声叹气,靠从市场称点猪肉从亲戚家赊点猪肉烘十几块腊肉对付过去。
杀年猪前几天,父亲母亲便把杀年猪的日子告诉了所有的本家、亲戚、好友,请他们喝“猪血汤”。
头天晚上,母亲会比平常多舀几瓢潲倒到潲盆,让猪吃得饱一些。母亲说,不能让猪当饿死鬼。
天麻麻亮,母亲便会把我的耳朵扯起,“杀猪了!杀猪了!”。急急忙忙爬起来,打着电筒往老屋赶。父亲、大舅、小舅,还有几个本家叔叔、哥哥已经把猪赶出了圈,出了门楼往堂屋方向赶了。母亲在堂屋早就摆好一张高凳,一个放了清水的木盆。快到堂屋,父亲大吼一声,揪住一只猪耳朵,大家便揪耳朵的揪耳朵,扯尾巴的扯尾巴,抬脚的抬脚,把猪抬到堂屋,架到高凳上。父亲用棕绳把愈发“嗷嗷嗷”大叫的猪嘴巴捆住。旁边的人把杀猪刀递过来,父亲用刀背在猪喉咙上拔几根毛,对空一吹,把刀对着那猪喉咙稳稳地捅进去,直到刀柄埋没,再一抽,便有猪血喷泉般地喷进盆子。母亲用手在盆里急急地搅着。待血放尽,父亲喊一声“放”,大家把猪往后一甩,那猪挣扎一阵,便往极乐世界去了。
有一年杀猪,不知是父亲的刀法走偏还是血未放尽,那猪竟然还围堂屋走了几个圈,实在是好玩而又惊险。
接着要刮毛。刮毛就像给猪洗一次热水澡。猪这一辈子(实际上也就是一年,最多两年,有的只有半年)都在又脏又冷又湿的粪坑里滚,却没想到能在死后干干净净地洗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热水澡。刮毛前,要把猪吹得圆圆滚滚,刀好用力。先在猪脚踝割一个小口子,用一根钢筋四处通一下,然后用嘴对着口子吹,吹一阵,扎住,用捣衣棒猛捶几下,再吹,再扎,再捶,直到把猪吹得圆圆滚滚,才用绳子把口子扎住。七手八脚地把它抬到架了一根板子的木盆上,开始刮毛。水是早就烧得滚开了的,打一壶开水慢慢地烫过去,那刀便“嚓嚓嚓”地刮起来,毛和污垢应声而落,逐渐地白多黑少,那猪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新娘子了。
然后是开膛、破肚。一头被刮得干干净净的猪,毛重起码在二百斤以上。要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开膛破肚并非易事。父亲要把一架楼梯取出来,摆在地上,把猪抬起,放平。把猪的后脚用绳索栓住一根棒槌,再把棒槌反扣住楼梯,大家“一二三”“一二三”地喊,齐心协力地把梯子慢慢地举起,靠墙立住,然后从容地开膛破肚。大肠、小肠要趁热取出来,洗干净,板油、猪肝、腰子放簸箕。这猪便只剩下一具骨架子了。再用斩骨刀把猪从背脊中间破开,卸下半边放案板,然后再卸楼梯的另一半放案板。
一头年猪,除了杀猪那天剁十多斤,请亲朋好友吃猪血汤之外,其他的都要用斩骨刀慢慢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开出来,放进早已洗净的几口大缸里,倒醋、白酒、生姜、鹽,搅匀,盖好,入几天味,拿出来,一块块的挂在堂屋的楼板底下,就像一排排小小的瀑布,看着就欢喜。
晾几天,水干了,这些腊肉都要再取下来,横一排竖一排地挂在火炉头,用灶火的烟气熏。过不了几天,这腊肉就会慢慢地由白到微黄,再由微黄到黝黑,最后由黝黑到苍黑,就像《水浒传》里李逵的那张脸。
那烟火熏出的腊肉,真正是香,而且解馋。来客了,不用花钱去街上买肉,取一块或割一截,炒了或蒸着吃,都很好。夹一小块腊肉,就能喝一大杯酒,宾主都喝得满脸通红,油光满面。若是“五匹马”、“八福寿”、“九长春”地再喊上几拳,那就实实在在地太尽兴了。
有些客少而节省的人家,头年的老腊肉可以接吃到来年烘的新腊肉呢。
如今过年,“嗷嗷嗷”的杀猪叫声已经少了。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养猪的少。过年到集市上称几斤猪肉,凑合过完年就走了。
养狗的却多,一到夜晚叫得欢。
大年三十
过年就像一部轰轰作响的列车——狂吃狂吃狂吃,四处乱走,到处狂吃,所以苦,所以累。
大年三十作为一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天,更要千方百计搞点好吃的,做年夜饭便是许多家庭的核心任务。在我们家,那是母亲的核心任务,父亲的核心任务是写春联。
那时候我们村子过年时贴的春联大半都是父亲写的。
头几天晚上,父亲便拿一支铅笔,几张稿子,坐在火炉边,琢磨对联了。父亲高小文化,当过民办老师,是方圆十几里很有点名气的读书人。父亲写对联,不像别的农村写手,只知道照抄挂历本上的对联,而是根据什么季节,主家什么家境,办什么事,有什么想法琢磨出来的——这已经是写对联的较高的境界了。后来我到政府办公室搞材料,给领导写讲话稿,主任告诉我们要考虑到“此情此人此景”,和父亲琢磨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总结不出来罢了。记得我刚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内心喜欢的父亲在堂屋的屋壁写了几幅对联,其中一幅“堂小更易闻风舞,檐低更易见鹏飞”,一直被我牢牢记得。另有一幅贴在八字门楼的长联,写得很好,在村里引起了轰动,内容却不记得了。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知道排比、对仗,乃至后来到政府办公室搞材料,又走上文学道路,父亲的启蒙与影响是巨大的。
可是父亲的毛笔字却不算好。小时候的那一点童子功,被那长年累月的锄头、镰刀练坏了,基本属手写体,不过,在农村也算是好的了。父亲的另一个特点是胆子大,写什么东西,用铅笔先写出来,裁好红纸,叠好格子,拿起毛笔,一挥而就。不像我,要想好想好,比划好以后才动笔——我本身就是一个拘谨的人。endprint
写毛笔字,笔墨纸砚不可缺。父亲有几杆毛笔,其中一杆毛笔很大——大毛笔写对联,小毛笔写帖子,都插在我和哥哥房子书桌的玻璃瓶里,平时不用,只等过年或人家办事请父亲写贴子或写对联才用,起一层厚厚的灰。砚呢?自然是没有的,用一个跌缺了一角像豁了牙齿的碗。写时,把墨汁倒进碗里;写完,便把毛笔架在豁口上。谁说那不是父亲最好的砚呢?
一大早,父亲便摆开桌子,拿一把镰刀,端一张高凳,开始写对联了。有的邻居几天前就拿红纸过来了,说要几幅几幅,父亲一一记下。不断有左邻右舍送红纸来,父亲一一问清,要几幅对联,大门、小门,还是神台。边裁纸,边说,这几幅适合你,去年你家里娶了媳妇,添了孙崽,发了大财,“去岁已乘千里马,今年更上一层楼”,这幅对联有什么含义,如何如何,来人频频点头,然后一挥而就。来人说:“辛苦!辛苦!”父亲含笑,微微点头说:“快回去贴起,办年夜饭”。
开始有人打鞭炮了。父亲还在写。
鞭炮打得愈发密了,父亲还在写。
鞭炮已经响得像打仗了,父亲还在不慌不忙地写。
母亲便有些怨,催道:“快写!快写!写完好办年夜饭。年年都是这样,吃年夜饭总在别人后面(吾乡习俗,吃年夜饭宜早,意为一年到头,凡事都在人后,吃年夜饭不可在人后,图吉利)。”
父親头也不抬道:“吃夜(饭)吃夜(饭),夜一点不要紧,不急不急。”
终于写完了,我和哥哥舀起稀饭,拿块洗碗布,搬起楼梯,去贴对联。
鲜红的对联贴在门框,让人心中无比的喜庆。
父亲开始做年夜饭。
年夜饭很简单,其实都是在拿猪出气——米粉肉、海带炖排骨、炒猪舌头、炒猪腰花……没有一样是离得开猪的。我向来以为,要了解农村的经济史,看一户人家过得好不好, 要看猪肉过年过节唱不唱主角。如果还是猪肉唱主角,那就不是全民小康,而是全面吃糠了。这两年,鸡、鸭、鱼、牛肉、羊肉已经上了农村的桌子,这说明农村的日子是越过越有滋味了。
吃了年夜饭,父亲要把柴火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在火炉头烤火,守年夜。火炉头上烧了一锅水,父亲爱喝那种烧得半开不开的滚水,“呼呼”地吹一下,喝一口,讲几句;再“呼呼”地吹一下,喝一口,讲几句。其实父亲更爱喝茶,可是那时候没有茶,只有喝一碗又一碗滚水。父亲爱抽烟,经常抽那种自制的用报纸卷起的喇叭筒。后来有了好烟,父亲常说那烟太假,抵不上喇叭筒来劲。
父亲的脸在炉火的照耀下忽明忽暗,父亲的讲话像火炉的烟一样时断时续。父亲常常说,去年一年,我们家做了哪些事,母亲、姐姐放牛、喂猪、种田,功劳很大,卖了一条牛崽,卖了一头猪,又杀了一头年猪,在家很辛苦。自己给别人砌房子,赚了多少钱。我和哥哥俩兄弟读书有长进,如何如何。明年我们家还要做哪些事,母亲、姐姐要做哪些事,自己还有哪些房子要砌,我们兄弟俩要更加加油读书之类的。火塘的火越烧越旺,我们的心也越点越旺,不知不觉,到了鸡叫。
母亲会说:“天不早了,歇着去吧。”
我们便歇去了。
隔壁的生仁叔叔家最有意思。每年的大年夜,他会给五个儿子发压岁钱,然后几爷崽一起,打“炸”,刮“登九”。当老子的把钱发出来,又把钱收回去。村里人都说,这个老子当得好。后来他们几个儿子,是我们村最早到广东打工的一批年青人。其中,老大在广东抢劫判了刑,其他的几个兄弟在广东也是呼风唤雨,这是后话。
拜年
正月里,去拜年,拜年讨个挂挂钱。
民谚:“走亲走亲,越走越亲。”拜年好像在亲朋好友之间扯起的那根线,再远的亲戚再远的朋友,不管平时有什么磕磕碰碰,但正月里还是要相互走动一下,吃吃饭,喝喝酒,叙叙情,表示大家还认这门亲,还有这份情。两家吵了架,有了隔阂,大人不方便,拉不下这个脸,打发小孩去。如果年都不拜了,说明这根线就从此断了,这份情再也没有了,两家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再没有关系。有的今年不拜了,隔了几年再拜,饭是有吃,酒是有喝,话语还是那么亲热,但感觉总有些隔,就像一根被扯断的线,重新接起,再光滑,总有一点小疙瘩。
各地都拜年,拜法各有不同。有的地方兴年前拜年,有的地方兴年后拜年。我们梧州瑶人兴年后拜年,并且基本上是初二才开始拜年。大年初二,要回娘家、舅舅家,所谓“娘亲舅大”,然后依次拜过去。至于为什么要等初二才开始拜年?我问过父亲。父亲说,过年前是新春,过年后是新年,拜年拜年,自然是拜新年,当然要等过年后才拜。后来参加工作才知道,很多地方都兴年前拜年的,拜早年更能表达尊重。特别是人到中年,在职场碰了一鼻子灰后才彻悟,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拜年实在是一个人职场生命中的头等大事。要多拜年,拜早年,早拜年,这与晚清官场达人李鸿章教导的“多磕头少说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拜年都比别人晚,提拔岂能不晚?更何自己天性疏懒,不屑拜年之道,职场焉有进步?反正自己是个散淡之人,慢就慢了,晚就晚了,不进步就不进步了,索性这辈子就这么闲散了去,也好。
拜年讲规矩,一般是晚辈给上辈拜,平辈之间互相拜。拜年要讲吉利话。不是亲朋好友,路上遇见了,互相道声:“新年好!”“恭喜发财”“高升”之类的,就算拜过了。村东头的王麻子喜欢做孽事。有一年大年初二,碰到村西头的刘聋子,想拿刘聋子开玩笑,说:“刘聋子,你老婆偷人。”那刘聋子听不见,以为王麻子说的是恭喜发财之类的,大声答道:“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大家笑得在地上打滚!以后再也不敢拿刘聋子开玩笑了。若是亲朋好友拜年,多少要讲点礼性,带点东西,一块腊肉,几升米,几个糍粑。若是长辈,还要带几个蛋,用粽叶包好,全部放进一个篮子,用帕子盖好。这腊肉、糍粑,你送我,我送你,在亲朋好友之间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自己家里,就像会走路一样。现在经济发达了,有买烟买酒买牛奶的。有的为省事,直接打红包,送钱,多好!
一大早,路上就挤满了拜年的人了。那时候主要是走路,骑单车,现在大部分是骑摩托。也有先富起来的,已经开了铮亮的小轿车了,前面坐一大家子,后面塞一厢子,“笛笛笛”的,好有面子。也有用箩筐挑了两个小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后面跟个婆姨,一家子热热闹闹。差不多到主家了,先打一挂鞭炮,报告主人。穿着一身新衣服的小孩叫公鸡般走在前面,满面笑容的大人提着礼物跟在后面。满面春风的主人迎出来,把人和礼物一块接进去。endprint
火炉的火旺起来,热气腾腾的茶端上来,五颜六色的糖果端上来,香喷喷的瓜子馃子端上来。话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像那茶里袅袅升起的热气,让心温暖。
亲戚是自己的镜子,总能照到岁月的无情。去年喝奶的,今年已经走路了;去年走路的,今年会打酱油了;去年打酱油的,今年去读书了;去年读书的,今年读大学或打工去了;去年读大学或打工的,今年结婚了;去年结婚的,今年生儿子了。青涩的,有毛了;有毛的,成熟了;成熟的,变老了;变老的,有皱纹;有皱纹的,更多了。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年轻时总希望长大,只有大人,心慌一个老。
菜一个一个的上,酒一杯一杯的喝。一切都是米酒化的。啤酒,“嘭”,干一杯;米酒,“嘭”,干一杯;白酒,“嘭”,干一杯。脸喝红,眼喝亮,心喝暖。酒喝不完,亲情喝不断。酒过三巡,好客的主人还要客人喊几拳,“响几下”,意为告诉左邻右舍,家里来了贵客。主宾之间,“五魁手”,“八匹马”,“九长春”地一通喊过去,嘴巴便开始打结,总觉得那地板有点不太平。主人早就准备了干干净净的客房,醉了,睡了就是。醒来,继续喝酒。
那边,殷勤的女主人要给小屁眼一点挂挂钱。只要没有参加工作的,都要打。胆子大的,会一把拿了过来,道一声谢。害羞的,左手挡着说“不要不要”,右手却扯起口袋,女主人趁勢就把挂挂钱放了进去。
“梧州奶崽穿挂挂钱——不要不要扯口袋。”
挂挂钱回去要交公,给母亲,交学费。
哪一年你真的不要——真的不一边说不要,一边扯口袋了,说明你真的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挣钱了。
酒足饭饱,客人要走,主人要留,留不住,便道:“也好,搭早走”。打一挂鞭炮,送客。
客人走了好远,主人送出好远,终于留步。
手挥得发酸。
唱戏
正月里,去看戏。
那时候,正月里总是很热闹,天天人来人往,客来客往。不像现在,“元宵节”还没有出,初三走几个,初四走一批,忽喇喇地,鸟一样,全飞到广东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俗称“三八六一”部队,村子寂静得吓人。
唱戏离不开戏台。那时候,每个村基本都有一个大礼堂,礼堂前有一个大戏台,专为放电影、唱戏、开大会用。我们村的礼堂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石头打底,红砖砌墙——我的哥哥、姐姐都亲自去挑过石头挑过沙子,甚为结实,现在都还在用,不过不唱戏,不放电影,不开会了。一年到头,红白喜事用几回。
那时候,我们农村正月里都是要唱戏的。方圆唱戏的村子,牛角湾、梁木桥、大路铺、大斗都很出名。
唱戏,唱戏,唱什么戏?记得是两种。一种是调子,类似于祁阳小调,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大戏。戏班子年前都请好了,一般是外地的。我们村不用请,自己有,请了广西巩唐的一个女老师傅教的。教了整整三年,演员都是本村的。我家叔伯姐姐彩娥,人长得俊,常扮小旦;之文表哥,人长得帅,常扮小生;明达叔长得牛高马大,威风凛凛,扮花旦;友鱼四哥滑稽可爱,演小丑。这些都是剧团的“名角”。友饮大哥,之武舅舅,克文哥哥,人长得没特点,但有特长,在剧团拉二胡、打鼓。我自己的亲姐姐子娥,人长得不大好看,也有用,就是演兵勇。大将出台,当兵勇的先要出来开道,“吼”一声大喊,跑出来,两厢摆开,也很威风。
演员平时都是白天做事,晚上排练。小时没事,经常去看,哪个演员讲什么唱什么,有什么动作,谁先出场,谁后出场,都记得一清二楚、滚瓜烂熟。记得初中时一次放牛,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排演过一次《红泥关》(《说唐》中瓦岗寨王伯当谢杀新文礼,新文礼妻子为夫报仇,抓住王伯当,看到王伯当风流英俊,舍不得杀,反将王伯当招亲一段),过了一回名角瘾。
唱戏那几天,家里客就多。远的自不必说,近的也会住上几天,父亲母亲的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吃嘛,炒几碗腊肉,打一碗蛋花,煎几块豆腐,炒几个小菜,挖一碗酸菜就成。父亲喜欢做一个醋芫荽。把地里的芫荽扯回来,洗干净了,切都不用切,连蔸一起直接放进碗里,放一把剁碎的酸辣椒,拍几片生姜、蒜子,放盐,再倒白醋,筷子拌几拌,立马可吃,既开胃又送酒。酒嘛,母亲过年前就熬了二三缸。瑶家人有句俗语,叫“惯酒不惯菜”,酒杯一端,一切放宽。两杯米酒下肚,从盘古讲到扁古。住呢,家里开满铺,一铺床睡三四个人,有时父亲也要挤到我和哥哥的床上,三爷仔一起睡,暖和。
“咚咚咚……”唱戏的小鼓已经敲了很久,父亲还在喝。客人说:“马上要唱了,不喝了。”父亲说:“这是响锣,还早,再喝二杯。”于是又喝了二杯。
家人说:“马上开始了,莫喝了。”父亲说:“响锣还没敲好久,还早,再喝二杯。”于是再喝二杯。
“要开始了”,我嚷嚷道,再不去就来不赢了。父亲摸摸我的狗脑瓜,说:“哪年不唱戏呢?不急不急,再喝二杯。”喝完,把杯子一丢,看戏去。
礼堂里早就人山人海。我领着父亲和客人,父亲端着炭盆,挤过人流,找到我们的凳子——凳子我一大早就摆好了,守了一整天了。
整个礼堂就像一个大辣椒酿,被人这种馅子挤得满咚咚,连窗台和礼堂外面的平台都挤满了人,热闹极了。一个村子唱戏,周围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外的人都会来看戏,挤不进去,那就在外面的空地上捡个马郎古(石头)坐坐,逛一下也是好的,表示自己来过了,回去吹牛也是一种资本。那卖甘蔗、卖葵瓜子和炒花生的,卖灯盏粑粑和油炸粑粑的,也会推着他们的担子,到那儿去卖。瓜子、花生都是一角钱一叠,油炸粑粑五分钱一个,甘蔗二角钱一截,来一叠瓜子或花生放在衣兜里,边看戏边嗑瓜子或剥花生实在是人间最大的享受,换了当皇帝也未必愿意去。
村里的老人说,当皇帝,不就是多嗑几叠瓜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台上灯火辉煌,照着那些化了妆的演员就像画出来的一样。戏基本上就是那几出,什么《三打陶之春》、《杨六郎斩子》、《平贵回窑》、《薛刚打擂》、《五女拜寿》之类的。我们倒是巴不得天天演,场场演《红泥关》、《薛刚打擂》,看那插野鸡毛的武生舞枪弄棒,好不过瘾。偏偏又经常演那些酸溜溜的《春草闯堂》、《绣楼镇塔》、《桃花装疯》之类的,一会儿小姐挪着莲步上来了,一会儿又是老生咿咿呀呀地唱,好不烦人。有胆大的小孩,蹿到台前,点起个鞭炮就往那台上摔,“啪”一声响,吓得那小姐、老生一惊一乍,那管事的跑出来几声怒骂,那小兔崽子早已蹿得不见了踪影。endprint
台下就像一大锅烧开的粥,热极了,吵极了,闹极了。有喊小孩找板凳的,亲戚之间打招呼的,姊妹们好久不见闲聊的,此起彼伏。前面那十几排,大约还听得台上唱了些什么,后面那些,根本就别想听清一个字,只看到嘴巴动,手脚舞。实际上这根本就没关系。所谓“唱戏”,那是台上,台下就是“看戏”,看一下女旦俊不俊,小生好看不好看,花脸威风不威风,丑角可笑不可笑,丫鬟伶俐不伶俐就可以了。唱什么演什么,谁去管呢。真正想看一下的,也就是父亲这类多少读了点古书的人。每次演员出台,周围的人都会问,这个人是谁?是好的还是坏的?若是好的,父亲便说是好的。然后又说,这出戏,是讲穷书生赶考、瓦岗寨反唐之类,丫鬟、小姐是好的,小媳妇是好的,岳母娘是好的,书生是好的,宰相是好的……,岳父老子是坏的,表哥是坏的,大儿媳妇是坏的,嫌贫爱富、为富不仁、官逼民反之类。听得周围的人“哦哦哦”,看父亲的眼神便有了一些“敬”。父亲似乎很喜欢担当解说员这种角色,比别人多读的那一点书这个时候总算派上了用场。也有那儿子、儿媳对公公不孝,对婆婆不好的,便勾起这些婆婆姥姥的无限心事。各人数起各家媳妇的长短,这个叹气,说:“唉!这个事本来不该讲,讲又难听,不讲又闷在肚里,上一回,某个事,儿媳如何如何,又前几天,如何如何,唉唉唉!”直抹泪。那个说:“你快莫讲,我家的那一个,上一回,如何如何,前几天,如何如何,唉唉唉!”直叹气。到底有多少个前几天,到底有多少个前几回,多少个家长里短,竟似这些婆婆姥姥的长头发般,永远也扯不清理不完。
礼堂的后面是后生妹崽的天下。后生们三个一丛,妹崽们五个一簇,不时地小声嘀咕着,互相搭讪着,他们不是来看戏的,是来看人的。若是对上了眼,他们便会直奔田峒、山岭而去,唱嘞嘞嘿(山歌)去了。
他们的戏在田峒,在山岭,在生活。
他们演出的戏,更精彩。
耍龙
正月里,去耍龙。
那个时候,正月里,我们总是要耍龙热闹一下的。记得每个村至少都有一条龙,村子大的,有好几条。我们村有五条,五个生产队,每个队一条。那时候的“龙”,不是神仙,不住在天上,也不住在海里,他就住在我们村里,他是我们大家的亲戚。现在的龙是神仙,平时深居简出,只有官方举行重大活动或红白喜事时才出现,离我们好远。
二季稻打完以后,已經晚秋,那是一段长长的农闲。地里的红薯挖了,山上的油茶摘了,柴火也砍回来了,人闲着没事,天气却好,白天太阳暖烘烘,晚上星星亮晶晶,正好练耍龙。
“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锵锵,咚咚咚锵……”吃罢晚饭,后生们便去练耍龙去了,收割后的田峒一马平川,深秋的月光月白如霜,再点几盏松明做的灯火,很有些沙场秋点兵的味道。耍龙的都是各个村组最出挑的后生,但对龙头、龙尾的要求就更高一些。龙头要求摔得高,中间的几杆才带得动,舞得圆。高大威猛的承保哥、明达叔都是多年的老龙头。龙尾要求甩得好,既要照应好龙头、龙身,顺势翻腾跳跃,又要做出许多滑稽古怪的动作,逗观众笑。矮小机灵的邓思坤叔叔是多年的老龙尾,他的两个儿子红富、红贵也是好龙尾。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年三十的晚上,耍龙就要在村里搞汇报演出了。吃过年夜饭,大家便拿着火笼,端着炭盆,背着凳子,到礼堂看耍龙去了。礼堂的高处挂了一张大汽灯,照得像白天一样亮。礼堂的四周烧了几堆火,供人烤,中间围出一个圆形的大场子。“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几通响锣过后,那龙便摇摇晃晃地登场了。龙像我们人一样讲礼性,先要给东边的人拜个年,再给西边的人拜个年,再给南边的人拜个年,最后给北边的人拜个年,然后逐路耍起来。其实耍龙那些技巧大家都不懂,无非就是看个热闹,看龙头摔得高不高,龙身舞得圆不圆,龙尾甩得跳不跳。“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后来参加工作写那些面目可憎、味同嚼蜡的材料的时候常用这么一句话,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耍龙的最高潮叫“满堂红”,就要把整条龙舞圆,龙头带着龙身、龙尾,一步一步地边舞边挪,耍一个圈圈。好的龙头能耍二个满堂红,队形都还不乱,观众会大喊“好!好!搞得好!”还有后生吹起一阵又一阵的“马子哨”喝彩。若是一个“满堂红”都耍不完,龙头泄了,龙身瘫了,龙尾乱了,台下便会喊道:“数卵毛!数卵毛!”也会吹“吁吁吁”叫的“马子哨”,喝倒彩。
五条龙依次耍完,接着玩耍狮子。“咚咚咚锵,咚咚咚锵,……”一个手拿一把折扇的滑稽可爱的“大头脑”出来了,接着跳出一个憨态可掬、五彩斑斓的大狮子。那“大头脑”走起路来左摇右摆,走一会儿折回来逗一下那狮子。那狮子却是一下伸一下头,一下缩一下尾,一下打个滚伏在那里一动不动,要等那“大头脑”折回用扇子把它敲醒,逗它伸几下头缩几下尾滚几下以后,才又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就这么逗啊摇啊地。场子的中间早就摆了一张高桌子,两条猴子几个跟斗翻了进来。那猴儿真是泼,一会儿钻到桌子底下,一会儿跳到桌面上翻跟斗,一会儿又在那桌子边猜拳,煞是泼得可爱。那摇摇晃晃的“大头脑”引着憨态可掬的狮子也到了桌子边,只见那狮子“呼”地一下,跃上桌子,在那猴子和大头脑的保护下,在那桌子上做出侧立、翻滚等多种高难度的动作,台下观众连连叫“好”,直到四下里吹起“吁吁吁”叫的“马子哨”,那才真正叫好呢!
耍完狮子后,往往还有一个“打根”,其实就是表演几套拳头、棍术之类,并不精彩。
大年初一,龙要到家家户户去拜年,在大门口拜一下,然后到堂屋拜一下,再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主家会端出果子、瓜子,筛好茶,请后生们坐一下,喝杯茶,吃点果子,嗑点瓜子,讲几句彩话。若有那新嫁了女,新结婚的,要打个小红包,叫打“新郎公(新媳妇娘)”;新砌了房的,也要打个小红包,叫“打新屋”。红包随大随小,只为讨个吉利。
大年初二,龙就要走村串寨,到别的地方耍龙去了。一个村子有几条龙,但出去只能一条,体现一致对外的意思。那耍龙的后生,身穿青布衫,脚穿白跑鞋,个个都精神。过一个村子,若想进去,便在进村时敲锣打鼓。村里管事的便会去抢那龙头,一个要留,一个装着要走,争抢几下,便顺势跟着主人,进村去了。若不想进去,便偃旗息鼓,这个村里管事的便不去理会,任那龙悄悄走过。有时候,一天我们村会接到七八条龙。endprint
小时候最让我惊奇的是,那龙和人一样也是极讲礼性的,两条龙在路上相遇,两边都要敲锣打鼓,打上一挂鞭炮,拜上两拜,才分头而去。
龙到村里后,首先要安排吃住。那管事的,便这个组安排几个,说:“今天,有几个后生在你这吃住,要安排好。”那个组安排几个,说:“今天,有几个后生在你这吃住,要安排好。”主人没有一个不是满口答应的(有客住在自己家里是很有脸面的事)。农村人对吃住并不讲究,但炒几碗腊菜必不可少,再煎几个豆腐,炒一碗黄豆或花生来便是极好的下酒菜。若再打一大碗蛋花,便是极讲礼性、极体面的了。
龙进村后,便到各家各户去拜年。一路上敲敲打打。到了门口,左拜一下,右拜一下。进了堂屋,对着神台,左拜一下,右拜一下,然后到堂屋中间,左边转一圈,右边转一圈,就算拜完了。客气的主人会端出果子,端出糖果、瓜子,筛好茶,请这些老表们坐一下,吃点糖果,嗑点瓜子,喝杯茶暖暖身子。若有那新嫁了女,新结婚的,要打个小红包,叫打“新郎公(新媳妇娘)”;新砌了房的,也要打个小红包,叫“打新屋”。红包随大随小,只为讨个吉利。
吃罢晚饭,全村人都要到礼堂去看耍龙去了,每个晚上总有二三场,多的七八场。看耍龙,看的是哪个村的龙头摔得高,哪个村的龙尾甩得跳,哪村的后生长得好,哪个村的“满堂红”耍得出彩。如果前面那条龙耍“满堂红”耍了一圈,第二条龙就想耍一圈半,第三條龙就想耍二圈,总要把对方压倒,赢得满堂喝彩,直到四下里都响起“马子哨”才好。也有那管事的,看看那龙头摔得越来越慢,实在耍不下去了,便会走进场子,抢着龙头道:“辛苦了!辛苦了!蛮好了!”那龙头便抖擞精神,再奋力摔几下,便趁势收住。也有那不懂礼的,偏偏不去劝那龙头,那龙头耍得实在气不过,发一声喊,拉起龙头便走。两个村自此结下梁子。“大年初一”,“二月二”,“六月六”,这些重大节日唱歌或赶闹子,两个村的后生不免会打上几架。
耍完龙,耍完狮,主家还要请后生们吃夜宵,一般是煮几斤面条,放几个鸡蛋。
便有那妹崽,你推我攘地过来,说:“老表,老表,唱个山歌。”那些后生,本来喉咙就痒,却装着说,不晓得唱呢。那妹崽就说:“谁不是学呢!”
起首唱道:“劝哥唱呦/劝哥唱歌是好事/劝哥唱歌是好事呦/不是外面去赌钱。”
那些后生也不是呆鹅,马上接道:“不会唱呦/手拿木叶不会吹/吹烂木叶不会补/唱坏歌头不会赔。‘
那妹崽接着唱道:“你有歌来只管唱呦/壶瓶有酒只管筛/有情有义杯杯满呦/无情无义半杯筛。”
那后生接道:“不会唱呦/壶瓶有酒不会筛/爹娘生来哥愚蠢呦/妹唱好歌不会赔。”
一来二去,鸡叫也不管,天亮也不晓得,竟是一个通宵。
第二天,那耍龙的后生,便在那妹崽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慢慢地挥手去了。
那时候耍龙耍得真久,从大年初二一直耍到正月尾。有的要耍到广西的八步、富阳、梧州一带,回来时,不仅龙回来了,还带回个鲜活漂亮的小妹崽。
吃正月,耍二月,一晃到了三四月。年就像一部轰轰响着的火车,愈开愈远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若要问你我,去年与今年,今年与明年有什么不同?觉得似乎一样,似乎又没有什么不一样。无非就是老人又老了一岁,中年的又壮了一岁,小孩又大了一岁。
可是终究觉得还不一样了。因为这点不一样,所以,才叫“新年”,才盼过年罢。那点“新”,叫盼头。那点“新”,叫希望。那点“新”,叫变化。
多少年就这么过来了。
多少代就这么走了。
作者简介:
唐友冰,湖南省散文协会会员。
单位: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畜牧水产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