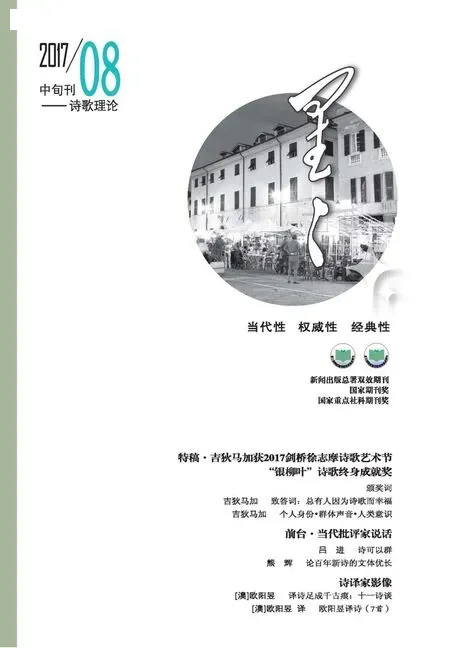论百年新诗的文体优长
熊 辉
论百年新诗的文体优长
熊 辉
舍弃沿用千年的文言书面语,采用明白晓畅的口语白话;背离传统诗歌的艺术津要,保留分行排列的自由外型,遂在汉语文学的历史中产生了一种新体,这便是我们常称的“新诗”。在诞生之初的草创期,不管新诗遭遇了多少诟病,接受了多少冷眼,甚或在寂寥中一度面临自我消亡的死路,但它在少数人刻意的“自娱自乐”中兀自生长,枝繁叶茂,遮蔽了昔日诗词歌赋的天空,成为中国文学园地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百年新诗的发生,堪称文学发展的奇迹。在知识阶层眼中,古诗文体观念和创作经验早已根深蒂固,在没有任何创作准备的情况下,胡适诸君立意用观念中的诗体取而代之。即便是在改革创新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想起新诗革命,尤有后怕,深恐它在“守旧派”的围攻中不堪一击。世事在偶然中演绎着必然,很多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因为应和了某些潜在的发展趋势,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界,硬是将不可能之事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18世纪以降,世界诗歌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苏格兰的彭斯开始收集整理民歌,英格兰的华兹华斯和柯列律治以“歌谣”的名义创作诗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诗歌变得浅俗易懂,摆脱蒲柏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诗风的束缚;美国诗人惠特曼及至后来的意象派运动,其旨趣无疑集中于解放英语诗歌的形式和语言。美国女诗人洛威尔的《意象派宣言》,被公认为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蓝本,而另一位女诗人蒂斯代尔的诗作《关不住了》,被胡适翻译成中文后视为新诗的“新纪元”,意即胡适心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白话新诗。由此不难看出,从新诗观念到新诗作品,胡适的做法带有很强的借鉴色彩。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借鉴”带来中国诗歌创作的巨大转折,新诗“横空出世”并迅速确立了文坛正宗地位。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胡适引入了什么样的新观念,更在于中国诗歌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变革和突围,又或者在于新诗的出现满足了什么样的时代诉求,几种因素的集合,促成了新诗的发生。
百年新诗的发展,最大的成功是确立了自身的文体优势。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说法,固然带有进化论的局限,却也道出了文学发展的普遍常理,要不我们就会一直生活在古人的阴影里,“自我”永远进入不了民族诗歌的谱系。正如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谈到,“后来者”诗人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修正比”,才能打败强者诗人进入历史。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是中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开拓者,他在《断无不可解之理》一书中,说中国诗歌表达的所有情感自《诗经》就已有之,历代诗人之所以还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表达,并佳作不断,主要原因便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新诗较之古诗,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语言和形式的疏离,亦即文体各异。我们常常见到很多人拿古诗平仄押韵之类的优长,来批驳新诗不押韵不整齐的“不足”,这实在有违比较的原则,好比拿马的奔跑去比牛的缓慢,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前者优于后者。殊不知,两个本就不同的物类怎么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实际上,新诗文体也有自身的优势,吕进先生在《中国现代诗学》中认为所有的抒情诗,包括新诗中的抒情诗都是“内视点”文学,我们不必拘泥于外在形式一端,而忽视了其内在的形式特征。推而论之,与古诗注重外在形式相比,新诗更注重内在节奏。郭沫若在《三叶集》中写道:“我想我们的好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表现,命泉中流出的strain,心琴上弹出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这虽有华兹华斯“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的影子,但却开辟了新诗内在节奏或内在音乐性的传统。何其芳认为,诗歌情感的跌宕起伏仍然可以造成很强的音乐性效果,大可不必像古诗那样仅凭借外在形式来造成朗朗上口的音韵效果。于是,新诗因其“内视点”的文体特征,建构起了内在韵律和节奏,比起古诗的外在音韵而言,不但不会制约诗情的表达,反而让形式与内容合为一体,或者形式成为内容的构成部分,显示出自身特殊的形式美感来。
新诗文体的另一优势,当然是语言的白话化。不少人认为,新诗采用白话文或白话口语作为表达语言,是诗歌语言的退化乃至灾难,因为其雅致和凝练的基本特征随之沦丧。应该警醒的是,此时的白话与口语之间并非等同关系,否则清末流行的白话报当被视为新文学的开端,又抑或是胡适所谓的古已有之的白话文学当被视为新文学一脉相承的前生。仅就诗歌的角度而论,按照俄国形式主义代表学者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散文或叙事文学的语言因语法的规约,造成对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诗歌语言则因语法和表达的超出机制,造成对散文语言的陌生化。据此而论,日常的白话口语与诗歌语言之间相隔三层,即便是白话口语,只要它成为了新诗的语言,那就与日常的白话口语不可等同视之。根据黑格尔《美学》中的艺术观念,吕进先生将新诗语言视为“媒介”,即诗歌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也是高度精神化的艺术,其媒介也从日常的物质中抽离出来而化为精神性的存在,故而诗歌是向散文借用文字媒介。从这个角度来讲,新诗中的白话口语也断然不是日常使用的语言。抛开俄国形式主义和黑格尔的诗歌语言观,我们还可以从语言形成和演变的角度来加以分析,进一步厘清新诗语言白话的文体优势。新诗语言在存在形态上与白话口语相似,但其来源却相当丰富,至少古代汉语、外国语言和日常口语是它的三大来源。古代汉语、日常语言和白话文血脉相连,彼此影响和滋生自不必赘述,仅就外国语言资源一端来讲,胡适、傅斯年以及鲁迅等人曾多次宣称,要用外语词汇的丰富性和外语语法的精密度来弥补汉语表达的缺陷,因此现代汉语几乎与生俱来地具有“欧化”或“外化”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表明汉语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由以上分析可知,新诗因采用了白话文而更具文体优势,新诗语言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语言张力,更具有较强的接纳性和适应性。这似乎也印证了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说,“旧皮囊”装不下新思想,于是新文学运动必然会发生,直接的后果便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更适应表达当下思想和情感。
百年新诗的繁盛,不只体现为作品数量的剧增和佳作的涌现,也体现为新诗批评的活跃。胡适在新诗发轫之初写作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后来的《谈新诗》等文章,倘若算是新诗批评的早期成果,那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等人对新诗作品的评论或关于新诗问题的看法,便汇聚成了新诗批评的主流,才得以使今天的中国现代诗学蔚为大观。诗歌评论也许并非源自批评的目的,而是根源于情感的交流。古时品茗或酌酒的兴致,无外乎文朋书友的诗词唱和;离别的忧伤或相逢的喜悦,也都消融成感人的诗句。有赠有还,那些答谢的诗词无疑成为对友人作品的最好回应;演变到今天,面对感动自己的诗歌,书写相应的心灵感悟,或者与之相关的世风民俗之杂感,就成为所谓的评论文章。随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建立,也随着各学科门类的建设完善,专门从事新诗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新诗研究俨然成为一门“学问”,成为人们专攻的术业。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似乎肩负着更为沉重的使命,论者倘若不能窥见作品隐秘的意涵,仅谈与己相关的感受,其评论会被严肃的学院派讥为“读后感”。在西方文论和批评方法肆意横行的时代,我们的确借助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空白结构”,可供言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就不再停留在心灵的沟通层面,它更多地呈现出思想和哲理的色彩,文学批评俨然成为书写时代的思想史。诗歌批评亦然,各种理性的分析充斥着诗歌评论界,只有心灵的碰撞似乎无以写作评论,它越来越成为知识性的写作方式,成为少数人可以从事的“行当”。甚至有些人仅仅是借助评论之名,暗行阐发自我心迹或思想观念之道,让诗歌评论远离了作品和读者。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评论包括诗歌评论的精英气或专业化,使其逐渐独立成新的文学文本,或者使其具备了与普通文学文本不一样的气质,那就是理性的思考和深度的思想。
伴随着新诗批评的兴起,专门的新诗研究机构逐渐建立,这真可谓百年新诗历史中的大事。现代时期的新诗批评,多为诗人谈诗,虽免除了“隔靴搔痒”的弊病,但缺少系统性的言说思路,终难见到体系化的新诗研究专著。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合著的《三叶集》,常被誉为是研究新诗的第一本专著,但其中对美学的论述不免破除该书谈新诗的专一性,况且它是三人的通信集,还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新诗研究专著。废名是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的先行者,其专著《谈新诗》仍由独立的论文构成,实际上就是一部谈新诗的论文集。1948年,朱光潜在正中书局出版的《诗论》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专著,此书虽不专事新诗研究,但却在中西诗学相互阐发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开阔视野,具有狭义诗学的普遍性意义。学者型新诗研究时代的到来,应该与新时期活跃的学术氛围有关,也正是由于大学集聚了一批专门从事新诗研究的学者,于是新诗研究机构呼之欲出。1986年6月,西南大学的吕进教授与方敬研究员、邹绛研究员一道,建立起了新诗历史上第一家独立建制的新诗实体研究机构,开创了新诗批评历史的新局面。吕进先生专门研究新诗文体,是典型的“形式论”者,其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的精要部分,就是谈新诗的语言和形式,这是一部体系化的新诗文体研究专著,此外还出版了《新诗文体学》《现代诗歌文体论》《中国现代诗体论》以及5卷本的《吕进文存》等。吕先生是那辈学人中将“新诗之所以为新诗”阐述得最清楚的学者,也就是说他充分把握了新诗的文体特征,而且他的研究系统性和思辨性很强,有深刻的西方美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作为支撑,相较于那个时代的其他新诗研究者言,具有突出的新诗研究品格。2010年9月,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成立,院长为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谢先生的新诗研究富有才情和思想的洞察力,其著作《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诗人的创造》《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等便体现了这一研究特点。此外,安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等高校纷纷建立了新诗研究机构,在高校推行学科建设的语境下,显示出新诗研究和批评的中兴。
新诗百年,无论我们接受与否,它已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并发展下来,成为我们无法送还的民族文学遗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新诗的美好前程,祝愿新诗多出名篇佳作,似乎才是我们今天纪念新诗百年的题中之意。

熊辉,1976年生,四川邻水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及翻译文学研究,兼事诗歌评论,现供职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