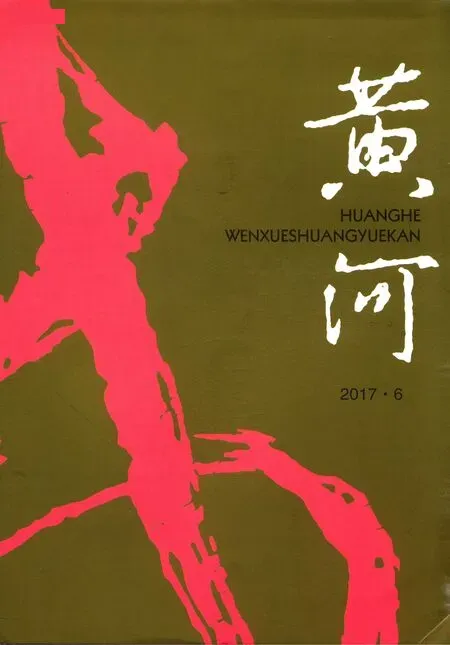黄河边墙(之五)
岳占东
黄河边墙(之五)
岳占东
K:古堡的荣耀
一
公元1518年秋冬的时节,大明皇帝朱厚照,站在唐家会堡上观看大河两岸年轻的士卒泅水渡河比赛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三百多年之后,唐家会将成为一片陌上田园。他当年摆放御座的烽火台已经荒草凄凄,残破的边墙若隐若现在庄稼地里,一群小儿沿着边墙唱唱跳跳地嬉戏,他们稚气未褪的脸上浮现出的笑容远比他当年的龙颜更加灿烂。
唐家会堡是黄河边墙之上众多营堡之一,从老牛湾到石梯隘口一百二十华里的边墙依河而筑,唐家会堡正居其中。唐家会堡便因此成为黄河之上官军往来的要津。黄河两岸调兵遣将全凭在唐家会摆渡,上可通达关河口,下可直逼河曲营。正德皇帝朱厚照之所以来到唐家会堡为的也是这个渡口,因为渡口对岸就是三秦大地,延绥重镇就在南下百十多里的地方,黄河的另岸定然风光旖旎,对于西巡的年轻皇帝来说,唐家会堡自然是他渡河首选的地方。
单从边墙营堡的角度来看,唐家会堡的的确确有其不同寻常的地方。首先是在堡与边墙连接处有一个巨大的边门。边门究竟有多大,史料未予提及,但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一处边门应该是衢通两岸的枢纽,叫铁裹门。“铁裹门”顾名思义必定是固若金汤之锁钥,其意要么实指边门为生铁包裹,能拒水火攻伐;要么寓指枢纽坚固,犹如铁桶裹挟一般不为蛮敌所破。在明代边墙之上称为“铁裹门”的地方不止这一处。可见内外通达的关塞枢纽既然都称为“铁裹门”,其固若金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不过看看皇宫大院紫禁城的大门,就能想到,皇家的宫门除了上面有规矩有序的门钉外大都是用纯粹的木料制成,边墙之上的门却为铁板包裹,可见唐家会堡之上的铁裹门讲究的是实用与坚固,而皇家宫门的气派却在钉钉卯卯之上被象征的意义虚化了。
铁裹门的外边便是史料记载的唐家会渡了。生活在民末清初的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引用更为古老的《边防考》这样记述当年的唐家会堡——堡在县西北六十里,有唐家会渡,为官军往来要津。唐家会堡在边墙之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便由这个门及其门外的渡口而决定。也正因为如此,在明宣德二年,即公元1427年,唐家会最早建堡,在正统和万历年间都有增修,如《边防考》所言:周一里有奇,当黄河渡口之冲。
唐家会堡因唐家会渡在边墙之上有了名望,在九边重镇的延绥镇(榆林镇)修筑边墙时,这里也成了他们边墙的起始位置。在今天的唐家会和铁果(裹)门村的对岸就是榆林市的墙头村。墙头即边墙之头,延绥镇的所筑边墙的最东头恰好与唐家会堡的铁裹门形成呼应。在今天沿河的庄稼地里,时隐时现的断垣残壁仍可见当年边墙的构制。边墙从东边的山梁上直冲而下,宛如一条饮水的长龙,沿河岸逶迤而去。现今的铁果门村就处于边墙的西侧,村北的最高处有残破的烽火台,当年的烽堠就设在铁裹门与营堡之间的高岗上。烽堠是边墙之上侦察敌情和传递信息的军事设施,其主要建筑是烽火台,当地百姓俗称“台墩子”,台下四周一般筑有防御的高墙。烽堠里住有堠夫,堠夫站在高高的烽火台上目极边墙内外的更远的地方,只要稍有敌情,堠夫便昼则举烟,夜则举火,用预先设定好的方式互传信息,已达到预警的目的。唐家会和铁裹门之间的烽堠与墙头村的烽堠遥相呼应,它们不仅肩负着传递两岸敌情的信息,就是两岸官军往来需要摆渡和吱吱扭扭打开沉重的“铁裹门”也需堠夫互通信息。
当年大明皇帝朱厚照沿边墙西巡,一队车骑浩浩荡荡遮天蔽日,据史料记载人数不下一万七八。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沿着边墙内的官道一路走来,其车马萧萧旌麾曼舞的情景不下一支蒙古部落的铁骑入侵的阵势。如果不是预先有探马飞书传报,边墙烽堠的台墩上一定会狼烟四起,说不定还会有暗箭鸣镝不时地从边墙的营堡上飞出。朱厚照的西巡尽管从京都出发是避开大臣偷偷出行的,但一入宣府威武大将军府,他便让自己的随行队伍一下子由几十人壮大到几万人。因为朱厚照的这次西巡不是以皇帝的名义而行,他进入宣府的威武大将军府便成了皇帝钦封的威武大将军硃寿。这是他在一年前第一次御驾亲征时给自己钦定的名分。御驾亲征的结果是他以威武大将军硃寿的名义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的队伍。所以这次西巡他很自然地绕开了皇帝的名分,在行进的路上专门发一道敕书给吏部,全文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硃寿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有了这道敕书他便是真正的威武大将军了,所以统帅着浩浩荡荡的大军沿边墙一路走来。
唐家会堡自宣德二年建堡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迎来了一位名为将军实为皇帝的大人物。当时堡里堡外大河两岸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们虽然没有详实的史料加以研读,但朱厚照来到唐家会堡必将第一次面对蜿蜒曲折的黄河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许是黄河博大宽阔的气势感染了这位年轻的皇帝,他在唐家会堡驻跸三日,突发奇想,专门组织堡内年轻的军士进行泅水横渡黄河比赛。时令已经是十月天气,两岸已经草木凋零,河水冰冷刺骨。但作为练兵的项目,威武大将军硃寿当然有权利看到自己士卒真实的作战本领。所以在十月的天气里,作为硃寿的朱厚照,和两岸的军士一起观看士卒泅水的情景。据说那一天士卒的表现感动了这位年轻的皇帝,他走下烽火台亲手将一杯酒赏赐给了堡内一名李姓的士卒。当然这是威武大将军硃寿的奖励,尽管在场的军士都知道这是一位年轻皇帝的亲手奖励,但却与皇帝朱厚照在名分上没有半点关系。
如果说到与皇帝有关系,是朱厚照如何面对眼前的这条大河的问题。按照《礼记·学记》的要求,古人认为黄河是海的本源,帝王祭祀时,必先祭黄河而后才祭海。朱厚照做皇帝十多年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黄河的真实容颜,所以尽管他是以硃寿的名义西巡,但作为皇帝他第一次亲临黄河岸边,那种内心的崇拜的感觉还是搅扰了他年轻的心,何况他还不单单是亲临黄河,他还要带领一万多军士渡河。所以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在唐家会堡必须恢复皇帝的真正名分来祭祀黄河,而那位他十分喜爱的“威武大将军硃寿”的名分却需暂且隐去。于是在十月初六的黄道吉日,再也无法嬉戏玩笑的朱厚照一本正经地面对黄河设坛祭祀。《御祭黄河文》是兵部侍郎冯清作为司仪代为宣读的,祭文为:灵钟坎德,功配坤元。土地蒙灌溉之庥,物类借润泽之利。故兹渡口,惟尔司寄。朕西巡狩,适经此地。泛泛扬州,青龙驾翼。招招舟子,元旗导御。往过来续,神功助济。备兹牲醴,阴飨,朕祭敢告。今天重读朱厚照的祭文,我们虽然能感受到皇家的凛然气派,但仿佛也能听到类似民间百姓的祈祷之音,其中隐隐折射出作为皇帝的朱厚照和作为威武大将军的硃寿两厢情愿的心声。
皇帝的朱厚照和威武大将军的硃寿在唐家会堡第一次出现了不得已的分划。作为皇帝他必须一本正经地亲祭黄河,作为威武大将军他肆意妄为不仅能统帅六师,还能让士卒在冰凉的河水里尽展本领博得他开怀一笑。当年面对这种名分上的分划,年轻的朱厚照看着营堡内的猎猎旗帜和滔滔不绝的的大河会作何感想呢?这我们不得而知,但朱厚照嬉戏人生的态度和他日后留有骂名的悲剧便在黄河边墙之上的唐家会堡开始流传。
二
唐家会古老的营堡在迎来大明皇帝朱厚照以前,已经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据史料记载,公元1501年,也就是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当皇帝第十四个年头,从黄沙漫舞的三月到骄阳炙烤的八月,蒙古鞑靼小王子、火筛联合蒙古其他部落,从宁夏镇和延绥镇的长城沿线对大明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攻伐。历时半年的战役,蒙古铁骑在长城沿线横冲直撞,大肆劫掠,唐家会营作为黄河边墙之上往来要津,自然难逃厄运。
之所以提及这段历史,是与十八年后朱厚照一路西巡有一个对照。
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眼里,正德皇帝朱厚照算不得一个圣主明君。人们这样看待朱厚照不外乎津津乐道的是他建豹房、罢经筵、宠溺宦官、四处游玩、自封官号,甚至与民间村姑调情都被编为故事而广为传播。不用说拿明朝当时的“程朱理学”正统思想来衡量朱厚照,就是用普通百姓的目光看,朱厚照这样做,绝非是一位好皇帝。人们在津津乐道一个皇帝绯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朱厚照的荒淫无度。如说他建豹房,是说他在豹房里广收奇鸟异兽和民间美女供他玩乐;停止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嬉戏无常,不愿读书上进;宠溺宦官虽然是明朝由来已久的积弊,但培养出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刘瑾,就无法让史学家们原谅了;四处游玩更不是一个皇帝该做的事情,而朱厚照却几次出入长城隘口,甚至在宣府为自己修造了镇国府,在那里不仅游山玩水还大肆强抢民女。还有一个皇帝自己将自己封为“大将军”和“镇国公”,无论如何是让史学家无法理解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如果单单从这些皇帝的绯闻中看朱厚照,我们谁都觉得这个仅仅活了三十一岁的年轻人确确实实是一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然而当我沿着黄河边墙一路走下来,又顺着黄河西岸坐车经偏关、朔州、大同、宣化几乎是一路沿着北去的边墙进京时,时经三百多年尽管道路在现代技术之下已经变得平坦而宽敞,但其间山岭高耸,沟壑纵横的景象让我不得不联想到三百年前的朱厚照行走在这荒凉的塞外沟壑里究竟能有多少玩乐的心态。尤其当我读到清人吴炽昌的笔记体小说 《客窗闲话》里所记载的朱厚照的故事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皇帝的荒诞身影,而是一个帝王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另一面。这则故事应该就是日后被不断演绎的 《游龙戏凤》的最早版本,当我读到李凤姐在居庸关下不禁坠马受伤后,凤姐与朱厚照的对话时,我的眼睛有点湿润。
视凤姐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宫禁。”请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弃天下,不忍弃爱卿,决不归矣。”凤姐一恸而绝。帝哀怜甚,命葬关山之上,宠以殊礼,用黄土封茔,一夜尽变为白,其英灵犹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奋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安忍背之。”遂还宫。
故事毕竟是故事,其中杜撰的成分一定不少,但细细一想在古代文人墨客心中,他们对帝王的期望是极其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期望帝王以社稷为重,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君子,另一方面又极其期望帝王怀有万般柔情,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当然在士大夫文人心里,一个帝王应该具有前一种标准就不乏是一位殚心竭虑心怀天下的好皇帝了。而恰恰相反的是正德皇帝朱厚照无论在古代士大夫文人眼里还是在史家的笔下都不符合这个好皇帝的标准。
一个演绎出那么多不为常人所理解的怪诞事体的皇帝,一个敢在塞外边墙之下与不可一世的蒙古小王子决一雌雄的皇帝,一个愿意自贬为将令百官啼笑皆非的皇帝,一个愿意沿着边墙历经艰险西巡的皇帝,他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态匆匆走过自己十六年的帝王生涯的呢?
走入唐家会古堡面对三百年后那座曾经被一代帝王踩踏过的烽火台,抚摸那段被荒弃的边墙,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冒出这样的疑问:明代为什么有那么多被皇帝宠爱的宦官?为什么有那么多被廷杖的官员?为什么有那么多清流及至后来的东林党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令年轻的皇帝不胜其烦的经筵日讲?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正德皇帝为什么会被民间演绎为仿佛带有某种精神偏执?
站在黄河畔的古堡上,感受穿越千年的河风,在黄河的浪涛里仍旧驶行者古老的渡船,如果时间能倒退到三百多年前,说不定那船上乘坐的会是那位西巡的皇帝。我向朱厚照高声喊道:皇帝陛下,你慢点走,你能否将你此行的目的告诉我这位三百多年后你的心灵的追寻者?朱厚照突然回过头来,一脸茫然的看着渐行渐远的河岸,他年轻而睿智的目光里满含不屑。在他不屑的目光中,我突然感觉到他的孤独和无奈,感受到这位二十多岁年轻皇帝的不易。
明代的皇帝应该是历史上最为孤独的皇帝,尤其像朱厚照这样幼年入继大统的少年天子,他们孤独更是与生俱来的。皇帝的孤独大都出于为权力所绑架,但明代皇帝的孤独却不仅仅是因为权力,因为他们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在“胡惟庸之案”中早已将皇帝手中的权力巩固得异常强大。他们的孤独恰恰是来源于不知道手中的权力该如何分配。宰相已经被朱元璋废除了,皇帝直接面对六部衙门的文武官员,除了身边有几位辅佐自己的阁老外,再没有自己可以依赖的大臣,何况那些满腹经纶的阁老往往又和六部的官员站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体。对一位久居深宫的皇帝来说,身边的亲信除了宫娥就是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所以孤独的皇帝只能依靠宦官来牵制六部官员和成日在自己耳边唠叨不休的阁老。一旦君臣意见不合,恼羞成怒的皇帝就让宦官将那些大臣拉倒了打屁股。大臣当然也不甘示弱,他们最有效制约皇帝的办法就是对皇帝实行精神控制。于是经筵讲学研读《四书》《五经》,用圣人的思想和祖宗定下的规矩控制皇帝成了六部文官和内阁大学士最堂而皇之的章法。从十五岁继承帝位开始,朱厚照就生活在这种被控制之中。年轻的朱厚照天性使然,他将少年的游戏精神转变成了对抗廷臣的行动,他想尽办法逃避经筵日讲,又想尽办法绕开皇帝的名分而行诸于皇城内外,让那些满腹经纶的阁老们无法从圣人的思想里找到约束他的依据而哭笑不得。当了十六年皇帝,朱厚照和那些大臣玩了十六年,他崇尚武功,希望自己成为像老祖宗朱元璋和朱棣式的帝王,所以他建豹房,与狮虎走兽搏击,在宣府建大将军府钦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磨刀霍霍准备与不可一世的蒙古小王子决一雌雄。在他二十七岁那一年,一场他亲自督战的应州大捷大败小王子让他从精神上获得了一个帝王所具有的征服的欲望,于是从那一年开始,他几次出入长城内外一睹大好河山,又不拘于太后葬礼,带着一万七千名士卒以威武大将军硃寿的名义浩浩荡荡沿长城巡边而来……
站在唐家会古堡的烽火台上,冥冥之中我仿佛是在与三百多年前的朱厚照作一场对话。如果河面上的船只里果真坐着正德皇帝朱厚照,那么我对他内心的诠释一定会让他哈哈大笑。
难道不应该笑出来吗?十八年前唐家会的那一场劫难,是蒙古部落突破长城沿线最旷日持久的一次战争。自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被蒙古部落瓦剌俘虏以来,明代的皇帝个个都若惊弓之鸟般深藏在紫禁城内,没有一个再敢于赤膀上阵御驾亲征。从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到1517年“应州之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只有这位为史学家所诟病,为野史所杜撰嘲讽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再次直面入侵。而十八年前的那场战争,让边墙内外几乎成了蒙古部落横冲直撞的无人之境,年轻的朱厚照能假借威武大将军硃寿的名义御驾亲征,又从容地沿着黄河边墙和内长城巡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让我们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个年轻皇帝的超凡智慧和诡异。
三
其实在边墙的另一边,这种智慧像唐家会烽火台上的荒草一般同样蓬蓬勃勃地生长着。
三百多年的前的边墙和边墙上的古堡早已都化为宁静的田园和村庄。走入唐家会这爿斜挂在黄河九曲十八弯岸畔上的村庄,秋日的阳光犹如一汪静水浸润着眼前的屋舍和田园,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在这个曾是古堡的村庄里很难发现在屋舍外的田园里至今矗立的那道高墙,墙的外面仍旧是田园,只是河对岸赭红色的山峁上星星点点突兀着的烽火台让人能联想到这里曾经是战马嘶鸣的边关要塞。
和我曾在一起工作过的张存亮老先生告诉我,顺着边墙下去沿河有大墩和二墩,在大墩和二墩之间就有好几个隘口,隘口都是以唐家会当年的驻守士卒的姓氏命名,唐家会有李张两大姓氏,隘口就分别叫张家口和李家口。张存亮老先生所说的“墩”就是指烽火台。张老先生是世居唐家会村,应该就是当年戍边士卒的后代,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唱民歌二人台,是黄河岸畔研究民歌和二人台的专家,所以他对唐家会来由的介绍远不如介绍民歌二人台的来由详细。但老人讲到边墙,却为我讲了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日军来唐家会村扫荡,走到村口遇到了村里拾粪的张老汉。汉奸问张老汉是哪里人,张老汉回答是张家口的。日军一听张老汉是张家口的,就说张老汉从几百里外的张家口跑到这里来,一定是八路军的探子。没等老汉分辩,一道白光闪过,日军的东洋大刀就将张老汉的头颅砍了下来。张存亮老先生说日本鬼子是误将唐家会边墙上的张家口当成几百里外当年察哈尔省的首府张家口了。
张老先生讲这则故事时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淡淡的微笑,但讲到日军对长城隘口名字的误解时,却眉头一皱顺口骂出了“日本鬼子”的话。那一刻我从他的神情变化之间感受到了老一代人身上所具有的民族精神。这让我不由地想到了边墙的长度和宽度。边墙之所以被称为长城,可见其长度不仅在外形上跨越了中国大陆东西,而且更主要的是它已经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穿越而过。而其宽度就更像是一片树叶上的叶脉,不只在外形上纵横交织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而且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早已经血脉相连水乳交融了。
三百多年前,墙这边的朱厚照想尽办法绕开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对付控制自己的庞大的官僚集团,而墙那边的蒙古部落何尝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呢?三百多年以后墙已经没了,边墙两边的人们也不分彼此,一种旷日持久的民族对峙历经岁月的洗礼变成了一种文明的相互交融和团结,边墙自然也成了中华民族一条无形的精神纽带。
在感受朱厚照西巡边墙富有智慧而不乏诡异的同时,我同样感受到的是边墙那边一个女人的智慧和胆识。这个女人就是同样像朱厚照一样敢于向传统势力挑战的满都海夫人,就是日后扶持蒙古小王子纵横驰骋至今都被后辈儿孙念念不忘的那个女人。
2009年7月份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召开的“中国西口文化论坛”上,一位蒙古族历史学家第一次为我讲了这个女人的故事:大约在15世纪末,一位聪明、美丽、善良的蒙古族姑娘茁壮成长在蒙古草原上,就在她与英俊潇洒的科尔沁王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她却被当时蒙古草原上势力最大的满都古勒可汗看准,年迈多病的可汗令她进宫做可汗夫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她满怀对恋人情深厚意的遗憾,别无选择地走进了可汗的后宫。入宫后,她并没有颓废和堕落,而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辅助可汗平息了一百多年来蒙古部落的内部战乱。可汗病逝后,再次面对各部落首领争夺大汗宝座的危机,她当机立断宣布下嫁比自己小26岁年仅七岁的小王子,在人生的变故中她再次牺牲了与心上人相聚的机会,牺牲了自己一生的爱情,维护了蒙古部落间的和平与统一。
这位姑娘就是满都海夫人。
据蒙文史书《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有关史料记载。满都海夫人原名满都海斯琴,她生于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是蒙古汪古部人。她下嫁的小王子是成吉思汗的世孙,原名巴图蒙克。巴图蒙克出生不久,父亲孛罗忽济农就在蒙古部落内部征伐中战死了,生母锡吉尔又被别的部落首领夺去。沦为孤儿的巴图蒙克几经辗转最后被祖母辈分的满都海夫人抚养。1479年,满都鲁汗去世,其他部落首领趁机向满都海斯琴求婚,都想通过联姻成为蒙古部落的盟主,这里面就有当年与她相恋多年并准备成婚的科尔沁王。但面对这些势力强大的部落首领的求婚满都海夫人选择了避而不见。
那天夜里,轩帐外战马嘶鸣,向满都海夫人求婚的王爷贵胄陆续在她的轩帐外搭建了行辕的毡房。孤冷的月色弥漫了整个草原,地平线上的清辉像薄薄的雪霜划出了一抹弧线,几只草原狼蹲守在这清辉里,发出孤独的嚎叫。满都海夫人手里捧着侍从刚刚端来的奶茶,她的目光落在了毡子上熟睡的巴图蒙克身上。那一副稚嫩的脸上,尽管遗传着成吉思汗家族宽展的面目,但在熠熠闪烁的灯光里,脸上细小的绒毛分明还散发着婴儿般的乳臭。那一年满都海夫人刚刚三十三岁,艳丽的蒙古袍下她年轻而丰满的身体像草原上撒欢的小母马一样躁动不安。作为蒙古大汗的遗孀,她目前手中握着两项让所有蒙古男人垂涎的权力,一项是她可以按照蒙古民族多年的习俗将自己年轻而丰满的身体随便送给自己钟情的男人,另一项权力是她不仅可以将自己身体送给钟情的男人还可以将已经病逝的大汗的汗位一并传给那个男人。在众多求婚的王爷中,她首先想到的是科尔沁王乌嫩博罗特,那个曾经和她相恋相爱到了谈婚论嫁的男人。想到乌嫩博罗特,她的脸上禁不住飞起一抹绯红,在入宫之前也只有这个愣头愣脑的家伙撩拨得她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子一样惴惴不安,要不是大汗令她进宫伴驾,现在和她生儿育女的应该就是这个家伙。可看一看熟睡的巴图蒙克,眼前这位称她为“伊吉”(奶奶)的小男孩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唯一的血脉,他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这个叫他伊吉的小男孩,一直在她身边长大,她对他倾注的爱远比那位科尔沁王乌嫩博罗特多得多。对乌嫩博罗特她最多的是男女间的仰慕,是一种说不清的欲望,而对眼前的这个小男人他除了倾注了母亲一样的爱抚外,他更多地倾注的是一种期望。现在恰恰令她左右为难的是她成熟的身体像一锅即将沸腾的奶茶,很渴望像乌嫩博罗特这样成熟的男人再多给她一点热度。如果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会引起任何一个对他垂涎已久的部落首领的反叛,而且她对眼前这位成吉思汗唯一的血脉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将付之东流。
在昏暗的灯光里,望着巴图蒙克熟睡的样子,一种女人特有的母性的柔情和内心的躁动让她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子亲了亲他稚嫩的面庞。按照蒙古部落多年形成的习俗,如果巴图蒙克到了纵横驰骋的年龄,说不定他会像继承一匹小母马一样将她据为己有,可他现在却是一个柔弱的孩子。想到这些满都海夫人禁不住用纤细的手轻轻地爱抚着巴图蒙克熟睡的面颊,嘴里嘟囔着还不快快长大嗔怨的话来。
后来无数的史学家在面对满都海夫人和巴图蒙克有悖伦常的婚姻时,都从各种政治意义和民族习俗方面给予三十三岁的满都海夫人一个高贵的诠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那一夜的抉择,也许满都海夫人一直徘徊在欲望与理智的边缘上,但他最终以理智战胜欲望,选择下嫁她所爱怜的巴图蒙克,让她从此成为一位在蒙古草原上不平凡的女人。
三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叶,好像注定了要产生像朱厚照、满都海斯琴这样离经叛道的人物。虽然历史学家对朱厚照和满都海斯琴的评判迥然不同,但在以长城为界的民族的交融史上,朱厚照和满都海斯琴的行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让我们不得不驻足观看这段被岁月尘封了的历史。唐家会堡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迎来了大明皇帝朱厚照,也迎来了被满都海斯琴一手培植起来的蒙古小王子,虽然对于当时边塞上的百姓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军事对峙和入侵原本就是文明交流的一种极端方式,黄河边墙和边墙之上的唐家会堡在三百多年前原本是为了阻隔,但越是阻隔的东西,文明的交流的方式就越是凶猛。在边墙废弃的日子里,那一条亘古千年的边墙最后化作了一条无形的精神纽带顺着黄河文明一路漂行。
L:消失的山寨
一
夕阳淹没在黄河下游的尽头时,王玺才走下山岗。
这应该是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以后的某一个初夏,黄河边墙已经修到了唐家会营堡。唐家会往南是一处被当地人称为“羊肝石”的砂岩石壁,当筑墙的士卒们将边墙上的最后一块夯板死死地顶到石壁上时,从焦尾城到船湾的这块河滩冲积扇已经被蜿蜒曲折的边墙包裹得严严实实。“羊肝石”砂岩石壁下就是称为“船湾”的地方,因这里河岸曲折,又且河缓水深,所以一直以来是作为唐家会官渡的一个渡口。在这处“羊肝石”石壁之上是否也应该修筑边墙,便成了总兵王玺必须实地考察清楚的事情。从老牛湾沿河修筑边墙一路走来,除了在石城口一段的峡谷上没有修筑边墙外,王玺率领的筑墙大军已经将黄河东岸的边墙修筑得犹如铁桶般坚固,这处“羊肝石”石壁从外观上看显然没有石城口的石壁高深陡峭,而且石质沙化,石壁大多数地方已经被雨水冲刷出了沟沟坎坎,这样的岩壁能否挡住冬季踏冰渡河的蒙古铁骑,不得不让他多了几分忧虑。
从早晨开始王玺便带领随从骑马上山。他们翻过“羊肝石”山岗的沟沟岔岔,进入一条东西走向的深沟。沟门与黄河相连,顺着沟底往东走,走到沟掌深处,横在前面的却是高高的山梁。这条深沟显然是一条东西不通的死谷,随行的士卒告诉他,当地人称这条沟叫“斩贼沟”,历史上东渡黄河的军队误入此沟,往往被对手包围在这条沟里杀个片甲不留,因此而得名。王玺默默地听着士卒的介绍,知道在黄河两岸的关口要隘上往往隐藏着这种暗藏杀机的地形,如果不是实地考察,他是无论如何想不到在这处不起眼的“羊肝石”的沟沟坎坎里会藏着这么一处可用来打伏击的深沟。他们翻过山梁,前面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大沟南通黄河,北达楼子营堡北部的高峁墩和吴峪口,是黄河东岸南北通衢的要道,因沟门由五花城营堡邬姓人家驻守,故名邬家沟。在邬家沟西边的山梁上耸立着高高的烽台。士卒告诉他,那座山梁就是杨家寨。
杨家寨?在太原左卫率兵打仗时,王玺就从各个卫所汇集而来的军事资料中看到过杨家寨的名号。这处山寨在洪武年间曾由镇西卫的官军镇守,后来随着洪武、永乐几次大规模的北征,北部边疆基本固定在河套以北的地区,所以这里的守卫逐渐被缩减和裁革,最后仅留下预警的烽台被保留了下来。
当王玺带领随从爬上杨家寨的山岗,远远地俯瞰西去的黄河和河岸上的群山,他便一下子明白了从船湾到杨家寨这段山势的地形地貌。这处山岗正好处在黄河的又一个拐弯处,是黄河东岸唐家会冲积扇与南部五花城冲积扇的连接处,整个山势看似被雨水冲刷得沟沟坎坎,可杨家寨所在山岗地势最高,而且处在斩贼沟与邬家沟的交汇处,在此扎寨屯兵不仅能突袭渡河误入斩贼沟的敌军,还能扼守邬家沟南北通衢的要道。在黄河岸畔的险峻隘口处,自古以来都修筑有大量军寨,这些军寨大都修筑在由河岸通往内地的两山之间,如五代时北汉朝修筑的雄勇寨、偏头寨,宋代时修筑的董家寨、横谷寨、桔槔寨、护水寨、下镇寨、许父寨、太元捕寨、虸蚄寨等军寨,都是由黄河东岸直达中原的交通咽喉,易守难攻。这些军寨平时是通衢两岸的通道,战时则成了两军对峙的壁垒。把守险要地势,修筑要塞关寨,不仅可以消耗敌人,甚至能达到以少胜多的目的。《墨子》云:敌以十万之众攻城,若调度得当,四千人足以防御。可见军寨对于保护中原功不可没。
想着这些,王玺便让士卒和他一起登上杨家寨破败的城垣。这处修建于北宋以前更为久远的山寨,历经风吹雨刷,虽经修修补补,但仍旧不失为扼守黄河东岸的雄关。城垣东西南三面临渊,周广近800步,分设南北二门,南门临近斩贼沟,北门通达邬家沟。站在西城墙上,河岸上的群山和远去的黄河尽收眼底。北部岱嶽殿庙前的烽台,南面五花城营堡后面的山岗上的烽台都遥相呼应,如若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不用点火为号,就是扯起嗓子长长喊上几声,也能让两处烽台上戍守的士卒听到响动。也许正因为如此,当镇西卫戍守的兵将被裁革以后,这里的预警也主要集中在两处不远处的烽台上。应该说,从镇西卫的将领走下杨家寨山岗的那一刻起,这处曾经在北宋年间和火山军统领的沿河六寨(雄勇寨、偏头寨、董家寨、横谷寨、桔槔寨、护水寨)一起发挥功效的军寨,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玺走下城垣,远远地看着东面的山梁上被开垦出来的梯田,那里正是桃红柳绿一派田园春光,与这里荒山秃岭野草萋萋的废弃军寨迥然不同。作为统领山西防务的最高指挥将领,他知道这些曾经旌旗凛冽的军寨和那些桃红柳绿的村庄是历代王朝同样不可或缺的立国之本,曾经由军寨拱卫的王朝虽然渐行渐远,但更为强大的营堡和边墙便顺应而生,成了大明帝国守家卫国重要形式,而那些田园里的农桑却一贯地在为整个帝国蓬蓬勃勃地生长。
这应该是每一个中原王朝永远无法走出的宿命。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大地上,几千年来,田园里种植的最早最多的应该是一种称为“稷”的谷物。所谓“江山社稷”,“江山”需要他们这些手握长矛的军士一寸一寸地攻占,而“社稷”却需要历代君王和他们的百姓在日月轮回中一点一滴进行打理。“社”是祭祀活动,是皇帝祭天法祖的大事,“稷”是五谷之神,农作物能否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同样是决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社稷大事”于是便成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国家大事。这种适宜于黄河流域干旱和半干旱丘陵地区生长的“稷”,当地人叫它“糜子”,再往北的地区称其为“稷子米”。“稷”的普遍种植,让黄河流域的百姓从颠沛流离的生存状态中逐渐稳定下来,而且人口也得以增加,过去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靠采集和放牧仅能养活六人,由于“稷”等农作物的种植,一下子能养活六十人。十倍增长的财富和十倍增长的人口,让中原大地成了无数英雄折戟逐鹿的所在。农耕民族的枭雄们打着“均田制”的幌子,纵横于黄河两岸,游牧民族的汗王们干脆不打什么幌子,闷声不响地纵马扬鞭杀将过来,于是在这条大河两岸,屯兵的山寨便成了几千年来经久不绝的军事堡垒。
在任山西镇总兵前,好多部下都建议王玺重新修筑历代遗留下来的山寨,用山寨的有利地势扼守南下侵扰的蒙古铁骑,而他实地考察时发现,黄河岸畔有大量沃土良田,而且已经形成大小不一的村庄,将军队屯于良田后面的山寨之上,无异于亡羊补牢。蒙古铁骑渡河侵扰,掠杀人畜抢劫粮食,首先遭殃的是沿河百姓,于是他率先在黄河岸边修筑沿河七堡,以此拱卫黄河滩涂上的良田和村庄。因为他知道,退守于漠北的元廷还没有反攻中原夺取江山的实力,他们的入侵仅仅是游走式的抢劫,而非军事意义上的占领。一座依山而建的军寨能挡住长驱直入的军队,却无法形成保护沿河村庄和百姓的壁垒。
站在杨家寨的山岗上,王玺有种抚今追昔的感觉。远远地看着黄河岸边自己率军修筑的长长的边墙,他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在天地苍宇之间,有多少英雄面对这条大河创下万世不朽的丰功伟绩,又有多少英雄将自己毕生的梦想埋葬在了这条大河的两岸。杨家寨以杨家军而命名,究竟是杨家的热血男儿成就了一座山寨,还是一座山寨成就了杨家的丰功伟绩?岁月沧桑之下,当年那些杨家的热血男儿早已成为了一段段若有若无的民间传说,而这座山寨却昭昭然于天地之间,像一个不散的忠魂,让他这位后来者在抚今追昔之际,慢慢地舒展自己的灵魂。
二
要说黄河岸畔的军寨林立,还数战乱纷争的残唐五代。
就在王玺走下杨家寨的山岗,看着夕阳将最后一缕余晖洒在这座行将消失的山寨之上时,他仿佛仍旧能感觉到这座山寨曾经有过的威武,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他能够想象到当年黄河岸畔山寨林立旌旗摇动的壮观景象。
朱温灭唐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黄河两岸的沟沟坎坎里仿佛一夜之间成了藏龙卧虎的地方,“火山王”杨信这位传说中杨家寨最早的开山鼻祖,便是发迹于黄河下游不远处的火山。
有关杨信的事迹,虽然在五代以来的正史中记载较少,但杨信的儿子杨业却在 《宋史》中有专门的传记加以记述。据《宋史》记载:杨业为并州太原人,父亲杨信,为后汉麟州刺史。杨业少时倜傥任侠,善于骑射,喜好打猎,猎获总数倍于别人。他心怀大志,忠烈武勇,足智多谋,尝谓其徒曰:“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建立北汉后,杨业在弱冠之年就被刘崇召为保卫指挥使,跟随刘崇南征北战,以骁勇善战远近闻名,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被国人称其为“无敌”。宋太宗北征,素闻杨业之名。北汉降宋后,太宗派使者召见杨业,即授其右领军卫大将军。班师回朝后,又授郑州刺史。太宗以杨业“老于边事”,拜其为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
杨业“老于边事”与父亲杨信在火山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不无关系。据史料记载,杨信本名杨宏信,因避讳宋太祖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名讳,宋人将其姓名改作杨信。杨信原本是火山一带的土豪,五代时,天下纷争,黄河沿岸再次成为北部边疆各种势力较量的战场。中原各路诸侯、北部的契丹、西部的党项都伺机而动,时常渡河入寇。为保为家园,杨信揭竿而起,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构筑山寨,自立为“火山王”,至此拉开了杨家在北部边疆一路拼拼杀杀的帷幕。
黄河岸畔的山寨也在各种势力的拼杀下,有如河边的红柳一拨一拨冒了出来。最早是北汉刘崇在杨家寨南边的得马水建立雄勇寨,刘钧在韩光岭建立偏头寨,在火山南建立桔槔寨,后来随着辽、金、宋各国军队不断征讨,董家寨、横谷寨、护水寨、许父寨、柏沟营等军寨都在战争中相继筑成。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随着北方战事平息,沿河六寨均已废弃,火山军只领下镇一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五代纷争的时间里,杨信在火山与契丹、党项和中原的各路军马相互征伐,让杨家军一步一步得到锤炼,直到练就了一代名将杨业。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契丹后梁和后唐大战之际,进掠河北地,杨信在火山与吐谷浑部作战。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契丹攻掠山西,党项等族攻掠云中、朔方,杨信据火山抵御党项。
……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李从珂称帝,石敬瑭据太原叛李从珂,契丹趁李、石混战,入掠云中,杨信在火山抵抗契丹。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杨信率部与契丹战于晋西北。
……后晋天福二年 (937年),党项、突厥、吐浑谷诸族大酋长拓跋彦超进据麟州,杨信与折从远结盟,共御拓跋彦超,夺取麟州自为州主。
……后晋开运元年(944年),杨信与折从远乘势北攻契丹,夺取丰州,后晋委任杨信为麟州刺史。
……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杨信与折从远、折德扆父子北战契丹,破胜州、朔州。
……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联合麟州杨信、府州折从远、夏州李彜殷诛杀契丹,建立后汉,杨信继为后汉麟州刺史。
……后周、北汉(元)年(951 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刘崇太原称帝,是为北汉,杨信携之杨业向北汉称臣,20岁的杨业被刘崇任为保卫指挥使。
……北汉天会四年(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是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军围攻太原,杨业御宋军于太原。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汉皇帝刘继元降宋,杨业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刘继元派人持信劝降,杨业面北长跪大哭,后解甲降宋。
在杨业归顺宋朝后的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廷在杨信自立为“火山王”的火山设立火山军,统领沿河军寨。
可以想象到,杨家将从战乱纷争的五代到四面受敌的宋代,他们是经历了何等的炼狱般的苦痛,又是经历了何等的化蝶般的升华,最后才炼成了一支忠君报国的队伍。当王玺走下山岗时,他仿佛仍旧能听到岁月长河里那种两军阵前厮杀的声音在耳畔萦绕不绝。作为戍边多年的将领,王玺能深深体会到“忠君报国”这四个字的分量,也能深刻理解为什么杨家寨这座废弃的山寨历经几百年仍旧坚挺地存在于当地百姓的记忆里。
黄河两岸的百姓和中原的王朝一样受馈于这条大河的滋润,也一样受祸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原大地的大好江山,不只为中原大地的英雄豪杰所垂涎,更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汗王们所觊觎。而且无论何人入主中原,最后都为这条大河所柔化,都继承了黄河农业文明所带来的福祇。而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最大的区别在于定居和游牧。《辽史·营卫志》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稼穑以食,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正因为地利所限,中原大地的君王身居九重深宫,无不推崇像杨家将一样死心踏地守护自己家园的忠臣良将。一座杨家寨的存在,不只表明了一个个中原王朝曾经有过的态度,也承载了黄河两岸百姓的代代企盼。因为中原王朝即使为游牧民族的汗王们所建立,在黄河以北的草原上仍会重新产生新的游牧部落,仍会有新的铁骑纵马扬鞭杀将过来。
这的确是中原王朝无法走出的宿命。王玺返回营地时,筑墙的士卒趁着黄昏时的凉意,仍旧在边墙上不辞辛苦地劳作,他们抑扬顿挫的号子声远比战马嘶鸣的打杀声让人温馨百倍。在边疆戍边多年,他深深地知道,大明帝国的边疆同样需要像杨家将一样忠君报国的戍边将士。杨家寨所在的山岗和三关上所遗留下来的李陵碑、陈家谷、金沙滩等地方,都承载了杨家将一代名将忠君报国的忠义。与杨业同保大宋江山的苏辙在出使契丹时,路经古北口的杨无敌庙时,不禁感慨万千,他在《过杨无敌庙》诗中曰: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由此可见杨业忠君报国的情怀,即使在北宋和契丹两国交兵的时期,仍不止为中原王朝所推崇,而且为北方游牧民族所钦佩。
在大明帝国再次与蒙古铁骑对峙的时候,当这种历久弥新戍边的责任再次降临在他们这些边关将领的身上时,王玺隐隐觉得,曾经山寨林立的黄河岸畔再次成为他们修筑边墙的关隘,这仿佛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宿命,而这座承载了一代忠魂的山寨,也是在亘古千年的道路上专门等待他们的再次到来。看着边墙上卖力劳作的士卒,王玺便有一种无比欣慰的感觉。那一刻他突然想到,这些戍守修墙的士卒也许就是大明帝国的忠魂,他们每修筑一寸边墙,就是将自己的一分忠义倾注到了边关之上,而眼前的这座山寨总像一盏不灭的明灯用微弱的光亮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内心。
在士卒们打夯的号子声中,王玺信步登上了已经筑好的边墙,他想察看一下这座行将消失的山寨是否能成为一段固守边疆的壁垒。
三
站在唐家会筑就的边墙上面,仰视杨家寨所在的群山,王玺有一种斗转星移的岁月沧桑感。眼前的边墙和那处曾经旌旗猎猎的山寨仿佛就像黄河里飞溅起的浪花,转瞬之间都化作了一道道随波而去的涟漪,而唯独经久不息的是浩浩荡荡的一河流水。
在他率领筑墙大军一锤一锤将黄土堆砌的边墙与杨家寨所在的山岗衔接时,其实无论是这座宋朝时的山寨,还是他即将修筑成功的边墙,它们只不过是历史长河里一个小小的沟坎,是弥补大自然缺憾的一道矮矮的土梁,在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这座山寨和这道边墙也许能暂时挡住一队铁骑的攻伐,却永远无法填平南北两地之间的差异。
据《魏书·高闾传》记载:北魏时期,拓跋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柔然的侵扰,中书监高闾上书皇帝,分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及其中原政权应该采纳的防御之策。他在策论里秉笔直书道: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者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扰而已。历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之故也。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守其国,长城之谓欤!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动,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侧。因地却敌,多有弓弩。狄来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
中国南北之间自古以来的矛盾,在高闾的分析中可谓一针见血。北魏的拓跋氏原来也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一旦入主中原,便视游牧民族为禽兽,这种由生存条件的改善而产生的文化歧视,贯穿了整个民族交融的历史阶段。如果从生存的环境客观地分析,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无异于是一群游走在大漠草原之上的“草原狼”,特定的生存方式让他们养成了特定的文化习惯,因而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中,所谓争斗、抢劫、攻掠可以说是最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和产生于农耕文明的汉族,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扎根于农耕文明的孔孟之道,更多地是注重谦和忍让、循规蹈矩、以礼而行,就像耕作于田垄之间的耕牛一样,四平八稳地守候着自己的田园。在戎马倥偬的半生中,王玺走遍了大半个帝国,每到一处他都少不了了解当地的民俗民风。他惊奇地发现,生活在中原腹地的百姓,即使是十字路口的房屋,都要将延伸到外面的棱角除了去,以便路人行走,完全表现出一种谦和忍让的态度。而北方边疆上的居民,别说十字路口,就是院门口的一块空地,也要拿篱笆围起来,唯恐被别人占了去。这种文化的差异,最能让他想到,北人防守的意识要比中原地区生活的人强上百倍。想着这些,王玺觉得自己这样兴师动众修筑边墙,无异于也是在黄河岸畔扎一道长长的篱笆。宋代的杨家寨能扼守住南侵的铁骑,他这道边墙却是要拒敌于黄河右岸,如果说山寨守卫的是一个南北的分界点,那么边墙围住的却是大明帝国的半壁江山。
在薄暮时分,王玺看着黄河岸上黛青色的群山和不远处烽台上的点点灯光,那一抹呈现在夜空中的轮廓分外逼真地矗立于天地之间,仿佛更像一座铜墙铁壁的屏障。那一刻王玺突然想到,当初山西巡抚李侃在向朝廷陈述山西边务时,认为黄河以北的橐莲台和沿河七堡都是山西要冲,如果山西无外寇为患,那么整个京城西部便无忧矣。因此他极力举荐都指挥田春和王玺统领沿河防务,认为他俩熟悉边事,应该专门带兵拒敌,且不可因为屯田而耽误了御敌的大事。同时,他认为修筑边墙和营堡耗时费力,必须调集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汾州等五州的军民才能完成。朝廷采纳了李侃的条陈,升任田春为橐莲台提督,王玺为山西都指挥佥事,统领黄河沿岸七座营堡。修筑黄河边墙和营堡原本是李侃巡抚山西时,他们这些边将向朝廷提出的条陈,朝廷虽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但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李侃在陈述边务时,再一次提出以调集五州军民的人力来修筑边墙,一下子将这个千斤重担直接压在他的肩上。
可以说,在边关为将半生,当他真正统领起如此众多的人马修筑边墙时,他才真切地感受到,在这种荒野里修筑如此浩大的工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在对待北部边疆防御的问题上,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修筑这种浩大的军事建筑,既使在宋、辽、金、元南北对峙,疆域飘忽不定的时期,像杨家寨这样的军寨照样矗立在黄河岸畔的山岗之上。大明帝国自建国以来,也从来没有停止修筑边墙、营堡、烽堠的步伐,而且对疏于边事造成外寇入侵的边将也严惩不贷。不久前守备大同左卫城都指挥同知范斌,就因为虏寇入侵,防御无备,而被朝廷降职,待罪守边。朝廷在众多边将中拨冗擢升他统领黄河七堡,继而委以总兵官之职,这与当年宋太宗重用杨业如出一辙。
想着这些,王玺便让随从叫来唐家会营堡的操守,让他禀报驻军情况。
操守说,唐家会营驻守旗军338名,有骡马26匹。设防14处,常驻兵33名,其中边墙之上的河湾口驻兵5名,张家口驻兵3名,李家口驻兵3名,沙渠口驻兵2名,暗门口驻兵2名,阴崖寨驻兵2名,马头墩驻兵2名,下窊墩驻兵2名,歇虎墩驻兵2名,平泉墩驻兵2名,双城墩驻兵2名,观音梁驻兵2名,杨家梁驻兵2名,杨家寨驻兵2名。其余兵卒轮流换岗,根据敌情集结设防。
王玺听说操守已经在杨家寨安排了驻兵,便没说什么。在他看来,杨家寨踞险而守,两名兵卒驻守,也就是望风放哨罢了。当蒙古铁骑踏冰渡河,营堡内自然有大批人马迎敌。
那一夜,听着黄河里经久不息的浪涛声,王玺在边墙之上坐了很久。筑墙的士卒都各自回营休息去了,只有随行的侍从陪着他静静地呆在边墙上。在月明星稀的夜空里,王玺突然觉得,眼前的杨家寨仿佛就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他也许早已看惯了那种铁马冰河的场景,也看惯了这种关塞林立的景致,他这位边墙上的将军也许就是老人似曾相识的故人,在亘古千年沧桑岁月里,也只有他们这些戎装待发的戍边人,能静静地蹲在他的脚下,细细地听他诉说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燕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