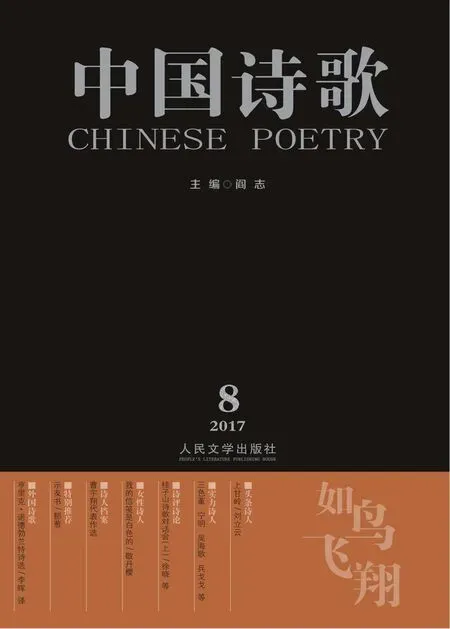上甘岭
□刘立云
上甘岭
□刘立云
如果我们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将是在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与错误的对手打
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布莱德利
1 战争档案
时 间:1952年10月14日—11月25日历时43天
地 点:朝鲜中部金化五圣山南麓上甘岭
参 战 方:联合国军(前期美7师,后期韩2师) 中国人民志愿军(前期秦基伟15军,后期秦基伟15军、李德生12军)
死 伤:(中方统计)联合国军2.5万人 志愿军1.15万人
指 挥 官:联合国军:克拉克、范弗里特、史密斯、丁一权
中国人民志愿军:王近山、秦基伟、崔建功、李德生战役英文名:Battle of Triangle Hill
战役意义:①中美两军最大规模、最残酷阵地战。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激烈军事对抗。
③中国人民志愿军迫使联合国军停止进攻。上甘岭战役后至朝鲜战争停战,再没有发生营以上规模战斗。
2 咽喉
战争是杀人的艺术,它最高最完美的境界
是一剑封喉
这就是那场战役的发生,并在六十年后
让我想起和试图还原的
理由?当东北亚的这座半岛再次成为世界的火药桶
战端一触即发
上甘岭。一座露天战争博物馆,展台
磅礴,赫然陈列它陡峭的天地线
被炮火大面积大尺寸
削低的高度;锈死在幽暗尘土里的
铁;还有它的荒凉、神秘和孤寂;它因长期无人问津
而被越来越深的草木掩盖的呐喊
呼吼,和骨头的断裂声,鲜血的滴答声
从那儿归来的人说,在月落星稀的夜晚
或湿漉漉总也见不到阳光的阴雨天
山顶上的争夺还在继续,枪炮声还像当年那样繁茂
和密集;当一切复归沉寂,泥土中
有人翻身,有人抽泣,有人坐在某棵大树下
反复清点失散的手指,但那张脸
血肉模糊,认不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我固执地认为,他不是中国人就是美国人
他们一个远渡重洋,一个在
严寒的冬天,脱下棉裤涉过
凛冽的界河,然后在这山脉淤塞的咽喉地带
展开搏斗和厮杀,把死亡像沙丁鱼般
压缩在恐怖的瞬间。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这些士兵啊
这些像虎豹般勇猛的人,他们
仆倒,他们死去
脚下的这片土地,没有一寸是他们自己的
3 范弗里特将军要摊牌
旷日持久,深陷在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
我猜想范弗里特将军的那颗胆
刚开始有拳头那么大,鸡蛋那么大,之后渐渐萎缩
渐渐萎缩,变得只有睾丸那么大
麦粒那么大。我是说抢在1952年大雪纷飞之前他即将在五圣山上甘岭,向当面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展开的摊牌行动
狂妄中有些战战兢兢,谨慎中又有点
胆大包天。军史专家们追踪说——
这或许是一个阴谋,一个父亲在绝望之时的
利令智昏,当老范弗里特的儿子小范弗里特
一个漂亮的飞行员,被中国人
击落,葬身火海
他进攻上甘岭,是要让更多的人失去儿子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联合国军美7师
与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
在上甘岭虎踞龙盘,壁垒森严,就像两座即将相撞的山
突然凝固,彼此听得见对方的打鼾声
磨牙声,和梦里的霍霍磨刀声
但志愿军控制的狙击岭高地(中方称537.7
高地)和三角山高地(中方称597.9高地)
就像两把尖刀,闪亮,锋利
狠狠插入美国人的咽喉
让他们疼得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而在某个早晨或某个夜晚,范弗里特将军
恼羞成怒,他一咬牙,一跺脚
哗啦啦调集16个炮兵连的1300门大炮,170辆
坦克,50架B—26轰炸机,决定
放手一搏。“克拉克将军,一台小小的
外科手术。”他这样信誓旦旦又稳操胜券地
对他的上司说:“我只用一个营的兵力
把共军逼退1250码。仅此
而已。
不过,这也够中国人喝一壶了。”
范弗里特将军还对克拉克将军提到了伤亡
这是不可回避的。“200名怎么样?”
他说:“我保证,不可能再多了,也不可能再少。”
那种不容置疑的样子,就像他即将召开的
那场新闻发布兼冷餐会,必须
聘请200名记者,购买200公斤葡萄酒
200只火鸡(将军们总是如此,战斗在即
士兵的生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数字)
4 美国兵
刘易斯或者威廉斯,在麦坚利堡大理石的墓碑上
我们读到过这些名字
而在1952年10月14日前夜,他们是
明明灭灭的一颗颗星,在上甘岭
美军一侧的树林里
闪烁。永远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那些来自弗罗里达
或亚利桑那州的白人和黑人
小伙子,歪戴着帽子
嘴里嚼着口香糖,把子弹上膛的卡宾枪像烧火棍那样
斜靠在肩膀上,正在热烈谈论着加利福尼亚
的风光,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景色
抑或胜利日那天
在圣地亚哥,水兵们像鱼那样游上岸来
把手捧鲜花的姑娘仰面朝天地
按在怀里,狂热亲吻;风掀起她们的白裙子
有如墨绿色摇曳的荷叶,托出
一朵朵粉红色的花
也有人背囊里装着美人画片和避孕套
把钢盔倒扣在地上,坐在那儿
慢悠悠抽烟,在心里盘算着
打完这一仗,该去
汉城的哪家妓院,度过即将到来的圣诞
炮火覆盖后向高地发起冲击,这是他们
天亮后要干的事儿,但在他们心里
那不过是一次狩猎
如同过去的某个假日,在犹他州或缅因州,带上面包
奶酪、睡袋,和皮毛油黑
发亮的拉不拉多犬
在原野或树林里,快乐地追一只兔子
5 如鸟飞翔
他感到他飞了起来;他感到他抱紧的头颅
他蜷缩成一团的身体,他身体里的
肌肉、骨头和血,也跟着飞了起来
就像在操场上听见哨音
欢呼雀跃着,突然跑散的一群孩子
黎明的天空是被漫天呼啸的橘红色火焰
像撕一匹白绸缎那样,陡然撕开的
山那边万炮齐轰!——那是些
大口径重炮,装填雷霆、闪电和风暴
嗓子粗得像山崩地裂;一溜儿排在伪装网里的坦克炮
也高高昂起,它们笨重的身躯爬不上陡坡
和悬崖,可司令官现在只要这些战争的
庞然大物,披坚执锐,摧枯拉朽
用它们力大无比的穿甲弹、破甲弹、碎甲弹
和榴弹,加入雷霆和火焰的合唱
现在大地像一面巨大的鼓,被一支支难以想象的
重槌,几千次,几万次,甚至
几十万次地,擂响——轰隆隆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轰隆隆……这时所有的耳朵,都有一种
声音被扑灭后,突然失重的感觉
所有在附近站立或行走的人
都像热锅里的豆子,被炒得蹦蹦跳跳
弹着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弹着点的爆炸声
纵横交错,排山倒海,密不透风
弹着点的爆炸声,是火药
在爆裂,钢铁紧密的躯体,在瞬间解体
火焰的翅膀携带着破碎的弹片
滚烫而锋利的弹片,像鸟一样,闪电一样,光一样
飞。当然当然,弹着点的爆炸声
在众人仰望的山的高处,在硝烟滚滚的山的
结合部、突出部和回旋部
而山上什么情况?正发生什么事情?
当那儿蝙蝠纷飞,此起彼伏的爆炸掀起的火光
和热浪,彼此淹没和覆盖;当唿哨一样
刮过山巅的B—26轰炸机,火上
浇油,投下一枚枚重磅汽油燃烧弹
并由此织成一张熊熊燃烧的火焰的网,一场
火焰的狂飙,火焰的海啸;当地狱在轰隆
轰隆的爆炸声中,毕剥毕剥的
燃烧声中,猝然打开一扇又一扇门……
他感到他飞了起来,像鸟儿那样飞起来
他感到从他的身体里,噗噜噗噜
噗噜噗噜,飞出来一只鸟
一群鸟:它们穿过火焰、硝烟和愤怒翻滚的云团
一路发出悲愤而绝望的鸣叫
之后沿着相反的方向,一根白羽毛
飘飘扬扬,像一朵雪花重临大地
那么,他是谁?他走了多么远的路
来到这里?有着怎样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
请原谅我说不出来
虽然我听出了他的口音,知道他在
异国他乡,像一棵庄稼那样,眷恋着故乡的
老屋、水井,和在水井边汲水的情人
6 一个死者的独白
漫上高地的那一刻,我们才发现
美利坚的傲慢与偏见
还有它武装到牙齿的
炮兵和坦克兵,仅仅充当开山放炮的角色
当我们在雷霆和火焰中穿梭,眼睛
被璀璨的光,一次次刺瞎
哦哦哦,这时候我已经分不清谁是
骄傲的猎人,谁是可怜的猎物
而岩石崩溃,山的高度被雨点般倾泻的
炮弹,反复涂抹和改写
从断崖到断崖,是一片红色沼泽
我说不出那种红,也说不出脚下几米深的
尘土,如何缠住两条紧张跋涉
的腿。我只知道我们的战场
其实也是我们的坟场,死水的气息扑面而来
啊,啊,你看见了吗?在山顶上隆重
迎接我们的,或者用将军的话说
款待我们的,那些用荷兰的郁金香
法国普罗旺斯的马鞭草
和薰衣草,像编织斑斓的春天那样
编织的花环呢?
还有砰的一声,像打开一道喷泉
一道彩虹的,那些产自维也纳或慕尼黑的
香槟酒呢?当然还有战地记者们按亮的
闪闪烁烁的镁光灯——在记忆中
他们的鼻子总是比狗还灵,比工兵营那些
探雷器的探头,还灵
每逢重大战事,比如——我是说比如——
我们如愿占领了狙击岭和三角山两座高地
他们一定会呼啸而来,把自己
当成一粒金黄的,脱膛而出的子弹
啊啊!真正在山顶上迎接我们,款待我们的
是死亡!是中弹后痛不欲生的嚎叫
是侥幸活下来的惊魂未定
是生不如死的恐惧、惊慌,和从此永远无法挣脱的
梦魇。具体地说,在山顶上迎接我们的
款待我们的,是脸膛被滚滚烟尘
熏得油光斑驳,只露出两只眼睛在骨碌碌滚动的
中国士兵,他们纷纷从尘土中,从废烟
升腾的堑壕里,一跃而起
同时用咆哮的苏制冲锋枪和转盘机枪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开
一道道死亡的扇面。那种居高临下的
横扫、洞穿和屠戮,就像秋天到了
一把把磨得星光闪耀的
镰刀,打开了它们锋利的刀刃
在麦地开始凶猛地刈割,刈割、刈割……
像山峦崩裂,河水倒流,一股股血
迅速从我们的眉心,我们的脖颈
我们的胸膛、下腹和四肢,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涌出来,射出来,甚至像打开的
高压水龙头那样,喷出来
然后,我们呈各种姿势倒下,缓缓倒下
再层层叠叠地交缠,堆积
层层叠叠地垒筑起高地的另一种海拔
最可怕最惊天动地的,是绝地反击
赤身肉搏,是死里夺路的刀刀见血
相互抢夺死亡的渡口
此时,他们中垂死一搏的一个,或者孤立无援
再不准备活下去的一个,会突然从尸堆里
跳出来,扑上来,像野兽一样
掐住我们的脖子,咬住我们的耳朵或喉管
再或者拦腰抱住我们中步步后退的一个
摔打,撕咬,轰轰烈烈地
滚下悬崖;更多的是拉响手雷和爆破筒
让互相间搂在一起,撕也撕不开
的身体,光芒一闪,犹如
灿烂的,在节日的夜空绽开的礼花
当黑夜来临,山冈出现暂时的寂静
同伴们相互搀扶着爬起来
但谁也认不出我的脚印,我们的脚印
我们就忠实地留在这里,怅望这山
怅望这断崖,怅望这波动如潮水的泥沼
我知道明年从这里长出来的
第一蓬青草,必定起自我的骨节
7 坑道!坑道!
范弗里特将军感到奇耻大辱,感到他
一世的英名被一时的愚蠢
无情欺骗和嘲弄了。怎么可能呢?
他想,怎么可能呢?仅仅只有3.7平方公里的两座高地
他以每秒六发炮弹的频率,狂轰滥炸
把那里的每块岩石,每棵树木
甚至每根草,都掀翻了
甚至这酷烈的钢铁之火,野兽之火
天堂之火,把两座高地上的
每块碎石,每粒土,土里的每只蚂蚱
每条蚯蚓,都火烤了一遍
油烹了一遍,怎么可能还有人活下来?
他们到底藏在上帝的哪一道
石缝里,长着
怎样的一颗脑袋,怎样的三头六臂?
“半座山都被掏空了!”死里逃生的刘易斯
或威廉斯,向将军揭开这个秘密
他顿时有些恍惚,有些懵
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好像突然被堵塞的
下水道;前胸和后背也凉飕飕的
仿佛整个人突然被剥光了,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虽然将军有预感,他觉得对方的武器那么
简陋,着装那么单薄,兵员
也征集得那么匆忙,甚至没有接受
最基本的训练。尤其他们的后方,他们的火车
和汽车,如同靶子,赤条条地暴露在联合国军的轰炸和射程
之内。仿佛从天空落下的一滴稍大的雨
就能把它们砸进尘土里
但是,当他们在高地驻扎下来,怎么可能成为
山的一部分,岩石和土壤的一部分
成为群峰之上的群峰?仿佛
他们作为山的魂魄,融化在
山的血液和骨骼里,山的心跳和呼吸中
现在他知道了!现在他知道这些瘦弱的
矮小的,黄皮肤的中国人
他们像猴子一样灵巧,虎豹一样勇猛
有时又甘愿做一只笨鸟,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一次次,一遍遍,反反复复地飞
就像战事还未爆发时,他们一锤一钎
一砂一石,竟把高地花岗岩
和石灰岩的腹腔,日复一日,点点滴滴
掏空了。是的!现在他知道了,现在他终于知道了
他骄傲的美利坚,他们号称无坚不摧的
飞机、大炮、坦克、卡宾枪和火焰喷射器
遇上了更骄傲,更坚不可摧的
一群人:他们简单、粗糙、坚忍,曲体在岩石中
藏身,就像水藏在水里,火藏在火中
8 没有姓名牌的军队
放下久久举着的望远镜,他不易察觉地
笑了一下。不经意嚅动的两片嘴唇
嘟囔着,含含糊糊地漏出几个字
不过他的笑,是苍凉的,有那么点愤懑
酸楚,凄苦,和无可奈何
而长久跟在他身边的人,听出了他
含含糊糊地漏出的几个字,带着他难以更改的
红安口音,而且是不怎么洁净的词
自称文明世界的人,他想,他们是
多么野蛮和残忍啊!依恃着
轰炸机、坦克履带、大口径火炮
从天空至大地制造碾压之姿,仿佛我们是一群
懦弱的,孤苦无助的蚂蚁
蜉蝣和飞蛾;而他们付出的代价
只不过在白衬衣的领子上,溅上我们的
几滴血。那么来吧,来吧,
就冲着我们的胸膛来,冲着我们扼守的
597.9和537.7两座高地来
问题是,你们是否长出了这样一副好牙?
放下久久举着的望远镜,他悬着的心又
一阵抽搐,传来无法言说的疼
他想起了他布置在高地上的那两个连队,那两个加强连
想起了那些他亲如儿子的
士兵,现在他们在战斗
在生命的悬崖苦苦攀登、坚守和困兽
犹斗,每时每刻都有人坠落,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而他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脚下的泥土
熟悉自己两个巴掌上的十根手指
他知道他们像牛一样憨厚
诚实,忍辱负重,在烈日下给他一滴水
就能活过来;在岩石中给他一道缝隙,就能扎根
萌芽,像手掌一样打开两片嫩叶
他知道这些农民的儿子,穷人的儿子,他们
从田野走来,信奉以牙还牙以命夺命
的哲学。与他几年前,十几年前
一模一样。因为他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穷人的儿子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肠胃里
胆囊里,至今还残存着故乡的水土。如果打个嗝
依然能打出红苕的味道。甚至,自从离开
长江边那片红土地,他南征北战,出生
入生,但至今还记得家里的
那把铜齿钥匙,放在门边的第几个砖洞里
因此,因此啊,当他的连队,他儿子般的
那些士兵,在那么高
那么狭窄,炮火又那么猛烈的阵地上
拼命夺命搏命;他知道他要做的
便是号令三军,把穿过风雨的旗帜,插到山顶上去
把一个军团赤诚的血,洒到山顶上去
像对方的官兵那样,脖子上挂一块姓名牌
那是六十多年以后的事了(连他
自己都无缘见识)
而我们一支落后几十年的军队,一支
土地的军队,农民的军队
此时由他们的将军——他的名字叫秦基伟——
带领,勇敢地去战斗,去赴汤蹈火
那种对决——在中国,叫针尖对麦芒
在世界,叫火星撞地球
9 山头鼓角相闻
3.7平方公里的两座高地,崔嵬,奇崛
风雷激荡。我们看见的是一只
巨大的,被高高举起,燃烧着
滔天火焰的大鼎。士兵们就在这只被烧红的大鼎里
翻滚,跳跃,匍匐前进
反复争夺战争的制高点,反复地
你死我活。脚下的尘土滚烫,松软,混合着
残损的铁,破碎的岩石,怆然散落的
断臂、残肢,以及喑哑的
呐喊、怒吼和呻吟;双方炮兵应和前方的
呼唤,你来我往地压制
与反压制,让一堵堵原本岌岌可危的
生命的墙,在轰轰隆隆中,加速倾斜和倒塌
空气里飘满刺鼻的硫磺味与血腥味
即使龟缩在用钢筋水泥浇筑的坚固
地堡里,如美军;抑或凭借坑道
昼伏夜出,像割断一茎茎草那样割断对方的呼吸
如志愿军;但主阵地的互换总是在
须臾之间,总那么频繁、血腥、惨烈
因此,死亡在频频提速,像夏日
骤升的水银柱,秋天渐渐丰盈的谷堆
数据是枯燥的,但累计这些数字,如果是
生命呢?再如果这些生命,时时刻刻
都像秋天的落叶,在狂风中
一片片飘零呢?比如,在三十公里战线上
仅对付上甘岭,我们的597.9和537.7两座高地
他们就动用了300门大炮
27辆坦克,40架来回府冲的轰炸机
已经和将要落入两座高地的
炮弹、航弹和凝固汽油燃烧弹,达190万发
再如志愿军一方,第一天战斗至黄昏
战前于坑道储备的弹药消耗殆尽
共发射子弹40万发,投掷手榴弹、手雷10000枚
另因卡壳和枪管打红而报废的
枪支,包括苏式转盘机关枪10挺
冲锋枪62支,步枪90支……
“山头鼓角相闻”就是说,山顶上的
生存与毁灭,就看谁能挺过致命一击
10 38个黄继光
借助夜色,猫着腰,作为第二梯队临时补充
上来的一个兵,他踩着滚烫的焦土
一步步前行
同时,他也在一步步走完他的烈士之旅
他是个勤杂兵,端水扫地跑腿那种
老兵眼里受宠的小兄弟
而目前的战况是:第一梯队打瘫了
打残了,第二梯队只剩下他们这些送信的、剃头的、做饭的
当他们第130次,或第289次(最终的数字
是第900次)从坑道突入表面阵地
他们从身体里掏出了誓词
掏出了忠诚和胆魄
最后只剩下慷慨一死,掏自己的命了
子弹从美国人的地堡里像大雨那样泼过来
他们借助凶猛的炮火
在刚抢占的阵地,如同抢种庄稼那样种植的地堡
以纵横交错的火力网,让你插翅难飞
前几个人倒在了冲击的路上。他被命令
带领两个兵,炸掉那些地堡
他说是!三个人像三粒豆子那样撒出去
那两个兵分别叫吴三羊和肖登良
他们交替掩护,都像他那样
猫着腰,一步步前行
一座地堡被炸掉了;又一座地堡被炸掉了
这时,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第三座地堡里像眼镜蛇
那样高高探起的夜视镜里
但他们毫无察觉,他们继续猫着腰
继续向他们认准的目标挺进
哒哒、哒哒、哒哒……地堡里三个
精准的点射
吴三羊仰面倒下,肖登良的胸膛
被一颗子弹钉在焦土中
再也挪不动了
猩红的血,像河水一样哗啦哗啦流淌
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他还看见一束光
嗖的一下,钻进了他的胸膛
他一阵战栗,黏稠的血洇了出来
把胸前的制服和弹袋,身体下的那一片浮尘
染红了。脑海里传来溺水般的晕眩
喉咙也喘不过气来,他知道
一道门就要关闭了,一把锁就要锈死了
但他的思维还那么清晰,还没有像他的
身体,熬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他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战斗小组三个人的任务
现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必须代替
吴三羊和肖登良,代替死在他前面
的所有人,顽强地活下去
把他们想做的事做完,然后去追赶他们
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重做一支部队的兄弟想到这里,一阵困倦袭来,他拼命
摇了摇头,把自己摇醒
他知道自己一旦闭上眼睛,一旦睡过去
就永远不会醒来了。因此他命令自己振作起来
挺住,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爬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后来,他趁自己的血
还未流干,艰难地爬啊,爬啊
往那座地堡的射击死角爬
然后他纵身一扑
用残损的身体,堵住了那根咆哮的枪管
是的,他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英雄黄继光
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135团9连通信员
四川中江人,1931年1月8日出生
1952年10月19日壮烈殉国
我还应该告诉你,黄继光是上甘岭战役38个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烈士中的一个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11 一个苹果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坑道,对准坑道的
逼仄、阴沉、潮湿;对准壮士们的嘴唇
因焦渴而爆出的一粒粒血;对准伤员们因得不到救治
而吐出的最后一朵白沫;对准山那边联合国军
疯狂炮击时,坑道里地动山摇的轰鸣
震荡,和头痛欲裂;再对准一个十七岁士兵
看大汗淋漓中,他的命,怎么被活活震碎
在花岗岩和石灰岩内部凿通的坑道
是用来屯兵、屯粮、屯一切
战争物资的;现在被迫用来囤积饥渴、疼痛,死亡
和战争的野蛮与惨烈。想想吧,电话线
被炸断了,补给线也被炸断了
对峙变得近在咫尺:占领表面阵地的美国人
(后来是韩国人)孜孜不倦,开始在
坑道的顶部,凿眼放炮
后来又在坑道两端,用火烧,用毒气熏
如同对付一窝地鼠
而我们的官兵,在一次次忍受饥饿
一次次舔过岩壁的水渍水痕
之后,仍然扑不灭喉咙里和舌尖上腾起的烈火
这时,一个苹果,将带来怎样的惊喜?
就是一只苹果!它是8000名运输官兵
擦过B-26像刀刃般俯冲的机翼
穿过冰雹般倾泻的炮火
送上来的。请注视他们负重蹒跚的背影——
8000条生命,一个个弯成一张弓
背上压着枪、子弹、急救包、炒面、水
罐头、压缩饼干、擦屁股的卫生纸
用来止渴的萝卜、苹果……拉开一道长长的蜿蜒
起伏的散兵线
在云雾缠绕的山峦中,那种阵势
像不像8000只艰难蠕动的蚂蚁,8000只
细小的嗡嗡飞翔的蜜蜂
为一粒米,一小口蜜,鱼贯而行?
而战争是一头沉重的大象,一条蛮横的大河
当这头大象柱子般粗重的腿,嘭咚嘭咚
踩过来;这条河流汹涌澎湃的浪
哗啦哗啦打过来
一只蚂蚁,或一只蜜蜂
将承受怎样艰难的生?怎样悲惨的死?
这个战地新闻和黑白胶片反复歌唱过的苹果啊
你应该知道,它是从30000斤苹果中
被送上甘岭的惟一
一个苹果
捧在手里,你的心假如是一道钢筋水泥修筑的大坝
你说,你能否阻止它崩溃?
12 像给灯添油一样
我不敢省略这撕心裂肺的一笔
动人心魄的一笔
否则,我会感到我在犯罪——
在上甘岭,子弹要节省;食物要节省
水要节省;蜡烛要节省;救死扶伤的
药品和纱布,要节省;战友牺牲时悲恸的泪水
要节省;吞咽压缩饼干和脱水干菜
的速度,要节省。必不
可少的死亡及死亡时间,也要节省
是因为战争太剧烈了!死伤如流水太迅猛
太湍急了!先一个连,一个营
再是一个团,再再是一个师
而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死,去被乌鸦般
飞来的弹片,砍断一条腿或一只胳膊
被飞溅起来的岩石碎片,击瞎一只
或一双眼睛;被凝固汽油弹腾起的烈焰
在瞬间,烧成一截截让战友们
悲伤的,仍会说话和动弹的焦炭……
正是这样,他们创造了“添油战术”
就像为寺庙点燃长明灯,每次往前沿哨位派去三个兵
不能多也不能少
牺牲了再派三个,牺牲了再派三个
再再牺牲了,再再派三个,派三个……
13 秦基伟将军警卫连
将军不看他;将军始终在看石壁上的地图
在等待作战室的电话响过后
参谋们向他报告战况。诸如坑道里
此刻还有多少有生力量
多少伤员?有多少个阵地失而复得
得而复失?诸如我们的炮兵阵地
是否隐蔽?是否能及时转移?
是否扛得住联合国军的飞机突然到来的轰炸?
是的,他现在常常说“我们的炮兵”
语气中流露出欢欣、钦佩
自豪和由衷的赞叹;也流露出他作为一军之长
对战局,还算游刃有余的掌控
因为“我们的炮兵”,其实是志愿军的
炮兵,毛泽东、彭德怀的炮兵
现在他们聚集在他的麾下,由44门重炮
一个卡秋莎炮团组成。而且现在
他们同样能把猛烈的炮火,稳准狠地
打到高地上去;同样也能
让美国人,让联合国军的士兵,像鸟那样飞
将军还在看地图,不看他,也不理他
这是因为将军知道他还站在那儿
因为将军知道,只要他不下命令
他就会一直这样笔挺地站着
不声不响,不摇不晃,不亢不卑
就像一棵树长在那儿,一枚钉子钉在那儿
他叫王虏,太行山的儿子,当然也是
一个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
将军记得那是1942年或者1943年
抗战后期,他的部队散落在晋西和冀东
撬鬼子的铁路,炸鬼子的炮楼
捎带着,把他从山村的土旮旯里
像挖土豆那样挖出来
此后他当了将军的卫士,也就是警卫员
一直跟着将军,为他牵马引镫
他与将军形影不离,既互为
镜子,又互为影子
将军的语言到哪,有时一刹那的闪念到哪
他就会出现在那里,像一棵树那样
长在那儿,像一枚钉子那样
钉在那儿。而他更愿意是将军肚子里的
一条蛔虫,每次把将军吃剩的
思想、智慧,还有和士兵一样粗糙的食物
再咀嚼一遍,然后融化在血液里
五六年过去,五六年跟随将军从战争中走来
现在他是将军警卫连的指导员
也可以说,是将军卫队的
卫队长,依然日日夜夜,在坑道口
在将军睡梦的边缘,守着将军
因而他比谁都知道,将军的部队不够用了
将军的士兵尸横遍野地躺在
上甘岭的高地上,这让将军耿耿难眠
夜夜翻身像翻动一扇磨盘
因此他对将军说,“让我带着警卫连上吧!”
说完便站在将军身后,不动
像一棵树那样长在
那儿,像一枚钉子那样钉在那儿
许多天又许多天后,将军终于回过头来
走到他面前,抬起双手
用力地拍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找准他的锁骨,重重掐了他一下
这天下午,上甘岭我537.7和597.9高地
打来电话报告说:军部警卫连96名官兵
到达主坑道24名
指导员王虏等在敌拦阻炮火中,光荣牺牲
一颗硕大而浑浊的泪
从将军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14 比钢铁更坚硬的
“欲壑难平,吞噬钢铁火药;城市乡村
士兵们生龙活虎的
生命
噢,战争!你究竟长着一个什么样的胃?”
如果范弗里特将军是诗人,如果他习惯地
在随身带着的笔记本上,匆忙
而潦草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想,他那颗苍老的心,一定无比的悲凉
战争打了十二天。十二天的战争神使鬼差
把一场营规模的战斗,打成了一场
战役,而且暂时没有休战的迹象
但在这十二天中,美7师的九个步兵营
齐整满员地投进去八个
可怕的是,刚投进去一个,就被打瘫打残了
再投进去一个,又被打瘫打残了
眼看一个师只剩下一副骨架,一副瘦骨嶙峋
风雨飘摇的骨架。仿佛上甘岭深藏着一个
巨大的,总也填不满的漏洞
仿佛这个漏洞,直通不算远的马里亚纳海渊
而战场依然在咆哮,依然张开
血盆大口,等待他继续填进去千军万马
在说不出的郁闷和懊恼中,脑海里
灵光一现
范弗里特将军想到把美军撤回去
把韩军换上来。虽然这是一个将被联合国军普遍怀疑
垢病,甚至嘲讽的方案
但他豁出去了,他觉得,这是他必须
承担的风险、偿还的罪孽,哪怕走上军事法庭
因为在这十二天中,他看到了
太多的血,太多的包括他儿子小范弗里特
在内的,美国士兵的血
而且这些血,这些血,由臆想中的
涓涓细流,渐渐变得浩浩荡荡
惊涛拍岸,就像巍峨的一座座大坝坍塌了
美利坚的儿子啊,蓝眼睛高鼻梁
英俊又伟岸,如果回到安第斯山或洛基山
戴一顶巴拿马草帽,威风凛凛
哪一个不是好骑手,好男人,让女人们沉醉
疯狂,爱得死去活来?可现在他们在流血
在汩汩地流,哗哗地流,止也止
不住。那战死沙场的,不是几个
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也不是预案中的200个
而是2000个,甚至20000个……
是啊!必须把拳头收回来了;必须痛定
思痛,拯救大兵瑞恩和泰迪
拯救刘易斯和威廉斯,并让他们喘息
休整、疗伤,从噩梦中醒来;还必须忍受
暂时的痛苦和屈辱,重新审视
山那边的这个对手,那些不可思议的
中国人,比如他们的顽强,他们的
前赴后继,他们不要命地以命搏命,以命夺命
他们过去年代经历的苦难与贫穷
屈辱和悲愤;他们比钢铁更坚硬的意志
他们面黄肌瘦的身体里
隐藏的剽悍和决绝,他们随时迸发的英勇
渐至他们能消化沙子和稻草
的胃,他们的骨密度和骨头中磷和钙
的含量;他们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
是的,比钢铁更坚硬的,是一种精神
它漫漫漶漶,绵延不绝
如同在那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从容不迫,永远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
15 板门店
你现在看到的是战争的一个休止符
听到的是一首战争挽歌低音区里的
无歌词混声伴唱
如果把它还原为东北亚的咽喉
这所孤零零存在了六十年的
老房子,应该是它上下滑动的喉结
多年后,这个咽喉上的扁桃体仍在发炎
与咽喉紧密相连的呼吸道
也不时红肿,溃疡,就像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
仍然有无名氏的遗骨,在挖掘机
挖开的地方,峥嵘
裸露,让流血的往事再次凸突出来
而写在纸上的协定总在提醒我们
战争是一座活火山
它暂时的休眠
只是在等待下一次更猛烈的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