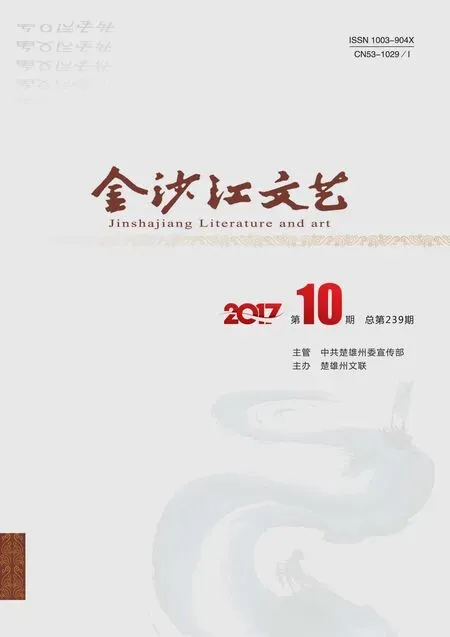落雪向南,南隅往北
张宗娟 (彝族)
第二次见到落雪是在南方小城里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街上,晌午落了一场雨,这会子倒是又晴开了,阳光刺破厚重的云层,似乎是不甘心被暮色夺了光彩;冬日的暮光,似乎是没有温度的,湿漉漉的青石板上苔藓肆无忌惮的生长着,这里似乎是这座南方小城里一处不会被提起的记忆。
我看见落雪的时候,她蹲在街道旁伸手去摸一只猫,那是一只黑色的猫,有着四只白色的爪子,她伸手去摸猫的脑袋,猫伸出一只白白的爪子挠她摸它脑袋的手。
此刻的南方小城暮色正浓,青石板街泛着熠熠的光,暮光里一个女子和一只猫,美好得让人不忍心去惊扰。
我看着咫尺之遥的落雪,上次看见她还在遥远的北方,冬夜昏黄的路灯下,她伸手去接飘零的雪花,燃生伸手去捋她散开的头发,似乎也是这样,美好得让人不忍心去惊扰。
我走到她跟前,猫怕生,蹭的蹿上了屋檐,很快便没了踪影。
落雪起身跟我说话,她说 “南隅,外面挺冷的,去店里吧”。
她身后的小店,店名很长,叫做“年先生与二小姐的杂货铺”,一个月前我给她发邮件,称自己是流浪的手艺人,想到她的店里做义工,为显诚意,我在邮件里附上了名字和照片,她在邮件里回复我说 “南隅,好美的名,好美的人,我等你来。”
我与她进到店里,店面不大,东西不多,却是精心打理的样子,玛瑙珠子银链子以及手工簪子和碎花裙子,每一样似乎都可以称为艺术品。
她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递到我的手里说: “南方的冬天,太阳落了,便冷得很,喝碗热粥会暖和些。”
我接过粥喝了一口,是挺暖和;我问她 “为什么店名不叫 “年先生与落小姐的杂货铺”呢?”
落雪没有回答我,她说: “南隅,我们去隔壁街的酒吧里看年夏打手鼓吧”。
年夏便是年先生,他白天在杂货铺里做手工艺品,晚上去酒吧里打手鼓。
酒吧里人不多,三两个在喝酒聊天,三两个被民谣歌手唱的荒凉生活惹红了眼,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台上那个认真打着手鼓的男子,落雪看着他却晃了神;他拍打的手鼓,是掉了漆的陈旧模样,鼓声却绕绕动听,似乎是在讲述某个古老的故事,透着酒吧里氤氲的光线,我笃定,落雪定是在想念 “沧笙”,或许也是想念屿山的。
“沧笙”是屿山和落雪曾一起经营的马场,彼年落雪是一名医生,屿山是专业的马术师,他们相识于一个马术俱乐部,落雪试图尝试通过马术训练让自闭症的孩子得以康复,她和屿山一拍即合,然后便一起经营了 “沧笙”。
“沧笙”不大,四周围满了樱花树,是个会让人心生喜欢的地方;一些患有自闭症的小孩被送来了这里,通过马术治疗,终于有小孩的症状开始好转。
一切似乎都进展得自然而然,包括屿山和落雪的爱情。
屿山在樱花树下跟落雪求婚,他们准备樱花盛开的时候在这里举行婚礼。
围满 “沧笙”的樱花开了,整个马场美得无需任何装点便能够撑起一场盛大的婚礼,可落雪却走了,她离开了“沧笙”,再也没有回到屿山的身边,再也没有。
很久之后,我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去过 “沧笙”, “沧笙” 早已不叫 “沧笙”,那里成了一个高尔夫球场,我站在栅栏外,看到有调皮的小孩子晃动樱花树,花瓣簌簌地洒了一地,我伸出手想接住一片花瓣,却连风都没有握住,那一刻,我似乎懂得了屿山的绝望与悲恸。
酒吧里,民谣歌手唱起了马頔的《傲寒》,正好唱到那句 “傲寒我们结婚,让没发生的梦都做完,忘掉那些错和不被原谅的青春”。
落雪揉红了眼睛,我在想,或许痛,是她和屿山的爱情里,她唯一还能拥有的东西了。
在 “年先生与二小姐的杂货铺”当义工的日子,白天我和年夏一起在后院做手工艺品,落雪在前厅打理店里的生意;晚上年夏去酒吧打手鼓,我和落雪跟过去看他打手鼓。
年夏沉默得很,不怎么开口说话,他打银器的时候和他打手鼓的时候一样认真;他在雕琢银叶子,我在打一支银簪子,在来当义工之前,我找专业的银匠师傅学过打制银器,他夸我打的银簪子漂亮。
我跟他打趣说 “那我用银簪子和你换银叶子”。
他讪讪的不接茬,继续在银叶子上雕花。
年夏雕完银叶子的那个晚上他没有去酒吧打手鼓,他在银叶子上串了根牛皮彩绳,然后捂在手里,去找落雪,落雪在院里喂那只猫吃鱼骨头。
年夏来到落雪跟前,猫刁起没有吃完的鱼骨头,蹭的蹿上了树,很快便没了踪影。
他将捂在手里的银叶子摊开来,说:“落雪,我们结婚吧。”
落雪说: “帮我戴上吧”。
年夏将牛皮彩绳系在了落雪的脖子上,他伸手捋了捋她的头发,他们没有注意到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的我。
就像在北方那个下雪的夜里,落雪伸手去接飘零的雪花,燃生伸手去捋她散开的头发,他们同样没有注意到远处路灯下的我一样。
白扑扑的月光照得小院透亮透亮的,我收好衣服上了阁楼,漫天的星辰在南方小城的夜里肆意的生长,那只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蹿了出来,落雪伸手摸它,它伸舌头舔她伸过来的手,年夏把那只掉了漆的手鼓搬到院里,鼓声落满小院;似乎一切都是尘埃落定的样子。
白扑扑的月光也照进了阁楼,我缩进月光照不到的角落里,我想念屿山,想念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屿山。
屿山会不定期的在一个网络平台上更新帖子,讲述他和落雪的故事,他讲他们相遇的马术俱乐部,讲他们一起经营的 “沧笙”,讲他在樱花树下向她求婚。屿山讲到这里却戛然而止,我在平台上给他发消息,追问后来的故事,他回复我说: “落雪离开了 ‘沧笙’,她再也没有回到屿山的身边,再也没有”。
我一直以为屿山和落雪的爱情故事大抵是杜撰的,直到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新闻报道的是一个无国界女医生,她结束了她的志愿医护生涯,准备回国,这个女医生的名字叫 “落雪”。
时空与故事重叠在了一起,我笃定,这个 “落雪”一定是屿山故事里的 “落雪”。
我通过那个网络平台给屿山发消息,告诉他落雪回国了,屿山却没有回复我。
后来,在北方那个下雪的夜里,我见到了落雪,还未能够与她相识,她却走了,只留下了燃生。
燃生和落雪一样,是无国界医生,他们相识于尼日利亚,燃生是驻地医生,落雪在产科帮产妇接生孩子,他们工作偶有交集,又一起结束志愿医护生涯,一起回国。
白扑扑的月光漫了过来,院里的鼓声停了,那只猫蹿来到我的脚边,我伸手想要摸它,它蹭地又蹿走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我将手机充上电,开机,未读信息涌上屏幕,点开来,全是导演发来的,他说: “南隅,这个月是你交稿的最后期限”。
然后我把充电器拔了,将手机继续关机。
我是一个编剧,有导演在那个网络平台上看到了屿山的故事,打算改编之后拍成电影,导演找到我,希望我接着把这个故事写完。
剧本其实几个月以前已经写完了,在我写的故事里,屿山一直经营着 “沧笙”等着落雪,落雪离开燃生,回到了屿山身边,他们在樱花盛开的时候举行了那个迟到多年的婚礼,故事的最后,燃生又回到了尼日利亚继续他的无国界志愿医护生涯,他在那里终于遇到了一个心爱的姑娘。
交稿前,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消息上说南方有个小店愿意收留无家可归的手艺人当义工,留下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名字以及一个邮箱,那个名字是“落雪”。
我又一次笃定,这个 “落雪”一定是离开北方的 “落雪”。
我给落雪发了邮件,在邮件里附上我的名字和照片,落雪回复了我,她说:“南隅,好美的名,好美的人,我等你来”。
我来到了这个南方小城,成了 “年先生与二小姐的杂货铺”的义工,小城里的落雪和故事里的落雪不一样,她温婉沉静,像极了青石板街上的苔藓,在小城里静默地生长着,独成一道风景,却甘于成为不被提起的记忆,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女子曾经致力于用马术训练治疗自闭症儿童,曾经在枪林弹雨的尼日利亚为产妇接生。
我疑惑,这样的落雪,怎么会丢弃她和屿山的爱情。
银簪子总算打好了,我将打好的银簪子装进木盒子里,我把木盒子递给落雪说: “送给你,我要走了,明天就走。”
落雪将木盒子接了过去,她说:“南隅,我和年夏的婚期订了,参加完我们的婚礼再走吧!”
我说: “落雪,你爱他吗?”
落雪转身去放木盒子,然后她说:“好好活着就是爱情”。
我不明白她话中的意思,第二天我还是走了,在漫天星辰还未消逝的早晨,悄然无声的离开了这个南方小城。
我在网络平台上给屿山发消息说:“屿山,我想见你一面。”
我又来到了 “沧笙”,可还是没有收到屿山的回复。
周围的樱花树上孤独的缀着几张枯萎的叶子,有个年轻的少年和我一样站在栅栏外,我走过去与他说话。
少年告诉我,他曾是一名自闭症孩子,他在这里通过马术治疗得到了康复,他偶尔会来这里,看看这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地方。
他说: “屿山老师不在了,落雪老师也走了, “沧笙”就被改建成了现在的高尔夫球场”。
我有些不解,少年讲的故事和屿山写的故事,似乎并不是同一个故事,我问他: “屿山去了哪里?”
我问及屿山时,少年情绪似有些低落,他说: “屿山老师在骑乘过程中,不幸落马,伤重不治。”
我的情绪在听完少年的话后瞬间坍塌,我想起了离开南方小城之前,落雪说: “好好活着就是爱情。”
如果真如少年所说,那在网络平台上讲故事的 “屿山”又会是谁?
少年带我去了屿山的墓地,我看到了墓碑上屿山的遗照,他和我想象的一样,有着一张英俊的脸。
我在网络平台上又给 “屿山”发了条消息,我说: “屿山,好好生活。”
导演又发来了很多条催稿的信息,他说: “南隅,明天要是还拿不出剧本,我就封杀你。”
我回复他: “姑娘我不玩了,再见!”
我一路向北,去了北方,留在了一个北方城市,我应聘上了当地的一家电台,当了主播,我不再写故事,而是开始讲故事,只是从此便只字不提 “屿山和落雪”的故事。
许久之后,我再一次登录那个网络平台,却再也搜不到屿山和落雪的故事了,有一条未读消息,是 “屿山”发来的,他终究还是回复了我,他说: “对不起,我不是屿山,故事是我听来的”。
转眼,又入冬了,地上的积雪越铺越厚,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我伸手去接路灯下飘零的雪花,有人在身后叫我:“南隅,好久不见。”
我回头,是燃生,有个漂亮姑娘紧紧的挽着他的胳膊,我说: “燃生,好久不见”。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也同样在北方,冬夜昏黄的路灯下,落雪伸手接飘零的雪花,他伸手去捋她散开的头发,我在远处路灯下看着他们,那时候的燃生,满足了我对爱情全部的幻想。
漂亮姑娘松开了拽着燃生胳膊的手,燃生上前跟我寒暄,他说: “南隅,你就像一只猫,突然闯进我的生命,又突然离开了”。
一只猫,南方小城里也有一只猫,黑黑的身子,白白的爪子,我突然很想念落雪,我问燃生: “落雪可好?”
燃生的表情似有些尴尬,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南隅,其实当年我们一起回国的本来是三个人,去机场的路上我们遭遇了恐怖袭击,其中一个女孩子为落雪挡了一颗流弹,女孩抢救无效身亡;回国之后,落雪执意要去照顾女孩的未婚夫,落雪离开之后,我们便没了联系。”
这一刻,我全然明白了,落雪那天说的: “好好活着就是爱情。”
我问燃生: “你爱她吗?”
燃生突然红了眼,他说: “多年前的冬天,落雪在飘着雪的冬夜里跟我道别,我看见远处路灯下有一个女孩,我以为我瞥见的就是爱情。”
我说: “好好活着就是爱情。”
姑娘又将燃生的胳膊紧紧的挽了起来,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当年的那种怦然心动,似乎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我辞了北方的工作,回到了南方小城,去了 “年先生与二小姐的杂货铺”,杂货铺还挂着当年的牌子,我记得我曾经问过落雪,店名怎么不叫 “年先生与落小姐的杂货铺”,她当时没有回答我,大抵 “二小姐”就是那个为落雪挡了一颗子弹的女孩吧。
眼下是正午,本是营业时间,杂货铺却关着门,四下打听,也未曾打听到年夏与落雪的消息,只听说,杂货铺已经关门好一阵了。
我租下了杂货铺隔壁的铺面,在里面卖银簪子以及碎花裙子,我将店取名为 “等”。
刚下完雨的南方小城暮色正浓,青石板街泛着熠熠的光,青石板上苔藓肆无忌惮的生长着,我笃定,我终会等到故事的结局,在冰雪融化的早晨,抑或星辰斑斓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