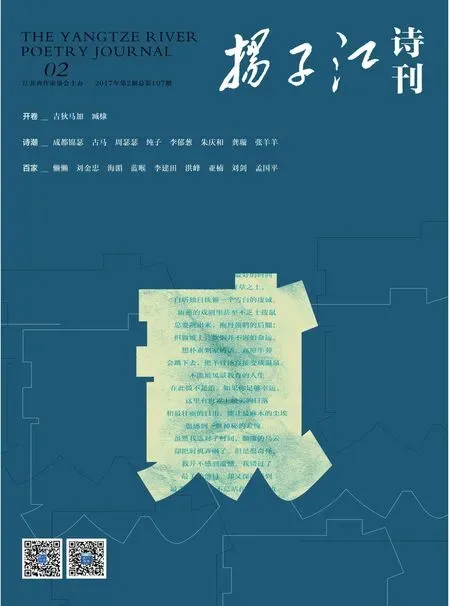陌生的脸孔:关于南音及其诗歌的印象式批评
海 马
陌生的脸孔:关于南音及其诗歌的印象式批评
海 马
1
我决定给南音写诗评,最初缘于两个原因:一是惊异、好奇;二是激动,或者说冲动。
2
这两个原因,实在太过感性、本能,说不上理性。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说,这也许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搞文学评论的人,则是不可容忍的缺陷。
现在,我因为这个决定而略有悔意。
在这个冬日的夜晚,残月在天,四野寂静。我喝了一杯咖啡和数杯浓茶,抽了半包香烟,仍然无法着笔。已是夜半时分,我感觉到腹中的饥饿。于是,我走到楼下的餐厅,吃了少许点心和肉脯,喝了半杯白酒。
3
不过,如果细加推究,我决定为南音写评,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自觉对中国当代诗歌所需承担的某些责任或义务。这个“第三因”,是道德或伦理上的某种认同和选择,也是人的道德意识或道德本能在作祟。
这让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篇评论写出来。不能退却。不能退却。不能退却。
我更不能做一个轻言寡诺的人。
4
我在“天降雨花·美在雨花”诗文大赛颁奖及诗歌研讨会上第一次认识了南音。其实,我首先认识的是南音的诗歌,这是一首叫做《新亭随想》的诗,获得了此次征文的一等奖。
一等奖共有两名。一名是祝宝玉的《龙泉寺》,诗风有些眼熟,让我颇感迷惑。另一名就是南音,整首诗写得有灵气,尤其是那句“讲到江山易主,未必比一株植物有趣”,让我在心里吃了小小一惊。举重若轻,这分明是诗词大家的作派。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名字我从未听说过,南京地面上有些名头的新、老诗人,即使没有见过面,也基本有所耳闻。但南音绝对是一个陌生人。
据主持人孔繁勋介绍,南音2016年4月才开始写诗,这更是让我惊异不已。她学的是中医,现在禄口一家医院的药房工作。我这才注意到,与我隔了两个座位的左边,坐着这个几乎一直保持沉默的女子。我发言的时候,表达了我的这份惊异。我说了两个观点,古人说“诗有别才”,我今天再次表示信服;有中文系背景的人,在写作时往往有诸多桎梏和教条,很多优秀的诗人或作家,恰恰都是非中文专业出生。
晚上一起吃饭。据说,是南音做东。大家欢声笑语,随意洒脱,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而南音,还是基本保持沉默,甚至还有几份拘谨、羞涩和不自在。她像客人,或者更像是一个小姑娘,或者初次上门的小媳妇。这与她的年龄一点也不相符。
也就在这个晚上,我知道了,南音即是毛新。
5
第二天,我给毛新微信,希望看到她更多的诗。于是,她发了《剥洋葱》等18首诗。
这让我更为惊异。一个人偶尔写一首好诗,这并不难,难的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能写出水平较高的一大堆诗。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初次接触诗歌的人。说真的,很多诗人写了一辈子诗,都没有一首诗能超过南音这组诗里的任何一首。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这组诗给我的印象是,一名叫南音的神、仙、鬼或狐,会写诗,性别不确,附着在一个叫毛新的江宁女子的身体里。我不知道他(她、祂、它)什么时候离开,或许,永生停留……但我必须向她(抑或他、祂、它)致意并致敬。
我给《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电话,告诉他我准备给南音写诗评。他正计划推她一组诗,于是,欣然应允。
6
我约她见面。
这不仅是“知人论世”的意思,更是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想寻找她这个人的性格、经历,与她的诗歌之间是否存有某种神秘的关系。毕竟,她不是女巫,不会随时召来一个神或仙,鬼或狐,附着在她的身体上;然后,就能写出了那些让人寻味和不可思议的诗来。
她立即显出了些许的慌乱和警惕。这少女般的慌乱,有点像第一次恋爱,被人约会的感觉。这慌乱像少女的,而警惕则又属于一个有人世经历的女子。
我只能笨拙地解释,我的突兀,别无他意。确实,我只是好奇,当然还有揽下的这份工作的需要。
就像面对从地平线上跃起的一颗陌生新星,我想寻找到它的前世今生以及运行轨道。
7
我见面的想法,因此消退。于是,我希望她发来更多的诗,不加挑选,我想寻找其间的写作轨迹。果然,在最早的一些诗歌里,我发现了其间的稚嫩,还有少量模仿与学习的痕迹。但即使在这些篇章里,也时有才情闪现。
她最初写散文。但从她发我的几篇散文里,实在看不出她的文艺天赋和才能。她喜欢阅读中国古典作品(这可能与她学中医有关),语言上有文言的倾向,有些夫子气。据说,“写的倒有上百篇,这样的随笔。后来因生活中小意外,我删掉了。”我所看到的《又是一年桂花香》《蔷薇物语》《墨落轻寒》《字词随想》等,属于劫后余生的产物。
但其中有一篇关于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评论,确实不错。感性与理性融合,这也是她诗的特色。她喜欢看电影。我想,这正是她写作的基础,除了阅读古典文学之外。看电影,是心灵和情感的重要体验和历练。电影,其形象性的表达方式,更与诗密切关联。
她之所以写诗,也纯属偶然。“我很简单啊。一个文学爱好者,以前爱散文和随笔。四月份偶然结识土牛,就学着写诗。后来发现诗歌的隐秘力量,便有点痴迷。”这是她的自陈。
而她的诗歌阅读经历,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开始就起点较高,接触的都是一些优秀诗人的诗歌。“几个月前不知道几个诗人,现在知道不少了。”“乱七八糟地读,喜欢辛波斯卡,阿米亥。还读了点王家新、路也、张二棍、雷平阳。”问她最喜欢谁的诗,“还是辛波斯卡吧,挺精致的。”“也买了两本胡弦的诗集,但不敢多看。一是惭愧,二怕学习的痕迹过重。”
有了这些阅读和艺术经历垫底,她能写出那样的诗也就不足奇怪或怀疑了。
8
后来,她为自己的拒绝见面作了如下解释:“这真倒不是顾虑。我本是女汉子一枚。我只是怕和你这么个纯文人谈得不尽兴,我肚子里真没啥墨水呢。”这是否解释得通?我早已不想细究了。
这是她对自己的描摹或刻画。
“生活面窄,平时接触人不太多。宅。”
“我耽美,热爱文字。有点小偏执,生活中有点飘。”
“其实我自卑的。”
“我本来就是个乡下丫头。”
“我不是装哎。我就是乡下人,走到人前心里总有点紧张。”
“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
“我习惯了生活中太多的冷漠与碰壁。”
“孤独和痛苦是常态,快乐才是非常态。”
“诗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
“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这句话,最为打动我。其实,南音确实挺像小孩子的,有点羞涩,与年龄不相称。这个年龄的女子,应该是非常老辣,无所顾忌,特别是南京女子。
说起那天晚上的请客,她说:“我只是觉得大家抬爱,借机会还了人情比较妥当。”“那天请吃饭,怕请不动。没想到居然请到。”“饭桌上有说有笑,一点不生分。呵呵,蛮开心的。”“我买酒时一直问愚木老师,这么便宜的酒不好吧?他非要买便宜的。”这是她的本色所在,纯洁、质朴、敏感、善良,知恩图报。
好诗人,也应该是个好人。
孟老夫子有“知人论世”说。我的信条是,好人写好诗。这是我的偏见。当然,人性是复杂的,人是多面的;在这样的世道里,更是如此。不过,即使是一个所谓“坏人”,也有好的一些方面,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少,一个“坏人”在写诗时,特别是写好的诗时,他身上好的、善的、真的、美的那部分一定是发挥主导性作用的。
9
她对诗歌和自己所写的诗歌则有如下认知。
“诗歌有魔力。”
“令人着迷,我说她是幸福的子弹。”
“水平不一,我状态不稳定。”
“以前太爱古典了,后来就与文字绝缘了。”
“命运很奇怪,又把我推到诗歌的面前”
……
也就是这些了,别无什么高论。不过,她的诗歌《伤口》里的一小段,也可以算是一段诗论吧。
“是的,直至今日
我依然愧疚于每一个清晨
也未能将生活的口琴吹得动听
我只是在梦里
将隐秘的根脉扎向童年的村庄
并在虚构的眺望里,学会了泪流满面的技艺”
10
南音写的多是一些咏物诗,写的是一些平凡的事物。比如:水中的石头、公园的座椅、一棵梧桐、忍冬树。再就是,写日常的生活及其片断:剥洋葱、七月十五、秋夜、风在吹,等等。
这都是日常所见的事物或者生活。不过,它们及物,且抵达了心灵。当它们出现在南音的诗歌里,就不再是寻常可见的那些物事或场景,它们具有了灵性,具有了诗意。
比如,在诗歌《剥洋葱》中,她写了一个极日常的生活场景,剥洋葱。“很多次我剥到洋葱/郑重而缓慢”,这虽是简单的陈述,但有动作,有情态。然后,迅速地切入一个新的界面,深入了“洋葱”的内部世界。“仿佛进入一个繁复的宫殿/每一个洋葱里/都住着另一个洋葱/它们完整而又迷人。”这里,同样既有描述,又有心灵的感受和感悟。但音调已经开始拔高,这就像唱歌一样。一般诗人也许会到此为止。即使这样,也算得上一首不特别坏的诗了,但南音没有因此停止。“——这多像/我们在剥取回忆/一层层的深处/都有一个更小的自己。”这个类比,既是一个小小的转折和停顿,在情感和境界上,却又是一个新的提升。一切并未到此为止,南音还在继续。“直至,到最后/与那个最小的,洁白的婴儿相遇/我们早已泪流满面”。这表面上仍然是客观的描摹,但我们每个阅读者都会心领神会,那其中的人生或生命体验,以及更为深层的情感、意蕴。南音的歌唱在达到一个最强音后,戛然而止;而其余音,却袅袅未绝。一首静态的小诗,如此安宁和不动声色,却让我如闻洪钟大吕。它让我联想到《老残游记》中描写白妞与黑妞唱北京大鼓的那段。我想起了音乐。
而《水中的石头》也是这样的一首诗,写的是极平凡的事物,水中的石头。该诗起句即不同凡响,“我不敢揣测/一颗石头/是否有过飞走的愿望”。接着,她写这颗水中的石头,“在灰调的湖心里/因坐化过久/它似乎进入一种禅定”。她将它与岸边的“百花”进行了对比,写出了石头表面上的不动声色,甚至是冷漠,“百花 依然开在岸边/一年年的起死回生/从未撼动过你的情绪”。全部的升华却在这最后一段,在与“岸花”的对比中,继续叙说石头,“一颗石头,并无愿望/若说到孤独,那只是世人的托词/一颗石头,也无花的动荡之心/它只是坐拥自己的影子/或者沉入污泥消磨黑暗/或者等待一种水滴石穿的力量”。诗人的心灵和生命感悟,全部投射在这颗沉默的石头之上。这最后一句,犹如一记有力的勾拳,完成了诗歌拳击台上的一次完胜。强健的对手倒地不起,掌声和哨声四起。
《公园的坐椅》《忍冬》《一棵梧桐》《无名之地》也都是这样的诗歌。它们让我坚信,南音并非偶得妙句;也让我预言,南音还将写出更好、更有力量的诗歌。
她的诗穿透了日常的、现象的世界,深入了事物的内部,并触及它们的本质和性灵。
11
这些诗歌所传递出的那些力透纸背的力量,正是来自她内在的、强大的心灵。
她的诗里有悲悯和悲伤。南音是善良的、敏感的、质朴的,这是她的为人,也是她的诗。“黑”,“沉重”,“伤口”,“孤独”,“冷”,“硬”,“冷漠”,“坚硬”,“苦难”,这些承载负能量的词汇频频出现。她有着内心的忧伤和黑暗,有着那些无言的悲伤,有着那些“内心的塌陷”。
在《无题》中,她说,“我并不能准确呈现一段内心的塌陷/就像我不能形容浆果被啄破后腐烂的过程”“相对于在喧闹中获得幸福的人/我更相信寡言者,他们更像我的同类/我们可能更为热爱低处的事物/一朵花开,一只断翼,以及万物俯身的阴影/我们怀抱清水,我们自备深渊/我们是夜晚领到密令的使者,/奔赴在各自的苦难里”。在《无题》里则这样写道,“我只是一个被月光划伤的人”。她甚至也明白这些悲伤的来历。“我知晓人性天生存有缺陷/并且人们怀抱歧义生活/我也见识世间荒唐种种,/颈椎病与咳嗽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
但是,南音没有沉迷或沉沦于这些沉重与忧伤,沉沦于这些内心的黑暗,她在寻找着解脱和超越,选择了解脱和飞升。比如,在《伤口》里她这样写道,“我们用悲悯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在这里,悲悯成为沉重生活的治愈之药或解决之道。而在《无题》里,她则说,“让记忆去追往事的鸟,/用虔诚的手去敲未知的门”让过去成为过去,去探索未知和未来。在《无名之地》中,她更是显出了某种乐观和积极,“我熟悉生活里冷漠而坚硬的部分/但总能找到一阵风或一片阳光为其解脱/这,并非出自于某种智慧/只是,这世间并不需要太多走投无路的人”。这是一种挣扎,更是一种灵魂锻造。“这片无名之地,在我的梦境之上/我注定无数次踅转,并且卸下自身的沉重/和对世事的犹疑/我一直接受着这隐秘的恩施/在白昼涌来时,仿佛重生般返回”。她寻求自身的重生,这也是人类需要解决和克服的共同境遇和生命难题。
事实上,写诗,也是她的某种解脱和超越之道,是肉身的飞升。因此,她的诗没有世俗气,更没有悲观和沉沦,它们是飞升的,向上的。
南音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在心灵与世界的交换过程中,她的诗不仅有着人生、生命和灵魂的体验,同时,兼具智性色彩。因此,她的诗往往有着极其内敛的表达,这让她有时候显得像个哲人。这样的诗,绝对不是少女所能写得出来的。这符合她的年龄和经历。
某种程度上,南音的诗具有了某种哲学上的思辨色彩,甚至宗教的神秘意味。这都是中国当代诗歌所稀缺的元素。
说句玩笑话,这符合一个未来大师的基本条件。
也许,这并非玩笑。
12
再说一句题外话。
我认为,在诗与哲学的鸿沟之间,如果要架设起一道桥梁,或者说设置一条渡船,女性诗人以其身份和特质,极可能成为最好的建造者或者摆渡人。而男性诗人,则有着天生的劣势。这也正像哲学家和科学家里少有女性一样。
这是某种偏见,也可能是另一种“性别歧视”。
13
在把南音的诗歌“奉承”到某个极致之后,是时候转折一下了。但是……这是中国式评论的某种惯性,我也不能免俗。
作为一个写诗不足半年的诗人,事实上,在南音的诗歌中也存有模仿和学习的痕迹。比如,“我熟悉生活里冷漠而坚硬的部分”(《无名之地》),让我联想起韩东的诗歌《温柔的部分》,只是反其道而用之。“那些笑语的蒲公英,一年蓬,风信子/怎样拉起手,绕着湖跳起圆舞曲”(《无名之地》),则让人联想起法国诗人保尔·笛福的那首著名的短诗《回旋舞》:“假如全世界的少女都肯携起手来/她们可以在大海周围跳一个回旋舞/全世界的男孩都肯做水手/他们可以用船在水上造一座美丽的桥/那时候人们便可以绕着全世界跳一个回旋舞/假如全世界的男孩和女孩都肯携起手来”。不过,这不是抄袭,而是化用。
她的诗句里还有一些生硬、费解的词汇或句式。如“在词语的密林里,我不曾停止过割棘”(《伤口》),这个“割棘”就属于这种。
另外,刚才说到她诗歌里的哲学升华。但在某些诗里,在这些升华里,也有着理念的裸露。我们从上文所列举的一些例句里,即可看出这一点,就不再举例了。这些哲理或思想的“裸露”,有如突出于水面之上的石头,给人突兀之感。我更喜欢“水里的石头”,沉潜,孤独,无言,喜欢它们那种默默的“等待”,以及“水滴石穿”的隐秘力量。当然,我也更喜欢《剥洋葱》里的风格,不动声色,不着一词,却尽得风流。
南音还有余地。南音还是一个身处写作“少年期”的诗人。
14
我是一名高校的行政管理者。行政和管理,是我日常做得最多的事。虽然,我往往喜欢以诗人、评论家自居。我正在进行着艰难的改革和创新,改变中国高校中那些被扭曲和异化的观念、制度以及具体的做法(我是一个革新者或革命者,即使我在为南音写作诗评时,也在试图打破那些固有的诗歌评论范式)。我在打仗。我在与一些庞大而固执的东西作战。我是《格列佛游记》里的那个格列佛,手握利剑,面对着一群“大人国”里的巨人们,身长却不及他们的膝盖。但我不是唐·吉诃德,我面对是真正的魔鬼和敌人,不是风车,也不是羊群。
在我所在的高校里,有人把我比作《亮剑》中的李云龙。我在战斗,也不断受伤。这是我另外的一个形象,就像胡弦在一首叫《南京六诗人肖像·金牛湖》的诗中所写到的我,一个隐秘地写诗的人,却有一个“高校宣传部长”的外在身份。但我,其实只是一个敏感、善良、温和、唯美且柔软的人,有一个“柔软的部分”。那个部分,最令我心动,那也许才是我的最大价值所在。我更为认可,诗人这个更为真实和可贵的身份。尽管在生活中,它总在有意或无意间被回避或隐匿(其实,在诗人不能成为某种职业的今天,很多诗人也都有类似的内心挣扎和彷徨)。我是一个腰间佩剑的人。我的佩剑本是一种装饰,或者身份的证明,但我确实常常在用它杀人,征战杀伐。其实,在诗与剑之间,我更愿意用诗来表达,而不是剑。作为一个诗人和评论者,我希望写出更多像南音那样的诗歌,并为朋友出写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诗评。也许,我在等待着“功成身退”,或者,“兵败溃逃”。我希望退隐江湖。
在写南音诗评时,我得以面对自己的心灵和人生,我看到了自己。在教育上,有“教学相长”一说;其实,在诗人和诗评者之间,同样存有这样一种关系。这是我此次写作的最大收获。
15
这样的诗评,只能是对诗人及其诗歌的印象式批评。但我希望,这里面有着真诚,真情,以及灵性的东西。
如果再次与南音在大街上相遇,如果她不喊我的名字,我不确定是不是还能从人群里认出她来?对我来说,这仍然是一张陌生的脸孔。但我对她又是多么熟悉啊,她的忧伤与沉重,内心的孤独与苦难,我竟然有如此刻骨和亲切的体验。通过她的诗歌,这些桥梁、河流或者隧道,我在某种程度上抵达了她的心灵,那是一个唯美、诗性、忧伤、哲学的纯净世界。
我认识了她,一个叫南音或毛新的女子,认识了她的诗歌。这是偶然,也是幸运。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她,认识她的诗歌。同时,我还希望她写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诗。
也许,这才是我写作这篇评论的初衷和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