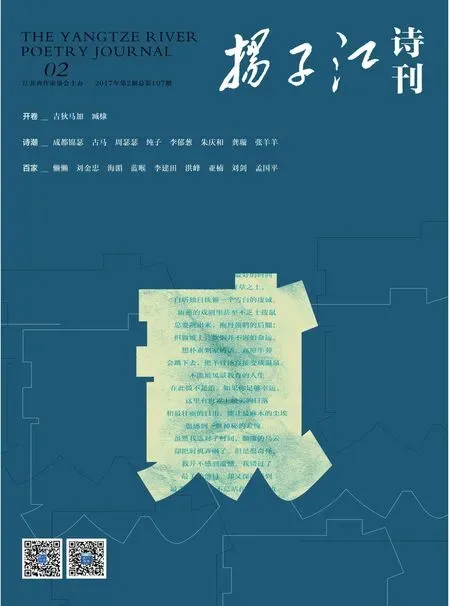从内心出发(组章)
杨胜应
从内心出发(组章)
杨胜应
杨胜应,苗族,1980年11月生于重庆,居四川南充。
落 叶
盛满阳光的树叶,撼动了黄昏。
但跌落不是落叶独有的,还有远处的太阳。整个大地不断地暗淡下来,包括雅江的山水和人。不知道是哪位高高在上的神灵,把秋风当优美的经文在诵读。每吐露一字,人间就荒凉一分。
这不是一枚枚绝望的字。亲人们早已修炼有术。
牛羊进圈,铁器上墙,还有灯盏在餐桌上释放光芒。还必须得提及灶膛里的火焰,那左右图腾依然脱离不了桎梏的比喻。唯有鲜美的素食和缭绕的炊烟,才能够把这种卑微的在场感扩散。
我就是被炊烟喂养的人。
知道落叶的心。落叶并不以明亮在枝头而骄傲。它们更愿意落到人间的低谷,成为蚂蚁棺椁的一部分。它们覆在大地的表面,像一件遮羞的衣衫。
每解开一枚纽扣,我就会痛失一位亲人。
白 云
白云在山巅啃草,溅落的露水更像亲人的泪滴。
伤心和绝望成为故土唯一滚动的风景。我渴望有一条长鞭,把羊群全部赶到蓝天上去,还人间一片雨水,滋养亲人们焦渴的心。
是的,我需要缝补父母身体上的裂纹,让他们的肌肤像春天的原野那么光滑平静。
但羊群全部都去了天上。我的忧心却填补不了人间的荒凉。
如果能够有一阵暴雨,把所有的云朵都落到故土。亲人们就会获得流动的比喻,并欢乐地截取、引用。父母的微笑,一定会成为辽阔里最轻柔的。超越五谷杂粮,超越人间灯火和清澈、宁静成为生死兄弟。
这时候再说到羊群,一定都是走动的快感。
它们高于村庄,成为我远观的塔尖。它们的颤抖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它们的消失一定连接着我的生命。真的,为了那最后的一声咩叫,我愿意把雅鲁藏布大峡谷挪移到身体,成全悲伤一词。
覆 盖
我的故乡,山多,风拐来拐去地吹。
亲人们就像一枚枚无根的石头,在山峦中转来转去。再重的担子,也无法让他们站稳脚跟,一路踉跄,一路颠簸,一路摇晃,故乡是一个随时可以葬人的地方。
多么让人劳累的地方啊,铁器永恒地发着光,就连草木都看不下去了,想牢牢地抓住亲人们的双脚,让他们慢一些,再慢一些。但怎么可能阻挡得了大家朴素的真理:如果不努力,土地就会荒废,如果土地荒废,庄稼就没有生机,如果庄稼没有生机,我们从哪里来那么多活着的机会。
所以,风再怎么吹,亲人们都会成为我们远离故乡的引路人。一步一个脚印,流血流汗也不叫苦叫累。走,再走,走着走着就是一辈子。
这无限的死亡和有限的生命,我们必须赞美,必须为这样的存在说出更多的旋涡、灰暗、迷茫,必须用更多的青山绿水虔诚覆盖。
与槐树有关
小时候唯一在上面数过蚂蚁的那棵槐树。
古老的槐树,用皮肤制造了无数的洞穴。蚂蚁住在里面,有被风吹动的房舍。
母亲经常站在槐树下喊我,喊不回应,就骂我。声音传到大山的深处,峡谷把声音扩大无数倍,却不告诉母亲我的去处。这被重复的声音,也是被风吹散掉的。
等我回来的时候屋顶已经释放出炊烟。这呛人的烟雾,淡蓝淡蓝的,像母亲用过的绸缎。多少年为了脚下的土地,母亲把它们藏在柜底。深深的,有着大海的呼吸。
如今槐树不见了,蚂蚁回到地上,有着潮湿的去处。
母亲久居老屋,有着灯盏照明。
每一个黄昏,所有的影子都有接地气的焦点;每一个夜晚,越是细微的光越带着纯纯的暗香。
老 屋
像老人一样,老屋们一栋接一栋地靠在一起。如果不是那个姿势,它们就会同时倒下,像人一样,失去了身体,丢掉了灵魂。
苍老、残破、倾斜,是寨子里最具民族风情的风景。谁能够在经过它们的时候,仰望它们的时候,深入它们的时候,能够发现,落日每天也在经过它们。
用瓦片遮盖的屋顶,以前是鸟雀站在上面,现在是枯萎的树枝积压在上面,一层层的。鸟雀来了,每一次都会带来细微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最后的吟唱,缓缓地抚摸着寨子里最后的人烟。
被反复想念,反复赞美,反复虚构的老屋、炊烟、鸟雀、草木、路径、家禽、稻草垛、栅栏,还在低低地发着微弱的光。
不妥协,不照耀,只逆向。
也许,存在就是证据。
想 法
麦子已经含泪退出舞台。
空出来的世界,需要一种不断膨胀的事物填补。
玉米,或者叫她苞谷。亭亭玉立、葱葱郁郁。一株连接着一株,把故乡打开成海。但我不能够说鸟雀是溅起的泡沫,而是热爱中的真诚。她随时落下,都能够落满那些贫瘠的土地。也许,这就是唯一的奢华,已经低调成伤。
颤抖依然属于群山的。牛羊在上面啃食自己的隐喻。除了蓝天还高悬在头顶,白云已经落地成为最近的暗示。亲人们仿佛唯一的欢悦之词,一会儿属于个人,一会儿属于全民。
当气候越来越热,我曾经有那么一瞬的想法:“故乡虽然一直高于流水,但她也不断地低于真正的蔚蓝。”
允 许
允许风是从内心深处暗藏的缝隙里吹出。
每种被吹动的事物,都是诵读的经文。
麦子是泪水,稻谷是汗滴。油菜、大豆、高粱、玉米,或者苞谷、红薯等都是获得存活的恩赐途径。在故乡,允许留守成为山清水秀的污点,允许鳏寡、遗孀、孤儿等被反复命名,允许他们在春风里摇曳,成为祈祷声中的安稳或者断句。
允许春风对他们的清点和检阅,允许雨水对他们的浸泡和清洗。
他们是一群,属于地方保护的对象,也属于中国特色化的公民。
我爱他们的挣扎、泅渡,甚至是死亡和消失,都不曾远离过自己的祖国。
我爱他们的绝望、惊喜,甚至是热烈和悲伤,都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
麦 子
一株小麦就是一个家庭,每个家庭都人口众多。
能够得到祖国允许,一定是得到政策保护的少数。
请允许我在这里使用民族。
父亲是土家族,母亲是苗族,我们几个兄弟,如何定义都可以。
小麦,大概是父亲的长辈的长辈遗留之物,父亲深爱着,汗水流在身上,忠诚在体内像骨骼那样组建结构。
母亲爱上父亲,像草木爱上了土地,尽可能地反射着所有向上的光明。
有时候是阳光的,有时候是月光的,那动作,那声响,我感觉得到,只有到了五月,小麦才因为麦子抱在一起而诞生。
所以说,麦子的含义是向自己低头。
因为沉默才显得强大。
照 耀
不断赶路的落日,照过每一寸天空,云朵,鸟雀的背影,也照过每一座山村的峰峦,树冠,辽阔的草地。
被照耀的事物,会反光的事物,抓紧自己的每一寸土地,释放着自己的每一种颜色,让乡村妖娆,美丽,让劳作的人像一个被温暖捧在掌心的神圣的瓷器。
这些瓷器,构成了整个村庄的关节,截住河流的浪花,引出大地深处的秘密,让草木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芬芳,让所有的田园开满花朵,漫无边际地向人间延伸。看不见的流动的美啊,需要眺望,踮起脚尖地眺望。
被反复赞美的人和事物,被反复浪费的珍贵时光。因为照耀,而让人想到了远行的丈夫,苍老的父母,以及铺天盖地低下头的麦子和还在拔节生长的绿油油的玉米、泛着金光的稻谷,它们在感恩照耀的时候,祈祷新生。
这些细小的孤独,总是成片成片地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