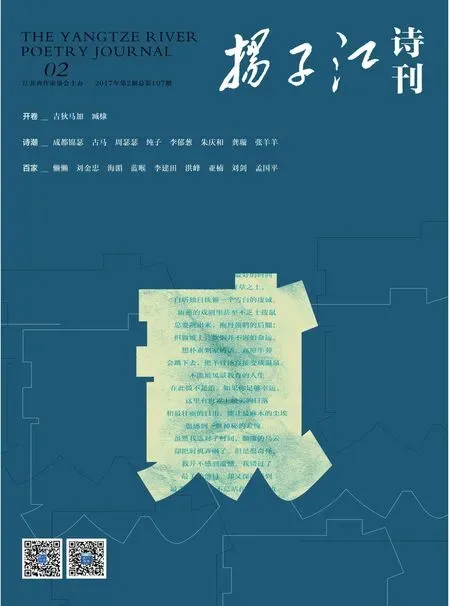蝴蝶梦(节选)
潘云贵
蝴蝶梦(节选)
潘云贵
潘云贵,1990年12月出生于福建长乐,居重庆。
一
噪音是容器,溢出,如脱缰野马,在时空维度上乱窜。
遥远的过去被凿出豁口,光线汹涌,注进绵长静脉,夹杂众多陌生音阶,如巨雷,滚向低处。
狂风疾走,海水翻涌,潮湿粗壮的长发,一根根冲向高空。鱼贯而出,翻腾着暂时臆想
的自由,又簌簌入海。
长风呼啸,海面狂澜加剧。黑色巨物哗然跳出,遮天蔽日。
鱼目圆睁,光芒四溢,日月羞赧,躲进云中。
北海之鲲,再次苏醒。周身摇摆,化为大鹏。振翅奋飞,翼如垂天之云,三千里水域镜面欲碎。风将汪洋掀翻,海浪咆哮,溅向穹庐。
一颗明星降落鹏顶,析出锋芒,幻化成人:黑发如墨,剑眉如峰,眼神笃定,宽衣素袍,衣袂飘飞,仙风道骨。
庄周骑于鹏上,拂尘一挥,烟云四散。
鹏扑展两翼,抟扶摇直上九万里,钻入时空的伤口。瞬间失去踪影。
天地被光吞噬。
时空另一面,雷声大作。
寄生在暗中的人孤独老去,时刻想摘取耳朵,选择一种静默。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无法忍受众声喧哗:那些声音,无休无止谈论房价、工资、婚恋、疾病的声音。
与之对抗的声音:山风在喊,牛马在喊,秋天落下的果实在喊,阵阵战栗的屋瓦在喊。
所有声音绕成漩涡,在深夜模拟海浪。涛声很旧,存在多年,痛却一遍一遍历久弥新。
庄周站在鹏上,俯瞰世间。
城市用金黄的暴力推翻贫血的土地,并吸食稀薄的膘。
雾霾如霜雪,凝结,降下,覆盖屋顶,露宿的动物被多重危险围困,屠宰。
流水的皮肤是黑的,没有纹路,像涂满油漆光滑的棺木。
鹏被阻截在摩天大楼的顶部,无法降落,像即刻要被塔尖扎破的气球。
飞机呆滞地飞过,两边机翼像刀子割过它的腋下,有灰扑扑的恨撒落。
无数人在事不关己的疼痛中酣眠,进食,如被运输的牲口,往返于橡皮擦随时抹去的航线。
自由只用于歌颂,不被实践,影子返回镜面,时间像蝉死去的壳。
庄周目光黯淡,他和他的鹏,落寞杵在天地间,失望,孤独。身体越来越小,有接近绝望的轻。
一只蝴蝶飞落。
三
蝴蝶这时醒了。
它周身发光,张开双翅,撒下金粉。
一粒粒——
与俗世的金黄截然不同的色泽,晶莹剔透,像纯净的雪,安抚我燥热的肉身。
我感到一股冰凉潜入体内,中和欲望的心火,灵魂顿时得到舒展,仿佛后背抽动着也要长出翅膀。
我睁开双眼,蝴蝶恣情舞蹈,像黑暗中的焰火,明亮,耀眼,却生生不息。
它突然飞往窗边,张望外围世界,并用力撞击玻璃。
噗——噗——
我急忙起身,打开窗户。
它撑开翅膀,像一对眼睛,看我一眼,便向外飞去,迎接自由与希望。
金色粉粒,一点点撒下——
每一颗尘埃都被点亮,每一寸空气都被净化。
黑夜被镀上一层层金光。
蝴蝶远逝,成为一个光点的刹那,闪电急促划过,雷声大作。
天空蒙上牛皮,有巨锤敲出沉重鼓点。风起云涌。
行道树摇晃着头颅,大雨落下,势如破竹。
人们睡在高楼竖起的石碑里,像麻醉过的羊群看不到死亡。
城市是一艘沉船。
哗——哗——
成群鸦雀从公园里、电线杆上、居民楼的阳台中、钉子户的屋檐上奋力冲出,得到诏谕似的飞上血红色的苍穹。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程晓驾车打瞌睡的事时有发生。2009年2月14日下午6点,程晓从电子厂下班后往电脑城赶,一揉眼睛就撞着了一个抱着玫瑰花去见女友的年轻人。好在凯迪拉克性能卓越,程晓轻点刹车,就稳稳地停住了,车头只是轻轻碰着了对方,并无大碍。对方却眼红他开着名车,说他是耀武扬威的富家公子,要砸他的车。凯迪拉克是程晓的命根子,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拉扯。“开着豪车撞人还行凶!”对方纠结了一伙不明真相的人把程晓打得鼻青脸肿,还砸坏了他的车灯。
巨型飞行物移到城市上空,突然张开宽阔羽翼,尖嘴啄着城市的塔尖,瞬间轰然倒塌。
大风在耳边刮出哗然声响。
人们依旧沉睡,丝毫感觉不到仙人的降临,像规避自身的丑陋、虚假、羞愧和不堪一样,规避黎明的到来。
信仰清瘦的时代,江山是易碎的瓷。
大鹏挥起两翼,飞行在时间的经纬中,步步惊心。
人类在哪里?
大雨淋漓,庄子濡水不湿,骑在鹏上,手持拂尘,重复斥问。
顶天立地的象形被一一肢解,抽空。
金、木、水、火、土,悬空,破灭。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藏在林立高楼里、灯火阑珊中的数据、字母。
一排排,一行行——
没有人形,没有血液,没有祖籍,没有历史,没有自由,没有未来。
比蟪蛄更渺小,比朝菌更微茫。
人类在哪里?
庄子衣带扬起,长发散在风里,丝丝摆动,落上白霜。
大地依旧回答空空。
在哪里,在哪里……
他撂了撂被风吹白的头发,面容一瞬间老了,心系苍生的他继续问着。
大鹏嘶鸣,青山沉默,河流汹涌向前,汪洋大浪滔天。
人们集体失声。
我此刻不再是风。
我扯起喉咙,努力嘶喊,但声音始终无法从口中挤出。
原来世界也没有给予自己说话的权利。
风呼啸着,雨哀鸣着。
尘寰低垂,即刻覆没。
人们在酣睡中继续被捆绑,蒙骗,面对外围世界仍然一无所知。也有人,在梦中走向深海,选择最寂静的死亡,没有伤口,笑靥苍白,灵魂在水面前行,要去远方旅行。
我飘向雷霆,闪电成为阶梯,一级级危险此刻成为可触碰的行板,我踏响,轰——轰——,时间的琴键发出拙劣的乐声,像一个又一个吸烟者爆裂的心肺。
庄子叹息,甩动拂尘,风雨即止。
光又渐渐析出,照亮现代文明筑造的空壳和废墟。
他骑着孤独的鹏,绝云气,负青天,离去,离去。
我……在……这……里……
被取走喉咙的木偶只能把话埋在心底。
时间把圣人的背影,吹成模糊的光。
四
醒来后,蝴蝶已飞走。
枯枝上的灰烬,模拟雪,降落。
把真相用旧的人,有一件漏风的衬衣,抵挡不住虚无的寒潮,摇晃倒下。
命运给予我们看不清的谜面。
现实与梦境,位于镜面两边,逐渐失去边缘。
繁荣的一天里,秒针、分针、时针,拖着虚影转动。白光四下流窜,逮捕所有倦怠的眼皮。
吵闹的街衢、马路和超市,依旧传来气球、轮胎、喇叭、广播、孩子和妇人的噪音,像陨石和子弹撞在耳膜上:
哧——哧——
这些耳目被真实与虚幻挤压,堵塞,人脑没有多余内存,任由直觉横行世间。青红皂白肆意涂染万物表皮,主体叙述代替共识和真理。
我是什么,白马非马,鱼在飞,鸟在游。
经典古籍放在图书馆里老去,历史物件藏在博物馆中生锈。
无人问津,只有尘埃驻足、怜惜。
人们各怀心事,各奔其途,无人注意谁在迷路。
少年们坐在课堂上热烈讨论明星长相,青年们忙于事业和爱情焦头烂额,老人们在敬老院里以流言蜚语、桥牌麻将静候无常。
平板电脑、手机、微博、微信充斥耳目,器官被绑架,以地球主宰者自居的人类逐渐沦为电子奴隶,不辨是非,毫无自知。
谣言止于智者,但智者早已失踪。满街都是昏睡的人、疯子和傻子,人人眼神浑浊,无人眼中笃定。
漏洞百出的躯体掉出太多善,赖着太多恶。
日月星辰像精美的布景罩在头顶上方,城中村像无人认领的孤儿在寒风中战栗,广阔的原野山林被推平成卫星城区,地平线被倾倒在越来越远的地方。
未来像一匹马倒下,世界还是一副空空的壳。
虚拟操控当下,实物失去意义。
我们和自己聊天,仿佛在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通话。长久的沉默在线路上生长。
人类活得不像自己,像穿着皮囊的机器、数据和纸片。
被挖出一个又一个的洞,埋进一颗一颗的炸弹:
嘀——嗒——
我想起老去的庄子,在暴雨中掷下的问句,如天鹅无法掰直的脖颈,滞留在人世混沌的湖面。
人类在哪里?
人类在消失!
离开可信任的母体,迷失在对现代文明的无限崇拜里。
没有祖籍,没有历史,没有自由,没有未来。
人比蟪蛄更渺小,比朝菌更微茫。
我们闭口不言,在巧舌如簧的镜中照影。
五
轰——轰——
冬夜响起巨雷,雨水穿过鸟群的脊背,如铁屑飘落。
被锈蚀的城市裸露出红色的肌肤,高楼是一块块软化的饼干。
岩层的骨髓被逐一抽干,海水从地下通道溢出,倒灌进人们的心脏。
时间盛着雨声,排向沉默的耳朵。
医生用听诊器听到魍魅魑魉吟唱,透明的伤口被蘸满碘酒的棉团擦拭出红色的眼睛。
我们活在充满虚词的城市,像在高空飘荡。
返乡之途越来越窄。
零点钟声响起,我们在夜的水上漂浮。
有人失足,结束路途,冰冷的掌纹盖着尘埃的被褥。
我接不住沉重的生活,我只能接住高处落下的阴影。
电热毯、被褥、热水袋温暖身体表面,孤独的内心,在无所适从中继续冷酷。
我钦羡在时空维度上穿行的人,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
我盼望庄子御风而来,重返世间,给我一颗自由的心。
他会再来吗?风声鹤唳,前程往事皆已风尘仆仆。
当他降临,又望见未来竖起一片乌有之乡,像块墓碑,基底万物聚拢,堆积:烟草、手机、身份证、交通卡、鞋靴、螺丝钉、报废的汽车、玩具、烂尾楼、化学制剂、转基因粮食、核电厂、癌症……密密麻麻呈现,像毛囊密集、突起的头皮。
烈焰只有火没有焰心,水果只有皮没有果肉与核,人们拥有肉身,没有灵魂,只熟悉单音词的词,铁锹撬出躯壳中多个自我,弱懦者受振奋,羞赧者获激励,节制者生欲望,贪婪者得餍足。
虚实没有边界,真相屈服幻景。
一个人连疼痛的位置都无法准确说出。
呼——呼——
风自窗外吹来,隐隐间,又看见金色蝴蝶。
它张开双翅,周身发光,并在两翼扑展间撒下金粉。
像黑暗中不灭的焰火,明亮,耀眼。
牵出月光,如丝如线,缠绕,缝合破损的楼宇、瓷器和陶笛。
蝴蝶停在一匹白马上,迎面奔来,穿过我身体中的尖利、木楞、苦楚、冲突、彷徨、迷离、感伤,流下一滴泪。
我的后背抽动着,抽动着,身体愈发轻盈。
一根根刺被拔出,随即,噗——
长出翅膀。
时空的甬道对我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