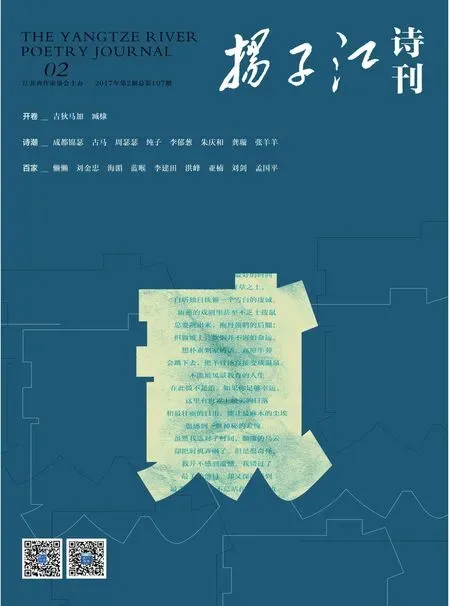黔西北记(组章)
徐 源
黔西北记(组章)
徐 源
徐源,男,1984年生于贵州省纳雍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营上,时光磨亮的古寨
重叠的人影,厚不过一本《平远州志》。
薄雾挂在碉檐上,露水做的村民,站在单薄的阳光中。戴明贤先生书写的对联,被刻入白色的石头,新修葺的刘家大院,还是大院,只是朝代衰亡,只是我来晚了百年。
老宅安详,柱头上斑驳的光阴,没有姓氏,野风自来自去,好像一种反讽。
走到寨子中心,遇到了古老的人,用针线挑理古老的炊烟,深邃的皱纹,谁也读不透。
每条小路,有自己弯曲的方式。石阶光滑,树影婆娑,沉醉于记忆。这一切,没人愿意提及人间。
向前,寨子尽头是悬崖,崖下有广阔的油菜田,菜花已开,仿佛金色的音乐,在山间漫延。许久,我心如蝴蝶,被清风送来的芬香抱紧。
瓦片收拢翅膀,睁着惊讶的眼睛,揣测我此生归宿。在营上,每个人终会陷入一场幻象。
我的呼吸眷慕草叶。阳光,被收入了新的县志。
德溪大桥,读旧信笺
左边是乾隆元年,搭建在辰科进士路元升的肩上,那时天下太平,朋友安好。右边奔跑着霓虹灯,在草木的根部萌芽,或泅渡,这时天下也太平,朋友们去了远方。
朋友们去了远方,大地便空了。我在桥上踱着步子,直到桥听到了我内心,涟漪般的孤独。
我在这座桥上遇到过一位女人,她从阳光里出来,又走进了阳光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知道我此刻,蒲公英般的愿望,像一首绒绒的小诗。
许多日子,我每天来到这里,打磨这座桥的骨骼。许多年后我把它的曲线赋予祈祷,直到黄昏,爱我的人不再回来。
爱我的人老了,我把彩虹挂在黑夜降临的地方。
静默,是一种态度。任凭德沟春景三千,任凭德溪美人三千,终不抵岁月的烟尘,亘古之美。终不抵桥的曲直,让我有了拨动竖琴的冲动。
时光,把我的影子,画在信笺上。窑酒于岩石根部,春鸟吟诗。只有回忆,读懂了历史;只有桥,读懂了流水。
韭菜坪,韭菜花里的高原
韭菜坪有多高,问一问衣袖下流淌的风便知道。一伸手,便触到天空滑溜溜的蓝;一踮起脚尖,便吻到云朵软绵绵的心事。
韭菜坪有多广阔,最老的人也没丈量过。呼唤——所有的山便从远方蠕动而至;所有的雾,便从脚下瞬间升起,缭绕于过去的空间。游人驾雾而行,这时的韭菜坪,便是天上一日,人间百年。
是的,韭菜坪有多美,看一看阳光照耀下,忘记吃草的羊群便知道。羊为神灵,变化莫测。
在韭菜坪,如果一朵韭菜花,在赞美与倾慕中,不能与你长相厮守,那么无边的紫色呢?浪漫的紫色!执着的紫色!仿佛你的未来也是紫色的,仿佛你的骨头也是紫色的,它们在石头上,绽开芳香。
哦!这便是高原上的韭菜坪,韭菜花里的韭菜坪。
沿着秋天透明的蝉鸣,我的身子,仿佛被风吹成一座,比韭菜坪还空旷的殿堂。
索玛大草原,与神为邻
一只蝴蝶踩着旋律,化作阳光;一匹老马啃着石头,长出翅膀。
凸起的山坡,是绵延的胸脯;凹陷的天坑,是先人干涸的眼眶。
每一朵索玛花都是一首山歌,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场撮泰吉。
风拂着茫茫草原,许多人的魂灵像鸽哨一样,被吹响。许多人的呼吸在《指路经》里,排列成辉煌的城墙。
在索玛大草原,与神为邻。千年前的山鹰在千年后的仰望中擦净黑暗,千年前的火把在千年后的膜拜中镀亮胡须。
一个人呼喊,要一千年后才能听见;一个人恋爱,要一千年后,才能醒来。
整个草原,像一只牛皮鼓,轻轻一敲,便把空旷填向了远方;整个草原醇厚得像一杯咂酒,抿一口,方知岁月如歌,此生爱恨,为浪漫尔尔。
我在清晨走进索玛大草原,最后在月亮上,顺着月光走下来;我从尘埃走进索玛大草原,最后在虫豸的喉头,沿着歌声走出来。
牵马的姑娘,像一把月琴,而我正被夜色浸染,吞噬。许多年后,她老了,她看着我,她在花香里,不愿意离开。
路氏翰林山庄,一只熄灭的烟头
岁月被风雕刻在木板上,光照耀荒草,也照耀内心的感动。
等我们的脸泛黄了,等纸张上的文字,变成歌唱的碑石,或手杖。
《路氏宗谱》上滑落一个安静的时代。
一门五进士,三代三翰林。回不去的辉煌,叫做文化吗?
我猛吸了一口烟,咀嚼山庄残败的影子。风吹着我的脸,把烟头扔在尘埃里,它那样安静,与我对峙,像一座小小的废墟。
阳光再次遗忘皱纹里的悲欣。
汗血宝马
在风中饮血,身体里沙粒蠕动、摩擦,从毛孔里溢出火花,把远方蹈成一条地平线。
沙漠,终于敞开了女人般宽阔的胸脯,落日骑在我的背上,英雄热爱渐暗的霞光。
从马骨上取下铜的回声,铸一把宝剑,杀敌无数,谁的心中没有理想?日行千里,追逐日月更迭。我就是速度,王朝被甩在蹄印之后。
那就在河边饮水,整条大河聚拢在喉头上。
许多年后,舔马汗的人死了,说马语的人死了,仰天长嘶,闪电、雷雨、黑暗,降临诗篇中。从潦倒中掏出才华与昔日的辉煌,为马写诗的人也死了,为马守身如玉的人也死了。
悬崖勒马吗?悬崖是我陡峭的背脊;天马行空吗?天空是我呼啸的校场。风沙在响鼻中,唱楚歌的人,眼眶里流出粘稠的月光。
一匹马的骨骼,可以建一个王国;一匹马的血,可以养活一个时代。卸掉马掌,重新钉在火焰上;割下马尾,拉响一把沙哑的二胡,我在琴筒里,江山忍受声音的分割。
就这样,一匹汗血马,活在英雄的宝剑上,死在艺术的礼赞中。
啊!以画马为名的人成了大师。画马的皮毛,画马的骨骼,画马的精神,但是他从没有画过马的灵魂。我在你们的内心里,没有谁能摒弃肉身,见到过真正的自己。
天空在远逝的马影中,被镜头推向模糊。只有摄像师,能捕捉每一次诅咒。
樱桃雪
河发源于樱桃花蕊,听水,流淌旋律,只有鹅卵石藏匿芬芳;桥沉默生死轮回,看风,打开春天,只有固执的樱桃树,挂满白色经文,面对大千,洁如菩提。
樱桃之心,走不出的命定乡愁。
放眼,白色的风,白色的阳光,满山之白,安静、舒畅。被樱桃花赞美的人,那些尘埃之骨,在春色中也还原了干净的白。
古典之白,雅致之白,无我之白。拟一片白,作信笺,写信给没恋爱的远方。抚摸白宽敞之心,人间在一朵雪上,没有岁月。
多年前,赏花的人,从身子里取出自己,置放在枝头。无数白色的小宫殿,在三月沐浴音乐。总有一朵樱桃花,能准确叫出她的名字,总有一张亲切的脸与昨日重叠。也总有漫长的人生,被它们映照。
三月,抒情漫过人间,给影子镶上银边。呼唤在山间化作鸟鸣,它有多洁白,春鸟之音就有多清脆;步履在夜晚化作星辰,它有多芬芳,星辰之语就有多少滑落至梦境。
你还在等待什么?在这里,十里春光,借花献佛,还是借花还魂?
樱桃花开,行走大地的我们,放慢人生,掬水,在河边清洗眼睛。那些没有根,漂浮于天空中的云,多么希望降落在一朵花上。扯风,晃荡着阳光,编织故乡。
最初的樱桃树,被光荣地称作:母亲树。三十年,仍繁花似锦。它的子孙千千万,它的功名万万千,香飘大江南北。它老了,明年,就要安静地死去,化作一缕花魂。
你再也看不见它,但它却可以,慈祥地看着你在人间,绽放如一朵有梦的樱桃花。
回忆美吗?感恩美吗?人间美吗?三月过后,樱桃初成,活如春天之眼。对峙,谁也读不懂岁月深处,我们被风雨侵蚀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