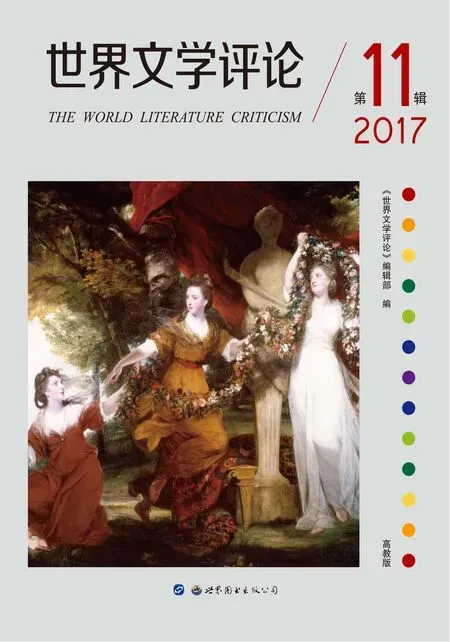游戏化的荒诞与无奈
——论《逍遥颂》的狂欢化
徐天娇
游戏化的荒诞与无奈——论《逍遥颂》的狂欢化
徐天娇
《逍遥颂》是著名作家刘恒的一部极富实验性的长篇小说。本文应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时代背景、生存空间、性幻想三个方面揭示了一群孩子颇具狂欢化色彩的言行背后所蕴含的追求平等、自由、反权威的精神。
《逍遥颂》 狂欢化 时代背景 生存空间 自由
Author: Xu Tianjiao
is from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引 言
刘恒是“新写实”的代表作家,《逍遥颂》是其应《钟山》杂志之邀,响应“新写实”而作,但文本却一反以往“新写实”的风格,试图站在新的角度和高度上创造一种新的风格。这是一次大胆的实验,刘恒尝试从时代背景、人物言行、生存困境等方面去组织构建文本,同时也坚持了“食色,性也”的一贯创作主张,对“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小说中很多场景的描写都体现了狂欢化的手法,虽然这种狂欢化还是比较简单的、外部性的,但是人物的语言对话具有激发、挑逗的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了狂欢化自由平等的精神。
首先,从小说的题目来看,读到“逍遥颂”,我们也许会想到庄子的《逍遥游》,认为这应该是一篇对“逍遥”的颂歌。但阅读后才知道原来是一群孩童,他们在压抑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着无聊的游戏,人物之间互相攻击、谩骂,都想从对对方的辱骂、贬低中获得一种快感。从小说内容本身我们看不到任何“逍遥”或者“赞颂”的影子,从而与题目“逍遥颂”形成反差,而在这一庄一谐的反差中,奠定了全文的游戏基调。如果进一步分析文本,又似乎可以挖掘到小说中蕴含的自由逍遥的精神。这群孩童被社会抛弃的同时也恰恰摆脱了相应的社会规则的束缚,废弃教学楼里的环境又相应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被外界所干扰的自由舞台,虽说黑暗封闭,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
一、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的狂乱无序
席卷全国的十年“文革”带来了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的颠倒混乱,理性的丧失导致大众心理上的狂躁暴动。虽说“文革”并不是巴赫金所描述、构想的狂欢节,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会发现这场政治运动牵动着全国上上下下的百姓,他们爆发出空前的热情,有组织但逐渐失控地进行各种游行、批斗,上演了一场场具有“脱冕”“加冕”意味的闹剧,这闹剧又是没有固定舞台限制的,它随处可见,是人们无从躲避的。巴赫金说过:“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进行当中,除了狂欢节的生活,谁也没有另一种生活。人们无处躲避它,因为狂欢节没有空间界限。”由此观之,“文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狂欢节的色彩。
狂欢节源于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节日宴会和游行表演,是在神学权威统治下,和官方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对抗的力量,其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文化转型的主导,与一元中心权威相对抗。那么联系我们中国的“文革”,当时实际的日常生活是严肃紧张的,人们也是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游行、批斗的。但反观这一历史时期,就会逐渐认识到事件本身的荒诞性,也会逐步发现这一特殊时期人们的游行、批斗似乎也是一种冲破既定秩序后的自我解放的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时空的特殊性,《逍遥颂》的文本便具有了一种张力,“狂欢化”精神与“文革”时期受领导、受制约的生活方式互为表里,在“狂欢无序”与“严肃正统”的二律背反中又相互生发。
当然小说文本所蕴含的狂欢化手法,不仅与“文革”这一特殊时代有关,也与作者创作文本的时代有关。《逍遥颂》创作于1989年,已初步具有90年代文学的影子。新启蒙是80年代精英文化的重要话语资源,而在90年代,大众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逐渐取得合法地位,并且逐步消解着80年代的精英文化,身处文化转型之际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困惑和迷茫的境遇。《逍遥颂》也许是作者借以摆脱自我困惑迷茫的途径;另一方面也许离“文革”时间太近,以致作者无法以超然的态度去讲述。那么结合《逍遥颂》文本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作者自身的创作背景,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文本,从而从文本表面的“严肃”与内在的“狂欢”的对比冲突中挖掘出蕴含的讽刺意味和追求自由的内涵。
二、狭小空间孕育出无聊荒诞言行
小说文本一开头就是“走廊里没有光”,接下来又讲到三一九寝室“屋里十分纯粹,黑得令人头晕”。紧接着是主人公们的亮相:“门后两位在下跳棋,窗户右边有人躺着看书。窗户左边的铺位上搁半个身子,另外半个身子斜倚在窗台,正在往地面瞭望”,仅从这些语句来看,似乎都很悠闲自在,但想想那令人头晕的黑,便感到荒诞滑稽了。虚拟的战争生活状态又使主人公们的行为就像进行一场“扮家家”的游戏。小说中的“总司令”“宣传部长”等严肃的头衔与滑稽的行为与令人头晕的黑结合在一起,又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狂欢色彩的结合。“文革”期间,人们的行动是严肃认真的,甚至是怀着崇高信念的,但是在今天读来却令人感到荒诞滑稽,时空的差异造就了这种新的阅读体验,再加上作者有意识的夸张,我们感受到的便是当时人们的疯狂可笑。那么现在看来的“狂乱无序”与当时的“严肃正经”就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达到反讽的效果。本文正是立足于这种反差来分析文本中的狂欢化的。
小环境的压抑、大环境的感染使主人公们似乎如小丑一样,进行着各种滑稽表演。但最主要的是这群主人公狂欢处世的态度使人物之间的距离拉近,一切事物都进入一种狎昵交往的地域。这群主人公远离了社会道德规范和正常秩序的制约,在几乎没有外界干扰的空间里形成了一种狂欢化的群体。
这个狂欢化群体,在缺少正确价值观的指引和正常的生存环境的境遇下,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如副司令时时想寻找机会把总司令拉下马,也就是对总司令进行“废黜”。最终,副司令如愿从总司令手中夺得收音机这一权威的象征。两人接下来进行的对话虽然在强调时间,但本质上是在弱化“时间”这一概念,在三一九(这已然是一种特殊境遇),空间和时间其实相对弱化,突出的是人物的一个个行为动作。接下来醒了的宣传部长和被副司令一一唤醒了的其他人,都目睹了总司令的丑态,并且对他进行攻击。最终总司令拉稀了,成了众人嫌恶的对象,其象征的权威性也相应得到了破坏。成为嘲笑对象的总司令似乎成了巴赫金分析拉伯雷作品狂欢化时提及的被废黜的国王,“国王就是小丑,他是全民选举的,然后,等他在位的时刻一过,他又受到全民的讥笑、谩骂和殴打”。这里被“废黜”的总司令,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人们对他的讥笑、谩骂,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权威的戏谑与反抗,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是大众文化试图与官方文化形成对峙格局,从而凸显出大众文化自身的价值。
上面分析的是狂欢节的“废黜”场景,接下来我们分析另外一个场景:
这群疯狂的孩子在抓住医科大学生时,对其进行殴打:俘虏的鼻子被打歪了,上唇鼻涕虫似的挂着两道血污;左眼肿成了一颗青蛋,在手电的光束中看上去,仿佛一只巨大的眼珠挂在前额上;后脑勺上端被薅掉了一大撮头发,露着一块头皮像得了秃斑。
这一段叙述对被暴打的大学生的各个部位进行了描述,可以说是典型的狂欢节式的解剖,并且之前医科大学生似乎还是少女的主宰,现成了被殴打的对象,也可以理解为被“废黜”的对象,当然文本中像这种富有狂欢节解剖式的场景描写还有很多。作者以这种方式描述,一定程度上把文本所描绘的生活看作一种戏剧,其遵循的也似乎是一种戏剧的规则。
以上我们重点分析的是人物的行为中蕴含的比较简单、外部的狂欢化,接下来我们重点分析人物语言(对话)中更加深刻的狂欢化:
“我要首先恢复你的语言功能。你的注意力太集中了”、“你妈……妈……你……” 、“你要放松,心情不妨散漫一点儿。修缮了你的语言功能之后,我要设法恢复你的交流欲望……”、“你,你。你……妈……”后勤部长口若悬河,坚持不懈地对作战部刺激。最终作战部长在给了后勤部长一个大背挎后,恢复了语言能力:“你想逼死我!”作战部长说话的那根纤维焊接成功,突然可以吐点别的字眼了。
两人对话的滑稽性跃然纸上,并且带有一定的广场式的粗鄙、笑谑意味。换个角度,则会发现后勤部长对作战部长语言的“激发”意义。激发,作为一种方法,意味着挑逗、激发交谈者说话,迫使他讲出自己的意见,而且要完全讲出来。后勤部长的激发为作战部长敞开个性与表达思想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样两者才可以达到交流对话的层面。并且作战部长的“三字经”在后勤部长和作战部长之间来回流动,音调和语气也不断加强,这种加强更促进了两人意识的对立冲突,从而营造出一种语言杂多的局面,使各种思想得以表达。
统观整部小说,争吵、辩论几乎没有间断,这种争吵、辩论打破了独白和一元中心的格局。并且这篇小说没有占绝对优势的主人公,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性格和语言,他们的语言又具有一种模糊、朦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展现不同主人公的意识,从而造成一种“众生喧哗”的场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所废弃封闭的狭小环境中,人物的言行极度荒诞无聊,而这些言行又充满了狂欢色彩。
三、无力抵抗中对性的幻想与滥用
《逍遥颂》从根本上来说塑造的是一群孱弱无力的孩童,他们食不果腹,没有方向感,更谈不上归属感,废弃封闭的教学楼似乎是他们自生自灭的世界。后来进入教学楼的老校长,本应是孩子们的领导者,却无力去拯救这群孩子,他对世界已陷入绝望。蓬勃有力的医科大学生也没有给予孩子拯救,反而把这群孩童推向“性”的深渊。
这群无家可归的孩子,虽然以狂欢处世的态度形成一种狂欢化群体,但他们自身其实没有力量抵抗生存现状。本是一群孩童,却在各种各样地折磨报复、自我践踏后,开始通过对“性”的探求、窥视来发泄和自我安慰。虽然我们可以把他们对“性”的幻想和滥用当作对抗社会的一种新的方式,但联系到孩子们从中受到的身心伤害,未免残酷了些。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大家对“性”有不同程度的迷恋,但最终几乎全部坠入“性”的深渊。后来到教学楼的少女与杀死自己父亲的医科大学生疯狂地结合,对“性”不了解却滥用,通过“性”来寻求生命的存在。可以说少女的行为具有极度的反叛色彩,颠覆了社会道德伦理,也不受其束缚。但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中感受少女在“性”中求死的想法,社会的折磨已经使她对“生”麻木而绝望,她把“性”的体验作为对“生”的最好的体验方式,在“性”中寻求满足和快感,她不去理会这种快感付出的代价,最终把自己逼入“性”的腐烂世界。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性”也是新生的象征,女性本身承担着物质化、贬低化和更新生活的功能,那么少女把“性”与死的结合也是一种典型的狂欢节式的结合。
小说文本有对“性”的直接描写,但更多的是对“性”的象征性描写,语言也具有“性”的暗示,如副司令、总司令找的“钥匙”、文本中出现的“棍子”等都具有暗示象征性器官的意思。在巴赫金研究狂欢化的典型作家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和肉体同等——身体本身、饮食、排泄和性生活的形象占了绝对压倒的地位。而且,这些形象还以非常夸大、夸张化的方式出现。同样,作者刘恒也在《逍遥颂》中对身体本身、性生活进行了夸大、夸张的展示,“食色,性也”是作者刘恒一贯的写作主张,在这篇小说中也不例外,小说从开始就有朦胧的“性”的存在,后来对“性”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描写,以至于全篇都充斥着“性”,似乎要以“性”的大解放来对抗强大的保守的力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权威相抵抗的姿态,但这种对抗付出的代价又是无比惨重的。
结 语
纵观小说文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其蕴含的狂欢化手法。一方面是比较简单的、外部性的狂欢化。如作者在文本中描述的很多场景,这些场景要么富有狂欢节式的解剖,要么具有狂欢节式的“废黜”。另一方面,深入文本内核,并且联系作者创作的时代环境,我们可以看出作品本身融入了大众文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反抗精神和自由意识。人物对话的激发性,人物语言的戏谑性,人物行为的喜剧性也反映出人物的狂欢处世态度,这已经悄悄与官方正统严肃的文化形成了对抗,也与一元权威形成了对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狂欢节反神学、反权威、反专制、争平等、争自由的倾向。但《逍遥颂》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毕竟处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环境的自由还是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的,其“逍遥”也就相应地具有了一定的荒诞性,那么这种反权威、反专制、争平等、争自由的倾向也就相对弱化了。
Ode to the freedom is an experimental novel written by the famous writer Liu Heng. Based on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this paper reveals a group of children's pursuit of equality, freedom and anti — authority in their carnival words and deeds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background, living space and sexual fantasy.
Ode to the freedom Carnivalization time background living space freedom
徐天娇,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刘恒:《刘恒自选集》,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3][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4]刘恒:《刘恒自选集》,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5]刘恒:《刘恒自选集》,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5页。
Title:
Gami fi cation of Absurdity and Helplessness — Analysis of Carnivalization of Ode to the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