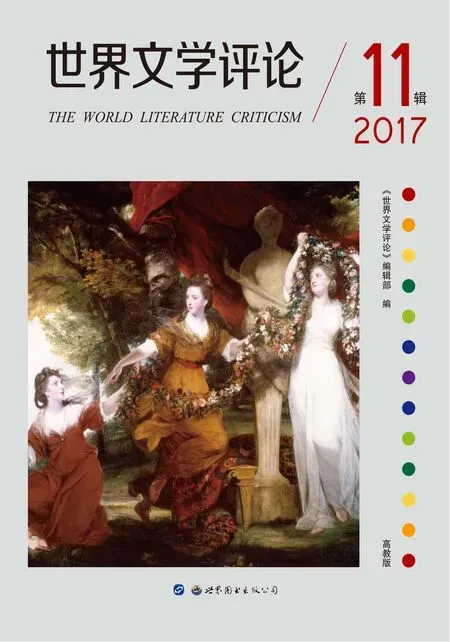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百年新诗
江少川
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百年新诗
江少川
我讲的题目为“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百年新诗”。所谓“海外”,指的是中国以外,指中国大陆、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地区或国家,称作海外。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是不能称作海外的(它可以称境外,不叫海外)。学界有人把台港澳称作海外,将台港澳文学称为海外华文文学,这种提法不对,是错误的。我讲海外华文诗歌,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地区或国家用华文创作的诗歌作品。
海外华文诗歌或者说作家群体当下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台港,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移居到海外的。这一批诗人,比方说,像洛夫、痖弦从台湾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虽然现在回到台湾,但是在海外生活了10多年,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海外华文诗人。第二批就是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中国大陆汹涌澎湃的出国潮中移居海外的,这样的诗人就更多了。这一波诗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与澳洲。第三部分在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是当下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域。不仅第一代移民中的老一代诗人始终坚持用华文创作诗歌,他们的后代,在重视华文教育的国家与地区,如马来西亚,第二代、第三代诗人仍然用华文坚持文学创作,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新生代诗人。散居在其他地区,如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也有为数不少的华语诗人。
海外华文诗歌,是中国新诗的一个特殊构成。是中国新诗的一种延伸,或者说是中国新诗的一种枝蔓、支流,它与中国新诗同源,与中国诗歌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相连的联系,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谈到中国新诗百年成就的时候,也不能不谈到海外华文诗歌。为什么说它特殊呢,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新诗构成了一种互补、互动、交流的特殊关系,给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或者另一种标尺。讨论新诗百年成就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海外的华文诗歌。海外华文诗歌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思考的。
第一,跨域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体验。海外诗人从原乡,即从中国移居异国他乡,面临着身份困惑,语言障碍,文化冲突,族裔歧视等等方面的困惑。他们处在异国异乡文化的边缘、族裔的边缘、生存的边缘。而同时,这种边缘处境也开阔了他们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经验。海外华文诗人从故乡跨向异域,他们拥具原乡与异乡,东方与西方的双重生活经验。置身于异质文化语境,东西文化冲突之中,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身份困惑的处境,给诗人带来一种新的生命体验,而这些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得以最集中而形象、生动真切的表现。给人一种新的审美感受。为华文诗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乡愁”是中国诗歌古老的母题,但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对故乡、家园的思念在诗中却表达出一种别样的生命体验:
旅居菲律宾的诗人云鹤有一首短诗:
《野生植物》
有叶,却没有茎
有茎 却没有根
有根 却没有泥土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名字叫华侨
一首小诗却承载着巨大的生命重量,表达了海外游子,无根的一代人漂泊异国他乡的孤独无依感与远离祖国、失去故土的痛苦思念之深情。
旅美诗人非马的一首《醉汉》同样感人至深:
把短短的一条直巷
走成一条曲折的万里愁肠
左一脚 十年
右一脚 十年
母亲啊
我正努力,
向您走来
同样一首短短的诗,没有长久漂离故乡,没有那种对故乡、对母亲发自肺腑心灵的情感,没有那种别样的生命体验怎么能写下这样动人情怀的诗篇?
再如身份困扰,这是当今海外诗人常写的题材。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欧阳昱在《双姓人》中写道“我的姓名是两种文化的结晶/我姓中国/我叫澳大利亚/我把它直译成英文/我就姓澳大利亚/我就叫中国/我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我拥有两个国家”。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不论你走到哪里,欧美澳、东南亚或天涯海角,身份的困惑与焦虑总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你、这类诗歌里体现的一种新的生命体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观照与参照系。
第二,中西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海外华文诗人在吸收传统,反思现代,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交融方面也给了我们值得思考的启示。诗人痖弦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把诗歌创作比喻成一条河,这条河有上游和下游,上游就是传统,下游就是现在。如果把这句话用到海外华文诗人身上,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前半生在中国,是中国传统;他们的后半生在海外,是现代。海外诗人就如同昆德拉所说的,前半生的那段时光和后半段的那段时光大体相等。成年时代他们的创作最丰富,但是潜意识、记忆力、语言,这一切创造的基础,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海外华文诗人也是这样。散居在海外的华文诗人在继承中国传统方面,与中国当代诗人相比,他们的诗歌创作好像更中国、更传统,为什么会这样呢?移民到海外,在一种异质文化、异域文化中,他们更能深刻体悟领略到中国诗歌传统的精华与精髓,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他们更能感觉到中国传统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这是其一。而到了西方以后,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生活,他们又能清醒反思中国传统的某些不足与弊端,他们在接受现代方面,反过来又对中国传统有着比较清醒的反思。一方面继承弘扬中国诗歌传统,同时又在在反思传统,我认为海外作家在方面体现得比较好。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吸纳西方文化精华,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技巧,为我所用,二者结合相融。诗人洛夫是一个典型,洛夫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有很深研究。同时他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写作的技艺。他对唐诗有深入的探求与新解,下过一番功夫,他继承古典诗歌传统,又融现代于其中,并且付诸写作实践。他对五十多首唐诗进行了解构,已结集出版。洛夫的《唐诗解构》,把中国诗歌传统与现代诗艺术技巧想结合,他在这个方面堪称典范。《烟之外》是洛夫诗歌的名篇,许多学者指出这首诗运用了西方超现实主义写法。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如“在涛声中我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潮来潮去/左边的鞋才下午/右边的鞋已黄昏了”。洛夫说:我的这种创作方法,在中国传统之中早就有,李白的《将进酒》就有“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个“朝如青丝暮成雪”实际上是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左边的鞋才下午,右边的鞋已黄昏了”这样的诗句,其实是继承传统而又能借鉴出新。
第三,双语写作吸纳两种语言的优长。海外华文诗歌值得我们当代诗人借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出现了双语诗人和多语诗人,这些双语诗人和多语诗人接受了两种语言。许多海外华文诗人可以用双语或多语写作。他们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探索和实践,值得中国当代诗人学习与思索。我们知道,思维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双语写作意味着他们可以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两种语言思维方式的互补、互为借鉴及其融通,无疑会丰富艺术的创作思维,开阔诗歌的艺术视野,增强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力。他们既能用中文写诗,又能用英文写诗。旅法诗人杨允达,出版过六部诗集,他能用中文、英文、法文三种语言写诗。旅美作家哈金的小说几乎全是用英文创作的,而他的诗集却用双语,出版有中文、英文诗集多部。旅澳作家欧阳昱用中英文写诗,他出版了十四本英文诗集,八本中文诗集,他的英文诗连续九年入选澳洲最佳诗选。他们在外语的环境中,能够用中文、英文写诗,他们可以用两种思维方式创作,这对我们用一种语言、一种思维来写诗的诗人是有启发的。从阅读层面考察,海外华文诗人能够直接阅读原著,美国的哈金读哈代的诗、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都是看的英文原著,没有看过中文译本,尤其是读诗一般不读译本。这种吸收、吸纳是直接,一手的,而非经过转换的二手,尤其是就诗歌而言,较之叙事文学作品,读诗歌原著的审美快感与收益绝非读译本可比。而我们现在的诗人,包括我们的诗评家,读的多是翻译文本。这也给我们很多启发。
下面我谈谈对百年新诗、包括海外华文诗歌的一些反思。
著名旅美作家哈金说:“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当代诗歌已经达到世界水准。这是盲目的说法,是自我安慰。”弗罗斯特说“诗歌要始于喜悦,终于智慧”。英美文学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是诗歌的终极成就,英诗传统中,总是把诗歌作为智识的载体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智”是“智慧”的“智”,“识”是“知识”的“识”。我的理解,智识是智慧的世界,知识识的海洋。
结尾我向新诗,当然包括海外华文诗歌提出来三个呼唤:①呼唤当代诗歌经典。②呼唤当代诗歌出现大诗人。③呼唤当代史诗、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