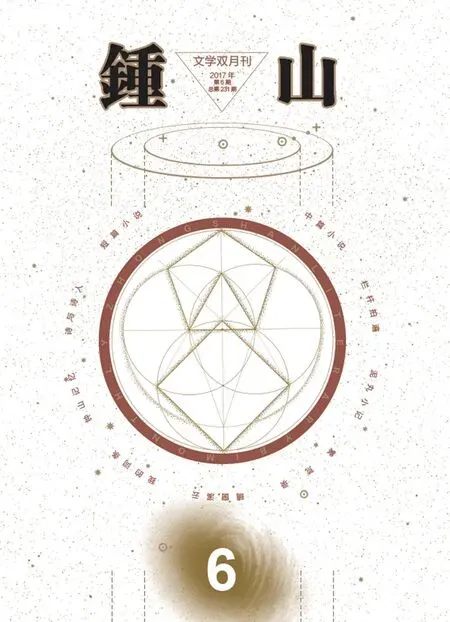对话文本、戏剧性与别处的生活
——丁及诗歌作品读札
小 海
一、诗歌与生活的对话文本
对话关系,作为一种潜在的文本,是存在于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的。丁及的诗歌,是他与生活的一种对话文本。诗歌中的对话关系,尤其是在他一些短小精悍的篇幅中,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丁及的不少短诗,这种对话关系呈现为基于生活与文本的“两度言说”。
在时间的缝隙
我如同穿行在又一个陌生的故里
在浓荫馥香的街区
做了一个陶醉的问路人
(《时间的缝隙》)
在异乡寻找故乡,时光缝隙中的小小过客,乐不思蜀后是迷途知返吗? “问路人”的实质是自我在对话,也是随遇而安的命运本身在自问自答。这种隐性的对话,不仅活泼,有生动的现场感,也使诗体形式本身更有弹性。这是一种因“陶醉”而起的自我迷失,自我放逐,也是自我的陌生化,蕴含着“我即他者”的意旨。更是自我在时间中的穿越,一种假设,一种省思。
丁及擅长将现实感甚至生活情境直接引入诗句,丰富诗歌活泼真实的内蕴,呈现戏剧张力,又能有效避免文本的呆板、空洞、死气沉沉。
午后,鸟的鸣叫越来越慵倦
湖边一排宝塔的水杉
等着我一起对茗
(《午后,对水杉的感觉》)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时过境迁,敬亭山幻化为湖边一排耸立的水杉树。是从“格物”,进入到了一种知己关系的确立?!壶中日月长,杯水之中,茶叶舒展,透绿迎翠;壶中天地宽,仿佛窗外的远水近树,移入眼底杯中,相映成趣。“对茗”,即物我两知,物我如一的共鸣产生了。诗人在“在时间的缝隙里”得窥人间的“一场好戏”,收入在时间这位“独钓岸边”的“老者”眼底,仅仅不过是一幕风轻云淡的平常风景。人间所有的喧哗与骚动,也不过是水杯中的那么一场风暴而已。
在一幅画里
有人把我们变成两只鸟
不停地吵架
张开的激动翅膀
撕裂了情绪
我们曾有人的肉体和思维
时间和另一个空间维次
把我们催生在鸟的森林
我们还在争吵
一对蚂蚁看着我们笑
他们想把心灵和我们对换
原因是我们的争吵
带给他们重生的机遇
他们原本是一对星星
只因在天空里吵架
泪水惹怒了月亮
换他们在土壤里思考
他们笑了
看到我们可怜的争吵
看到了人的企图
他们不想再啃骨头了
想借我们的身体回去
(《把我们变成两只鸟》)
爱尔兰诗人叶芝曾说:“和别人的争论,产生雄辩;和自己的争论,产生诗。”在《把我们变成两只鸟》这首诗中,无论是鸟儿、星星还是蚂蚁的“争吵”,呈现的都是几组对话关系。“想借我们的身体回去”,在完成一种人格化的置换。从这首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歌常常缘于自我的迷失、辨别,以及争辩与确认,“争吵”的实质是在“时间和另一个空间维次”设计的一场自我对话。是否是一首自我的归去来辞?能够确认的主体又是谁? “在一幅画里”抑或“鸟的森林”中? 此刻我是谁? 往昔谁是我? 其中的自我追问,自我搏斗,也许诗人明知故问,“梦里不知身是客”(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想借我们的身体回去”借尸还魂的是诗人?“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的还是诗人? “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藉由自我对话达成的自我实现而已。此刻,也许自然会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那句著名的墓志铭:“我和这个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他生前的所有诗歌不都在诠释这“争吵”的真谛吗?
猫回头叫我,用生物的语言
像它一样,我
从那个金字建筑的最底层爬出
用幽幽的眼光,埋葬白天
从此,走入黑色,猫的天空
(《一只猫回头叫我》)
这是“从那个金字建筑的最底层爬出”的猫,“用生物的语言”,在另一重时空里完成的对话。这种对话机制的确立,缘自“一只猫回头叫我”。这其中还有白昼与黑暗的无声对峙与对话,白昼代表了世俗的人间世界,黑暗也许代表着纯粹的世界,情感的秘境,让诗人宁愿以黑暗美学来“埋葬白天”。
曾经,包裹多少情欲的果实
多少茂密的生机,随枝条向上扩展
绿得惊心的空气中
夹杂着那个季节发酵的味道
(《蜜月期已过》)
前朝的簪插入当令的髻
耳廓灌满呓语
(《游春》)
飘乎而过的火焰
惊艳了谁
谁路过了谁
我将熄灭在灰烬中
你将去哪里
(《飘乎而过的火焰》)
丁及将这些内心的叙事和独白,情感的能量与释放,巧妙放置于诗歌的空间结构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交换、体验的对话关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与生活世界对话的独特文本。
诗歌中对话关系的确立,还让诗歌有了注重音律、调节节奏的效果。这是基于对话双方对位关系基础之上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内化为个人的节奏与风格,或者说文本与诗人个人精神气质的呼应。
当然,这种音乐性的产生,不再是外在的、显而易见的一些形式规范,而是如结构、段落、句式、气息、呼吸等组成,一种属于个人精神气质层面上的东西。正如丁及诗歌中的能量生发与诗句张力,就在于语调的敏感度和起承转合中的一种奇特的分寸感,类似个人呼吸的节律。例如这首《梅》:
时时下雪,飘落你气息
一点一点的,那花骨朵儿
落入我的骨架
未开,欲开,盛开,将残
四时的景,成冰
(《梅》)
音乐性在诗歌中的作用,一直是个神秘而有诱惑力的话题。可能因为音乐与诗歌本来就像是同体共生的一对连体婴儿,有一张类似双胞胎的共同出生证明。诗歌,诗歌,歌诗同源,这是诗歌与音乐两种艺术形态最早的发生学。这种亲密的关联,曾让诗与歌彼此生发、共同成就。钱穆先生说:“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中国文字特殊,诗之本身即涵有甚深之音乐情调。古诗三百,无不入乐,皆可歌唱。当孔子时,诗乐尚为一事。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乐必以诗为本,诗则以人内心情志为本。有此情志乃有诗,有诗乃有歌。”(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12年7月版,第120 一121 页)古代诗歌中的声韵、音律犹如纽带将诗与歌有机串连结合,诗(或当代所谓的歌词)不是歌中的毒药而是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汉语,或者说当代诗歌中诗与歌的关系,不再具有古代诗歌中“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渔翁》)般的自然关联,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重启。
二、音乐性的消减与戏剧性的强化
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困境,往往是以反诗歌的形式来破解的,包括引入了其他艺术的元素进来。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当代,诗歌依然是一种最开放和最具活力的艺术形式。虽然说,无论是在抒情诗还是叙事诗的传统中,戏剧性本身也是作为诗歌的古老基因之一而存在着的。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是,在当代诗歌中音乐性衰减的同时,诗歌的戏剧性因素却大大增加了。当代诗歌中戏剧元素的强化,是诗歌现代性的一大表征,给诗歌增添了别样的活力与风采。
墨西哥诗人、诺奖得主帕斯的名作《大街》就是在诗歌中充分运用了戏剧写意、传神的高妙技法,营造出独持而又极具张力的氛围,使人如同在观赏一出惊心动魄的心理实验剧。
这是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道。
我在黑暗中行走,跌跤,
爬起来,踏着干枯的落叶和沉默的石子,
深一脚,浅一脚。
我身后也有谁将它们践踏:
我停,他也停,
我跑,他也跑。
当我转过脸,无人静悄悄。
一片漆黑,没有出路,
我在街口转来转去
总是又回到原处,
那里没人等我,也没人将我跟随,
我却在将一个人紧追,
他跌倒了又爬起来,
一见我便说:没有谁。
(帕斯《大街》)
诗歌的戏剧性直接指向了纷繁复杂的当代生活导致人们产生的强烈欲望和行动,这种由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内心嬗变,这种紧张、深刻的矛盾冲突,在人的心理与行动中引发的影响,使得诗歌更富激情与张力。
红谷茶马记得我脸庞
整个冬天漂流
贴着冰洁溪水
烤鱼浮起青草叶
熏黑的木头做成山里
鼓动东河的床
我单骑千里追寻
注入一沟翠月
浸没了淙淙初夜
(《想起束河古镇的你》)
这仿佛一出古装侠客剧,令人身临其境,心潮澎湃。侠客想象本身,历来就属于中国传统的文人趣味,先秦侠士刺客,如《史记》中的战国四公子列传等,难道不是文人趣味的创造物吗? 来看看《荆轲刺秦王》就知道了:“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见《战国策》)丁及的《想起束河古镇的你》,在“一沟翠月”注视下,“淙淙初夜”的“单骑千里追寻”,确实让人浮想联翩。敢问,作为剧中人的束河古镇的你,到底是谁呀?
喜鹊在弦上跳
拉一拉邮递员神秘的手
好想和瓶儿碰杯
(《花开的秘密》)
丁及诗歌《花开的秘密》中的戏剧性是出人意料的,我们知晓了开始,却没法猜测到结局。“神秘的手”也是“上帝之手”,出乎意料,让人大跌眼镜,这恰好是对戏剧性的最佳诠释,也是戏剧性所需要的典型效果。
钢铁的大指针遍布城市的半空
我们随它的指向而迁移 一次次
在顶层的阁楼居住 光阴被秒杀
只剩下疲倦的眼 一只摩天轮
制造那些钢铁的大指针 是黄色
骨架 是绿衣包裹下的火柴者
大指针挑着鱼钩 随它任意转动
不停制造空的空间 弯曲空间
入夜的大指针 似乎停止转动
我们奔向护城河 用水弥补黑洞
大指针鸟瞰着 绘制户型与风景
在女人裸露的背上 一架生物钟
我浮在半空 和他一样的高度
在最矛盾的时间里 读你的胸针
现在就真实地读 一条江的心跳
你吻着我 拆着他的欲望机芯
(《大指针》)
《大指针》 这首诗可以拿来作卡夫卡小说《审判》的背景设置,作者营造了一种独特、神秘的氛围,令人犹如置身一个难以洞悉其构造、也无法了解其意义的宇宙时间中,等待生命的终结审判。当然,作为贝克特剧作《等待戈多》的舞台布景也不错,虽然原剧的背景设计似乎是乡下或者荒凉的郊外。就是说,这首诗的戏剧性是作为背景式而原在的。
我来到这个城市多年
每天穿着消防衣
之前我生活的那个城市
到处都是雨衣
这个城市的白发
起源于水中的火焰
(《水中的火焰》)
像上述《水中的火焰》这类诗,更像是以荒诞剧或者静默的哑剧形式存在的。主角“每天穿着消防衣”扮演着隐身人,却在剧终时点燃“城市的白发”,恍若“水中的火焰”。
而丁及的另一首《桃花日》,则又是以舞台音乐剧轻歌曼舞的形式呈现的:
那些日子总在荡漾
被南风漂染的衣裳,轻浮的暖色
一朵朵,或昏迷,或先知的笑容
蘸满了那些符号的水
那些日子劫我,漫山野的
你容颜的光,一次次临幸
那筒钟形的夹袄,夹着红晕
先于我解开,灼灼带露
那些日子撕破了我暗灰的皮
引你——挑起蜜乳,进入我身体
(《桃花日》)
这其中有李渔式的对日常生活的观照与热爱,所谓“春之为令,即天地交欢之候,阴阳肆乐之时也。人心至此,不求畅而自畅”(李渔《闲情偶寄》)。同时,又有唐寅式的勘破与自我放逐,让人想起《桃花庵歌》中的句子: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
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
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
……
两者不同之处体现在收尾的篇末,《桃花庵歌》落在了:
世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记得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作田。
丁及的《桃花日》终篇落在明明知晓人生真相的“那些日子撕破了我暗灰的皮”,却依然“引你——挑起蜜乳,进入我身体”。
从丁及的诗歌中不难看出,诗歌中的戏剧性,有时意味着情感上的能量补充。在这同时,我们也得以窥见这种戏剧性,又有一种江南才子自我解嘲式的放诞、散淡与悠然的气息。
三、从历史中醒来,或生活在别处
就是这块空地
历史书上说
曾倒了不少精巧的行宫
多少人当成终点
挟着罗帷中的美人走了
而今,风景依在的
是我的露营帐篷
看雾霭褪去青铜战事的鼓印
松谷风笛声声
听多少王孙栋梁的腐朽
(《快到山顶的那块空地》)
咏史,是诗歌的传统主题。古往今来的咏史诗可谓蔚为大观。诗人们访古寻幽,凭吊往事的目的,既是为了探究真相,表达个人的历史观,更是为了感时寄兴,言志抒怀。丁及的这首咏史之作也可归于此类。山顶是那昔日威权的所在:“历史书上说/曾倒了不少精巧的行宫”; 山顶是那爱情传说的所在:“多少人当成终点/挟着罗帷中的美人走了”;而今的山顶,更是那光明的所在:“而今,风景依在的/是我的露营帐篷”。用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人物斯蒂芬的一句话来说“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在设法从梦里醒过来。”帝王将相们的旧宫殿,哪怕是历史的制高点,不过是今天几个野营者的宿营地。生活在远方,也是生活的高处。无论是心灵的自我放逐之地,还是历史的沉淀之地,我们依然可以安眠,就像《尤利西斯》中的那位都柏林人一样。“松谷风笛声声/听多少王孙栋梁的腐朽”,回到当下与现实,诗歌则又有着扫除历史幻影的功能。
据说,一只中式灯笼引起的
那一场大火,并没有吞没那些金砖
我们,在金黄的夕阳里走入新宫
看到那些金砖,铺设的统一模样
顿时,有种重见天日的金黄颤动
朵朵野花一样,飘附在金砖之上
一个巨大的底盘,形式飘然而升
(《有关金砖》)
从金砖的前世今生中,我们看到刚直的金砖在“弯曲”的历史中的形态。今日苏州城北,有一座以金砖命名的御窑博物馆。金砖从皇家走入了民间,从“统一模样”的垄断到衰败、散落,诗歌让金砖轮回的意义有了“形式飘然而升”的回归。
丁及更多的诗歌,表现的是穿越历史、神话的迷雾,步入现实后的感受。在回到具体的诗歌中时,能够发现,诗人抛弃陈词滥调,通过自身的即刻感悟,让诗歌回到人间生活之源的不懈努力。
今天,我的驼鸟开始迁徙
他们走入清山门阙
那圈城垣的倒影
隐约在肥沃的田圃
房子又从地里生长出来
呼吸在原来边界之外
(《城市边界》)
谁推去高坛,接手一把羽毛
谁在喊我们枕着心声入眠
(《眠》)
墨绿色的镜面
见到夏季繁盛的枝条
见到横穿竖杈
被枝条分解的天空
城市的一个眼
蛙的咕咕挑开惊热
小小的空寂在景象后
雷雨来时
浮萍的张力平衡于每一条颈项
护住了深流的平静
只是这个夏季不知情
被越来越多的房盒包围
汽车开在池塘边
……
(《夏季池塘》)
只有将历史的“驼鸟”驯养在“城垣的倒影”里,只有“推去高坛”,在“枕着心声入眠”后,才能让诗歌“自然生长出来”“呼吸在原来边界之外”。在“被越来越多的房盒包围”之后,我们向往天上那“被枝条分解的天空”和地下“深流的平静”。在不断变得局促、僻仄的城市居所和日益平面化的日常生活中,想象力的解放成为另一种精神瑜伽与放飞心灵的手段。
我看到你了,长在村边的菜花
被一洼浅水,描出黄色
我,不禁起了浪
(《下乡记》)
唐人白居易在《忆江南》中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的春天被日出时的江水映照得那么绚丽多彩,那么生机勃勃。那醉心迷人的春色,就在咫尺近旁,却若生活在别处,哪怕相同的地点,因了最美的季节,最美的时辰,因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诗人会“前仆后继”,一次次“跌入”同一片风景之中,因为感同身受之人早已融化成景:“我,不禁起了浪。”
“生活在别处”,多么响亮的口号,曾经是法国天才诗人兰波高扬的旗帜,也是兰波用短短的一生去为之努力践行的梦想与传奇。可是,我们是否曾认真假设过,远游的诗神一旦归来,又将如何面对当下、此岸的庸碌生活?
诗歌的一个功能难道不是为了在庸常的生活与平凡的风景里,发现、体悟不凡、神奇与永恒吗?!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给平庸的东西以威严,给日常的现实以神秘。”类似于让我们醒着做梦,生活在别处。“化腐朽为神奇”,是诗人在诗歌中接近神性的创造力。可能更重要的不在于生活本身如何,而是你发现与对待生活的方式。
我们一直在草起草落中生存
我们诞生在草地,用草擦干脐带的血
我们吃草,生病的时候也吃草
我们住草棚,草帮助我们呼吸空气
我们恋爱于草地
青草的香味激发了我们的情欲
我们的力量在草堆的翻滚中壮大
我们呐喊于草场,驰骋于草的疆土
我们又做着草的生长旺盛的实验
我们看到几千年的水在草的经络中流过
而草的根系在时间的土壤里蔓延
草又生长于我们身体
满身遍野生长于我们皮肤的每一个沟壑
我们浇灌了我们身体的每一棵草
我们不怕火
草的青绿指引着月光的沐浴
阳光下,爷爷在庭园浇草
孩子们在草地上绽放了笑容
爷爷的眼前是一片苍苍莽莽的草地
有牛马羊群的叫声,他们知道草的委屈
但光环始终在草地上产生
墓碑树立在草地
一个草莽世界又一次诞生
(《草起草落》)
我们像古树一样躺下
不再分离
(《我在银杏果里等你》)
我把心脏安放在丁香花蕊中
随五月一起跳动
每一条绿色枝丫
指引我出生的每一条路
……
于是,我的心脏变绿了
安静而有力 起伏着
在红色墙面 心生更多绿意
(《安放在丁香花蕊中》)
丁及的作品中,写下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自然之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水、草木构成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山水自然岂止只是怡情养性啊,几乎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性命”。山水的形态如同张潮《幽梦影》中所说:“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所有这些自然界与精神世界的山山水水,几乎构建起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实,对于大地、此岸、人间的眷恋,古今中外的诗人概莫能外。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放弃神女卡吕普索的小岛和神仙的日子,历经艰辛,只求回归贫苦的人间故乡伊塔卡。这也意味着他选择了放弃享乐与永生,要在有限的生命里辛劳付出,在愁苦与忧思中度过余生,迎接死亡。这是另一种大地之歌与生命诗学。
唐朝诗人李白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上山,上山,上一条山路
自然的暗,自然的亮,自然起伏的路
自然的温度,自然的雨量
自然的石头,渐渐看上自然的花
上山,上山,上一片山坡
大孩,小孩,乖孩,熊孩,全在山坡
泉水响了,风在跑了,去放一群牛哇
你插个班吧,坐在我边上
听对面的山,讲一堂有滋味的课
(《上山,上山》)
“听对面的山,讲一堂有滋味的课”,是啊,大自然是最好的心灵抚慰剂,青山明月是最好的导师、最高的训戒。春花秋月,寄兴遣怀。青山明月,生死同衾。这些自然山水,不在别处,却在人间。
这让我想起唐代两位诗人之间的酬唱。王昌龄在《龙标野宴》中纵酒高歌:“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李白听到王昌龄远谪贬为龙标尉的消息,写下这样的诗句来宽慰好友:“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赠瞿秋白之辞)一片冰心可鉴,依然在山水明月间,可谓心有灵犀。这也是尼采的对大地说“是”。
人间要好诗。对诗人来说,世界依然在守候着某种宿命。
2017年8月匆草
- 钟山的其它文章
- 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