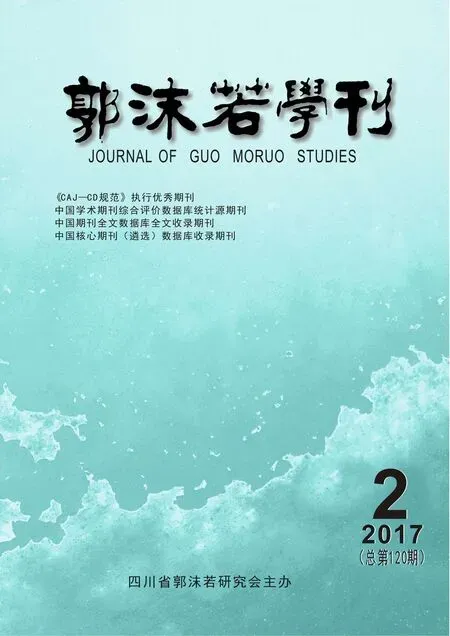北伐,开启郭沫若亦文亦政的人生模式
蔡 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北伐,开启郭沫若亦文亦政的人生模式
蔡 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投身北伐,在郭沫若的人生经历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郭沫若参加北伐,既是其主观意愿的选择,也是时势使然,是时代对于他的选择。北伐的经历带给郭沫若若干政治遗产:以“从事实际活动”,来确认自己“日后的动向”;进入政党圈;获得从政的历练;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等等。当北伐之后郭沫若又重新做回文学家的时候,他在实际上为自己开启了亦文亦政这样一种将延续其毕生的生存方式。
北伐:郭沫若;政治遗产:亦文亦政
如果把郭沫若的人生行旅描绘为一条长长的轨迹,那么,1923年他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直至1937年7月从作为政治流亡之地的日本再次回到上海这十余年间的经历,应该是其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段轨迹。因为他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个领域所成就的辉煌,以及他在思想上所经历的转变,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一历史时间段。
再往小一些的时空范围看,一个人的一生,无论一帆风顺,还是历尽坎坷,但人生路上的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这几步决定了其人生的基本走向。投身北伐前后,就是郭沫若在其人生路上紧要处所走出的几步。这一段经历似乎没有那么光彩夺目,尽管“戎马书生”的慨当以慷足以让人热血沸腾,铁马金戈的战场硝烟毕竟没有为郭沫若成就什么。然而,投身北伐,对于郭沫若是一段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人生经历,它预示了,或者说开启了郭沫若人生行旅的模式。
一
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之际毅然投笔从戎,并非心血来潮,也不是诗人的浪漫心性使然,他的选择在其人生之旅勾画出的轨迹延长线上实际已成必然。可以看看北伐之前郭沫若有着怎样的经历。
自从扬起“创造”这面大旗,郭沫若与创造社作家在上海滩的文学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正方兴未艾。而1926年2月底,一个来自广东大学的邀请,却让他毫不犹豫地南下广州,并且把创造社的主力也带往广州。之前几年,郭沫若曾有过几次受聘往大学任教的机会,他都推辞未就,这一次何以全力以赴呢?因为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聘用教授任教的邀请。由广东大学代理校长陈公博署名写给“沫若田汉先生”,催促他们南下的信函,表达的是这样一种邀请:“我们对于革命的教育始终具有一种恳挚迫切的热情,无论何人长校,我们对于广东大学都有十二分热烈的希望,于十二分希望中大家都盼望先生急速南来”。“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深望先生能尅日南来,做我们的向导者。”
从事“革命的教育”,“做革命青年的领导”,而且是作为“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被邀请,郭沫若显然乐于接受广东大学给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定位,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能“从事实际活动”,而不再仅仅停留于文学园地之中耕耘的机会。
广东大学不是一般的国立大学,而是相当“党化”(国民党)了的大学,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在将要把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的计划里,国民党人是准备让其“达到党化地步。将来凡系党员入校肄业,一律免费。非党员则要交纳学费。”陈公博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政治身份执掌广东大学校务,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对于由守旧势力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掌校非常不满,在邹鲁去职后即于1925年底任命陈公博代理广大校长。在代理校长期间,陈公博准备革新教务,并开始施行了几项新的校务措施。从陈公博的邀请中,郭沫若应该是看到了可以有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郭沫若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活动尽管遇到不少困难、挫折,但毕竟做得风生水起,何以他会萌生了去从事实际社会活动的想法呢?这又得往前看看1924年的郭沫若。
1924年4月,在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归国一年后,郭沫若携家人又返回日本。他这次到日本,计划中有两件事:一是寻找读大学院(研究生院),继续研读生理学的机会。二是翻译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前者未能如愿,后者则很快完成了,并且成为郭沫若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史事。
由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已经预示了郭沫若在人生之路的选择上将发生巨大变化。郭沫若对于河上肇学究式的讨论和回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大满意,也不认同河上肇“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认为那“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宣称:“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我对于今日的文艺,只在它能够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上承认它有存在的可能。而今日的文艺也只能在社会革命之促进上才配受得文艺的称号。”郭沫若修正了此前的文艺观,将文艺与社会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
于是,“这些觉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的。我想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际活动。这,是决定了我日后的动向的。”
再次从日本回到上海,郭沫若在文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多了起来:到宜兴做社会民生的调查,与“孤军派”、“醒狮派”的国家主义者论争,参与同乡会的活动,到一些社会大学讲课……郭沫若说,“我那时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得到广东大学邀请,郭沫若当然会毫不迟疑地应聘赴任。
1926年3月底,郭沫若抵达广州,走马上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上任之初,郭沫若就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搞文科革新。他提出了一些革新教务的具体措施,由此引出了一场激烈的择师风潮。郭沫若被推到这场风潮的风口浪尖上。他提出的革新教务措施受到一批代表守旧势力的教师的顽固反对、抵制。他们宣布罢教,向校长呈文要求“罢斥”郭沫若,并将呈文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呈送,又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但是郭沫若的革新举措得到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的全力支持。该党部专门召开了党员大会,通过四项议案,以示声援。
5月初,择师风潮以革新势力的胜利宣告结束,郭沫若得到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的高度评价。在该党部写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他的文字和演说,很能增加党化宣传的声势”,“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
郭沫若在文科革新与择师风潮中的表现得到国民党人的充分肯定,于是,5月中旬,由时任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介绍,郭沫若加入国民党。之后5月底,郭沫若受命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夏令营讲习班的教务工作负责人之一,并将讲授“革命与文艺”。其他将开设的课程有:蒋介石讲授“北伐计划与国民党政策”、周恩来讲授“国民革命与党”等。紧接着6月初,他又与吴稚晖、张太雷、何香凝等受聘为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暑期政治研究班教授。
6月21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陈公博为部长)改组而成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召开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郭沫若以准备进入政治部,还未到任的身份参加了会议。7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提出“统一政府之建设”,“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的目标,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和参加北伐。同日,国民革命军在东校场召开誓师大会,会后,约十万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开始北伐进军。22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从广州黄沙车站乘火车赴韶关北上。
从3月底到广东大学,至7月下旬离开广州随军北伐,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郭沫若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弃文从政(军)。但是,考察过郭沫若自1924年以来一路行走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人生角色的转换,既是他主观意愿的选择,也是时势使然,是时代对于他的选择。
二
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政治工作干部,而且负有领导责任,郭沫若已经无暇,或者说无意进行文学创作了。一个历史细节很有意思:《洪水》创办一周年,出版了一期纪念专刊。因为是“自己纪念自己”,所以刊登的都是创造社作家的作品,郭沫若的诗歌自然是不能缺少的。但正在北伐途中的郭沫若显然无心创作,于是,纪念专刊从《瓶》中选取两首诗合为一首,以《着了火的枯原》为题刊出。不知道的人以为这首诗是郭沫若新作。总政治部主管有一份《革命军日报》,由潘汉年主编,报上辟有文艺副刊,但在整个北伐期间郭沫若只有一首纪念蒋先云的诗刊出。足见其“弃文”之彻底。
对于郭沫若而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转换了人生角色当然很“酷”,譬如被人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但更重要的是,他非常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社会角色的担当,也能把它做得很好。所以仅仅两个多月后,他便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且受命往南昌,在总司令部主持政治部工作。蒋介石还委任他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在“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南昌特别党部”成立时,郭沫若当选为执行委员。宁汉分裂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仍任命郭沫若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任命他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这支部队是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主力部队,后来南昌起义的部队也出自该部)副党代表(党代表缺)兼政治部主任。这些都可以说明郭沫若所具有的能力和所做的工作是被充分认可的。
北伐是一次军事行动,它给予郭沫若一段军旅生涯的经历。但北伐又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中包含了更多政治、政务活动的内容。北伐是以军事行动,打倒军阀势力,从而实现国民革命的政治诉求、社会理想诉求。所以,随军事胜利而来的有地方政权的更迭,在北伐过程中有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争斗,有国民政府(宁汉)的分裂,直至南昌起义国共两党分道扬镳。郭沫若拥有的身份和职务,使得他在历经这一次次历史事变的时候不可能是局外人,而必然是参与者。他的人生经验因此大大丰富起来。
那么,北伐的经历究竟带给郭沫若一些什么政治遗产呢?
首先,参加北伐使得郭沫若实现了意欲“从事实际活动”,来确认自己“日后的动向”的愿望。而且北伐不是一般意义的“实际活动”,是一次社会革命的实践。这应该是一直生活在学校和文学园地中的诗人郭沫若,在实现了思想转换之后,在走到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之际所渴望的机会。正如他在赴广东大学之前为“凿死”自己先前的思想“混沌”而写的一篇序文中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
其次,北伐经历把郭沫若带进入政党圈。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中,离不开政党,所以,一个人要置身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必然要具有党派身份。郭沫若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组织创造社的时候,曾特别强调“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但是他甫一到广东大学,很快就认识了政党的作用和力量。他的教务革新正是由于得到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的大力支持,才得以推行。
加入国民党,是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政治生涯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不只是此前作为一位浪漫诗人的郭沫若在表面上一个政治身份的变化,党派身份直接影响了他此后人生角色的定位和人生道路的走向。正是国民党员的身份,使得他能够进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参加到北伐的军旅中,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北伐后期,他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与蒋介石决裂,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而中国共产党则把他视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南昌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仍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郭沫若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民治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此开始,党派身份决定了郭沫若的一生。即使后来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活动在社会生活和政界时,那个“无党派”其实还是以一种政党关系为支撑。
其三,北伐经历给予郭沫若以从政的历练。
从宣传科长做起,到作为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副手,再到独自主持一方工作的政治部大员,郭沫若在军队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方面应该是有着很好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在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工作职责,还不仅仅是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它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因为北伐的目标之一就是“统一政府之建设”。所以蒋介石会授命政治部起草“文官考试”、“惩吏条例”等有关吏治的章程。随着部队一路北上的军事行动,原在军阀势力治下的地方政权需要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部就会根据需要,参与到各种工作中去:经济、教育、社会团体管理、农村工作、地方新闻工作,乃至涉外工作等等。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邓演达兼任了湖北政务主任委员,郭沫若也曾被要求担任湖北省政府教育科长,只是他坚辞未就,但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科政治教官。郭沫若还被国民政府委定作南京东南大学改组为东南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与刘湘、刘文辉、杨森、杨闇公等一起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临时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虽然在实际上郭沫若没有具体承担地方政务工作,但这样一番阅历,对于他在政务方面的历练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北伐前后的经历为郭沫若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郭沫若交往和活动的空间,主要是在文学家、艺术家的圈子里。到广东以后,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几个月和投笔从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他活动和交往的圈子大大拓宽了。在文学家、艺术家之外,他广泛结识、交往了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人,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几个领域。在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内的讲习班、研究班等的授课和北伐期间政治部的工作,直至后来的南昌起义,使他与国共两党(其实还有后来的一些民主党派)领导层的主要人物都有了交集或交往。可以说,北伐的经历,开始把郭沫若带进了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精英政治圈(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内,虽然他从未进入到这个圈子的中心。
当然,郭沫若在是时拥有的人际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别,有的可能只是一面之交,但是在中国这个重视人伦关系、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这样一个关系网络的拥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郭沫若后来无论是为文,还是为政,这些人脉对于他都是一个无形的资源。譬如,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建过程中,郭沫若成为三厅厅长不二的人选,当然与此不无关系。那张被称作“五光图”的照片(郭沫若与北伐故旧陈铭枢、张发奎、黄琪翔、叶挺五人于1938年1月重逢于汉口时留下的一张合影)是颇有历史意味的。
三
随着大革命失败,郭沫若走完了北伐之旅。1927年11月,他辗转香港回到上海。血雨腥风之后,北伐的经历并没有随风而去。
经历了那样一番轰轰烈烈,大起大落,郭沫若似乎并没有做什么精神心态的调整,没有一点踯躅停顿,很从容地就又重新做回文学家的角色,投入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中。他在创作《恢复》中那些诗歌时,甚至重现了创作《女神》和《瓶》的那种“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的亢奋状态。这样的诗歌创作状态,按郭沫若自己后来所言也就只有过这三次。《恢复》的创作,最多有一天写成六首的。显然,在《恢复》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创作灵感的激发,还是诗歌所抒发的思想情感内容,都是郭沫若从北伐前后所经历的人生体验中所感悟和获得的。
参加北伐,是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践行社会革命的一段人生,所以,北伐的经历、北伐的政治遗产,使得郭沫若在重新做回文学家的时候,其文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内涵也已经有所不同了。革命文学不仅是表达在一个口号或理论概念上,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同样,再往后看一点,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之时,因为远离了国内的社会现实,远离了一起实现文学梦想的创造社朋友们,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领域。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在一开始就成为郭沫若鲜明的、坚定的学术立场。亡命日本,与他参加北伐是有因果联系的,选择这样一个学术立场,无疑也是他在有过北伐前后那样一段人生经历之后的必然趋赴。
郭沫若的人生中有三个关键词最为重要,即:文学、学术、政治(从政)。这代表着他最主要的几种人生状态,或者说是他人生的几个组成部分。它们最初是由北伐的经历串联起来。而当郭沫若脱去北伐的戎装,蛰伏于上海窦乐安路一处弄堂小屋里,淡定地又拿起文学家的笔时,他在实际上为自己开启了亦文亦政这样一种生存的方式。
在如何对待为文与从政的关系上,郭沫若所经历的,与瞿秋白曾在被排挤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而去上海搞文艺工作的经历有些相似。难怪瞿秋白最后在福建汀州狱中写出的信是给流亡日本正潜心于古文字研究的郭沫若的。他对郭沫若说:“可怜的我们,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又不无羡慕地谈及读到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的一新著,《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最后祝愿郭沫若“勇猛精进”!
显然,在处理两种不同人生的转换时,郭沫若表现得更为自如、洒脱,这也可以看做是北伐给予他的政治遗产:亦文亦政,入而能出,出而能入。再一次在出入之间转换人生角色,是十年之后郭沫若秘密归国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波之中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当然是续缘于北伐军旅中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的郭沫若。
在中国的士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有如何在“庙堂”与“江湖”两个政治空间之中安身立命的问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社会责任担当,也是他们所葆有的一种精神境界。入世,是士文化传统的根本所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要入世的,能出世,也是为的日后仍然可以入世。郭沫若尽管在日本十年“读的是西洋书”,在这一精神特质上仍然遵从着士的文化传统。在冈山读书他时常徜徉其中的“后乐园”(得名于范仲淹《岳阳楼记》),大概总在默默给予着文化提示;而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雄心,未必没有得之于班超们的凛然之气。
但是既然存在“庙堂”与“江湖”两个政治空间,就有选择的可能。一个人的进退,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坚持。而怎样才能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行走,并且进退自如,则要审时度势,处理好个人与时势的关系。一个人的选择和坚持不可能全凭个人的意愿,时势是绕不过去,也避不开的。如何能顺应时势前行,而又不失初心。这大概要考验一个人的智慧、经验,当然也离不开机遇。
亦文亦政,郭沫若一生的“成”得之于此,他的“失”,又何尝不是由此而来呢!在人生行旅的进退之间,郭沫若并不能总是从心所欲,但有一点应该肯定,他从未忘却为文为政的初心。人们在评说郭沫若,特别是晚年郭沫若的时候,其实首先应该梳理清楚作为诗人、战士、学者三位一体(周恩来的评价)的郭沫若,或者说具有多重社会角色的郭沫若,是怎样从历史舞台深处走过来的。
(责任编辑:廖久明)
[1]陈公博函催郭沫若等南归[N].广州民国日报,1926-02-18.
[2]广州民国日报,1926-04-09.
[3]孤鸿——给芳坞的一封信[J].创造月刊(上海),1926,1(2).
[4]创作十年续编[M].上海:北新书局,1938-01.
[5]广大特别党部报告[A].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党务月报[C].1926(2).
[6]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N].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27-05-23.
[7]广州民国日报:据1926年6月2日、4日、9日.
[8]李一氓回忆录[M]。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1926年6月《广州民国日报》).
[9]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9月.
[10]郭沫若.文艺论集·序[J].上海:洪水,1925年12月(第1卷第7号).
[11]郭沫若.编辑余谈[J].《创造》季刊,1922年8月(第1卷第2期).
[12]周恩来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建议[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在民众方面,推举郭沫若为知识分子的领袖.
[13]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J].中央通讯,1927(7).
[1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N].工商报(江西),1927年8月2日、3日.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M].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A].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5月.
[17]汉口民国日报,1927-03-29.
[18]广州民国日报,1927-01-06.
[19]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五日国民政府令[N].汉口民国日报,1927-04-06.
[20]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J].近代史研究,1981(2).
C912.1
符:A
1003-7225(2017)02-0002-05
2017-05-03
蔡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