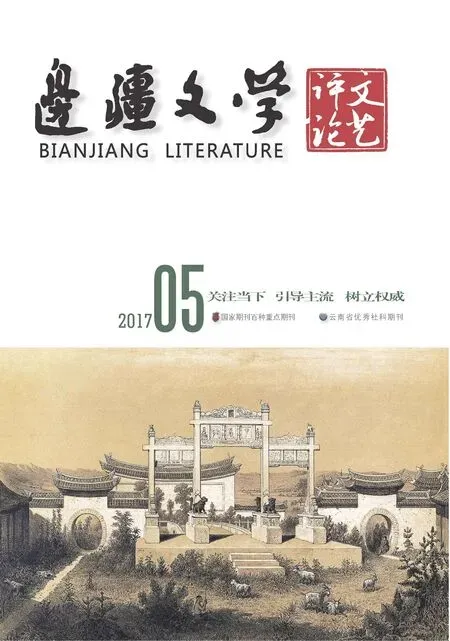遥远的乡情
——邓安克民族民居绘画艺术
刘明玉
遥远的乡情——邓安克民族民居绘画艺术
刘明玉
民居对于人类而言,其意义远远不只是房屋本身所具有的物理性质,而是蕴涵在房屋形态之中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识。云南民族民居所反映的民居建筑文化丰富多样,带着人类童年的绮丽色彩。邓安克的民居系列油画作品自成体系,风格浓郁,蕴含着他对云南民族民居建筑表现的独特把握和理解,邓安克用画笔表达着自己对民族民居文化的一片深情和理解。绘画艺术表现的民居形态,并不仅仅是艺术家漠然的客观呈现,更是其心底对生命和文化的肃然敬畏。邓安克依托这一“方言表达”,由此成就了其艺术语境上的特立独行。
一、精神与情感的映照
邓安克自幼生活在云南,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从小就受着云南民族文化的熏陶。作为画家,他的画笔总是不自觉的触及到故乡云南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在他的绘画题材中,云南的民族民居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或许就是他的乡土情结和家园情怀使然。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民居承载了我对家乡的情感,也让我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静静立在那里的民居,让我百感交集。”这种发自心底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使他的画作自成风格,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任何一种绘画语言的使用,首先是人本的体现,艺术的精神最终反映的是人的精神。邓安克的民居系列油画作品自成体系,风格浓郁,蕴含着他对云南民族民居建筑表现的独特把握和理解。云南民族民居“深蕴着一种为它自身所特有的、被灵光照耀的、神圣的原始信念以及由人们心底深处流出的强烈情感所编织成的、人类童年的斑斓梦幻。”民居对于人类而言,其意义远远不只是房屋本身所具有的物理性质,而是蕴涵在房屋形态之中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识。特别对于云南民族民居而言,由于云南各民族本身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各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也各有不同,因此所反映的民居建筑文化就更为丰富多样,邓安克正是用画笔表达着自己对云南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各民族民居文化的独特理解和情感。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两重特质,既代表着自己,有代表着自己所属的区域环境所赋予的民族文化内涵。
二、邓安克云南民族民居绘画的情感根源
(一)为民居造像与邓安克的乡土情结
每个人都有着深埋心底的乡土情结,应该说“故乡”是人类共同的心灵栖所,寻找精神家园是人类共同的心灵归依,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特别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之一。
邓安克自幼生活在云南,深受云南本土文化的浸染,壮美的山河、奇异的风俗,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深植其心,魂牵梦萦。作为一种文化源头,成长背景必然激起艺术家表现欲望的萌生,而以民族民居入画,与其说是艺术家的艺术旨趣所指,还不如说是他深埋心底的乡土情结下,涌动着表达的欲念。邓安克在民居创作手记中曾说:“三十多年了,我对它仍然依恋不舍,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享受和快慰,它以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许多伟大的画家都曾受乡土情结的牵引而创作了众多伟大作品。比如米勒,作为一位伟大的田园画家,他在画布上呈现的是宁静的田野和田野上辛勤劳作的人们。他画田园和那些劳作的人们,与其说是为着田园的美,不如说是为着他深埋心底的乡土情结。1863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这一生,除了田野,没有见过别的,所以我只能尽量说出我在田野工作时所见到的经验。”米勒说他除了田野没见过别的,当然不是说了的眼睛没见过别的,不是说他多么的孤陋寡闻,而是他深埋心底的乡土情结过滤了田园以外的东西,他的兴趣在于田野,在于那些他熟悉和热爱的劳作的人们。邓安克的艺术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情节呢?画笔下的云南民居无不包含了深沉的感情。艺术家对题材的兴趣,本身就折射出其艺术观和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更是一种缓解和释放心灵深处,甚至是潜意识之中的紧张之弦。对邓安克而言,这种紧张之弦就是对乡土的眷恋和热爱。
建筑是人依存于自然空间的“人化”形式,它承载着人的理性认识和文化精神,它既是物质形式也是精神外化。建筑依赖一定的自然环境,依赖于一定的材料,但它又受着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约束。云南民居建筑亦存在着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的不同民族民居建筑的风格样式不尽相同的状况,这也是文化约束的结果。邓安克的云南民族民居绘画,其目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得以透视民族精神的内核。在乡土情怀的牵引下,邓安克画布上的相对静态的民族民居建筑折射出洋溢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活态的心灵跃动,绘画语言中表达了丰富的生命信息。
作为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土壤,任何地方的文化,都具有地方特色,即具有本土性。本土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本地区的原生文化,二是外来文化经过交流互动逐渐具有本土特色,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结构,邓安克艺术创作的动机,才把这种影响深植于心灵之中,让乡土情结外化成对家园的热爱和迷恋。邓安克曾说:“我非常喜爱画家米勒,多少次我站在他的画作前久久不愿离开,他的每张作品都散发着浓郁乡土的芬芳。”他还说:“一到那些民居之中,就兴奋不已,我觉得我又回家了,我又能听到看到很多故事,我又能吮吸到母亲的乳汁。”他既栖身于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上,更用画笔在表达追寻和触摸着他梦中的精神家园。普吕东说:“我只画使我感动的东西,正像希腊人用斧头砍大理石一样,正像老斯惠林克人一样在大风琴上奏出的音调一样。”
(二)邓安克云南民族民居绘画的风格特征
1.梦幻般的空灵意境
邓安克的民居油画,总是表现出一种类似中国画一样的空灵。其画面所表现的民居形态和营造的意境,让人觉得是那么的熟悉,似乎触手可摸,而又是那么的悠远,遥不可及。一方面,画面上那些形态各异的民居建筑,只要对云南民居有些了解的人都能约略的加以辨识,大致能说出民居建筑所属的民族名称;而另一方面,画面所营造的空灵意境却又让人产生“此景只应天上有”的幻象。欣赏者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游移,产生了奇特的审美愉悦。
“空灵”本是讨论中国古典艺术的概念。司空图在《诗品》中形容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遇之匪深,即之愈稀”等等,就是具有朦胧、蕴藉风格的空灵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又说:“不即不离,不黏不脱”。形象地说明了“空灵”的基本特征——说此又非此,说不是又是。这是一种微妙的关系,正如“水中之月”看之即有,触不可得。从艺术家的角度而言,要创造具有空灵的意境作品就必须有空灵的心境,所以苏轼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内心要有自由之境才能创造那种空的感觉,有了灵秀之气才能体察外物之妙。
邓安克的民居油画就是极富空灵意境的创作,画面中弥漫着清透而迷人的易趣之美。宗白华说:“精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他引欧阳修的话:“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味之心难形。”说明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只有这令人“事外远致”的心襟气象,艺术中的神韵才能油然而生。
那么,邓安克营造空灵意境的心襟是怎么样的呢?邓安克之以民居入画,和他深埋心底的乡土情结有着极大的关系。云南有壮美的山河,众多的民族,可入画者多矣,为什么偏偏以民居入画,且一再表现,自成系列。居室住屋,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依存,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不是其物理空间本身了,它更体现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寄托。我们说,艺术起源于情感的传达和演绎,艺术家必须依赖社会认可的符号作为载体。邓安克之所以表现各式民居,除了个人文化偏好之外,我想这更是他的一种精神渴求和心理归依,在对民居的表现中体会艺术的空灵之气,体会艺术的淡泊之质。
2.静谧和肃穆艺术特质
邓安克民居绘画的另一个特征是画面意境的静谧和肃穆。
按常理,表现民居画面中多会出现人或动物,以求浓郁的生活气息。但邓安克的民居油画中却很少有人,即使有也只是作为点缀的符号。没有人或动物的画面,自然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宁静。观邓安克的画,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这种静谧之气。这种静谧意境给人一种超脱的孤独感与疏离感,即使是十分熟悉这些民居形态的人,也会感觉到画面中所透露出来的悠远和神秘的气息,这些东西离我们很近却又十分遥远,分明就在眼前,但似乎又不可触摸。这种奇妙的感觉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感受,仿佛孤独的灵魂渐渐地融入自然之中,与画面中的一缕炊烟,缈缈的一同飘向未知天际。
3.虔诚情怀的表达
邓安克的民居绘画在其梦幻般的空灵意境之中,还体现了画家宗教般的情怀。
云南民族民居建筑,大都多多少少都带有宗教元素,或是形制,或是构造,或是装置,或是装饰等等。其建筑本身体现着主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传统。从此中意义上来说民族民居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民族宗教的符号,宗教作为一种基本元素被融进了建筑之中。这里暂且不说民族民居建筑本身所体现来的宗教色彩,邓安克在表现这些民族民居建筑时所释放的一种潜意识的“表达”,他的这种“表达”可以称之为宗教情感的释放。
邓安克的民族民居油画创作,总是带着一种十分虔诚的心态,他把民居看成是神圣的精神家园,仿佛是精神栖息的圣殿,是理想国,是灵魂的归依之所。在邓安克的民居油画中,人仅仅作为一个符号的存在。民居是人居住的地方,但在邓安克的民居油画中偏偏缺少“人”的存在,这固然是艺术表现的主体体现的技术原因,但更是画家心灵深处的、潜意识的某种精神折射。画家是在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国,寻找自己的心灵栖所。他要对话的不是人,而是自然,是他心灵的“居所”,在这里,画家个体的生命力和人类的共有情感,人类的生命形式,构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特别是在高度物质化的现代社会中,宁静、纯朴、闲适,让心灵为之松弛的地方显得让人不可企及。画家在追寻自己心灵栖所时,仿佛不是用画笔在画,而是宁神静思时的想象,是在用精神构筑灵魂的皈依之所。邓安克是在用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心态描绘民居。
艺术家内心的孤独感使其作品承载了更多精神的自由。也许是不满于现代都市的喧嚣和尘世的纷繁,邓安克的目光总是投向云南的山野,投向那散布山野之中的与自然一体的星星点点的村寨和民居。也许只有内心的孤独才会产生强烈的对“家”的渴望。在人的生命中应该有两个“家”,一个是社会,一个是大自然。既然现实社会中的“家”总被喧嚣和虚假所充斥,那就选择另一个“家”——大自然。作为艺术家,对现实世界的敏感程度远大于常人,所以历史上那些伟大的 诗人和艺术家都曾有逃离现实社会的渴望,中外皆然,从陶渊明到凡·高都是这样,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他们与日月对话,与山水交友,与草木絮语,聆听天籁,放达自我;他们在自然中感到了温暖,在天地间放飞理想,内心获得了巨大的自由。邓安克的孤独感使他总想在山水间寻求片刻的宁静,民族民居被他生命化了,他在追寻着它们,在与它们对话谈天。在他的画布上,夕阳下、树林间、田野上那些或成片或独立的民居放射出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在用线条色彩叙述着那遥远的乡情。邓安克不但自己心向往之,也使我们心向往之。
邓安克在画布上也许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结语
邓安克的民居绘画除了色彩、构图、肌理等绘画因素之外,他更多的追求着情感张力的外化。在冷峻的精神孤峰上,展现着属于艺术和艺术家的孤独和内心的自由。
人人都需要精神家园,但艺术家却担负起了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拍卖锤清脆的声音跟艺术本身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正如艺术评论家邓启耀在评论邓安克的画作时说:“艺术家有责任重造我们的精神家园。”邓安克用画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着真挚情感的精神家园。
【注释】
[1] 蒋高宸编著:《云南民族住屋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1页。
[2] 何广政编:《爱与田园的画家——米勒》,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96页。
[3] 艾中信编著:《世界美术》,1983年第4期,第37页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