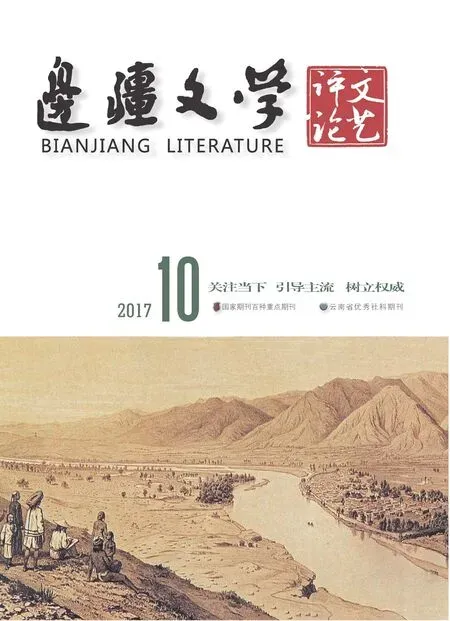社会大变迁时代的人文关怀
——读潘灵《偷声音的老人们》
田 野
边疆阅读
社会大变迁时代的人文关怀——读潘灵《偷声音的老人们》
田 野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或速或缓地都在不停变迁。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一个继承与创新、解构与建构、毁灭与再造的过程。在变迁平缓的时代,人们对这种创新、解构、毁灭、再造的感受并不那么灵敏,而在快速变迁的时代,许多人都能感受到由此带来的震动,或强或弱,或隐或显,包括震撼与惊喜、憧憬与期待,也包括挫败与失落、迷惘与惆怅、不适与痛楚。潘灵的新作《偷声音的老人们》(载《大家》杂志2017年第4期,下称“偷声”)深刻地触及了这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我们已经迎来并正在经历着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疾速最强烈的时代。可以设想,时光倒回三十年以前,如果有人说将来某一天,我们可乘坐时速四百公里的火车,早晨从北京出发,中午到上海享用午餐,或者将来某一天,人们通过握在手里的通信工具,可以真切地看到太空宇航员活动的情况,或者将来某一天,只需在一个小小的移动屏幕上轻轻点拨几个键钮,我们需要的美味佳肴即可快速送到自家餐桌,或者将来某一天,有人用电子屏幕买卖商品,形成数以万亿计的大产业,传统商场关门歇业,即使不被投进疯人院,也会被认为大脑严重进水。蓦然回首的不解与惊奇,正是源于这个疾速变迁的时代:科技快速进步,生产力快速发展,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
相比而言,自殷商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达三千余年,社会都是悠悠地变化的,即使到近代文明产生后,社会变迁的频率、强度及其多样性的后果,也远今非昔比。更何况近代文明对中国社会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多及于城市,对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传统农耕文明而言,冲击并不是那么快速和强烈的。潘灵笔下那些老人们偷声音的行为,就是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经受社会变迁强烈冲击的结果。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眨眼之间变成宽敞的大道、高耸的大厦、浩瀚的湖泊,这对人们心灵的冲击、情感的撕裂是可以想象的。这个家园,不仅仅是生存的空间,更是寄放灵魂的平台。说起灵魂,人们容易想到的是不见其影、不闻其声的空灵、虚幻的东西,甚而被认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其实不然,它一点都不空幻。那炊烟袅袅的山谷,房前屋后的桃李,梁前柱后的玉米棒子,满堂堆放的土豆垛子,浮满烟尘的老腊肉,布满污垢的老茶壶,还有那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位的神坛,也还有黎明的公鸡报晓、午后的鸟语蜂嘤、傍晚的蛙声蝉鸣,所有这些都是灵魂的物化载体,没有哪一样是空幻的。恰恰相反,它们的意义主要地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精神方面。就物质生活而言,现代城市生活比之要方便百倍。没有这些,并不影响物质生活,却活生生地剥夺了人们世世代代骨子里延续下来的情感寄托,解构了对生活的理解,动摇了对过往的敬仰,模糊了对未来的想象。这种环境变化的不适与痛楚,只有深植于农耕文明的人们才能深切体会到。
毫无疑义,这样的时代是令人欣喜的,是满满正能量。正因如此,我们告别了贫穷和愚昧,告别了封闭与落后,走向更为宽广的未来。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衣食如此富足,见识如此广阔,生活如此便捷。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社会疾速变迁也带来另一面:传统家园的消逝,生活环境的迁移,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会间暂地带来某种不适,或失落与留念,或迷惘与惆怅,甚或是一种千百年来故土难移的情感撕裂。权威资料显示,十年来我国有九十万个村庄消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平均每天有二百多个村落人去屋朽。对此,作家的意图不是试图去阻止或减缓这种变迁的进程,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去关注正在发生的一切。社会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时代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当大变迁的量变积累不足时,想快也快不了;当社会变迁条件发育成熟时,想慢也慢不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潘灵以他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感悟和对现实生活的细微观察,以某大型工程移民社区为背景,描写一群老年移民住进新社区以后的失落、挫败、困惑、郁闷、烦恼和种种不适。为解决这些问题,老人们组织自救队,偷录公鸡打鸣的声音来治疗杨玉明老人的失眠症。在偷声音的过程中,意外被送进派出所。社区主任韩晓峰委派市文联挂职体验生活的作家韩家川去处理。韩家川通过驾驶员小王了解了社区生活的许多隐秘细节,巧妙周旋化解了矛盾,把老人们领回社区。但社区老人们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问题依旧,不仅杨玉明老人,还有钟汉老人,也潜在地还有偷声音的老人以及其他的老人。移民社区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还有产业发展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社区服务问题等等。作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描写市井生活,展现矛盾纠葛,反映时代变迁,揭示移民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内在规律。
《偷声》的主题是当下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时代性话题:在社会变迁中,如何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一种历史情感的绵绵维系,传统习俗的殷殷依恋,孩童时代的美好回忆,现实体验的舒适感受,未来生活的懵懂期待。简言之就是能回味过往,能适应变化,能憧憬未来。为此,需要处理好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有一些东西是应当变的,比如在猪圈上层睡觉,无论它多么符合传统习俗,从科学与健康的角度,都存在许多问题,应当变;再比如巫师跳神治病,无论祖先使用了多少年,它都是过往时代人们认识能力和医学发展局限的结果,应当变;还有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建设项目需要迁移的村落,人们居住的环境总得变,这些都是社会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一些东西是不应当变的,比如农耕文明中淳朴善良的秉性、热情好客的情怀、你来我往的交流、乐于助人的品质以及传统的文明礼仪。还有一些东西只能是渐进性地变化,在破与立、毁与建、继承与创新、沿袭与发展中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乡愁需要一定的物化载体、文化仪式、生活范式,总之就是反差不宜太大,毁损不应太多,变迁的裂痕不能太深。
读罢《偷声》,笔者觉得有几点可稍加赘述。首先是主题重大。作品敏锐地把握社会大变迁时代脉动的节律,以工程移民搬迁社区为背景,以长期深受传统农耕文明浸染的老年移民为对象,以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生活为主题,准确捕获现代新型社区的市井生活,细腻描绘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反映人们的烦恼与快乐、困惑与希冀、迷惘与憧憬,进而揭示出社会大变迁时代人文关怀这个重大的时代主题。这体现了作家的大义与担当。
其次是入题新颖。一群来路不明的老人,或弱或残,莫名其妙地在“黑如铁”的夜空掩护下,神秘地跋涉在崎岖山路上,既像魔幻故事,也像侦探小说。要不是主人公们的体质状况,还会让人联想到: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这种落笔伊始就引人入胜的手法,一连串的悬念瞬间映入脑海:老人们为何方神圣?身处何境?究竟要干什么?偷声音?偷声音闻所未闻!偷什么声音?怎么捕获声音?偷来干什么?牵引读者好奇地一探究竟。待读者终于知晓是一个描写不城不乡亦城亦乡的移民社区的故事时,才从玄幻小说的空茫意境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继而想进一步探究我们的身边——这种司空见惯又熟视无睹的新式社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体现了作家的匠心独运。
再次是手法巧妙。作品安排三组相继出场后又陆续交织的人物有序入戏。陈三爷、麻脸大、疤老二、许老四、聋五,都是年届古稀的老年移民,他们引出后面的故事;社区主任夏晓峰、市文联干部韩家川、派出所沈所长、市文化局耿副局长、驾驶员小王,属于基层工作者,以他们烘托作品的主题;肖逸庶为代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官员,以他们拓宽作品的视野,升华作品的主题。这些人物都是鲜活而生动的,既有职业化的脸谱,也有各不相同的个性,仿佛都是我们身边的真实人物。作品以这些人物展开故事情节,突出创作主题,如同手撕笋皮,节节开剥,层层递进。先是神秘老人神秘出现。再是老人偷声缘起。一群祖祖辈辈当农民的老人,在城乡建设高潮中被迫迁离故土,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开始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浑身的不自在。无论它如何宽敞明亮,如何整洁卫生,如何阳春白雪,它终究不像自己的家。于是,人们怅然若失,寝食难安,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年老体弱的、故土情重的、带养身病的开始出现状况,心悸、失眠、幻觉、妄想,听不见公鸡打鸣就无法入睡。接下来是心心相惜的老人们开始组织自救队,寻找失去的声音,为杨玉明老人,也为每个人自己。但是,自救队的行为“萌”得近乎荒唐,结果惹出大事,把人家几千元一只的斗鸡给弄死了,意外进了局子,说不清,道不明,出不来。这是小说很有趣味的一个情节,符合乡村社会底层民众的行为方式,也契合民谚所说的“老还小”的人生过往规律。再往后,作品主题不断丰富和拓展,基层工作者渐次登场入戏,围绕文化传承、社区工作、产业发展、迎来送往等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突出矛盾纠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揭示作品主题,作品的拟人化描写精彩而到位,读起来有味。“音乐仿佛是一只莽撞的鸟,从窗外飞进耿副局长的办公室”,“这声音尖厉、高亢、嘹亮,甚至还显得粗鲁、蛮横,仿佛它是挤压出来的,是压抑了太久的,所以这声音是带了情绪的。它带着挑战,但似乎又不知道对手在何处,有点像失去方向的怒狮,只顾横冲直闯。”这种拟人化的生动描写,把麻脸大及老伙伴们的内心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那句“不知对手在何处”,反映了老年移民迁徙后莫名的不适与烦恼。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不适,虽然它可能不尽人意,但谁都没有过错,仅仅是莫名的压抑,燃的是“无名火”,这就是大变迁时代容易出现的焦虑心态的典型表现。唢呐这种非科班出身的民间乐器,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宏大、粗犷、厚重、豪放,如果演奏功夫凝练到家,可以不间断地循环换气,把演奏者的情绪发泄出来。在此可见作者观察生活的细微之处。老人们偷声的场景,正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真切空间,小说从头至尾使用的地名、人名、习俗、传说、物化标识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似曾经历的感觉,既可理解为艺术的渊源和超越,也体现了艺术与现实的契合。
最后是画龙点睛,升华主题。钟汉老人去世,许老四从乡下女儿家回来。陈三爷问他是否因为对钟汉老人有心灵感应,钟汉老人道出原委:“乡下那日子,再去过,就不习惯了,特别是在这社区坐惯了马桶,现在蹲那蹲坑,不仅脚受不了,鼻子也受不了,梆臭”。这一对白使作品主题得以理性升华,厚重感瞬间加码,令人深思。变迁是痛苦的,但变迁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那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铁律。作品点到为止,故事留给读者继续创作,特别是留给社会学家们和公共管理者们去创作。
笔者以为,这一点很有价值。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无限的解读空间,在于读者的见仁见智。读一部作品,有人看到阳春白雪,有人关注下里巴人,有人感受到窗户紧闭的压抑,有人为门缝里若隐若现的阳光而欣喜若狂。我不愿把《偷声》视为问题小说,仅仅读出“被城市化”的灰色幽默。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被城市化不一定是负面的,恰恰相反,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进社会变迁正向发展的需要,不应夸大被城市化的负面意义。只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顺势而导,应势而行,都是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正向能量。祖先的许多东西,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里面蕴藏着精华,也夹杂着糟粕,一律言好或决然否定似乎都不可取。一位名人说过:谁要忘记过去,谁就是背叛,谁想回到过去,谁就是疯子。这或许可作为此问题的最好注脚。我们不一律反对“被城市化”,要反对的是违背民意,忤逆民心,乱点鸳鸯谱,瞎指挥,穷鼓捣,胡折腾。
一篇小说,除了阅读消遣与欣赏,如果还能让读者在掩卷之后引起某种延伸的思考,那作品无疑是成功的。笔者想到的是,在社会大变迁时代,不仅被称为弱势群体的特定阶层,就是志得意满的人们也同样面临从生活方式到思维习惯的调试。这需要政策制定者、组织管理者、科学文化和社会工作者们给予足够的关切。在社会治理与服务中,见事见物又见人,既看到变迁带来的益处,也留心其间暂性的负面影响,以悲悯的人文情怀去关注那些变革中产生不适的人们。韩家川似为此做出了某种示范。他通过驾驶员小王去捕捉市井生活中不为人知的隐妙细节,协助基层组织化解矛盾和困难,甚至不惜为治疗钟汉老人的失眠症而学半夜鸡叫,结果被宫桂花泼了一身精心准备的屎尿,已经不是落汤鸡,而变成满身污物的落粪鸡。夏晓峰同样令人首肯,虽然似乎打上某种特定职业的烙印,但并非源于主观上的冷漠与麻木,而是一种习惯性的迟钝。事实上,不仅那位社区主任,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对时代跳动的脉搏并不都是那么敏锐的。面对社会大变迁时代人们的不适与焦虑,需要更多的韩家川、夏晓峰们行动起来,做时代的有心人,以更强的注意力、更勤勉的作为去顺应社会变迁的需求,探索大变迁时代社会工作的规律,化解社会矛盾,安抚社会情绪,为快速飞奔的时代列车安上减震阀,尽力减缓它对人们心灵感受乃至社会运行的冲击。应当说,写乡愁的作品不少,但《偷声》的主题超越了一般的乡愁,从小我之愁变成大我之愁,从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思乡情节跃升到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
笔者不是搞创作的,也不是弄评论的,对文学实属外行。以一名读者的阅读感受,《偷声》似乎也存瑕疵。本是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当我们跟随作者的思绪进入跌宕起伏的情节时,作品硬是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旧好与陈三爷生拉活扯在一起,既不搭调,也让作品紧凑感顿时消减,神走意游。小说要有人物,人物要有故事,故事要有内涵。讲述故事可以设置悬念,可以煽情,让读者跟随主人公命运同喜同悲,或扼腕叹息,或荡气回肠,或涕淌泪流,实现精神共鸣,情感共振,价值共融。在这个意义上讲,拉出半个世纪前社会变迁的长焦未尝不可,教科文组织官员的登场也无可厚非,都可拓展故事的视域高差,但官员旧交的登场就变成多余的累赘。要是把肖逸庶六十七年后回乡的情绪波澜变成唢呐文化传承的恩恩怨怨,或者顺着他欲言又止的对白揭示难以割舍的乡愁,那故事就变得更加紧凑而丰满圆润了。在人物角色安排上,沈所长办理“偷鸡”案的思维和语言不尽符合生活的真实,稍显牵强;作为年轻移民代表的豆腐西施宫桂花本该有更生动的故事来拓展作品的内涵,但多次出场却戏份不足。尽管如此,依然瑕不掩瑜,《偷声》是一部好作品。
(作者单位:云南出版集团)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