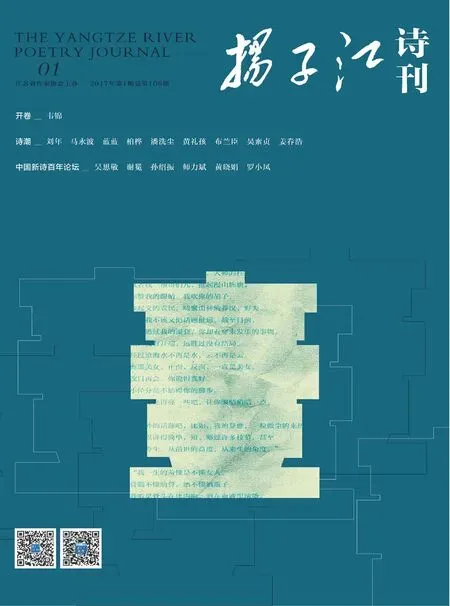我理解的好诗人(外二篇)
李 犁
○随笔○
我理解的好诗人(外二篇)
李 犁
1
我理解的好诗人永远是一个不随波逐流又特立独行的人。
好诗人是孤独的。孤独一是来源于他走在时代前面,思想的先驱都是不被人理解的;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坚持他所看见的,而不走别人的路,保持人的自然属性原始性,绝不让自我被大众异化,不与人同流合污。
好诗人是一个说真话,有正义感,对丑恶时刻保持愤怒,并永远说不的人。由此就构成了诗人与政客和商人的对立,在古代更与黑暗的统治者格格不入,因为专制的统治者都是肮脏和丑恶的集大成者。所以在古代,诗人的命运极其悲惨。
因此好诗人要和统治者保持距离,并时刻要拍案而起。苏东坡曾经问他身边的女人:先生肚子里是什么?大老婆说是学问,二老婆说是大粪,只有他喜欢的小妾说是一肚子愤怒。还是苏先生视为知己的小妾理解诗人。
好诗人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精神和品质的行为者,那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践行者。除了蔑视权贵还是质疑权威传播智慧的大者。不但说真话还要为真理而献身。他代表着社会的乃至人类的良心。所以我反对季羡林说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在真理被强暴的年代这样的态度是没有责任感的,更没有勇气。那我只能这样理解,你说的是废话或者是屁话。
好诗人是一个无缘无故去爱和恨,并把眼泪和金钱献给卑微的弱小者的人,也敢把仇恨和砖头献给欺凌弱小者的人。(虽然可能诗人最先被头破血流)。要“痛苦上升为同情的泪”(蔡其矫语),更应该是不痛苦也为别人的痛苦流眼泪的人。尽管他们的眼泪很廉价,甚至有时他们的介入可能更给被同情者添乱。
好诗人是一个遇到别人在意的事情,他们不在意,譬如功名利禄。别人不在意的他们却视为生命,并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譬如真理名誉爱情友谊等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
好诗人是一个胸怀广阔拥抱生活的人。诗人不应是一个狭隘者,屁大的事就耿耿于怀就上火甚至骂街。诗人的胸怀不能成为大海也要像广场让更多各种各样的鞋来把它踏实并拓宽。
同时诗人要永远保持热情和激情,热爱一切该热爱的。所以我反对诗人自杀,死不可怕,在不美好的生活中,敢于活着才是一个强者。我们既然不怕死,就从死的方向往回活。那样我们的人生即使不面朝大海也能春暖花开。
好诗人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不但能养家糊口,也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和热情。所以我反对诗人是寄生虫,更反对诗人以行乞为荣。
2
诗人永远是语言和艺术的探索者和创新者。因为有诗人,诗歌艺术永远在变化和流动之中。诗歌的最佳状态永远是喜新厌旧。先锋的新鲜的一旦静止就会变得平庸僵化,就会遭到遗弃和不屑。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歌永远在路上,永远是后来赶上者的艺术。
但是在今天做个诗人是很不幸或者很危险的。因为诗歌这块土地上,已经被古今中外的诗人们翻耕无数次了。所有的花样所有的手段都被诗人们使用过。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前辈诗人们的牙慧。
从民歌到朦胧,从英雄到平民,从崇高到平凡,从知识分子到民间写作,从诗意到口语甚至下半身甚至演变成光腚行为,除了大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其中不排除诗人们在集体突围,突破中外优秀诗歌的包围和技术上的牢笼,想走出一条没有足迹的新路。
于是越来越小的诗歌草原又被折腾成一片又一片的荒漠。诗人不愧是世界上最能折腾的拓荒者和语言的流浪者。诗歌永远在折腾中,诗人们在折腾中自己抚慰自己快乐。当他们从自我膨胀的梦中醒来,他们悲催地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上。
其实不论你给诗歌穿上什么样的马甲,都不是诗歌的灵魂,诗歌的灵魂是人的灵魂。诗歌的力量也不是你的吼叫谩骂,或者你的哭泣和沉默。题材无大小,诗艺有高低。床前明月光虽然渺小,但它能撼动灵魂,是因为作者的心灵和灵魂先被触及了。
因此诗人需要零和一。让诗人和生活零距离,让诗歌一步到位。换言之就是让诗人的心脏与生活的心脏零距离,诗人才能只一下就抵达诗歌的心脏。
3
最后要说的是诗人在今天的现状。只说普遍的。当下我们见到的更多诗人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人,分裂的人。没办法,为了生存需要流下屈辱的泪。这样的诗人也算不错的诗人,但不是大诗人和好诗人。而最让我鄙视的是拿诗歌当幌子,和丑恶勾结,利用诗歌沽名钓誉,甚至貌似真诚地歌唱虚假的伪诗人,劝告这样的以诗谋取个人私利的诗歌混子,你们肮脏的灵魂别再糟蹋诗歌,也别再往诗人这个圈里挤了,这个圈只能让你一无所获,丢人现眼,赔了夫人又折兵。
诗人需要一种支撑
诗人有时候需要一种支撑,这不是通常说的信念和信仰,而是具体写作时候的自信。这包括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自信和对自己生活现状的自信。
前者让我们敢写多写经常写,后者则让我们保持内心的平静,不慌张不浮躁。
自信哪怕是盲目的,对一个诗人也是有益的。因为过于理智和清醒会使我们的写作停顿或者夭折。我自己的体会是对诗歌知道得越多,看得越清晰越不敢写,觉得自己很多东西都不配叫诗。这样写作就陷入停滞和观望状态。
而对不如意的生活现状和生存状态的清醒和不自信会让我们整天焦虑,慌忙,犹如悬在半空中的鱼。这无疑会断送写作的好状态,甚至让我们对生命和生活开始怀疑和失望甚至绝望,很多自杀的诗人就是从这样的心态开始。
所以一个好的诗人要保持这种自信,哪怕是盲目的糊涂的,甚至是阿Q的强加给自己的,也要坚持并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才能真的贫穷能听见风声也是幸福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包括所有诗人,都是多余人。就是那种游离生存核心,在生活边缘背着手,睡眼蒙眬地四处张望的一群闲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也并非全是诗人不合作的生活态度,更多的是与生活本身不需要他们,而他们又不知道怎么介入生活有关。
其实在社会变革和重大事件中,诗人从来没有缺席,而是呐喊着冲锋在前。这是天生敏感激情和不可遏制的冲动的性格使然。诗歌从来没有回避过生活的洪流,只是二十几年来,由于整个文化都处于边缘地带,诗歌只好被迫地去挖掘内心和潜意识,在技术上做自身的探索和完善。这种写作状况使诗歌成为私语者,也使诗歌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读者和生存空间。
但是诗歌没有消亡,这是因为诗人的良心和责任还在,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旦时代呼唤,他们会义不容辞地递上自己的肩膀和使命,让诗歌再次成为带领时代呼啸前进的大纛。
2008年5月份的汶川一场大地震彻底让诗人和生活发生了共鸣,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诗人与生活与时代与民族休戚与共,肝胆相照,诗歌本身也在这次大事件中,有了方向,有了温度,成为有血有肉,能安抚人的心灵,振奋人的精神的一杯水一块面包一面旗帜。
我终生难忘我在北川的十个日夜,那是我老泪纵横的十天。它让我感受到真正的苦难和力量。每天几乎二十个小时的工作,让我无比的疲劳也无比的充实,我从没感到自己会这么有用。我虽然没能像消防战士那样搬运钢筋水泥,但我可以把一瓶水,一个面包亲手送给那些正经历着噩梦的老乡们,我也可以一天弓着背一张张写着遗失人群的名字。当我用结结巴巴的语言朗诵着自己的诗歌,看见孩子们因为我的存在眼睛里没了暂时的悲伤,我内心涌满了巨大的幸福。
这就是生活的核心,诗歌的源泉。我记下了他们,我记录了时代,诗歌就是紧紧拧在生活和时代上的一个螺丝帽。我也更加明确了诗人和诗歌的本质——爱!永远的关爱,无缘无故地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诗歌和我的胸襟还有我的人生都因此而变得广袤和踏实。
这些再次证明,看似无用的诗歌,总是在人生关键的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当一个人最幸福和最悲痛的时候,譬如人在恋爱时候或者生死关头,都会想到诗歌,或者写几句或者念几句来抒发情感或给自己壮胆。这说明人和时代是需要诗歌的,当然好的诗歌永远离不开人的情感,人的心灵,人的灵魂。所以诗人们在写作上需要更直接的,单刀直入的一步到位,而不是一味地让诗歌穿靴戴帽,花里胡哨甚至于云山雾罩。诗歌和其他体裁一样,也需要生动的细节,而永远拒绝假大空。
所以诗歌和诗人应该是苦难的承载者,和苦难同行,给苦难中的心以温暖同情和力量。我也鄙视那些用诗歌去粉饰太平,尤其是整景的虚假的根本不存在的繁荣和高大,这样的诗人是给权势者擦屁股,借诗歌实现自己的野心,最后脏了自己埋汰了诗歌。因为真正的诗歌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何况实际上没有“锦”,添得也不是花。
诗歌始于地理
上世纪被称为乡村诗人的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声称:“文学始于地理”。他出生在美国西部,但一直生活在新英格兰的乡村。乡村的生活成为他写作的地理和源泉。他用浪漫来美化乡村,目的是以此来提升弱势地域和人群的价值,来缅怀和提示的理想乐园。并以此来与当时的强势主流抗衡。这里乡村仅仅是诗歌乃至于他思想和行为的符号。
真正的乡土诗人是一个被乡村的地理从里到外彻底同化了的人,他就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一棵植物,他自己本身就是乡村地理的一部分。他从骨子里热爱这片土地,也深爱让他灵魂出窍的诗歌。但当他从都市深入到乡村的本质,浪漫和唯美与乡村的苦难和残酷相遇,他的写作就出现了凝滞,甚至凝重。于是诗歌就染上了感伤。
所以真正的乡土诗人绝不是浪漫主义者,他诗歌中的飞扬和唯美仅仅是他对诗歌文本魅力的本能追索,当写作与现实相遇,他就从虚妄的空中回到了真实坚实的大地。他就开始悲悯大地,忧虑现实,他们是善良又怀揣美好的现实主义诗人,这让他们诗歌的视角一直向下,直到抵达土地的核心和命运的根。那些轻到风中漂浮的风沙、枯草,月光和梦想;那些重到永远无法移动的龟裂的大地和灾难;还有这中间忙于生忙于死的人和牲畜,怨妇的眼睛和壮汉的臂膀,都成为他们诗歌中哀伤与同情的对象。这让他们的悲悯和关怀,审视和批判都那么具体并可见。
但是有时焦虑和担忧把本来清亮的诗歌变得凝重和疼痛。就像一条流速缓慢的河流,远远看去,平静明亮,但走进水里,你会发现光洁的表面下挟裹着很多复杂物。这些水下的东西让诗歌的色彩深沉,也使思想凝重。
其实大地上永远没有卑贱者,卑微与伟大都是乡村的主人。怎样超越苦难,让愚昧消亡,让幸福降临,让美好永远,这是乡村诗人的母题,也是他悲悯和关怀的终极。
不能不提一些伪乡村诗歌。有些诗人为了写诗,在遥远的城市,在空调的冷气弥漫的书斋里,抒写着烈日、镰刀、庄稼和农事,用一粒稻谷,一粒麦子甚或一片白菜来冒充乡土诗和充当乡土味。而对乡村的精神,农民的命运还有大地的气息却无法深入其中。这隔靴挠痒的写作,让人感到苍白和枯萎,像没了血液的干尸。
好的乡村诗歌让人看到了鲜活,感到了血液在流动,仿佛听到了一种生长的声音。这是生长着的诗歌,有生命的诗歌。
当诗人的情感与贫穷的乡村彻底和解,换了心态的诗人开始对脚下的土地顺从甚至匍匐,像一个仆人和儿子,这时他会把诗歌中的杂质挤出,让文本变得更纯粹和自然。此时的乡村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种象征,一种被筛选和提纯了的美和黄金。这时诗歌变得平实而单一。不需要隐喻,也不需要色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要任何粉饰和漂亮。只要真,唯有真实才是最好的颜色。这也让诗歌文本变得实实在在,可亲可爱起来。
彻底地返回大地,回归自然和童年,摈弃所有的装饰和技巧,让心灵和文本一起真实自由朴素简单,让我和物融合,忘记自己,以便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用河流来比喻,那就是秋水。所有的裹挟物都已经沉淀,河面和河底都呈现出透明和清澈。
但越简单的越难。云山雾罩地弄点形容词和不着边际的比喻是最容易的。简单却变化无穷,它不仅需要作者的技法,更需要作者有相同的心灵和品格。一个卑下的灵魂永远不可能做出伟大的行为。只有心灵和品格已经操练到和青草一样朴素简单的境界了,并陶醉甚至沉醉其中,才能在卑微的草上发现诗意,这是用自己的心去对应另一个心,用自己的品格去迎接另一种的品格。
中国古代禅宗认为的人生三境界,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用在写作上就是说写作伊始,只是对事物简单地摹写和照搬,后来发现这样太死板且没有情趣,就开始否定真实,用想象和比喻来改变山水和其他。再然后发现这一切太花里胡哨,太虚假和不真实,于是重回原来,真山真水,返璞归真。然而人回来了,但心态和精神不一样了。写出来的虽然还是那山那水,但境界已经升华。
只有经历了人生的真真假假,繁繁华华,才能洗去铅华,才能感悟出只有真实自由、简单朴素才是人生和艺术的最高境界。也只有具有了这样的心态和境界才甘愿做故乡大地上忠诚的儿子,才能自由自足自在地用文字素描大自然,才能做一个真正的用诗歌演绎乡村的哲学家。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圆桌○
(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