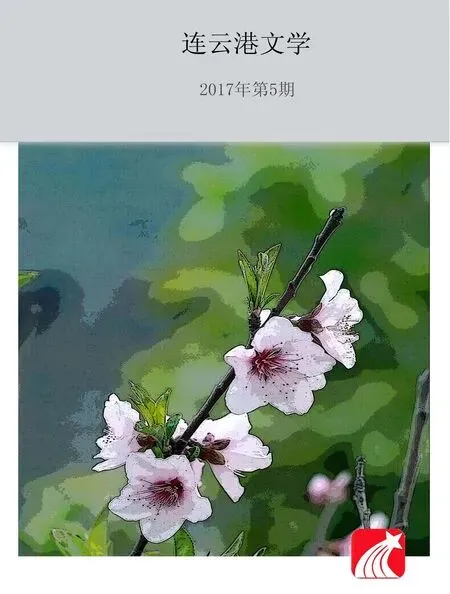槐香五月(外一篇)
王秋霞
槐香五月(外一篇)
王秋霞
又是槐花飘香的季节。
乡村的五月,是槐花盛开的季节。成串绽放的槐花,垂挂在绿叶纷披的槐树枝间,散发出阵阵扑鼻的清香。嗅着花香,放慢脚步,放飞思绪,让记忆沿着一路花香,再次回到童年的五月,遍游从前熟悉的地方。
童年时光在姥姥家度过。姥姥的家在沂蒙山区——一个长满槐树的村庄。三十多年前的五月里,农家院落、道路的两旁、山野村头,那一嘟噜一嘟噜白白的槐花,远远望去,仿佛树冠上覆盖了一层白茫茫的雪。在一个整洁干净的四合院门前,我的姥姥摘了一簸箕的槐花,满心欢喜地等着我的到来。
每年五月,母亲会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驮着我走过一段长长的山路,然后再乘船过一条宽阔的大河,下了船再走一小段路,就来到了槐花飘香的村庄前面。姥姥的家住在村中间。姥姥家的前门是前街,长长的青石板路自西向东延伸。石板路上,走着我曾经熟悉的人们;姥姥家的后门外,是后街,有一个三十多亩的槐树林,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
每次去姥姥家,我都兴高采烈。一进村,我就急迫地大声喊起姥姥来。姥姥张开双臂,高兴地答应着我,一只手把我从从母亲背上轻轻地抱下来,把我拥进怀里;一只手端起盛满槐花的簸箕,笑着问我说:“姥姥的小宝贝,到姥姥家累喽,饿了吧,姥姥这就给你做槐花饼吃去。”
清清的水面,映照着姥姥曾经端庄、典雅的影像:明眸、皓齿、银簪。一双修长的手,轻拢慢捻,揉捏压擀,于是,花香入面。
屋外,炊烟随风而动;屋内,母亲和我坐在灶前,添着柴火,火苗跳跃着舔着锅底。姥姥在灶台和面案之间忙碌着。在我的期待中,铁锅里飘起缕缕的香味。姥姥的槐花饼,两面焦黄、里面滑嫩、香味浓郁。
烙饼的白面,应该说是年上“吃剩下”的年货。年初一至初五的早上,都要吃饺子的。一年的白面,除了这几天外,就留下来,等到四时八节,姥姥就会用白面做出相应时令的各色面饭或面点。
色香浓郁的槐花饼做好了,姥姥把饼放在面案上,用刀切开,一小块一小块的,很均匀。姥姥搂着我,微笑着把一块饼,用干净的玉米皮包起,露出一大截,递到我的手上。
“槐花白槐花香,槐花深处是娘舅庄;槐花饼香又香,俺去姥姥家把饼尝;槐树林长又长,老娘舅疼外甥没二样……”姥姥教会我很多的歌谣。淳朴的歌谣声中,我感受到姥姥大家庭中,那份古朴、真挚、绵长的亲情。
姥姥妯娌四个。于是,我就有大姥姥、三姥姥、四姥姥。大姥姥家里有一个大我三岁的表哥,名叫桑墩;三姥姥家里有一个长我一岁的表哥,石柱子;四姥姥家里有一个表妹秀儿。
姥姥用干净的玉米皮把槐花饼分成三份包起来,让我拿着。然后驮着我,走到后院的槐树林里,去找表哥和表妹。槐树林枝繁叶茂、鸟鸣阵阵、花香浓郁。正在树上摘槐花的两个表哥和秀儿表妹,在枝叶间应着姥姥的呼唤,一个个哧溜溜滑下树来。桑墩表哥边吃槐花饼边拉着我的手,对姥姥说:“二奶奶,我奶奶今儿早上还念叨说,槐花都开了、家里的樱桃也熟了,你江苏的表妹再不来,这满树的樱桃你们三个小馋佬都已经吃一多半啦!”
小时候,我管大姥姥叫樱桃姥姥。大姥姥家在槐树林的东边,家里有一颗碗口粗的樱桃树。姥姥心灵手巧,会做各式的衣服、鞋子、会剪纸、会画画……姥姥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但姥姥很少闲下来,槐花飘香的季节,姥姥会把那些干不完的活,带到槐树林里干,看护着我和我的表哥、表妹。樱桃熟了时候,大姥姥上工前,常会用她的蓝布大襟褂子,兜一大兜的红樱桃给我们四个。
三姥姥的煎饼烙得跟纸似的薄。我们用煎饼卷着槐花还有咸菜丝吃,一样津津有味。四姥姥最年轻,穿着碎菊花图案的对襟褂子,我喊她花姥姥。花姥姥常常抱着我,领着表妹秀儿在槐树林里捉迷藏,让我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找到做游戏的快乐。
小时候,一直不会走路,姥姥、大姥姥、三姥姥、四姥姥背上的光阴,是那样的踏实、温暖。看着桑墩表哥他们在树上爬来爬去,我心里很着急。我拉着姥姥的衣襟小声对姥姥说:“姥姥,我也想去爬树,去摘槐花。”
我的一句话,竟然把姥姥她们的眼泪扑簌簌地惹下来……
姥姥放下手中的针线,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说:“好孩子,你以后会爬树的,也会走路的,姥姥挣的钱都留着给你看病用……”
姥姥们在槐树林里静静地坐着,我从姥姥的怀里,依次被大姥姥、三姥姥、四姥姥抱过去,姥姥们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一颗颗滑落在我的心里……
在姥姥们疼爱的目光中,童年的槐花香携裹着我,一步步远离了那个亲情洋溢的槐树庄。
槐花纷飞,渐渐远去;花香缕缕,牵动我情,思绪在童年的五月里放飞,放飞在那一片白茫茫中,放飞在我童年的欢乐里。让我忘却眼前的繁忙,让我疲惫的心灵随着槐花飞扬……
那时的故乡时光缓缓
田野之上,阡陌纵横。
一轮夕阳,缓缓落入岗岭上的那片松林。
哞——哞——牛叫声穿透渐渐笼起轻纱似的薄雾,荡着悉悉簌簌的秋声,不紧不慢由远及近……
30多年前的故乡,时光缓缓,耕牛遍地走。
农耕时代,牛在乡亲们的心中,那是个金不换的宝贝。小牛犊一降生,乡亲们就会把一个铜制的小铃铛拴在牛的脖子上。
故乡的田野连绵起伏。春来,一层层梯田一层层绿,赏心悦目;秋至,七沟八坡十面梁黄红绿相间,色彩斑斓。故乡四季美如画,但是,播种、收获季节手提肩挑的艰难,浓缩在乡亲们古铜色的脸上;犁田、驮运等大部分繁重的农活,落在了牛的身上。
初春,牛爷爷和三三两两的乡亲们吸着旱烟,扛着犁头牵着蓄养一冬的耕牛,悠闲地向农田走去。牛蹄轻快地踩着羊肠小道牛铃叮当悦耳。经历秋冬的霜冻雨雪,田间地头板结的泥土变得异常松软。牛爷爷架好犁头,轻吼一声,牛儿开始将积蓄一冬的力量奉献给它的主人。犁头缓缓地穿梭在土壤中,发出沙格棱棱的声音。
牛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并不姓牛,不知咋的,乡亲们都热情地称呼他——老牛。老牛像头牛一样,谁家有活,随叫随到。我们喊他牛爷爷。牛爷爷吃住在牛宅照看生产队的牛群。那会儿,生产队的牛有10多头,集中圈养在村后的牛宅上。牛宅坐北朝南,有10多间牛棚连在一起。牛棚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场地,供牛白天晒太阳,最南端并排6、7个长方形的化粪池。牛爷爷的3间牛屋靠西头紧挨着牛棚,牛宅大门朝西。
牛爷爷的牛屋里摆设很简单,除了牲口槽、架槽杆、拌草棍、料缸、草筛等工具外,就是一张爷爷睡觉的木头床。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村里的石头哥他们一起给牛爷爷放牛。石头哥是我们的牛倌。
放牛的日子,是悠闲的、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甚至是很惊险刺激的。我们胆小喜欢看牛吃草,看着牛长长的、灵巧的舌头,不住地将青草卷进嘴里。牛吃草的时候,会不住地、很有节奏地甩动尾巴。牛吃饱了,软乎乎的舌头,轻柔地舔着我们黑黢黢的小手。石头哥胆大心细,会在牛身上给我们表演惊险刺激的高难度动作。
石头哥吹着口哨,站在牛背上。牛开始走动,石头哥稳稳当当地站着,接下来,一个倒立,竟然倒立在牛的脑袋上,两条腿举在空中,一会儿并拢在一起,一会儿分开。来回几次之后,石头哥会翻身再次骑在牛身上,用脚后跟猛一敲牛的肚子,牛便飞快地哧通哧通地跑起来,四蹄不停地掀动,将一块又一块的泥土掀到空中。这种跑动是威武雄壮、惊心动魄的。有时,牛会哞——地对天大吼一声,似乎整个岗岭都在颤动……石头哥玩够了,会翻身下牛,躺在草丛中。牛喘息了一阵,扇动几下大耳朵,便低下头,安闲地吃草。
放牛归来,我们稳稳地抓住牛犄角,坐在高高的牛背上,随着石头哥很威风地走过田野,那时,眼睛里只有天空,只有起伏的田野。牛蹄叩击着干硬的黄土路,发出噗哒噗哒的声音,悦耳动听。
等我们放牛归来的牛爷爷,会坐在村头老槐树下的石碾上等我们。
缓缓的少年时光里,与牛相伴,有一份简单、朴实、温馨的乡情。
夏收时节,庄稼登场了。金黄的麦穗一车又一车地运送到场晒场上。“五月田,早一天长一拳”。刚收过麦子,趁着墒情青壮年劳动力牵着壮牛抢时耕种。晒场上有妇女负责翻晒,夜晚牛爷爷打场。
打场的牛是老牛。牛老了,拖着那个青石磙时,显得很吃力,牛爷爷看着它慢吞吞的步伐,尖尖的、塌塌的屁股,很心疼。牛爷爷没有办法,还得大声呵斥它,甚至偶尔还要举起鞭子,在它的身体上抽打一下,催它脚步快点。
牛爷爷也疲乏至极,一边打盹,一边跟着滚动的石磙哼着号子。牛爷爷哼号子,一半是催牛,一半是让自己醒着。
夜深,牛爷爷的号子声,在清冷潮湿的空气中飘荡着,显得有点儿苍凉。
灯光昏黄,一场麦子打下来,老牛的脸上流下两行泪来。
当场上的麦秸秆碾得平展展的时候,就要翻场,然后接着再碾。通知翻场的是锣声。
锣一响,姑娘媳妇就拿了翻场的草叉,往场上跑。
夜里,劳累一天的姑娘媳妇,一时醒不来,那锣声就会长久地响着,直到她们一个个打着哈欠而来。
第一场麦子碾下来,很快就按人口分到了家家户户。
新麦子有淡淡的麦香,放在石臼里捣捣,做成大麦粥,香喷喷的。牛爷爷他们舍不得吃,用鼻子嗅着这醉人的香味。互相慨叹着新麦粥的香味。石头哥和我们端着大黑碗,在月亮下嬉笑着、走动着,走到谁家,都有麦粥喝。
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吃了几天麦粥,脸上又有了红晕,身上又有了力气。
时光缓缓的岁月里,故乡像一辆破旧的牛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风里雨里地向前滚动着。车轴缺油,轮子破损,各个环节都显得有点松弛,咯吱咯吱地转动着,样子很吃力。但,它还是一路向前。在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乡亲们牛一样地默默耕耘、负重,力竭而逝。
秋天,又是一个忙碌的季节。
朦胧的夜色中,牛爷爷他们弯着腰,背着山一样的庄稼,吃力地往村里赶。牛爷爷的老牛老了,牛爷爷舍不得使唤了。
牛爷爷的牛通人性,从不偷懒,耍牛脾气,甚至比人还温顺、厚道。它们默默地随着主人干活。有时高兴,它们会对天长吼一声。一年四季吃草,农忙活重时,才能吃上豆饼渣、麦麸什么的,生病时,才能喝上一盆豆浆。它们与牛爷爷朝夕相处,要是几天见不到牛爷爷,再见时,就会伸出长长的温暖的舌头,舔舔牛爷爷的手背,牛爷爷由着它们舔,从不在意它们湿漉漉的唾液。
秋风一天凉似一天。树上的树叶干焦焦的,纷纷坠落。
最后一行雁阵飞过故乡灰蓝的天空后,连绵起伏的田野变成一片片没有光泽的黄褐色。风一大,枯枝败叶打着旋儿碰撞,发出沙沙声。
秋天走完了它的全部行程,冬天到了。牛爷爷已经好几天不能吃一点点东西了。
牛爷爷的那头老牛少了牛爷爷的照顾,也像牛爷爷一样倒下了,看上去没有任何原因。牛爷爷的老牛倒下去的时候,声音很大,如墙一般倒下的声音。
石头哥他们和我一起跑到牛栏边。
老牛倒在地上无助地看着我们。它没有长鸣,甚至都没有发出轻微的哼唧声,它竭力地抬起似乎特别沉重的脑袋。老牛的目光极度疲惫、温顺、慈和,微微睁开眼睛,用尽力气,给我们一个慈祥的笑容。
老牛,在牛爷爷之前走了。
岁月轮回,时光流转。故乡那段浸透了汗水、泪水与欢笑的清苦岁月,悠悠远去,渐行渐远……
许多年后的一天,在县城的广场上,猛然看到一座耕牛的巨型石雕——高昂的牛首,呈四蹄有力地向前奔进之势。瞬时,我的思绪向着记忆深处的故乡奔跑而去,那段时光缓缓的岁月,那片贫瘠的黄土地和土地上那些牛一样劳作的乡亲,鲜活生动地扑面而来。
那段缓缓的时光,珍藏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流淌在血液里。那个地处偏远的小乡村,不仅仅是哺育我的故乡,它是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我,和清贫、朴素、艰难的少年的回忆在一起,永远无法分隔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