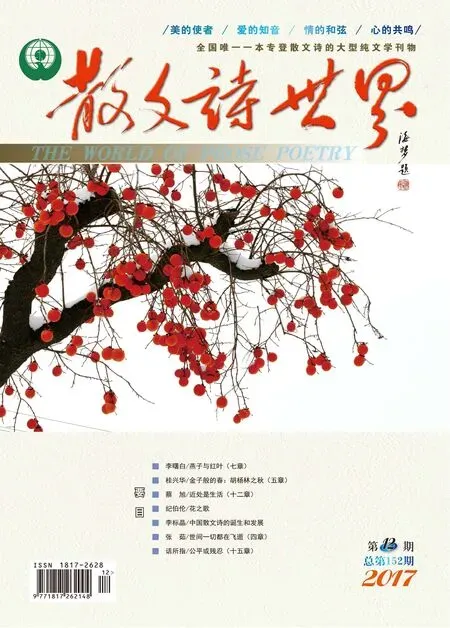近处是生活(十二章)
蔡 旭
近处是生活(十二章)
蔡 旭
借 光
熄灯睡觉时,妻子要把窗帘拉得很紧很紧。
不能让一丝楼外的光线,入侵她的安眠。
我却是相反。总要偷偷把窗帘,掀开一点点。
即使只是一线天,也很关键啊。
不仅在起夜时,它可划出一条指引。
更得有一丝光明——
照亮我的梦境。
疼 痛
我的左上臂,莫名其妙地痛了起来。
几个月了,一直在痛,越来越痛。
痛得举不起来,痛得提不了东西,痛得睡不着觉。
有人说是肩周炎。
外科医生说是肱骨外上髁炎,又叫网球肘。
骨科医生说是四边孔统合征。
拍片结果,说是脊椎关节病……
这伤病不管姓什么,总有一个相同的名字:痛!
我把自己交给疼痛专科诊所。
医生按着,我不禁喊了起来。他说:这就对了。
一针刺入,痛得我呲牙裂嘴,也只好拼命忍着。
这时我见了墙上的标语,才终于乐了——
“疼痛是生命鲜活的感知。”
哦,知道疼痛的人是幸运的。
尽管痛,毕竟开了一张存在的证明。
面包树
现在才发现,我在这个住宅小区里,已经与这些面包树同居三年了。
在我住进来之前,它们在此已固守多年,一直同小区居民们毗邻而居,不离不弃,又互不过问。
只知它身高叶密,站在行道上可美化视线,站在酷暑中可遮出荫凉。
它阔大的叶片,一把绝好的蒲扇。女人拿来遮阳,小孩把它挡雨。
现在看到树上累累的果实,一问,才知它竟是大名鼎鼎的面包树。
据说它是天然面包厂。果实含有大量淀粉与维生素,营养很丰富。
把果子从树上摘下,放在火上烘烤,就是松软可口、酸中有甜的美味。
我忽然想起艰难的少年时代,曾在地理书上读出了对它的渴望。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充饥,我吃过糠包、豆腐渣,甚至红树林的种子……
如今,面包树就在面前,却无人赏识。
让它熟透的果实,一颗颗坠烂在草地……
是不是这小区的人们,也都和我一样?
躺在富足的日子上,不再担忧舌尖与肚皮。
已是无欲无求的境地,不再追求未知的新鲜。
你我他,无论熟悉与陌生,一样擦肩而过……
街边榕
很惊讶这一排街边的大叶榕,为何在台风的考评中,一败涂地。
不是说它们老实、稳重、坚定、顽强,才选拔到关键的岗位?
平日里,它们绿荫如盖,遮雨蔽日,被评作年轻有为的标杆。
连小鸟也只围着它们奏鸣。
说倒就倒了。被不讲情面的台风,评定为经不起考验。
不过,获得高分的也是榕树,它稳坐在公园里。
撑起了天空,靠的是抓紧了大地。
一条条下垂的气根,落地就能生根。
街边榕的失足,看来不是因为选材,也不因为年轻。
它也长胡须呀,在微风中也飘得有型有范。
只可惜,街边的地皮太宝贵了。
人们总是把它们的须根剪掉,不让它们顺理成章落地……
清洁工
带着无法清扫的年龄,古稀之年来到城市。
日复一日,打扫时光,及时光的遗弃。
凭一把劳累大半辈的骨头,不愿接受子女的供养。宁可忍耐物业公司的苛刻,领取没有保险的低薪。
潮涨潮落的汗水,在工作服上绘制变幻的地图。却让楼层与梯道,光洁如镜,一尘不染。
整栋楼的人上上落落,每天都与他擦肩而过。很少见有人点头或招呼,只当他是自动转圈的机器。
有一天,人们突然记起这个不知姓名的老人。
地面,正绽放烟头与纸屑的花朵;梯间,弥漫着无法抵御的臭味……
想念是如此迫切,似乎他比市长还要重要。
还不可或缺。
留 影
不一定景色拍全,不一定角度最美。
把景区的招牌拍进来就行了。
不一定眉清目秀,不一定眉开眼笑。
不会被错认是别人就行了。
对帮忙拍照的人,我这样说。
我站在时间中间,站在往事中间。
固定的是身影,移动的是风景。
不变的是本人,变动的是年龄。
我是一支标签。
把记忆留下,把生活填满。
无字的“到此一游”。
有据的以照为证。
父 训
那时候我们小,不懂得相让。
对好的东西,只知道争抢。
我和妹妹,都喜欢吃白菜的心。又嫩,又软,还有一点清甜。
两双筷子,就在菜盘子上空刀枪交加。结果是,妹妹的脸上下起了大雨。
父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只是说了一句话:“这不是菜心,它是菜头。”
菜头又粗又硬,还有根须,不是我们所爱。
于是风停雨歇,让我们啼笑皆非。
六十年了,父亲早已不在,这句话还在。
那片由嫩变粗的菜心,一直放在我的眼前。
让我往往在蠢蠢欲动的关头——
顿失了争抢的冲动。
回 暖
盖了一个冬天的棉被,也出来晒太阳了。
久与寒冬为伍,已变得潮湿、板结、僵硬、笨重。
在与阳光亲密接触之后,终于恢复了初心。
舒展了,蓬松了,轻软了,暖和了。
又同先前一样,可亲可近,人见人爱。
总是会变的。会变得冷硬,也会回归松软。
只要能听从阳光的感召,都有好转的可能。
何况,它毕竟有良好的本性。
有一片,雪白而柔软的心。
蚝 炸
蚝炸的妙处是内软外脆。
酥脆的是米浆糊成的外皮,柔软的是生蚝,鲜嫩的代名词。
更妙的是可以亲见它的生成。
一勺裹着许多小蚝的米浆潜进油锅,不一会,就浮起一艘喷香的游艇。
点几粒椒盐,包一片生菜,才不会上火,别有风味。
一个小摊坐在黄昏的街口,围拢着一排等候的大人,以及一圈渴望的小眼睛。
小时,我也是围观中的一个,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能偿愿。
总要观望多少回,才有一次心满意足的品尝。
正因机会的难得,才有了更多的回味与挂牵。
据说有一位从小被拐卖的人,在远方偶然尝到了它的美味。
忽然唤醒了童年的味觉。
连忙追问掌锅师傅从何处来,竟然找回了他丢失的籍贯。
还天外归来,哭倒了一片望眼欲穿的亲人。
气 球
越吹越大,越吹越大。
看着气球逐渐膨胀成一只篮球,小孙儿不禁鼓起掌来。
他举着它到处奔跑,像举着一面旗帜。
把它抛上空中,跌下来,又拍上去,让它在空中飞扬。
只半天,就玩累了。他把它放在房间的一角。
第二天,篮球不见了,只见到一个拳头。
孙儿很不解:怎么会这样呢?
我是知道的。
没有人吹它,没有人拍它,没有人理它——
它自己,也会泄气。
老 钟
不甘为时间所管,便听从了王禄松的诗教:
“干脆变成一个钟,去管时光。”
用一只大手,去指示钟点。
用一只长腿,去分秒必争。
为了不落在时间后面,把发条上得紧了又紧。
日夜兼程,风雨兼程,睡觉时也得睁着眼。
奈何长年累月,我的钟终于败下阵来。
多次修整,仍然力不从心。
气也喘了,腿也短了。
睁着眼,听时间的马蹄声擦肩而过。
我和我的钟,带着老胳膊老腿,蹒跚而行。
尽管总是走在时间后面,但毕竟几十年了——
总算没有虚度时光。
唱 歌
哦,多久没唱歌了?
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节,快过60年了。
在洗澡房大吼大叫的岁月,又过50年了。
唱忠字歌的狂热时代,也过40年了。
30年前流行歌泛滥,想唱而不好意思张口。
20年前卡拉到处OK,没有勇气去抢话筒。
10年前,所有的激情热情抒情全都跟着退休了。
哦,多久没唱歌了?
现在却被朋友圈鼓动,而跃跃欲试。
说它同喝水、睡觉、走路一样,是养生的必备。
说它比跑步与游泳,还更为健康。
老中医说的,还能增强免疫、舒缓压力、预防疾病。
谁不想享受美感、排遣郁结、心旷神怡?
唱歌这么好,谁不想唱?谁不愿唱?
当然我也要唱。
不敢向着高山大海唱,不敢向着大庭广众唱,我也会——
在心中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