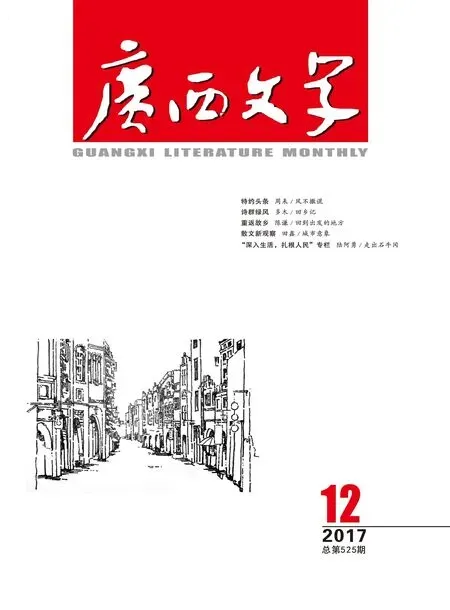被风吹凉的夏天
唐丽妮/著
1
深深的巷子,仿佛是在地下,有风,黑乎乎,总也爬不到尽头。
那时,我大概还不到一岁,站不起来。爬累了,就两手撑地,仰起头来望过往的大人。可是,没有人理会。只有放声大哭,才有人蹲下身来,拍一下我说:“哭哭又笑笑,鸡儿鸡母带入庙。”庙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个暗的小洞口,我看见一只鸡儿钻进又钻出:咦!洞的那边就是庙吗?那里面静悄悄的,偶尔传来一阵响,一阵凉风。等稍大一些,我才明白,洞里那片幽深也不是庙,是洗凉房。
但后来跟人讲起这些,没人相信我这记忆深层的情景,都说一个小屁孩,不到一岁,哪会记事?可我明明就记得呢。或许,人类记忆的源头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比如我,对于一个“庙”字的好奇与探寻,看到的却是一个农人洗净泥巴的地方,以及泼水时带来的凉风。
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我们一家借住一个远房叔叔的房子,但这房子原也是我们家的。老屋是一座很大很深的宅院,有个名字,叫兰亭家祠。三座两廊,厅堂悉备,头座两边侧室墙上嵌有十多块石碑,上面刻着祖宗的遗训,是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留下的。
从黑的巷子,爬到老屋大门前的微阳下,似乎很快,也似乎很慢。只因记忆自己会有许多取舍。
我已是能跑能跳。阿公带着我和弟弟来到大门前,龙眼树下,水渠边。渠水不是很清澈,老屋的两个女人在那里洗衣服,几个比我大的孩子光身子玩水。
我扯着阿公的裤腿。阿公抱着弟弟。弟弟光着屁股,玩阿公的胡子。阿公的胡子很长很白。那天的太阳光薄薄的,像淡淡的影子落在我们身上。阿公的白胡子闪着一圈好看的黄色光芒。阿公的影子比太阳影子更淡,更长。大门旁,老屋最后的一截土围墙上,奶果藤很老了,但很绿,像墨。阿公在那上面,也留了一点淡淡的影子。我不知道阿公会不会随着影子钻到那点墨色里去。我手心里全是汗。
我记得阿公常说:“人随太阳而来,也将随太阳而去。”
太阳的淡影子也落在老屋前的田垌以及田垌的那一边——被老屋和另两个小村子围着的山坡,是亚叉寨,山嘴有一间孤零零的房子。
“那是我们的新屋,以后我们搬到那里住。”阿公指着说。
我不晓得说什么,便没有作声,和阿公一起望着对面的新屋。
满天的云,暗暗的灰。新屋坐在灰云下的山嘴上,新鲜的黄色土墙,新鲜的黑色瓦顶,屋旁满是翠色的竹子,青色的木薯地。
不同于老屋的幽深,那是一种像是秘密似的生机。
对于搬屋,我没有印象,而有一天突然醒悟了新屋周围的那些小土堆是“坟”。很多坟,很多金罐,藏在竹子和木薯地的中间,那里头装的都是死人骨头。
我问阿公:“为什么要把新屋修在这里?”阿公没有回答。我又问,“老屋不是我们的吗?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份?”阿公还是不回答,他的眼睛又深又湿,像古井,映照出两个小小的我。好一会儿,他才说,多好啊,我们又有房子住了。
天黑了,我哪也不敢去,把阿公的腿抱得很紧:
“阿公,快关门!锁落栓了吗?锁落栓了吗?”
门外,不到五步的地方,是一座很大的坟。屋子两边也是坟。屋后高高的土坎上,正对着后窗,有两个小圆洞,像两只黑幽幽的鬼的眼睛。圆洞里放着两个破旧的金罐,金罐里也装着死人骨头。我不知道这些死人骨头是坐着的,还是躺着的,但必然是白森森的,瘆人的。
刚搬到新屋的时候,我不认识坟。在那些像上灯糍粑的圆土堆上,母亲在周围晒过衣服、被子;我和弟弟玩过打仗,骑过木马;我在上面摘过野草莓;弟弟还在坟头撒过尿。鬼们一定很生气。
夜里,尽管盯着阿公锁好了门,我还总是用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很担心鬼们会偷偷飘进房,长舌头伸出来,舔脸,吸血。
阿公说,鬼跟人一样的,也有头发,她在夜里到河里洗头发,丢了好东西她会哭,得了好东西她会笑。我想,鬼的头发一定是白色的,很长,山风也吹不动。夜里,她从竹枝上跳下来,轻飘飘地穿过稻田,到河里洗头发。
我猜,一个女鬼,她会喜欢紫红色的花,像满山坡的稔子花那样的。如果是一个小鬼,她一定会跑到瓦顶上,侧着身子,从细细的瓦缝溜进来,再爬到床上,挤到我和阿公的中间,慢慢地把我吃掉,她就长大了。
我想离开这里,到老屋去住,那里人多,热闹。不像这座山,除了我们的新屋子,到处是坟,到处是鬼。
2
阿公说鬼是怕太阳的,也怕人。
白天太阳大大的,新屋门前的大坟一点儿也不可怕。特别是,坟前有一个大草坪,密密地爬着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草,还有地稔子也一起趴在这里,像绿地毯似的,终年绿着,又干净,气味又好闻。
往这草坪一站,望对面罗斗坡的老屋,老屋的样子就变了:像头青灰色大兽、狮或者虎,蹲着,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冥想,但屋顶上屋脊翘得很高很精神。它肚子里的东西全看不见了,长长的连廊不见了,叠罗汉似的天井不见了,雕花的门和窗也不见了,当然也看不见老屋里的人从这个门串到那个门,看不见十六婆和监叔。
我喜欢十六婆,还有她的木薯粥。
十六婆住在老屋的地下室,有一张圆圆的慈眉善目的脸。十六婆总是穿着一件青色的边襟扣子衫,成天端把小板凳,坐在巷口纳鞋底。她纳的鞋底很厚很厚,我数不清一共有几层。十六婆把钩锥尖在头上划两下,耸起右肩,把锥尖用力往鞋底里钻,额上冒出了细汗,才穿得一针,然后嗦——嗦——嗦地拉线,手臂扬得很高,脸上皱纹一条一条都展开了。我不知道十六婆做那么多布鞋给谁穿,不过阿公穿的黑布鞋跟十六婆做的黑布鞋是很像的。
巷口的檐阶下有个小天井,长了好多斑驳的青苔。我一个人蹲在那里玩插秧游戏,搬一点沙土围块小小的“稻田”,学着母亲和婶婶们在田里弯腰插秧的样子,把青苔剥下来,一蔸一蔸插到沙土里。“秧苗”被插得又歪又扭,一会儿疏一会儿密,但我自己看着高兴,傻瓜似的又蹦又跳。
太阳晒到头顶了,十六婆放下针线,招手叫我过去。
“瞧这妹儿,脏得哟!”十六婆一边不住地咂嘴摇头,一边又禁不住撩起她青色的衣襟来擦我的脸,扯平我的蓝布花衫,拉我走过长长的黑巷子,打上一碗黄稠稠的木薯粥,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好吃!几好吃!”我吧嗒吧嗒舔碗底,含含糊糊地说,“婆婆,我长大后种一百亩田,送你一百担谷子,让你天天吃干米饭!”
“好,等十妹长大了,送我谷子!”十六婆说,“十妹心性像阿公,像十世祖阐伦老太公哩,好!” 不知怎么的,十六婆的鼻子忽然有点塞住了,像刚打了喷嚏似的。
“阐伦老太公是谁啊?他在哪呢?”我奇怪地问。
“婆婆也没见过呢。听讲他是一个顶好的人,勤力又省俭,识挣钱,置得好多田地,这大屋子就是他盖的。”十六婆用眼睛画了一个大圈,好像大屋子就被画在她昏暗的灶房里一样,浑浊的眼睛闪出亮光,接着又说,“阐伦公盖了祠堂,把他置的田地房产都归祠堂,大家都有份哩。听说连县太爷都来贺喜呢。可惜啊,后来有人赌博、抽大烟、吃官司……”
“有一年大旱,村里的人都收不到谷子,没米下锅,我家米缸也是空空的。你阿公从外地高价籴米回来,在村子里平价卖出去呢。不然啊,婆婆大概活不到今日了。你阿公,好人咧!”
这些事情,十六婆唠叨很多次了,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啦。不过,她夸阿公是大好人,我赞同。我觉得,天底下再没有比阿公更好的人了。
还有什么高价平价这些怪怪的词,我听不懂因而不太想听,我的心思就盯着十六婆滑溜溜的木薯粥了。然而,十六婆的木薯粥不是最好吃的,最好吃的是监叔的白米粥,又稠又香又白。
我当然也很喜欢监叔。
老屋顺山势建在一个坡上,一户比一户高,一个天井比一个天井高。监叔就住在最后一个天井后头,还要再上几级台阶的地方,是老屋最深最高可又是边沿的地方。监叔说他的屋子原来是看牛的长工住的。门前是长巷子的尽头,临巷这一面墙是木板的,从巷头走下阶梯,便是牛栏和猪栏。牛栏和猪栏的外面是果园,再往外,就是一块连着一块时青时黄有时又光秃秃的稻田。
监叔长着一张长长的脸,镶有两颗银牙,说一句话鼻子就抽一下。
监叔门从来不上锁,他叫我随便进去。因为他家里没有小孩子,就连大人,也只有监叔一个呢。只要他说谁可以随便进,谁就可以随便进了。
有一次,在老屋外青汪汪的稻田边,我的姐姐阿婧问监叔要银儿买作业簿,监叔从他裤子里面的兜里掏出两角钱就递给阿婧姐了。我站在阿婧姐的后面,咬着手指想了想说:“金凤讲谢六铺儿的水果糖很甜的。”监叔看看我,从另一个裤兜摸出两个银儿说:“唔,唔,买糖果去。”
后来阿婧姐告诉我,有个学期没钱交学费,她还是问监叔要的哩。
我觉得,这么好的监叔应该住在我们家才对,跟我的七叔和八叔一样。如果我问阿爸阿妈七叔八叔要银儿买糖吃,他们可不会给我,好像他们口袋里连一个银儿也没有似的,甚至他们连煮粥的米也不够似的,因为我们家里的粥是稀的,不是稠的。
可惜,监叔并不住我们家。他一个人住在老屋又高又深的木板隔的房子里。在夜里,他孤单地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到他房子后面那几头牛久不久哞地叫一两声,会不会伤心呢?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去想这些。
我饿的时候,如果监叔不在家,就自个儿拿碗舀粥吃。监叔的白米粥,稠得干饭似的。在当时,是村里最好吃的了。有时,我还会带着小伙伴来吃,把监叔锅里的粥都吃光了。我当时哪里懂得一个农人出了半天力气锄地,回到家,揭开他的锅,发现粥全不见了,会是什么个懊恼心情哟。但是,监叔从不生气,依然抽着鼻子对我说,饿了就来吃,以前监叔也常吃你阿公的饭。
我不晓得,监叔不是阿公的儿子,为什么会常吃阿公的饭,他吃了阿公的饭,为什么又不住我们家?但是我发现,每回他到我们家玩,离开的时候,说的话竟然跟我阿爸推单车出门去昙雅小学教书时的口气是一样的:“阿公那么老了,你们俩别到处乱跑,别总让阿公一个人在家里,要给阿公捶背捶脚,记住了没?”
待我和弟弟一起点头“嗯”一声应下后,他又说:“饿了就到我家吃粥!”
实际上,去监叔家很惊险。从十六婆家往廊上走,要经过阿水家门口,阿水家住的屋子是老屋最好最大的屋子。阿水的阿爸常常和我七叔吵架。论辈分,七叔大一辈,但他们年龄相仿,从小很要好,后来却因一棵祖上留下来的龙眼树而反目成仇,有时还会打起来。阿水似乎对我也恨之入骨,一看见我就龇起他白森森的牙来吓人。他们家还有一条凶恶的大黄狗,守在门口,见人就“汪汪汪”吠个不停。我总是等阿水不在家,大黄狗又睡着了,才敢贴着墙根,心惊胆战地经过他们家门口,然后飞一般地往监叔家跑。
我成日在老屋里跑来跑去。老屋上头的太阳火红红的,果真连一个鬼都看不见,而且有好吃的好玩的,比新屋不知好了多少倍呢。可是,阿公却不爱去老屋玩。
3
“监叔的粥很好吃,吃了肚子很饱!”在监叔家吃饱了,回到家,我拍着肚皮对阿公说,“监叔日日煮好大一锅粥哩!明天阿公去吃哦!”
“又去吃你监叔的稠粥了?他那点谷子来得不容易!以后不准去,听到没有?”阿公停下手上笔,认真地对我说。
我踮脚趴到桌边看见阿公又在算算术题了,几张黄色的草纸被画了很多横七竖八蝌蚪般的式子。
听说阿公以前当过地主,当过乡长,教过书。我还听说阿公养过蜂,一个人在一座山里养蜜蜂,酿出了很多甜滋滋的蜂蜜。那是队里觉得一个曾经的地主应该在那样一个孤寂凄清的地方去反思错误。不过,阿公反思了几年,也没有反思出错误来。我听说,传说中青面獠牙的吸血鬼可能就躲在那座山里。而阿公竟然不怕,一直都活得好好的,真了不起!
我发现,阿公最爱出奇奇怪怪的算术题给村子里的人算了,让人家算几十年也算不出来。算术题一旦被阿公出好,就会在村子里的白头发黑头发大胡子小胡子之间传来传去,这些有趣的人在劳作闲暇之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就闭着眼睛掐手指,或在地上用树枝划拉。算对了呢,就把锄头挥得高高的;算不对的呢,也不计较,锄地也很响,仿佛是要把那点被遮蔽的智慧用锄头去锄通透似的。就在几年前,我偶遇村中一位老人,他竟背出阿公当年的一道算术题,他说我从黑发算到白发也算不出来,你是大学生哩你能算得出来吗?
阿公点烟也跟别人不一样,可以不用火柴,也不用火机。秋夏的午后,太阳热辣辣的,阿公卷一张草纸搁在阶前草地的一块土砖上,又拿出他的老花眼镜在墙头上对着阳光晃来晃去,捉得两道阳光,再把那两道小小的阳光缓缓地移到草纸上。不一会儿,那卷草纸就冒烟了,起火星了。阿公把烟头凑过去,烟就神奇地被点着了,被阿公美美地吸到肚子里又变成烟圈转出来。然后,阿公就举着他那用太阳光点燃了的草纸到灶房引火做饭了。
阿公自己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妙事,他可不像别的老人爱拄着拐棍在村子里到处转悠,但他也不去老屋。虽然他自己在老屋出生长大的,虽然老屋住的都是他族里的亲人,虽然老屋的老人都很尊敬他,晚饭后常到亚叉寨里来找阿公一起咕噜咕噜抽水筒烟,但阿公不去老屋,我可不晓得是为什么。我更不晓得阿公为什么在老屋没有了他自己的房子。阿公不爱我问他这些事情。
可是,有时候他会说:改朝换代的事,谁说得清是非?太阳啊有起有落,戏台子啊有上有下……
我想不明白老屋跟改什么换什么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老屋跟太阳和戏台子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阿公爱看戏,也爱看电影。
每逢过年,老屋搭戏台,大队也会搭戏台。不管哪里请了牛娘戏,哪里放电影,阿公都要去看。我也跟着去。我提着煤油灯走前面,阿公扛着独头凳走后面。
有一个小年夜,北风呜呜地叫,还下着毛毛细雨,好冷好冷,冷得我一直抱着竹编的火笼不肯放手。大队又请了戏班演牛娘戏。阿公说天气冷,不要我去,也不要人陪。他一手扛着独头凳,一手拿着煤油灯,独自去了。阿公走下山坡,沿着水渠,穿过一片稻根朝天的稻田,又穿过一片稻根朝天的稻田。
在老屋大门外,阿公的煤油灯被风吹灭了。
阿公掉到水渠里,摔坏了脑子。
阿公脑子坏了后,不再算算术题,也不用太阳光点烟,也不再看戏不看电影。有时他一声不出,有时喃喃地说着只有他一个人才懂得的语言。吃饭的时候,阿公还会把吃了几口的粥又倒进粥锅里。
阿公已经不能照顾我了。夜里,阿妈安排我在她的房间睡觉,跟两个姐姐挤在一张四面有围栏的小床上。阿妈带弟弟睡在大床上。每天晚上,几个小人儿在房间里嘻嘻哈哈,拥拥挤挤的,我竟然不再担忧鬼,香香甜甜地睡着了。
可是,常常是第二天,天蒙蒙亮阿妈起床煮粥,我也醒了,跑到阿公的睡房,钻到阿公低垂的蚊帐里,闻着帐子里浓浓的老人气息,我就会又想到鬼。
一天清晨,我坐在呼呼大睡的阿公旁边,忽然想到,会不会是水渠里的小鬼钻到阿公的脑子里,阿公的脑子才会坏掉的?
我猛地打了个激灵,心中无限地害怕悲伤起来。
4
亚叉寨山嘴这一间独屋,实在是过于清冷,阿妈七叔八叔到地里干活了,哥哥姐姐们上学了,这一整座山就阿公一个白胡子老人,以及我和弟弟两个小孩子,无聊得很。
阿公脑子没坏之前,看书、玩算术题、玩太阳点烟这些妙事。有时候,山下有人用竹床抬着一个病得不轻的人经过,阿公必得放下他的妙事,下山去拦住人家,问一问情况。有时候,抬过的是一副棺材,等人家下葬回来,他就拦住那四个刚刚放下死人还未洗手的扛杠佬,也问一问这个人是害什么病死去了。阿公好像不单是不怕鬼的,还觉得鬼也是有意思的。但也只是阿公一个人觉得有意思,我可是被惊得像只兔子,远远地就躲到稻禾里去了。
阿公脑子坏了之后,我和弟弟就更没什么可看可玩的了。
总之,每一天,蟋蟀蜻蜓捉过了,竹根逛过了,木薯地钻过了,连坟堆我们也都爬过了,太阳还是高高的、白白的,在天上瞪着大眼睛。我知道离天黑还要很久呢。于是,就时常到老屋玩。有时我带弟弟一起去,有时我自己一个人去。老屋有个坏坏的人,他是个年轻的大人,但他常常不用出工干活,因为他有肺病。这人一见弟弟他就捉住弟弟的小鸡鸡说要像阉鸡那样阉了。有一次,他家的一只大公鸡追着弟弟满院子跑,好像真是要把弟弟的小鸡鸡啄走一般。我的弟弟就怕得要命,因此常常不肯随我到老屋玩,他情愿一个人给阿公捶腿,在坟堆里窜来窜去跟小鬼捉迷藏。
在老屋里,过家家是小伙伴们玩得最多的游戏。
金凤比我们都大,每次她都演妈妈,安排阿北演爸爸,我演小妹妹。每个人都得听爸爸妈妈的话。
金凤装成一个新娘的样子,坐在老屋门外水渠边的龙眼树下,拿一块手绢半遮着脸,羞答答地等着阿北去娶她进门。
阿北从老屋一厅出发,持一根竹枝,做出骑着高头大马的姿势,嘴里“啲嘚啲嘚”把春风得意的马蹄声制造出来。
阿北一来到老屋大门外,金凤就站起来了。他们手拉着手沿着长长的石板路,经过果林、甘蔗地、菜园子,穿过地堂,跨过三厅的大门槛,上到二厅堂,再到一厅。
一厅就是头座,是致敬堂,当年太祖公公和太祖婆婆就端坐在堂上,迎接贵宾,接受儿孙们请安,接纳各房新娶的媳妇。
我的阿公就是在这里与我的奶奶拜堂成亲的吧?阿公牵着奶奶拜堂的时候,脸上肯定不会有白胡子,黑胡子茬茬也不会有呢,他一定跟他书本里夹着的那张相片一样:长而方的脸光光的亮亮的,有棱有角,鼻子高高的,两只深黑的眼睛被心里的激动烘得像是要飞出阳光来。奶奶必然是极迷恋阿公的,她一口气给阿公生了八个儿子三个女儿呢。我阿爸和我的大伯二伯三伯四伯五伯七叔八叔,他们排着队投胎到这户人家里来,让我的阿公每隔两年就得请一次上灯酒,在致敬堂这里烧香告谢祖宗,又添丁啦,香火越来越旺盛啦。我可想不出来,阿公的十一个大孩子小孩子跑来跑去,这里是怎么样的欢腾。我的太公躺着抽大烟呢,他可不管事。但是,我那当家做主的太婆往雕花的太师椅上一坐,心里一定呵呵笑。
然而,我能看到的致敬堂,除了空荡荡的祖座,什么也没了。阿公天天挂念的“睦宗族、勤职业、尚忠信、绝四戒……”十八条遗训就刻在两边侧室的墙壁上,可在侧室我看到的却是满满的柴火。现在族人娶新妇也不用到这里来拜堂,可直接迎到自家的新房去。
但是阿北和金凤喜欢在这里装成新郎新娘,拜堂,成亲。他们对着祖座,胡乱鞠躬,一边拜,一边哈哈笑。我觉得,祖宗们一定不爱听到这样的笑声,因为祖座屏风上,镂空的花没有哪一朵是笑着的,都好像是一张张端庄的脸。我想象中拜堂的新妇,应是绞着手抿着嘴眼睛不敢看人的。我的奶奶那时应该是这样子的。老屋西廊阿哥新娶的阿嫂就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她过门的第二天,才看到她笑的。那天一大早,她在天井弯着腰洗脸,一扭头,看见我蹲在旁边眼直直地盯着她,她就笑了。她牙齿真白,笑起来真好看。好看得我都吓了一跳,所以她一笑,我就一溜烟跑了。
拜完堂,阿北和金凤就跑到二厅后面的走廊,抱在一起,不许我们看。阿水说他们是在亲嘴。阿水还说,阿北摸了金凤的小奶子。后来阿北把半截砖头放进金凤的裤裆里,又拿出来,说妈妈生小宝宝了。金凤把砖头宝宝搂在怀里,哼着没有字的歌谣,好像是,那真的就是她的宝宝一样。
最后,他们要出去玩了,金凤就把砖头交给我,要我在家里看宝宝,她带领众伙伴到六廓河游水去了。河那边,很快就传来“拉嘎嘎”的欢笑声。
我抱着砖头,呆坐在三厅的门槛上,呆望着白花花的阳光水般泼到硬邦邦的地堂上,溅起一道道白光。我不明白,金凤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把我留在家里抱一块不会哭不会笑不会动的砖头。我抬头看看天,刺得眼疼,河里的水一定很热,一定有毛毛夹蟹子,夹金凤的屁股。
5
除了过家家,爬墙头也是伙伴们爱玩的游戏。但是,金凤不允许我爬上墙头去。墙头明明是地堂的墙头,地堂是老屋晒谷子的场地,可金凤说是她家的,如果我爬,就推我下来。
“你是地主妹!”金凤大声说。
“我不是!”我惊跳起来。
我没见过真正的批斗大会,没见过传言中一个地主是如何顶着尖尖的高帽子被一群人摁倒跪在台上低头认罪,以及一个地主婆如何被剃光了半边头发被强行摁进粪水桶中。但整个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地主。他们害怕、惊悚、鄙夷、愤怒,还有人暗暗地兴奋把牙齿磨得吱吱作响。我那时尚不懂得人类的进化史,不晓得一个古人猿可以演化亿万年变成现代人的样子,更不晓得一个现代人有时候也会跳过种族、跳过民族、跳过国家、跳过部落,回到洞穴里扒开被尘土掩盖的遗址,挖出残存的那点动物性。此时,无关文明,无关阶级,只是人与人虚拟的对立的悲哀。年幼的我不懂这些历史,不懂得包容,也不懂得自我保护,只是本能地否认和反抗。
“你是!因为你阿公是地主!”金凤抢着又说。
“我阿公不是地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地主”这个词跟自己跟自己家的亲人联系了起来。我被吓了一大跳,一点也不相信。
在电影里,我见过地主。他们又吝啬又狠毒,长得也很难看,半夜躲到鸡笼里学公鸡喔喔叫,把他们家的长工骗起床,让他们天不亮就到地里干活。
地主是这样一种模样,怎么可能跟我的阿公发生联系呢?阿公一整天待在亚叉寨的小山坡上,只爱玩算术题和太阳光点烟这些奇妙的事情,或者把他瘦瘦的身体放进竹躺椅里假寐,他那么高那么大,怎能钻得进鸡笼里去呢?而且,半夜里,阿公老咳嗽,哪能学那么响亮的鸡叫呀?
所有电影里的地主做过的狠毒事,阿公都没有做过哩。所有阿公做过的事,电影里的地主竟一件也没见去做呢,比如说给人看病。
阿公是会诊脉看病的,村子里的人,或者村子外面的人,他们捧着昏昏的脑袋,或者捂着疼得似刀绞的肚子,爬上亚叉寨的小山坡,请阿公开一个方子。阿公摸了手把脉,又让张嘴看过舌头,问一些话,然后就用草纸写起了方子,有时候他也会先翻一翻一本发黄的书。这些生病的人拿了方子,就到街上拣药回家煎汤喝去了。有的人来一次就好了,也有的人要来两次三次。有一个女人,她很想要一个孩子,可她又生不出来,就来求请阿公。阿公照例诊脉诊舌开药方,那女人喝了几服药后,果然就养出了一个胖儿子。她就抱着儿子,带了酒和一藤篮的荔枝来感谢阿公。阿公不收,她就生气地说:“四公,您积德行善不收诊费的规矩我懂,可这两斤酒给您提点神,几个荔枝给侬儿仔甜甜嘴儿,都不得吗?!”
那荔枝很红很鲜亮,一股特别的甜气儿像夜里无法停下来的小老鼠的脚步那样在屋里到处乱窜,当然也钻到我和弟弟的鼻子里去了。我们很希望这些荔枝能够留下来。管不住的口水被我和弟弟吞得咕咕响。而且,被那女人一进门就塞给我和弟弟的荔枝在手里快急出汁水了,它们只想跳到我们的肚子里。
阿公看看我和弟弟,就说:“街坊邻居顺个手的事情,哪有什么德和善?酒我有你带回去,就把荔枝留下吧。”
像这样的事情,我可没见电影里的地主做过。阿公怎会是地主?我不相信金凤的鬼话。
我跑去问十六婆,我的阿公以前有没有在半夜学鸡叫?
“怎么可能?!”十六婆十分吃惊,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我在那一瞬间变成了一个怪物。
“那阿公是地主吗?” 我又问。
“这细妹今日怎么啦?什么地主不地主的,都是人!你阿公是知书识礼的大好人!”十六婆皱了皱眉头说。
“阿公到底是不是地主啊?”我扯着十六婆的衣袖,不依不饶,紧追不放。
“好好,都告诉你吧!妹儿啊,你们侬儿仔不懂事啊。”十六婆停下锥鞋底的钩锥,顿了顿说,“那时候,刚解放,要划成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现今非要划出一个不一样的来。每个村都要划一个地主嘛,队里就划了你阿公,这,其实有点冤。你阿公其实地也不多,没做过歹事,却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们知情的老人都敬重称他‘文明地主’的。可年轻仔不懂啊,你阿公和你阿爸他们……吃了好多苦!”
我没有想到,阿公竟然真的是地主!更没有想到,地主,竟然不全然是“半夜学鸡叫”的地主,还有像阿公这种不像地主的地主。我呆呆地望着十六婆。
十六婆抬起她的眼睛,那里面好像是打开了一扇门,一下子就深了,远了,望不到底了。她接着说:“我们是同宗呢细妹儿,你阿公在东廊,婆婆在西廊。大田产那是几辈子之前的事情了,田地多得啊,望都望不到边。这大屋就是那时建的。老祖宗禅伦公原为族人盖个敬祖宗的祠堂,后来却又建成了大屋子,人也住了进来。有人说,祠堂阴气太重,本不适合住人……后来慢慢败落啰。特别是,到你太公这辈,你太公他抽大烟,金山银山都化了烟,东廊的家产在他年轻时差不多都败光啦!幸好啊,你太婆能干,一把锄头东扒西挖,一点一点,又赎回来一些。可谁能想到后来会划成分呢?我们西廊更差,赌博、吃官司,一麻袋一麻袋的银钱背出门去……没了,都没了……没田没地哪来的地主?你阿公有七八个儿子呢,个个壮得像牛,那点田产,也用不着请长工!还半夜鸡叫?你这细妹儿,小傻瓜!”说到后来,十六婆竟然笑起来,可笑着笑着,眼泪却又跑了出来。真是奇怪。
“哭哭又笑笑,鸡儿鸡母带入庙”,我学着大人的口气说。这一句话每天都被用来安慰村子里啼哭的大人和孩子,让人家明白,哭与笑的距离就在于你转念间的情绪。我用手给十六婆擦着眼泪,脑子里出现一个幽暗阴凉的小洞口,我曾以为是庙的那个通往洗凉房的小洞口。我不知道,庙,是不是用来专门收集哭过又笑过了的人的,我更不知道好心的十六婆会不会被收到那庙里去。因为她哭了,也笑了。我不行,我哭就是哭,笑就是笑。
现在,我是想哭的,因为我的阿公是个地主。虽然他会诊脉看病,会太阳点烟出算术题这样的妙事,虽然十六婆一再说他跟别的地主不一样,他是文明的地主不是狠毒的地主,可依然抹不去“地主”这个可怕的印记。我的心变得重重的,像一坨湿了水的棉花。但我不恨阿公,我可怜我的阿公,心疼他老弱而松脆的膝盖骨。我不知道阿公有没有被摁着跪过,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他的膝盖骨在疼。
我想让金凤他们也明白我的阿公跟电影里的周扒皮是不一样的。
可是,金凤不听我的解释,她像个瘦猴子,黑衣黑裤黑鞋子,和阿水金昌二妹阿月他们,还有我的堂姐姐,三下两下,爬上最高的墙头。
“地主就是地主,讲到天上你阿公也是地主!”金凤坐在高高的墙头上把脸也抬得高高的,使我看不见她的眼睛。
“啐!”金凤的口水吐到我的头顶上,像喷鸡蛇的毒汁一样。我感觉我的什么东西塌了,碎了,冰冷地疼。眼泪要流出来,又被什么东西摁了回去。而另一个东西又在我心里长了起来。
夜里,我跟阿公讲,阿公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抱着我。
第二天,我醒了,发现阿公一夜都没有动过,他还是像昨晚那样抱着我。
6
很多年以后,老屋老得不成样子了,里面住着的人早已搬出,到大城小城或到街上居住。我亦远离故土,远离老屋,甚至一度忘记了老屋。
一个夏天,出差北京,顺道到故宫一游。随着拥挤的人流穿过威严的楼宇宫殿,我内心空空如也,不见皇帝,不见群臣,不见宫娥太监。可他们分明又裙袍嘎嘎响着来回奔跑,把我当作透明似的穿过我的身体。而那眼前的金瓦红墙却像是不存在似的,像一幅画似的,挂在蔚蓝的天空下面,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于是,我回头望了望,又望见了千里之外的老屋。却又惊讶地发现,当年偌大的数不清房舍的罗斗坡老屋,以及屋上铺着日影子的灰色天空,也像是不曾存在似的,只是一张灰色的画,挂在青山脚下绿镶黄的稻田间,被风一阵一阵地吹着。
风来自当年那如“庙”的小小洞口,那神秘的阵阵凉风,还是那样凉而神秘。我看到,阿公还在的,十六婆还在的,监叔也还在的,十三娘也还在的,就是金凤阿北他们也都还挤在墙头上吵吵闹闹的,当然还有别的人,比如爱唱戏的疯子。
吹风吧,吹风吧。老屋吹凉了,整个夏天也就凉了。我仿佛听见阿公在天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