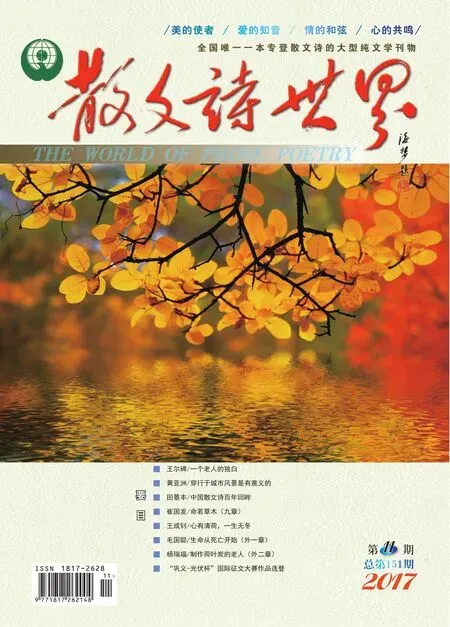乡愁的滋味(九章)
许泽夫
乡愁的滋味(九章)
许泽夫
喊 魂
村里唯一的村医踏破木门坎之后;
马龙山上所有的草药都煎着喝熬着喝煮着喝之后。
我依然高烧不止,昏迷不醒。
母亲不得不信了二姑奶奶的话:喊魂,趁着魂还没走得太远。
母亲决定把我的魂喊回来。
喊魂是要一呼一应的。父亲在大山深处的窑厂,姐姐在百里之外的寄宿学校,而我,躺在床上胡话连篇。
村里人躲得远远的,他们不愿意,生怕一应之间,我的魂回来了,自己的魂被喊走了。
半大的牛犊,还没有穿鼻钩,就像穿着开裆裤的男娃,跟着母亲来到村外。
母亲怜爱地望着它,只有它了,我的小生命悬于它了。它像明白母亲的心事,舔了舔母亲满是冻疮的手,算是应了。
母亲凄然地喊一声我的乳名。它欢快“哞”了一声。
母亲又喊一声我的乳名。它又欢快地“哞”了一声……
少年不识愁滋味。它以为这是一场游戏,平时常和我做的那种。
一呼一应。
一喊一答。
从上半夜喊到下半夜……
我迷迷糊糊听到一阵阵天籁,从噩梦中醒来,套上父亲笨重的大头鞋,跌跌撞撞到了村头。
母亲见了,抱着我喜极而泣:我的魂被她喊回来了!
牛犊也来分享,它长着稚嫩双角的头颅直往母亲怀里拱。
母亲腾出一只手,紧紧抱住了另一个半大的儿子……
向日葵
我是一棵小小的向日葵,你是我的太阳。
你一寸一寸抬升,我就一寸一寸望你;
你一分一分发热,我就一分一分感动。
你从地平线踱到黄昏。
我抱着头,仰着脸,从东方到西天。
谁挥起一把无情的镰刀,把我的头颅生生割下。
我的躯干,笔直站在原地,为爱情,做一根招魂幡的旗杆。
家 乡
村东,老井填平了。
那枚乡愁的月亮,孤悬在夜空,无从栖息。
村西,竹林砍光了,在竹影里偷偷亲嘴的初恋无遮无掩了,一阵沙尘风就刮得无影无踪。
村前的老槐树死了,那口涂满厚厚一层铁锈的大钟,恋母似地倒悬在树梢,大风起时,发出呜呜的哀鸣。
村后的小河枯了,河堤上的杨柳,望着最后一道光波,蛇一样消失于苍莽原野,裸露的河床由肚皮般的白变成死尸般的黑,它们绝望了,一棵接一棵气绝身亡。
游子的乡愁,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燕 子
南下打工的爸爸妈妈被钉在了卡号上。
外出觅食或幽会的小黄狗认不得回家的路了。
但春风记得这间小屋,衔着春风飞来的燕子认得屋梁上的家。
它离开时,形影孤单。
再见时,它带来了自己的儿女。
奶奶像见到了久别的亲戚,唱着山歌:“小燕子,穿花衣,不吃俺家稻,不吃俺家米,只在俺家下个仔……”
天刚泛亮,奶奶打开门,让燕子啄食晨曦。
夕阳西沉,奶奶手搭凉棚,翘盼燕子成双成对归宿。
奶奶按下不谙世事的小孙子手中顽皮的竹竿和弹弓,轻声细语解惑。
奶奶佯装大怒赶走凶巴巴的小狗。
燕子是家里的吉祥物,奶奶是燕子的保护神。
燕子像个懂事的孩子,进进出出都绕着奶奶飞三圈,唱一支好听的歌,直唱得奶奶笑逐颜开。
……
奶奶去世,我泪流满面。
回到家乡,凝望空空如也的屋梁,我泪流满面。
冲着家的方向长跪不起
岁月无情,母亲岁数越来越大了。
眼更花了,座机上的数字看不清了;
耳更聋了,电话铃声听不见了;
手脚更不灵便了,再不能挪到村口眺望了。
但神奇的是,无论我走到哪里:大洋的彼岸、开放的城市、闭塞的乡村……母亲都能准确地掀开梦帘,坐到我身边。
每次醒来,我都冲着家的方向,长跪不起。
爷 爷
清明的细雨中,爷爷引领着我,在墓地穿行。像挨家挨户串门,每到一块墓碑前,他都由衷地记住每个人的好。
这是大爷,好人哪!那年饥荒,给过我一小筐山芋。
这是二婶,好人哪!二十二岁守寡,赡养公婆,把两个未成年的小叔子和一双儿女拉扯大。
这是三姑父,好人哪!庄稼地里一把好手,一生不欠人钱不欠人粮不欠人人情。
……
从东到西,从村头到村尾,爷爷把故去的村人讲解给我听,这些人有的我记忆犹新,有的印象模糊。
讲完了,爷爷有些累了,蹲在地上一言不发,像一块新錾的碑。
母 校
把最神圣的场所腾出来,把祖宗从神龛上抬下来,让孩子们排着队唱着歌进进出出。
把最有学问的人从水田里请上来,四季穿干净整洁的衣裳,不经风吹日晒,却拿整劳力的工分,让孩子们不叫辈分,只恭敬地叫老师。
不允适龄的女娃不上学。
不允牛呀猪呀狗呀跑进校园。
不允撒疯的醉汉撒泼的怨妇扰乱学校秩序。
始终有歌声、笑声、读书声。
始终有阳光、明天和念想。
今天路过,窗户像被摘除瞳仁的眼睛,而教室的门,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惊讶地望着我。
我依然在内心叫你:母校!
握锄的母亲
母亲从不空手出门,镰刀、砍刀、扁担、箩筐、铁镐、铁锹……这些如十八般兵器,母亲拿得起放得下,出手不凡。
上年纪了,母亲已使唤不动大多数农具。
母亲随手握一把锄头,如武士的佩剑。
关键时刻,月牙形的锄头,可以当拐杖。
更多的时候,母亲在田头转悠,农活早已不指望她,但她离不开农活。
麦田的土疙瘩,一锄下去,四分五裂。
棉花地里的杂草,锄到之处,纷纷倒下认错。
水田的缺口大了,水在流失,母亲挥动锄头,三下五除二,阻住了任性的水流。
她已分不清哪块地是自家的,哪块地是左邻右舍的。谁家的都一样,都是长五谷杂粮的土地。
母亲土里刨食土里长,土地就是她的娘家。
握锄的母亲,仙风道骨。
深入地头的母亲,是一把延续了两千年的铁锄。
铧
我第一次这么认真打量着它,是在一个风景区的民俗馆,挂在刻意描绘的墙上,如干瘪的吊瓜。但透过古铜色的锈迹,我感受到它内心的光芒。
自小与牛与犁铧打交道的我,居然从没有端详它,就像喝母亲奶水长大,却从没有凝视过母亲的脸庞。
丘陵上,一头牛拉着一张犁,犁后是我微驼的老父亲,在四季穿行。
铧,犁的末端,潜入到地层,被黄色的或黑色的、板结的或潮湿的泥土掩埋。它所经历的艰辛和磨难,唯有它自己知道:根的纠缠,蚯蚓的哀鸣,石块的阻拦……它别无选择,遵循着父亲的指引和牛的足迹,一往无前。
它有锋利的刃,它有太阳的光,月亮的辉,但它深藏不露,一心一意将荒废的土地垦成良田。
有些东西珍贵却被我们忽视:阳光、空气、水……还有铧。
有些东西容易被忽视却在闪光:埋在沙里的金子、无私的母爱……还有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