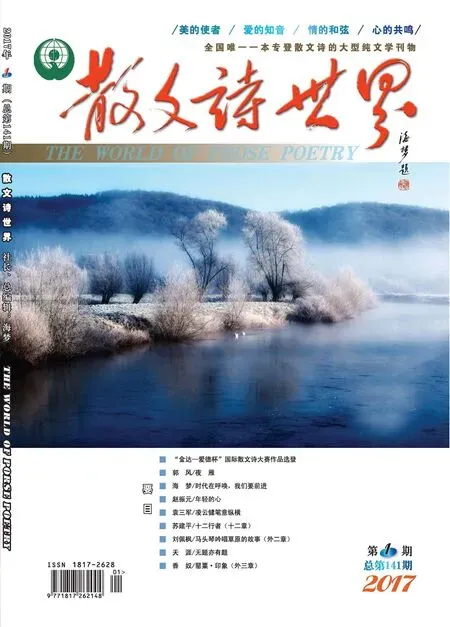十二行者(十二章)
浙江 苏建平
特别推荐
十二行者(十二章)
浙江 苏建平
司马迁:在层层叠叠的图书馆里
从床上滚下来的那一刻,从刀下滑出来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缩小,尽可能地缩小。
这来自于对宇宙的观察:星星们挂在天空,只是一个个小点。
在这一刻,他看清了自己的身体,看清了身体所来与所去的地方:大地。
所以,他选择了尘埃的命运。或者,尘埃的命运终于把他等到了。
在时间上,他走进了黑夜。他缩小为一个影子。这影子令他欣喜。
在空间上,他走进了一个坟墓:埋葬书的地方。现在他打算用这些书来埋葬自己。
他开始闻:竹简的味道,刀笔的味道,绳索的味道。新鲜的与腐烂的,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
生与死的味道:他的粮食,他的血液,他的空气。
借助于它们,他忘却尘根。肉体的尘根。
可是他伸出手去,高及星辰,或远至天边,抓住了另一条勃动的巨大的根。
山川皆在胸中,人物皆在奔跑,事件正在重演。而文字和书籍,正在等待着更新。
寂静的时刻,神秘的启示跳进他的心,语言的潮水涨起。
他这样告诉自己:
他们习惯于灭根。灭根无损于他。他要自己创造出一条巨大的根来,给无根的历史续上。
他把这条巨大的根命名为:太史公。
这一刻,他成功地缩小了自己:躲进了太史公的影子里,化成了一个个细小的文字。
这些文字一直在人间游荡。
杜甫:在动荡又动荡里
他写过剑术,那伟大的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从形到声,剑都在昭示着功业。可是,那剑从不曾来到他的手中。
他写过策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是,宫廷仿佛海市蜃楼,那道门槛却不可逾越,它以人间的“低”否定了诗人的“高”。
他写过山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可是,一切都跟那只鸟的眼睛一样,破碎的在加速破碎,使他的视网膜受到重压。
他写过白骨,“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否定这乱世,不仅钱币如纸,更是命贱如纸。他以“有情”唱这“无情”。
当然——
他写过黄鹂和白鹭,美好的小生灵,精灵般的小生灵,它们是如此无知,如此自在,如此地给了诗人一个宁静的时刻,尽管那么短。
他写过无边的落木和不尽的长江,时光简洁,枯荣也是简洁,像他翻过的一页页书,上面写着百年的多病,和多病的乡愁。
他写过伟大的李龟年,那时光,在相聚时藏起了面孔,一旦沧海桑田,便露出了时光的牙齿。诗人,或者音乐家,他们和万物一同衰老。
他写过草堂,在草堂,他渴望让脚停下来,可是,那脚走过的地方始终埋在他心中,没有停下过离乱动荡的脚步。他深知:那些苦楚,要加倍高于他自身的痛苦。
这所有的一切化成了他毕生的真理:
经历什么,便承担什么。
于是,他在人间种植诗歌,种植文字,甚至种植巨大的沉默。
正如无中含有,他的沉默中包含了所有的声音。
包括无声者发出的更为沉默的声音。
甚至这声音主要由它们构成。
兰陵笑笑生:在无名的存在里
他戴上了面具。
这恰到好处:隔着一道玻璃,他透视的事物无可遁逃。更为重要的是,他站在了人性的底线上。那是一条地平线,可是,像最稀有的东西,竟无人能识。
他走的路,是在深山。深山寂寞红。
其实,他的凡胎肉体,随便地浪掷在城市中,浪掷在曲柳小巷里。
浪掷的生涯,诗书在胸腹中,但他知道,他在等待它们结晶成钻石。而结晶,等同于炼金术。
他精通食,于是他在食中炼金,几吊几文,既轻又重,人间主要由它来衡量和称重。
他精通色,由色而金,他看到眼睛中、血管中、话语中、风雨中流淌着的梦想,这些梦想,在一些人是丝,在另一些人是麻,有时甚至是草。
城镇、街道、客栈、酒馆、府邸、民居、谣言、俗语、钱币、刀、酒、狗、猫、鸡、他、他们、她、她们:
一一过来受命,
一一变成了诗。
这伟业,是拆除众人面具的伟业,对众人而言,没有退路,不留情面。
于是,他简洁地戴上了面具,
化作无名。
在闹市中,他走在深山里。
他深知:唯有借助这无名,他才能放开歌喉,歌唱这人间的曲折,歌唱人间这不能言说的谜。
王羲之:在最优美的笔画里
风恒吹。光恒亮。水恒流。俗世的笔画,本就简单。生活令人安之若素,一天一夜,等同于一生一世。
在那个属于酒神的时刻:
他独自创造了新的世界。
张择端:在众生里
他用一生的时间,来表达一个时刻。
那个时刻,是一个表情的时刻,是一个动作的时刻,是一个想象的时刻,也是一个定格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他布局,他描摹,他勾画,他刻镂。
在这个时刻,他安排众多的声音,他隐藏众多的声音,藉此,他寻找更多的声音。
众声之中,饮酒者自饮,吆喝者自吆,哀愁者自哀,歌者自歌,笑者自笑,怒者自怒,而无声者永无声。
车声隆隆。雷声隆隆。万声隆隆。
这一切,在星空下,在大地上,在桥上,在路上,在心中,在不知所来与不知所去之上。
这些人,生活在所有的时间里。
尽管每个人经历的时间是那样的短。
这些人,这么多人,所站的地方,使自身发出了光。
众神众态均在胸中。他也把自己画了进去,画进了宇宙之镜之中。唯此,他使易于磨损的事物不再磨损。
他是多么小心翼翼:
聚集万千的目光,他描述了一个海。
冯梦龙:在卑微者中间
他拥有那么多的命运。
动与静的命运。夭折与存续的命运。被堵住的命运。行走在大地上的命运。被大地吞没的命运。被其他命运遗忘了的命运。总之,往低走的命运,在低处的命运。
这样,他把自己变成了嘴巴。不是一张嘴巴,而是复数的嘴巴,说着复调的声音。
那嘴巴讲故事,钢嘴铁牙,或花拳绣腿。有些沉于水,有些埋于墓地,有些流失在左右心房的空洞之中。
那嘴巴唱民歌,他的舌头千树万树,孢子飞扬,弥天漫地,抑扬顿挫。街头有一缕阳光,深山也有一缕阳光。这阳光加速着它们的繁殖。
那嘴巴说他们,用下里巴人来说,用深街小巷来说,用路途而穷来说,用低音和更低音来说,甚至有时用无声来说。
说成为他唯一的命运。这命运也是一种欣喜。
他站在旷野里。
白天,他用尽视力寻找躲在黑暗里的一切。
深夜,他层层剥开好让它们发出明亮的光。
关汉卿:在人间的扮演里
少年是一种伤痛。身份也是一种伤痛。早年他受到的教导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那是说:盐就该撒在伤口上。
伤口:溃烂,新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万物的辩证法在他胸中萌牙,滋长。
所以,勾肆瓦栏,梨园角落,恰好是呼天抢天的所在。
在这之前,他精于描脸的颜色,精于描眉的颜色,更精于描鬼的颜色。那来自于他的胆量,酒的胆量,高音的胆量,
以及欲什么无什么的胆量(注:欲哭无泪)。
他一生所有的灵感来自于这样的时刻:
六月,
飞雪。
他深知自己的才华,尽全力扮演一个矛盾的角色:
他把对人世间所能有的无限柔情,
全都塞进了一颗硬梆梆的铜碗豆。
陶渊明:在寂静的南山
美好的山。美好的水。
美好的老爷子。美好的老太婆。美好的孩子。美好的男女。美好的鸡鸭。美好的猪狗。美好的酒食。美好的小偷。美好的待偷之物。美好的村庄。美好的白天。美好的黑夜。美好的朝霞和夕阳。
美好的朋友。
美好的陌生人。
美好的菊。美好的秋天的菊。美好的眼中的菊。美好的南山前的菊。美好的注定要凋谢的菊。美好的诗歌中的菊。
美好的生长中的菊。
这美好的花。
还有这美好的桃花源,在纸上建成。
那几乎是一个秘密。
来自天上的秘密。由他偷来。
他歌颂这美好的一切,除了他否定的一切。
在这世上,他只否定了一样的东西:
网。
庄子:在哲学的故事里
死亡降临。可是他有手,有盆,有歌。他编织在云端的曲子。
人间太小,不能解释。
虫蚁太大,宇宙差不多尽在其中。
变色龙、枯叶蝶善于隐藏自己。从它们出发,他一一给林中的树木下了定义。那定义如此简单,人世的嘴和手却够不着。
这样,他出了谜题,又带走了所有的谜底。
关于他自己,他只设谜题,没有谜底:
一只在所有季节、所有地方、所有梦境、所有虚构、所有语言里翩翩飞舞的蝴蝶,在神经质地飞翔,优美地飞翔。
苏轼:在球形的人生里
明月降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妻子死去,他把歌唱变得神圣。与僧同游,那酒通达天地,那船像一尾活的游鱼。
而英雄们,被他写在了水上。
甚至他把所有人的骨骼拆开,重新组装笔划和画笔,祭以寒食。
在别人加一分的地方,他减一分。在别人减一分的地方,他又加一分。加减成为他毕生的使命。
如此沉重,他便化成鹤,在球形天才的舞蹈中,以轻驭重。
于是,他稀罕地掌握了那唯一的黄金分割律:
万物所来,即万物所去。
曹雪芹:在未完成的路上
太多易逝的事物:像一条河,流动着又吞没着一切。包括正在生长的花草,凋落的叶子,腐烂的果子,甚至那一双双追逐它们的眼睛。
金子也会腐朽。银子也会腐朽。
那用金子和银子算计的日子,更易腐朽。
他开始编织一个舞台。他编织舞台上的一张网。他编织网中的一只只蜘蛛。他编织善良的蜘蛛。他编织恶毒的蜘蛛。他编织走投无路的蜘蛛。在这个舞台上,几乎所有的蜘蛛都走投无路。
他编织蜘蛛走投无路时的合唱。
而这,仍不能抵御生活的腐朽。
在京城,一个黑脸胖子酒渴若狂。他曾凭借风筝的手艺赚取银两。他的黑夜过早来临:
人心不过是石头。
石头却可以幻化出柔软的生命。
他把最后一件雕刻的手艺命名为“石头”。一颗未及完成的珍珠。
一如世上太多的生命,他在未完成中完成了时间。
鲁迅:在无物之阵之中
先生,您是否寂寞?——比寂寞更深。
那一定是孤独。——孤独还不够。
那究竟是什么?——这个世界太吵了。
您是说世界的声音太多?——事实上又太安静了。
这是您发现的矛盾?——世间总是词不达意。
什么东西令您厌恶?——也许没有。
您喜欢什么?——那比没有还要少。
可是您写了那么多事。——只是一块块黑夜。
您还写了那么多人。——那是一个个无物。
您的读者在不断增加。——但愿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