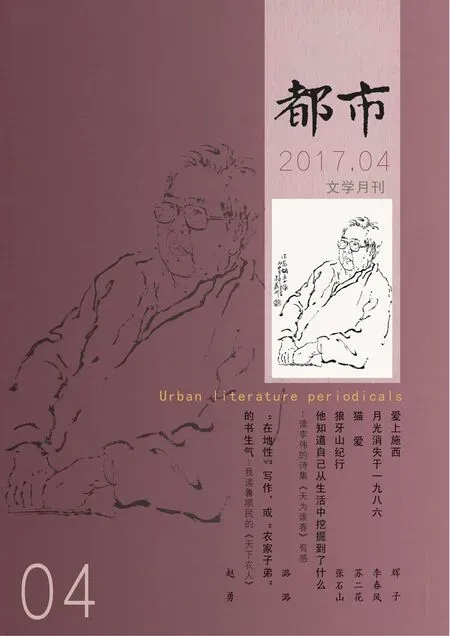“在地性”写作,或“农家子弟”的书生气
——我读鲁顺民的《天下农人》
赵勇
“在地性”写作,或“农家子弟”的书生气——我读鲁顺民的《天下农人》
赵勇
一
我知道鲁顺民是作家,编辑,长期经营《山西文学》,从副主编一直当到主编,但许多年里,我都是在跟他的后一种身份打交道。大约十年前,他就开始跟我要稿,有时还要命题作文。2008年,他给我出题,命我写篇《一个人的阅读史》,我一激动就答应下了,答应了之后却很后悔。盖因当其时也,我既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雅兴,又长年写论文,不会写散文,就想拖着赖着,让这事黄了。但顺民老弟不依不饶,他过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一会儿称老兄,一会儿喊老汉,软硬兼施,一脸坏笑,仿佛是要笑出我的斗志。后来,他见我依然慢腾腾,懒洋洋,死猪不怕开水烫,就跑到我博客上撒泼打滚,说:“指头支着磨扇等,你看着办吧。”又吓唬我:“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儿哼哼。”他这一招挺管用,我怕磨盘倒了压住驴,就一咬牙,一跺脚,紧赶慢张结,一口气写到两万五。他也不含糊,先是分两期刊发我这篇长文,第二年,又邀我去他老家河曲开会,给我颁了个散文奖。
这编辑当得让我心服口服,从催租逼债,到授奖发钱,整个就是一条龙嘛。
但是,作为作家,鲁顺民都写过些什么,我却不甚了了。两三年前,他给我寄本书——《礼失求诸野》(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那是他与另一位作家张石山先生的长篇对话录。这本书很有趣,也很让我长见识,但却是两个人侃出来的。他写的书是什么模样呢?
初见《天下农人》时,我吃了一惊:540多页,小32开,厚得像块半头砖,这可不是两三袋烟工夫就能读完的(为了与他这本书搭调,我得采用久违的农业时间进入叙述)。而一篇篇挨着细细读过去(确实是挨着读,没有挑三拣四,更没有走马观花),让我对这个黄世仁生出了许多敬意。
鲁顺民的老家紧挨着黄河,这本书头两篇写的就是那条河。在我的印象中,能把河写出神采的还有别的作家,其可能写到了黄河的“燃烧”,写到了主人公游黄河时与河水的搏击,很豪迈也很悲壮,理想主义的精神,甚至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跃然纸上。但读了鲁顺民笔下的河,就觉得某位作家还是有点“红光亮”。那是外人眼中的河,书生意气的河,也是“以我观物”的河,所以,这类作家大概只能写出河的表象。这也难怪,谁让其没生在长在黄河边呢?
鲁顺民就不同了,他从小到大与黄河厮守,写出来的河就特别地道:“黄河不愧是一条大河,河水流动的声音也绝不同于一般的小溪小水,小溪小水哗哗哗哗地流过去,浅着一条青色身子,在石头上划动出哗啦哗啦的声音。黄河绝不是。大部分时候,黄河几乎不动声色,没有什么动静,河水像烫平的布一样蜿蜿蜒蜒游动过去,难以想象,一条那么大的河,流在那么大的山川之间不动声色的情景。……河水流过去的时候,是在喘,是在呼吸,或者是潜伏的兵阵,在河底下追亡逐北。水互相搓揉着,使人疑心水底下一条水怪陡然搅动,或者,竟是什么能量被霎时崩破,远远地,袅袅地,多年的艄公能够听得出河底下暗伏的阵阵杀机。”(第4页)这是深谙黄河习性的摹写,既传神写照又不张牙舞爪,稍稍几笔,气象全出。从此入手,他写艄公如何“听河”,河水如何“饱”得可怕,又写七九河开时,河水怎样最为凶险。他讲述了一件往事:当年他在河曲老家当中学老师,班上三个愣货学生憨大胆,踩着凌块子验证数学几何,物理浮力,结果一人掉进河里,差点丢了性命。当三个家伙嘻嘻哈哈若无其事说“掉河里了”时,鲁老师来了一句:“惊得我,肝花像被狼掏了。”(第13页)
读到这里,也让我想起一件往事。那年在河曲,这边正开会,那边三个作家还在船上喝酒,喝到兴奋处,三人比赛似的跳进了黄河,仿佛验证“洗不清”是何境界。鲁顺民得知消息,立马让张石山前去“救”人。张石山赶到,想把那三个王八蛋骂上来,但他们志如铁,意如钢,高声断喝:你不下来,我们就不上去。张石山斗不过酒鬼,只好宽衣解带,下河捞人。当鲁顺民听说三个酒鬼跳进黄河时,他是不是想到了当年那三个愣货,是不是又一次惊得狼掏了肝花?
我想,只有清楚黄河的脾气,心里才会时刻装着凶险,那是局外人根本无法窥破的秘密。
我从顺民意识到的凶险谈起,实际上是想说我对这本书中一些篇章的整体感受,因为在许多处地方,我其实也读出了凶险和后怕,比如煤矿透水,土改打人。即便他写自家往事,字里字外也是怕。比如,当年高考,顺民像我一样也是个糊涂蛋,头一年自然名落孙山。于是他说:“若不是风摆杨柳连担了三天大粪,若不是连着几夜在地头浇水,若不是碰见一位温厚的老师,若不是自己暗恋的女孩子突然不理你了,好家伙,我很清楚第二年不回课堂重新补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第18页)这是不是后怕?再比如,假如没有卖户口那出戏,顺民的父亲即便家有存款,哪能给全家子弟买回城市户口?这不也是后怕吗?
写到这里,我要特意谈谈他那篇《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了。此文讲的是顺民父亲得知可以买户口后,拿出积攒的一万二,给全家四人买回城市户口的故事,而托关系、排长队、受屈辱、办此事的,正是作者本人。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回事。究其因,大概顺民家是农民,但毕竟还是“城里的农民”(第34页),而我家则是村里的正版农民,离城里还有三十里地。当年我父亲听说过这档子事吗?不知道。即便听说,我估计他也只能当成天方夜谭,却是断然不敢有起意的念头的。这意味着同样是农民,城里是一番景象,城外则是另一个世界。而由此形成的感受和体验虽不相上下,但我与他还是有一些细微区别。顺民说:
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受农民户口之累了,考学的时候,报志愿,有一栏就是填写你的户口属性,我们只能填“农应”或者“农往”,不能填报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是专为市民户口的同学准备的。因为是农村户口,我们没有被招工的权利,我们在学校里只配在集体劳动的时候积极一些,我们在那些市民户口的女同学不理不弄的眼光中发育严重滞后。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市民同学举手!我举起了手。因为我家住在县城边上,根本不知道“市民”“农民”的区别,以为住在城边子上便是市民无疑,不想,老师从隔着四排的教台上奔驰而下,就像一个嫖客发现身底下的处女竟然没有出血,狠狠地打落我举起的手,说,你家是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个烂农民装甚装?(第30页)
这是鲁顺民的创伤体验,但刚刚九岁就能收获如此重创,显然与他住在县城根儿有关。他在《怀念一种》中说:我们这个群体,“一色的农民子弟,一色的贫穷和单调,一色的窘迫和荒芜,因为是一个近城村落,从小学到中学,同学们不是县委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就是城镇职工的子女,构成非常驳杂,几乎就是县城与城郊人口构成的一个翻版,不必说,同样复制着校园外社会里的高低贵贱。”(第83页)这就是说,因为住在城乡结合部,他小小年纪就已把自己的“童年经验”搞得丰富多彩了,而我在他那个年龄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小学、中学都上在大队、公社的庙里,前后左右的同学,一水儿的农家子弟,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敢看不起我?我能看不起谁?只是活到十五六岁,我进县城读开补习班时,我才进入了鲁顺民的叙述框架,“烂农民”的感受才扑面而来。所以,这一窍我比顺民开得晚了好几年。
开窍之后,我就觉得自己的臀部盖上了“农家子弟”的圆形印章,就像崔健、王朔、姜文等人胸前别着“大院子弟”徽章一样。但同样是农家子弟,我又与顺民不同。迄今为止,我一直浑浑噩噩着,对自己的这种身份毫无反思。而从上大学开始,我这三十多年似乎一直是一种“进城”的姿态。每进一次城,就远离农村一回,直到一不留神混成北京市民,距离我的农村已是750公里。我也是个码字的,但这么多年里,我既写不出赵园那样的《北京:城与人》,更写不出威廉斯那样的《乡村与城市》。做出来的东西不接地气,就惭愧,就惶惶然,就像顺民书里说的那样,“恨不得对着镜子自己煽自己两个耳光”(第78页)。所以,我读《天下农人》,除读出其他意味外,还读到了一种重要功能——提醒。我得向顺民同志学习。
顺民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当过八年中学语文教师,成了乡下的市民。后来他入省城,进作协,一片风光,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农家子弟身份。或者是,由于他不停地“上山下乡”,不断地常回家看看,他的农家子弟身份就不断被唤醒,被确认,然后又推动着他收心内视,直到打量出它的卑微与屈辱,反思出对它的爱恨情仇。《怀念一种》是他的沉痛之作,因为他的发小赵俊明意外身亡,而赵俊明并没有像鲁顺民那样幸运,他半辈子活在河曲的大山里,始终是“烂农民”中的一员。于是顺民思考道,自己能够走出大山,很可能是一种侥幸,甚至是一个意外。他进而由小到大继续追问:“现在才明白,我们出生的六十年代,成长的七十年代,在整部中国史中,是何其糟糕的时代,……我们这一茬人,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并且活着,或者死亡,都是在干着一件又一件不该干错的错事,在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可不可以说,我们如此活过,又如此走向归宿,除了我们自身的错误之外,还可以找到别的责任认领者?”(第90-91页)
这是对我们这代农家子弟之命运的沉重反思。实际上,这种反思也断断续续地穿插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让本来不是演奏这一主题的乐章多出了一种低回的乐音。例如,那篇《失忆的蛟龙》的长文,本来写的是河曲一家敬老院的凋敝和衰败,但顺民却时不时地拐到农家子弟那里,宕出一笔,开枪放炮。他说,我们那一茬高中生若是农村户口,要想不回家种地,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高考,其二是参军,如此,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换来一纸城市户口。这是感叹赵俊明们的命运,但又何尝不是对整个农家子弟出路的一种描述?今年过年回家,母亲跟我讲起我那个外甥的心愿时,居然与鲁顺民的说法一模一样。外甥对我母亲说:姥姥啊,我这辈子有两个心愿没有实现,一是没考上个大学,二是没当成个兵。说完这番话没几天,他就像赵俊明那样,也意外身亡了,年仅26岁。那么,我这个外甥作为高中毕业的农家子弟,是不是早已窥破了自己的命运?
鲁顺民宕开的另一笔是:“我,杨凡以及许许多多昔日的农家子弟,拼命地读书进考,还不是为了脱去‘农皮’出人头地?”(第219页)由此说开去,他想到了费正清的一段论述,又延伸出自己的一番思考:
在乡村社会的普遍观念中,就人运用的体位而言,谋生使用的肢体愈多,则身份愈低下,使用的肢体部位愈靠上,则身份愈高贵。在乡村社会里,那些最为高贵的人往往是只动动脑子就可以谋得一碗饭的人。这种粗糙朴素的等级地位观念与其说是中国特有的文字造成的结果,不如说是乡村社会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从农家出来的子弟,首选的职业就是进入行政单位,案牍劳形,最后谋得一官半职。实际上,在乡村,一个走出农村的人的社会地位高低首先是行政级别的高低,其次才是从商从工及其他。而所谓工作岗位,在乡村人看来,充其量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我们这些靠着头脑吃饭的家伙其实远远没有走出乡村,这与你熟悉和不熟悉乡村关系甚少。(第221页)
验之于我本人的乡村生活经验,顺民的这番总结可谓千真万确。拿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混成这般模样,或许并非我父母最初所愿。但我就这么不管不顾,硬是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们也就只能无牛狗拉车,将就着使,凑合着用了。山西青年作家浦歌写过《一嘴泥土》,小说中,困在柿子沟里的王大虎没事常常瞎琢磨,他想以后写小说当作家,结果不时被他父亲拾掇一顿:“‘作家?’父亲说:‘我不反对,不过那是闲余时间做的事,你可不敢当主业,那样的话(父亲略微瞪大眼睛,像老虎紧盯猎物一样盯着他,投下似乎有千钧之力的看透一切的精明目光,同时上嘴唇微微翘起一点,鼻子随即上皱一点,显示出无限的轻蔑和担心,所有动作到位后,再有力地顿一顿头)——连你都养活不了,好我的娃。’”他父亲为他规划的身份是,首选当秘书,紧跟市委书记县领导,其次做记者,在报社混成无冕之王。不得不说,这个父亲何其心明眼亮,他太熟悉乡村社会的行事逻辑了。
但为什么“我们这些靠着头脑吃饭的家伙其实远远没有走出乡村”呢?鲁顺民在这儿并未展开,我倒是想顺着他的话“接着说”。
我们这代农家子弟有些特别,如果说“80后”是“尿不湿一代”(张颐武的概括),那我们这些“60后”就是“屎布一代”。在买布也要用布票的年代,我们听说过驴肉夹火烧,没见过“芝麻烧饼汉堡包”(汪曾祺的说法),便只能吃高粱面,煮山药蛋,滚铁环,打弹弓,在田间地头疯玩瞎闹穷开心。及至年齿稍长,乳臭未干,又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了。于是,固然都是农家子弟,我们这代人或许比后来者更熟悉乡村,更亲近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即便念了个大学,有了点出息,终于在城里落脚,也常常舍不得大块吃肉,没学会大碗喝酒,无法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其装扮行头,脾气性格,便都有了农民的种种特征。我儿子小小年纪时就笑话我:你怎么像个民工?我说,你小子还挺有眼力,但准星稍差,你爹我好歹也算个包工头吧。又想起当年高校改系建院,我们这个院下面就设了研究所,我也差不多干了十年文艺学研究所的所长。这种建制我不喜欢,明明就是文艺学生产队,干嘛搞得那么神秘兮兮?如此高大上,那你还怎么“出水才看两腿泥”?
作为农家子弟,鲁顺民却是这样一类作家:别看他现在混得人五人六人模狗样了,他还牢记着自己屁股上打过印,盖过戳,他腿肚子上的泥巴多着呢。
二
我已写出一堆东西,但其实只涉及《天下农人》的一小部分内容。这本书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运行,一是自己的故事,二是别人的生活。前者顺民是收心内视,后者他则在以己度人。而后者,又构成了本书更重要的篇章。
这大概与他的写作性质有关。顺民并非专攻小说的那种作家,而是主打散文和报告文学。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写报告文学的作家是很吃香的,他们写得风生水起,读者读得也心惊肉跳。但随着80年代的终结,报告文学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其中的道道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关于这个话题,前几年我写《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国作家》2010年第10期)时有所触及,或可参考。当然,不死不活期间,它又鸟枪换炮,转世再生了。现如今,它的名字叫“非虚构写作”,代表性作家是写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梁鸿。
可以说,《天下农人》的许多篇什就在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写作的谱系之中,而依我拙见,要想把一篇报告文学写好,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问题意识,能否直戳社会的痛点。由此再来看顺民的这路作品,我就觉得他扎得稳,沉得深,立意高,一些篇章起笔看似漫不经心,但读下来却又让人悚然一惊。例如,《公办王家山》,表面上聚焦全国劳模——王家山小学校长马世奎,但实际上写的是乡村教育之痛。《扶贫流水》初看散漫一片,但实际上写的是扶贫困境之痛。作协须扶贫,作家去扶贫,许多事情“只能通过平时积攒下的私人关系才可以奏效”,(第211页)这种状况我在季栋梁所著的《上庄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中已见识过,这自然已是困境;而更大的困境还在于,扶贫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违背了“救急不救穷”的古训。进一步追根溯源,此种补救又与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有关。在不断的旁逸侧出中,鲁顺民其实想要呈现的是几乎没被人关注过的问题:对于一个高考落榜生来说,没能跳出“龙门”本来已是一种失败;而返入“农门”,却很难一下子融入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中,不得不经受第二次失败。当然,经过一番“思想改造”的过程之后,他们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已毫无悬念,但问题来了:“现代教育之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有别于传统的‘另一类人’,十年寒窗苦读,结果最后和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民别无二致,那要学校干什么?”(第268页)当鲁顺民如此思考时,我想到了迪尔凯姆(?mile Durkheim)的说法:“应当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鲁顺民虽拐弯抹角,绵里藏针,但最终却是揭开了伤疤,指向了社会的痛处。而这些疼痛,往往有伤大雅,很可能已被主流意识所删除。这个时代鼓励的是“有了快感你就喊”,你怎么可以疼得吱哇乱叫呢?
更疼痛的是山西的矿难。山西煤多,煤矿就多;煤矿多,矿难也就多。王家岭矿难发生时,顺民与赵瑜等五人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然后撰写了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而《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应该是他参与这篇报告文学写作的副产品。尽管这次矿难有115人获救,出现了所谓的奇迹,但在他这篇大块文章中,我依然读出了锥心之痛。下煤窑的都是农民工,至少在山西,这依然是农家子弟脱贫致富的重要出路。我的一个弟弟在一家煤矿已干了多年,他已彻底厌倦了井下的日子,但不做这样生活又能去做什么呢?
在这次矿难中,顺民记下的几个细节颇为惊心。当他遇到一个求援的老乡时,老乡对他说:“小老乡啊,死了谁苦了谁,女人悲伤上一阵,拿上一笔抚恤金,再寻个男人,又还不是一家人?吃男人穿男人,男人死了嫁男人。哪里也个这。”(第389页)这种说法很残酷,却也道出了乡村世界的逻辑,更是说出了农民对待拿命换钱的基本态度。当被困的王吉明等人有了被救的希望时,他们并不敢贸然应答。因为有着丰富经验的王吉明知道,每遇事故,煤老板不是先想着救人,而是先打算灭口。(第405页)这种做法悖天理,灭人欲,却很可能是煤老板对付矿难的基本逻辑。当王家岭矿难的营救出现奇迹后,一部电影马上被编写出来:一位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的实习生与150多名工友被困井下,互助自救。谁都不知道,这个大学生的父亲,正是井上指挥救援的省长。省长强忍悲痛,度过八天八夜的不眠之夜,谁都不知道他唯一的儿子被困在井下。(第409页)这是丧事当成喜事办的宣传逻辑,如果这部电影拍出来,就有了所谓的“满满的正能量”。而所有的这些逻辑加在一起,疼痛固然还是疼痛,却也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无言之痛,成为了扯不断理还乱的无理之痛。它一方面降低了疼痛的质量,一方面又拉高了疼痛的指数。
鲁顺民就这样在疼痛中行走着,调查着,思考着,实录着,他时而上山,时而下乡,时而访谈煤老板(如《小经历——一位山西煤老板的自述》,时而面对村支书(如《村支书老苗》。许多时候,他的写作其实已越过了文体边界,既不像散文,也不像规整的报告文学,而只是以手记、口述实录、即时记录等方式存在着。这似乎是小道,是写作的剩余,但往往又能让作品爆发出特殊的能量。他显然不是那种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作家类型,而是靠不断地行走截获写作素材,形成创作灵感。于是他不断走出作协大院,不断返回老家河曲,不断行走在三晋大地上。他就这样走来走去,满脸风沙,两脚泥土。我甚至觉得他是在用脚来思考的作家——思考的范围与幅度取决于他丈量过的距离,取决于他眼到心到之后是否走到。
套用一个新译法,这不正是一种“在地性”(locality)写作吗?在通常的使用中,“在地性”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那是被全球化挤压出来的不得不重新面对的地方性,其中隐含着地方性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与交往,矛盾与冲突。但我所谓的“在地性”,首先是一种写作姿态。这是一种植根于本乡本土的写作,紧贴地面的写作。从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紧迫问题,常常成为其写作动因。其次,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对于城市而言,“在地性”的“他者”应该是全球化,但是对于乡村世界而言,这个“他者”更应该是城市,是一个“地方”之外的全省乃至全国。第三,“在地性”写作既是记录当下的写作,也是介入当下现实的写作。如此写出来的作品甚至有可能速朽,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它本来甩掉的就是“千年蛤蟆万年鳖”的思想包袱,就像列维评论萨特那样:“打‘介入’这张牌,就是不要像瓦勒里生前所做的那样,就是抵制‘为后世写作’的诱惑。介入的作家,就是‘在死之前曾经活过’的作家。捍卫介入,不是别的,正是抛弃死后扬名的幻影。”
把鲁顺民及其《天下农人》代入如上分析,我觉得他(它)非常符合“在地性”写作的特征。他把自己的写作之根牢牢扎在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而他的“介入”与其说是因为报告文学或口述实录等等文体,不如说是因为他农家子弟背后的另一种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是他所谓的被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另一类人”。这样,农家子弟只是其身份底色,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观察与思考、调查与分析,才是他身份中的重要支点。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部反思农民命运的书中看出了一种书生气,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那正是知识分子的幽灵在书中徘徊。或者也可以说,顺民时常在用“另一类人”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同类,入乎其内时,他是在悲悯,是感同身受,是“了解之同情”,他们的痛苦变成了“我”的痛苦;出乎其外时,他又能从自己的同类中拔地而起,成为爱伦·坡、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提出、欣赏和论述的“人群中的人”,于是他东瞅西看,南下北上,反观、反思乃至反躬自省,目光中就多了一种冷峻。他像我一样,骨子里恐怕还是乡下人,一回到河曲,他就能盘腿而坐,原形毕露,一副农家子弟的嘴脸。也唯其如此,他才好访贫问苦,受访者才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当然,他又是城里人,走进作协时,他则抖落尘土,换身行头,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不得不伏案操觚,不得不把自己的书生气诉之文本而后快。就这样,鲁顺民裂变成两种人,有时一分为二,有时合二为一。或者是,他像一个导演,随时给自己发出指令,以便自己能在两种身份、两种角色之间自由穿行,迅速切换。
鲁顺民的“在地性”还体现在,他总是从相对于市民的农民,相对于城市的乡村,相对于全国的山西,甚至相对于现代文明的传统秩序进入问题之中的。比如,矿难采访之时,他依然琢磨着农民的定义:“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怎么去定义?其实,农民并不复杂,农民者也,不就是那些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为生存而四处奔波的人吗?”(第388-389页)再比如,走访王家塔时,他思考的是煤炭与农民、与山西、与中国的关系:“一边是源源不断往外运送煤炭,一边是当地老百姓无法支付昂贵的薪炭价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资源富省的索取大于补偿,一个个曾经富足的村落的日益衰落仅仅是表象,而它的背后却是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与经济活力的严重不足。”(第129页)而在《扶贫流水》中,这种思考又有了升级版:
成也煤,败也煤。黑色的煤带走山西太多的东西,也强加给山西太多的东西,这都是这些年来的极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带来的恶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是一艘大船,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永远高踞一等舱的位置,而东部江浙诸省,则可能由二等舱上升为一等舱,其他中部省份,甚至如内蒙、宁夏等西部地区,也有可能由三等舱进级为二等舱,但山西不可能,长期的能源重化基地定位,制造业消失殆尽,根本没有进级的资格,它永远是中国这艘大船的一个提供动力的锅炉房。(第196页)
我的老家晋城就是一个产煤大户,我自然也清楚,这么多年来,这种掠夺式开采给全国带去了什么,给山西带来了什么。而顺民的这番思考更是让我确认了山西目前面临的困境。当能源结构开始调整之后,山西现在恐怕连“锅炉房”的位置都守不住了,它当然进不了三等舱,如今却更是被逼到了甲板上,茫然四顾,心里恓惶。而几十年的开采,也给我家乡带来了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大部分地方已成采空区,想找一大块坚实的地面都难乎其难。今年过年回家,听说晋焦高铁即将动工,但去哪里建“晋城东站”呢?专家们琢磨来论证去,最终选定了离我家门口不远的一块地盘,因为据说,唯独那片土地还算结实,下面没被采成大窟窿。
从传统秩序去反思现代文明(主要是政治文明),更是鲁顺民笔下的一个固定视角,《天下农人》中许多篇章都有这种视角,兹举一例。关于赵树理,我也读过不少著作文章,但鲁顺民说他有“乡绅情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有这种情结呢?因为赵树理出身于“自耕农”(土改时被划为“中农”成分),而在1942年前后,自耕农占到乡村人口的60%以上,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均为小比例存在。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成为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赵树理熟悉这种乡村社会结构,于是1949年之后,无论他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化会议上唱反调,还是后来冒死写万言书,都是因为他太了解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太知道农田里的那点事了”。于是当他洋洋万言不能自己时,他已非作家,“但他是一个农民吗?显然也不是。这时候的赵树理,是一位面对自耕农完全消灭、传统乡村秩序完全塌陷而痛心疾首的士绅面孔”。因为有士绅情结,他“哪里能够容得乡村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在营造和维护着关于乡村社会的某种秩序,他心目中肯定有一个理想的乡村国的。”(第152页)先不论这种观点的好赖,单就这种思路,就刷新了人们对赵树理的认识。这是“在地性”思考开出的花朵,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动不动就想借助新理论、新名词把赵树理装扮一番的学者,是断然想不到这一层的。
因为“在地性”写作,我发现鲁顺民的语言也很有特点。从整体上看,他的语言有书卷气,但又往往就地取材,穿插其中。这样一来,用词就地道,句子也灵动,充满一种乡村智慧和乡野之趣,甚至有一种改良山药蛋味。例如,他说高粱“钢丝面”难吃难咽难消化,“刚刚下肚不到三分钟,经过高压加温压缩的面条会一根一根站起来,撑得肠绞胃拧,没有人不吐酸水。”(第21页)他说刚有“大哥大”那会儿,“通话的时候就跟拿着一块砖头捂在脸上一样。”(第37页)他说,“黄老师特别厉害,他瞟一个眼神都让我们骨软三分。鸡不敢踏蛋,狗不敢吃屎。那是真怕。”(第75页)他说马世奎的媳妇当年嫁给他时,没有嫌他成分高,但从民办教师等他变成“公家人”,却用了整整十八年时间,“就像是守了十八年的寒窑的王宝钏终于等到西凉军马的滚滚烟尘。”(第169页)这些比喻、描写,多取自乡村世界的农业意象,再加上他不时用农业时间进入故事,不时拿来久违的用词或鲜活的表达(如“贫农、地主、成分高”“起浮财、挖底财”“吐苦水、挖穷根”“有钱不住东南房”“咱割上球敬神呢,咱自己疼,人家还不高兴!”“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毛”),就更使语言脸红脖子粗,一蹦三尺高。有时候,他又下笔凶狠,有了汪曾祺所谓的“生吃大黄猫”的效果。有一次,他问一位老干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不是为报家仇国恨?老干部说哪里哪里,那年村里唱戏,请来七大姑八大姨在家吃住五天,瓮里白面下去两指厚,老爹心疼,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从此之后,又是一连五天,家里天天吃糠,直吃得眼前的老干部拉不下屎来,好不容易拉出屎来,又止不住劲,一直拉得脱了肛,他爹在炉沿儿上温热鞋底子才好不容易揉回去”。老干部怕再吃糠,再脱肛,就拍屁股走人,当八路去了。(第19页)这段描述不仅是生吃了大黄猫,还解构了以往那种庄严的革命叙事。
这就是鲁顺民的“在地性”。对他来说,“在地”就是在河曲,在山西,在农民,在语言;“在地”不仅是要在地面走,而且还要挖地三尺,起获一批鲜为人知的史料。
①浦歌:《一嘴泥土》,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②转引自[德]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③ [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