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分类法变迁考略
董琳+何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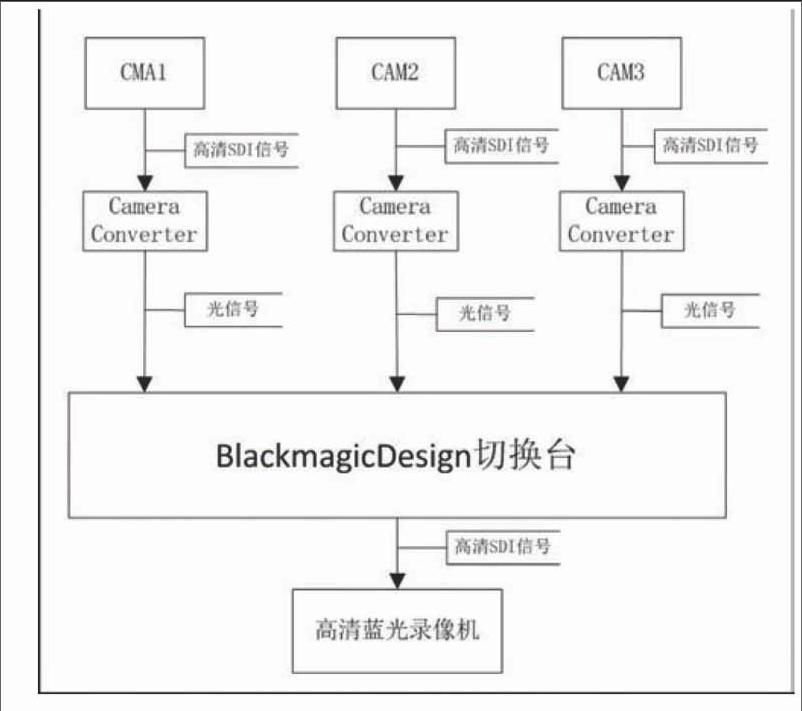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馆受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影响,在图书分类领域新说不断、百家争鸣。清华图书馆几次富有成效的新分类法的创立也都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密切相关,经历了从登录号到新书一旧书分类法,到十进制法补编,再到八大类法的发展过程。以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十进制分类法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分类法变革的现实意义,理清了新法创立及废弃的脉络、时间、思想精髓,探讨了分类法变革的契机和原因。论证将清华图书馆从事分类编目的开始时间从1923年提前至1916年。找到了与“补杜法”代表作《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已遗失)分类思想最接近的论文《编制中文书籍目录的几个方法》。
关键词杜威十进制分类法 清华图书馆 民国
1研究意义
1876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创制杜威十进制分类法。1910年,孙毓修首次在《教育杂志》上介绍了《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下文简称“杜威原法”)。这部分类法的国际地位毋庸多言,其对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民国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分类法尚未统一,电子书目尚未产生,分类、编目作为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直是图书馆里的重头戏,多有前辈学者甚或图书馆馆长不惜花费时间心思研究改良,以寻找或创造出一部本馆适用的分类法并编制出本馆的书籍目录为任内大事和荣耀。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仿杜威分类法”“补杜威分类法”“改造杜威分类法”的代表作。
清华图书馆自1912年建校之初,受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影响颇深,从没有分类编目到引进美国杜威分类法,积极投入改编和创制新分类法,经历了“仿杜”“补杜”“改杜”的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清华图书馆学者对我国图书分类法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据笔者统计,20世纪上半叶先后有四位清华图书馆分类学者共出版图书分类专著3部,发表论文4篇,编制有一定影响力的十进制分类法3部,改编或创制著者号码表3部。这四位学者分别是:戴志骞、查修、洪有丰、施廷镛。《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中肯定了清华图书馆的贡献:“20世纪上半叶我国编制文献分类法中影响较大的有16部,有2部在清华图书馆产生:《中文书籍分类法》(查修1925年)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施廷镛,1931年)。”施廷镛《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八大类法”。
开展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有关十进制分类法的研究,现实意义有三:其一,目前,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有已编目杜威号图书3万余册,八大类普通图书30余万册,八大类中文古籍22万余册。这些图书除古籍外均作为特藏存放在图书馆老馆,采用闭架借阅服务模式,由馆员入库提调图书。除这两种分类法编目的图书外,老馆还藏有大型法图书、中图法图书、1976年前西文期刊、民国中文期刊等闭架馆藏约60余万册。这就要求提调馆员对旧时分类体系及其排架方式有较为清楚的了解,以保证在提调、上架、整架、清点图书时快捷准确。其二,对于编目来说,做旧书(古籍、民国文献)的时候也不少,对于旧版图书依照年代、馆藏地套录相应的旧版分类法。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图书分类仍采用1930年施廷镛创建完成的八大类法。由于年代久远、流传未广、历经战乱和南迁等因素,完整的分类法体系及一些重要相关资料已难觅其踪。这些遗失的资料包括查修的《杜威十进法补编》,施廷镛的《中国著者姓氏号码表》《日本著者名姓氏号码表》,以别号、团体、机关、学校等为著者号的附表,同号区别表。资料丢失增加了套录工作的难度和准确度。研究过程正是资料收集整理和挖掘发现的过程。其三,以清华图书馆为窗口,真实再现中国图书馆那段分类法缺乏、中文书籍分类问题众多和以分类编目作为图书馆工作重头戏的历史。厘清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受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影响,不断创造新法的发展过程。
2十进制分类法在清华图书馆的沿革
2.1登录号时期(1912-1920年)
1931年5月,时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二十年之清华图书馆》一文,回顾了清华图书馆自创建之后20年的发展情况,文中关于编目叙述如下:“本校从前图书,只有登录号数,而无分类号码及书目。至民国十二年,始从事图书分类编目”。12从这段话中,我们得到两个重要线索:一、清华图书馆有分类编目前依靠登录号管理图书;二、清华图书馆有无分类编目的重要时间节点是1923年。笔者翻阅史料,试图寻找有关登录号时期更多的史料记载。
顺着历史的脉络往前追溯。1924年,作为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编目工作人员的查修,在其《中文书籍编目问题》一文中提到,“故解决我国书籍目录形式问题,应由账簿式改到卡片式”。从查修所述当时清华图书馆的信息显见:民国初期我国图书馆书籍目录的主要形式为账簿式目录。顺着这个线索,笔者找到了清华图书馆最早的中西文账本式目录数百册。其中,第一本西文账本式目录的设立日期为1916年,用手写花体英文记录了图书馆收藏的第1至2000册西文图书,每册书的登录号、作者、书名、分类号、书次号等数据著录在一行之中,按登录号顺序由小到大排列。目录中的两个重要字段“Class”(分类号)、“Book”(书次号)是杜威分类法的基本分类单元。从登录号为1的图书开始,每册书的分类号及书次号字段都有填写。第一本中文账本式目录设立日期为民国九年(1920年)10月4日,用毛笔小楷记录了图书馆收藏的第1至5000种中、日文图书,每种书的著录格式、排序方式均与西文目录保持一致,但目录中分类号、书次号字段为空。
这两本账本式目录力证了洪有丰关于清华学校早期编目开始时间的说法欠妥,事实上在1916年,清华学校图书馆已采用杜威法进行西文图书分类了,并非洪有丰文章中提到的民国十二年;至1920年中文图书尚未分类,未分类前的图书仅有登录号;1916年清华学校制作出了最早的西文馆藏目录。
清华图书馆登录号时期出现在分类号未确定之前,时间大约从1912年建馆之初到1920年。登录号按书籍购入先后为序,西文書是一册一号,中文书一种一号,并不重复。在清华图书馆西文图书分类号的产生早于中文图书分类号。无论对于已经分类的西文图书,还是对于到馆但未经分类的中文图书,登录号均起着统领和排序的关键作用,并在排序排架作用上等同于分类法。但登录号不能直接传达图书的主题、性质、形式等信息。endprint
2.2戴志骞中文新书一旧书分类法时期(1921-1922年6月)
1921年,在西文图书分类法产生5年后,“清华学校图书馆亦出一种分类法,略分吾国书籍为新旧两种:旧籍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新籍仿杜威十类法而稍加变通”。这部分类法由戴志骞创立,以下简称“戴志骞法”。1923年,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的戴志骞发文,“故本馆将新旧各籍分开,旧书照原有经史子集丛分别为五部,新书则参用杜威十分法为十部。合新旧书共为十五部”。此文第五章给出了当时暂定的清华图书馆分类二级简目。1923年,到馆一年的编目员查修撰文《编制中文书籍目录的几个方法(民国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六月的经验)》(1923年11月出版,下文简称“《方法》”),介绍了他初到馆时图书馆所采用的中文图书分类办法及著者号,“分类中文书籍的办法是将所有书籍分为旧、新两种。对于著者号码的办法是将每书著者的姓及其所在的朝代找出,将朝代的字写前面,著者姓的笔画数写在后面。无名氏的著作就将书名第一字的画数写下。机关出版书的办法也是如此。”查修不光印证了这段历史,还描述了配套的著者号码给号法。前后三段记录跨越十年,描述基本一致,廓清了戴志骞法大致的时间跨度为1921年至1922年。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中西图书种类激增,中国图书馆之前普遍采用的四库分类法或改良四库法,弊端诸多,如不足以概括新书门类,只有分类,没有分类号码等。国外传人中国的分类法中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使用最便利,但其并不适应中国主题笼统含混的古籍。中国图书馆学家不断探索,以杜威原法为蓝本,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分类法。于是,中国图书分类出现了新旧、西中混合的局面。先有沈祖荣创造《中国书目十类法》(1917年出版)。沈祖荣虽首创统一中西图书分类的新法,影响重大,但能为中文古籍用者极少。此时的清华图书馆里中西文图书已由1912年的2000余册,发展到1917年的西文图书5000余册,中文图书33726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杜威原法用于中文图书分类尚显简略粗糙时,戴志骞并没有贸然采用杜威原法统一中西文图书分类,而是采取了折中稳妥的态度,主张新旧并行,创造出新旧并行的中文图书分类法。
戴志骞坚持使用杜威原法分类西文图书,所以戴志骞法只针对中文图书。对于中文旧书,沿用经、史、子、集、丛五部门类,辅以十进制号码。经、史、子、集模拟杜威原法各给1000号,分000-999,丛书仿西书传记编发。此法首次将杜威十进制和数字符号标记的思想融入四库分类体系,改良了四库分类法,肯定了分类号对于图书排架的重要性。戴志骞法对于中文新书的分类更大胆,仿杜威原法,采用十大类,类目详见下文表1。该法十大类中仅五大类与杜威原法相同,其将教育、政法、兵事提升为大类,将600艺术改为实业艺术。类目提升增加了教育、政法、兵事、实业的容量,凸显了时代需求的热门图书;将文学、语言合并为800文学语言。戴法新书分类的类名、次序与杜威原法大不相同,仅采用了杜威原法十大类与十进制数字记号的形式,是继沈祖荣后创造性地构建仿杜威分类法的又一次尝试。戴志骞抓住了当时分类的难点和关键——如何应用十类法分类中文图书。他为后来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查修受其影响继续探索新法。但因其对旧书的分类并未脱离四库法,缺乏新、旧图书的划定标准,图书馆内有中文新书、中文旧书两套分类法显得累赘,所以自查修入馆后,即讨论废弃。
2.3查修《杜威十进法补编》时期(1922年7月一1930年5月)
查修1922年7月自武昌文华学院文科图书馆科毕业后,进入清华图书馆编目部工作。他采用母校出版的沈祖荣《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代替戴志骞法,试用了6个月发现很多不妥的地方,于是请学校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医学教授进行了增补。是时恰逢清华图书馆职员会议,会上鉴于分类法问题的重要性,大家进行了仔细的讨论。会后(大致在1923年3月)戴志骞认为一个图书馆西文书用杜威原法、中文书用仿杜威法,麻烦且不方便,遂授意查修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
查修分类法的主要思路是将杜威原法未用的号码用于分类中文图书,将四库书籍编入杜威原法中。学界均认为查修法是增补杜威法的代表作。而今,查修那本著名的《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1924年出版,以下简称“《补编》”)已不可寻,但笔者仍从查修同期发表的相关著作中窥得一二。1923年11月,清华图书馆职员会议召开8个月后,查修在其论文《方法》中介绍了自己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的思路,即将四库法分类尽入杜威原法的思想。此文出版早于《补编》,出版时间距《补编》接近,推断是最接近《补编》分类思想的著作。文中查修举例将经部放入杜威原法最前空处000-009(除经部乐入780音乐,小学人495.1中国语言学;史部人951中国史,史部传记入920传记,史部地理入915.1中国地理。);子部按内容入杜威原法分类,如哲学入181.1中国哲学;集部文学入895.1中国文学;丛书入080特别收集或汇集。此外,查修还制作了详细的中国历史分类表和中国行政区划分类表。《方法》中查修采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著者号码表,对表中未涉及的同类同著者、同类著者姓氏相同等实际问题均给出了解决方案,但并未明确给出四库法类目对应的杜威分类号。查修论文《中文书籍分类法商榷》(1925年出版,下文简称“《商榷》”)依然是在探索搭建中文图书对接杜威原法的办法,文章继承了《方法》的分类思想,明确了采用填空和扩充的办法对接杜威原法。《商榷》中查修尝试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各类归入杜威原法合适的位置,对于内容明确的类给出分类号,内容混杂的给出入类原则;他取消了《方法》中个人传记用“传”有别于集传、个人哲学著作用“哲”以别于中国哲学总集、个人文学著作用“集”以别于中国文学总集的做法,认为用杜威原法“最好是用数码一直到底,例外愈少愈妙”;强调“分类书籍最要紧的事,是看書的内容”。1927年,查修负责编目的《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下文简称“《目录》”)出版。书中不光收录了当时清华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图书,还收录了查修编定的中文图书十进分类号码表,给出了四库提要所涉及的所有类目对应的杜威分类号,并对书中编目图书按四库分类。endprint
从分类体例看,《目录》较《商榷》和《方法》与杜威原法更统一,《商榷》和《方法》使用四库分类体系给杜威号,《目录》将四库分类散入杜威体系中。从内容来看,《目录》《商榷》和《方法》一脉相承,《商榷》中多次提到对《补编》和《方法》的修改。《目录》较《商榷》和《方法》更完善,有了完整的分类表,体现了查修分类思想不断演进的过程。《方法》的分类思想最接近《补编》,体现了查修起初的分类思想,《目录》出版时查修分类思想更加成熟。从实用性看,由于时间所迫,查修并未在《目录》中给出每本书的分类号,未免遗憾。查修文中多次使用“实际上颇称便利”。等类似词句评价新法,说明新法已投入实际应用或小规模试用。相较国内同期许多未见投入使用,仅是主观意见的新创分类法,查修新法又有进步。
《补编》是学界公认的西法输入时期“增补杜威法”的代表作。“自此法问世后,一般图书馆之已用杜法,以及正欲分类者,颇多采用者,其于中国图书馆界,颇受影响。”“增补杜威十进法之目的,为容纳中国图籍。其大都将四库分类劈开,将各门类分别归纳于相当地位。此法之创始,当以查修氏首其例”。笔者通过对《目录》细目的研究发现,查修并未停留在“补杜法”阶段,他已不满足于仅对杜威原法进行扩充和增补,在《目录》中他还对杜威原法提出了修改和质疑,实施了“改杜法”。以300社会科学为例,“社会主义置于银行与财政之间,似属不伦。350行政,政治中一小部分。自称一类,理殊不和。遂将行政置之政治类下。”此外,他还修改多处类名:如将328.3Legislatures(立法机关团体)改为“立法”,“330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查修对清华图书馆分类法的贡献止于1927年秋,他被公派前往美国留学。在查修离开后第3年,查修法仍在清华图书馆中沿用。查修法时期是清华图书馆民国历史上唯一一段将中、西文图书统一分类的阶段。
2.4施廷镛八大类分类法时期(1930年5月一1963年)
1928年,洪有丰就任国立清华图书馆主任。洪有丰锐意进取,多有建树。从其1929年创办的《清华周刊·图书馆增刊》(下文简称“《增刊》”)中,笔者找到了这个时期清华图书馆分类法变化的线索:清华图书馆中日文图书分类采用查修分类法,在“中文书籍较少时还可应付,书籍增多以后,查修法渐不适用”。限于“时间及经济均难办到”,只能“依旧法略事修改”,于是对目录类、金石类进行了重新编排。1929年夏,“图书馆新购杨氏丰华堂藏书,加之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等陆续增购的新书,中文书籍逾6000余种5万余册”,分类骤感困难,于是决定对中、日文分类法进行彻底改革。1930年,洪有丰支持施廷镛参酌中外各家分类法,编制新的分类法草案,并将草案送请校内外各科专家修改,最后确定新的分类法分为八大类八千小类,通称八大类法。1930年5月起,“凡馆中未编之中、日文新书均照新法分类编目,此后又将原使用旧法分类的书籍一律改照新法重编。”在采用新法分类的同时,为了排架需要,又重新编订了《著者号码表》。“根据藏励酥之《中国人名大辞典》、凌迪知之《万姓统谱》、吴荣光之《历代名人年谱》等编成“中国著者姓氏号码表”。根据芳贺矢一之《日本人名辞典》等编成“日本著者名姓氏号码表”。以别号、团体、机关、学校等为著者号者,制附表多种。其同号者,制定区别表。”
关于八大类法的创立,施廷镛在其工作报告中写道,1927年前图书馆藏书6万余册,1928年增至15万册。按查修法分类,西方文学、西洋史书少分类号多,中文图书书多号少。“遂经主任之决定,参酌中外各分类法从事改编,并将所拟各科分类草案,分请校内外专门学者予以审定,而后合编成分类表,即八大类八千小类”。报告还道出了著者号码表编制经过:原用杜定友《著者号码编制法》简略产生同号多,新编著者号码表“所收姓氏较杜表增多三倍,增订区别之法,免重复之弊,且时代先后,亦有定次,可籍见学术创承之序。”
从此,八大类替代查修法被用于中日文图书分类,直到1963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简称“大型法”)出版。至今,清华图书馆古籍图书依然使用八大类分类。
诚如《增刊》中所说,八大类法参酌中外各家分类法。对比看,八大类法的确留有洪有丰法、沈祖荣法和杜威原法的印记。八大类继承洪有丰自创的分类法体系。两者在大类上区别不大,仅仅合并两类,改名一类。将洪法“000丛”“一00经”合于“甲总类”,将“四00文学”改成了“庚语文”。在二级类目上,八大类与洪法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挪动了一些类目的位置,调整了一些学科,更加突出了中国的地位。将实业交通从社会科学下调整至应用科学,在“丙自然科学”下增设“动物”“植物”“人类学”,将“中国哲学”“中国文学”调整至二級类目。八大类沿用了沈祖荣仿杜法,依然将哲学、宗教合并列类为哲学宗教,语言文学合并列类为语文。较杜威原法,八大类保留了杜威原法十进制数字标号的形式,巧妙引入甲乙丙丁文字类名作为一级大类,将每个二级类数量从杜威法的100个扩充至1000个,为今后馆藏的发展提供了更充裕的空间和弹性;八大类法合并了两个一级大类,修改了一些二级小类;此外,八大类通过提高子目层次,另立新子目,或对一级类目的名称和次序进行改造,以容纳中国书籍。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仿杜”派。
事实上,采集各家精华又经教授修改的八大类法,流传未广,应用也不似同期刘国钧、王云五等分类法广泛,已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和河北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过使用。大抵原因有二,其一,记载八大类法的书籍《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和《著者号码表》均未正式出版,影响了其传播范围。仅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1931年编印)中有甲一百号分类细表。其二,八大类法较清华图书馆之前用查修法,打破了中日文图书与西文图书统一分类的局面,更违背了图书馆界寻求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意愿。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是中外统一制,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虽不强求中外图书统一分类,但有关西方科学的类目也能在该分类表中找到相应的位置。endprint
目前留存在清华图书馆的《八大类分类表》是手刻油印本,其中八大活用表和八大类目完整。印本册子中并未加盖清华图书馆馆藏章,却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圆章和“赠送印刷品”字样。北京大学1951年建立图书馆学系,推测该册子曾用于教学或交流并因而得以收藏,但目前尚未找到相关史料佐证。《著者号码表》仅存《中国著者姓氏号码表》,《增刊》中提到的《日本著者名姓氏号码表》,以别号、团体、机关、学校等为著者号者的附表,同号区别表已不见踪影。
八大类法在清华图书馆应用前后长达30多年,客观地说,除了因为与当时学科发展的匹配度较好,也与国内同期连年抗战的混乱环境影响有关。当国内局势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对于书籍的保存、搬运和守护显然比揭示、提供服务更为重要。
2.5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创立的四种分类法大纲
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创立的分类法与杜威原法一级类目大纲比较见表1。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分类法均套用了杜威十进制数字分类号的形式,在杜威十进分类法基础上做了一些本地化尝试,是中国化的杜威分类法。清华图书馆创立的戴志骞法、查修法、施廷镛法是民国时期分类编目成果的一部分,是清华图书馆民国时期的工作缩影,体现了清华馆员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其在中国分類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3清华图书馆分类法变迁的原因
分类法终究是一门分类图书的学问,反映时代、人文、科技特征的图书,其性质、主题、装帧会不断变化。当旧法无法适用于新书,分类法势必随图书与时俱进。清华图书馆民国时期分类法经过四次大的变迁并非偶然,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无相关,根本原因和契机有以下几点:
(1)西方分类思想和分类法的输入中国。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美国《科特氏分类法》等由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留美学生带回中国。这些分类法中以杜威法使用尤其便利,其具有数字排列、简单易识记、能够反映新兴学科发展等特点,优于国内传统四部分类法。杜威原法的传人给中国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分类思路,其十进制的分类思想精髓很快被国内图书馆接受,国内图书馆纷纷将其作为模板,开启了一轮改造四部旧法,创制新法的潮流。民国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期间中国各地产生的“补杜”派、“改杜”派、“仿杜”派新说不断。
(2)新学科的产生。清朝鸦片战争,海禁大开,西洋学术输入国内,国内学术渐起变化。伴随西文图书的引进和中文新书的出现,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科目繁多,中国旧法四部、五部分类已不能统摄。新学科的产生是分类的契机也是挑战。以戴志骞法为例,戴志骞创立新书分类法将四部中并不包含的物理和化学等学科列入。又以杜威原法为例,144年来,杜威法大约每隔7年左右对印刷版进行一次修订换版,对类目进行调整。
(3)社会需要。以戴志骞法为例,戴志骞法产生于民国初期,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实业兴国的治国方针下,兵事、实业图书多出。该法将教育、政法、兵事提升为大类,将艺术改为实业艺术,类目提升增加了教育、政法、兵事、实业的容量,更凸显了时代特征及社会需求。
(4)图书新书增多。清华图书馆民国史中两大分类法的创制都与待编图书增多有关。查修《方法》述及“当时馆内书曾经登录在簿子上的已有两千一百五十部,共二万三千七百五十册。尚未登录的也有几百部的样子,书籍虽然不多,但一编目起来却很费时间。”施廷镛工作报告述及“而此三年增进之书,凡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九种,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册。加之十八年度以前积存未编之书,凡一千六百五十五种,两万九千零七十册。”随着图书增多,清华图书馆已朝着大型图书馆的规模发展。面对大量未经分类编目的图书,因旧法使用不便,查修和施廷镛都选择了编制新法。为避免重号或分类号太长,施廷镛甚至将分类号数扩大至八千二级小类。
(5)馆长驱动和优秀的编目馆员。蒋元卿在《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中给出了全国71家图书馆在民国二十三年前后所用的分类法,有15家图书馆使用自创的分类法,清华图书馆是其中之一。同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约1/5的图书馆创制了新法,笔者认为人的因素尤为重要。清华图书馆四次大的分类法的创立,与戴志骞和洪有丰两位馆长的推动密不可分。不难发现,戴志骞和洪有丰身上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们是中国早期留美回国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均获得杜威创立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学士学位。他们目光远大,勇于创新,不仅推动分类改革,自己也创立有新分类法。查修多次提到,“戴志骞先生同我说我到这里的主要工作是编制中文书籍目录”“承戴志骞先生提醒了不少意思”“戴志骞先生又同我磋商了几次”。施廷镛也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洪有丰馆长对八大类法的意见,如“遂经主任之决定”等。可见两位馆长对于分类法改革的推动与支持。创新的想法有赖馆员的实施,查修和施廷镛正是实施分类法创新的骨干馆员。查修毕业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学院图书馆专业,是中国较早一批接受专业训练的图书馆人才,毕业即受聘到戴志骞领导下的清华图书馆工作。在清华工作的5年间,到馆即着手改编分类法,先后改良沈祖荣法,创制杜威十进制补编,多次修订补编。施廷镛到清华图书馆工作前曾在东南大学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任职,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施廷镛1929年底到馆,在洪有丰领导下,1930年即着手改编新法。正是富有创见的馆长与优秀执行力的编目馆员成就了清华民国历史上一段段对分类法的革新。
4问题及展望
因着对清华图书馆十进制分类法历史和现状的深入了解和思考,笔者领悟到几代清华编目人对分类、编目兢兢业业的态度和创新精神,看到了现今馆员对清华老馆藏的守护和珍视。也发现这批老馆藏在分类编目和管理使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几代编目人的工作态度。查修在其《中文书籍编目问题》中强调新书进馆,需用“教育家对付个性的眼光仔细考察书中不甚明了的书名、著者姓名、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本、代购者、价值、是否赠送、购期、收期等”。施廷镛也在其《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中写道,“有书名不全、卷数残缺,佚姓缺名者,有无刻板时间及处所者,每遇一问题,辄费若干时间。”透过这些文字,一个个认真严谨的编目馆员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今,笔者在整理编目数据及翻阅架上图书时,发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同套图书不同卷期,登录号连续,馆藏地和分类号却不一致;馆藏地信息错误;年代信息缺失;实体书未挂电子馆藏;条码贴标粘贴随意,歪歪扭扭,甚至遮挡书内重要信息。编目工作虽不能完全无误,但这些明显的错误与粘贴习惯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足以避免。简单推断,较查修与施廷镛时代,做这些工作的编目馆员对于基础编目工作的重视程度一般,编目质量有待把控。
闭架服务模式及其利与弊。由于十进制图书距今年代久远、版本珍贵,所以采取闭架服务模式。闭架模式方便了管理者,但读者不能进入书库浏览,给读者找书带来一定困难。目前利用馆藏电子目录检索相关类目,返回结果并不理想。写作此文时,笔者得知校内一位哲学系教授查找馆藏早期西方哲学图书而不得,不免思索良久。如果是开架服务模式,这个需求并不难解决,直接入库浏览相关类目就可获取。但在闭架模式下,读者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有所获。作为图书管理者,在选择闭架管理模式时,应思考改善读者使用体验,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电子查询目录,建立可供浏览的电子类目大纲树,制作纸本闭架库书目,加强对读者分类法知识的相关教育等。
安装RFID磁条。理想状态下图书分类、编目后,按排架顺序上架,日常整架,应不存在丢失或无法寻找的情况。但在实际工作中,面对读者需求,因老馆藏资料类型、分类方式、馆藏地及出借方式多样,对于馆员的熟悉和熟练程度都是考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馆员,也会因误看、误放、错架、随意取放、编目错误等原因无法找到某本书,有时需要多库地毯式查找。随着国内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笔者设想如果老馆藏能安装RFID,实现智能定位,既方便读者查找图书,也方便了工作人员日常的清点及整架等工作。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