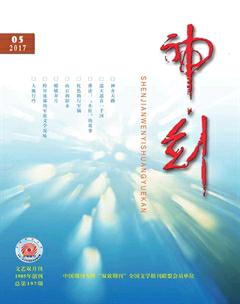醇厚浓郁的军旅文学况味
朱增泉+朱向前
一
朱向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军旅文坛有“三株口服液”的戏称,意指朱苏进、朱秀海、朱向前三个文学同龄人。其实,追溯朱氏文脉,自南宋朱熹之后近千年中还真鲜有大家,几乎从朱熹直接就断崖式地跌到了朱自清、朱光潜。当代文坛也素无名家。只是到了新时期以后,军队文场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小朱家军,“三朱”之前尚有朱春雨,之后又有朱旻鸢,特别是你朱增泉,以诗人、散文家名世而官至中将,也算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一个个案。
你常常说:“我是军人,不是诗人。”十分注重于强调你的军人身份,与一般文人大异其趣,给人印象深刻。确实,在当代中国军旅文坛,像你这样先当好一个兵,从战士到将军之后,再来进入文学,绝无先例。老一辈军旅作家如徐怀中、王愿坚等都是少小从军,一入伍就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从军也是从文;或如刘白羽、李瑛等干脆就是携笔从戎,以笔为枪,打下了一片天下。新时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军旅作家们大都类似我们“三株”,都是从新闻报道、文化宣传、业余创作起步的,随后一部分进入了专业创作队伍,一小部分步入仕途,官至将军的同时也与文学渐行渐远了。而你真是一个异数,五十岁时,已经领少将衔,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要职,却在不经意之间,深受到战地官兵激情的感染,詩兴被炮火所点燃,诗情大发而不可止,一个箭步跃上当代诗坛,这绝非一般人所能为。此其一。其二,入伍前你仅小学毕业。但你终生学习,终生成长,在工作中学,在写作中学,不断挑战自我,不断攀登新高。去年我与朱秀海有一个长篇对话,题目就叫《六十再识朱秀海》,也就是说他终生读书,终生成长的幅度及潜能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我预判他必成大家,六十再识,七十再看吧。在这一点上,你们二朱极为相似。其三,你经常在业内自称为业余作者,但你对文学的虔诚与执着远非一般专业作家可比,你已经出版诗集14部、散文集20部,还有一本书法集,无论其质与量,都已经超过了不少专业作家。就此四点而言,我认为你在当代军旅文坛上是个极为特殊的观察对象,既没有先例,也难以复制。能否请你就此发表高论?
朱增泉:我反复强调“我是军人,不是诗人”,“我是业余作者”,这都是事实啊!不妨先从我的学习经历谈起。我是1947年下半年开始上小学的,钱穆曾当过我母校后宅中心小学的校长,那时钱穆已经离开后小很多年了。但教我们算术的一位女老师华素玉是钱穆的亲戚,我听她说钱穆是自学成才,并说钱穆提倡学问要一辈子努力,靠一点一滴积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后来长期坚持自学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现在,我的母校新建的教学楼大门口立起了一尊钱穆铜像,学生们每天上学都向他行注目礼,钱穆在我家乡的声望很高。
我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很好,后来因为家中缺乏劳动力,加上我们后宅镇上当时还没有中学,上中学要去另一个镇上寄宿,费用高,家中承担不起,只能辍学了。我高小毕业是1954年夏天,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来临,农村急需一批高小、初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担任记工员、会计、文书之类。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互助组时当记工员,初级社当工分会计,高级社当财务会计,人民公社当生产队长。我当人民公社生产队长时19虚岁,17周岁,还不到入伍的年龄。
“大跃进”运动中,我因为不肯虚报高产量,成为了受批判的对象,于是,便报名参了军。
当兵以后,我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人生道路还长,靠小学文化去走漫漫人生长路肯定不行,赶快自学。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清醒、很自觉的,几十年如一日,自学没有中断过。我自学读书,开始没有计划,什么书都看。“文革”期间,反倒是我比较有计划地读书的阶段。先是用4年左右时间学马列,精读了30多本马列原著,有了一些理论基础。然后又用了4年左右时间学历史;接下来又用了4年左右时间读文学名著。学马列正课时间也能看书,历史书籍和文学名著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读的,养成了熬夜读书的习惯。后来我又参加了河北省成人自学高考,主要想检验一下自己长期自学的成果究竟如何。一共12门课程,每年考4门,考了3年,我一遍通过,平均每门课73分。我通过日积月累的看书学习,一是增加了知识,二是增强了自信。
朱向前:你这一说,自学的理念和路径都很清晰,就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且明显受到了大乡贤钱穆先生的影响,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在。儒家讲求“修、齐、治、平”,为此悬梁刺股,发奋读书,然后“学而优则仕”,这是一条通衢大道。其实,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甚至构成了中国文化赓续的另一个伟大传统,或可称之为“仕而优则学”。自科考取仕之后,一千多年的时光里,文人多为仕人,仕人基本都是文人,文人与仕人大体是合二为一的。当然有不少人把读书科考当作敲门砖,一旦鲤鱼跳龙门,登堂入室,开衙建府,不但把书丢之脑后了,而且连儒学的基本精神与要求都抛到爪哇国去了。就人数而言,这恐怕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但是,另外一部分秉持儒家理念的大文人如曹操、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张载、王阳明等等,一直到当代毛泽东,却是“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在治国理政安天下的同时,读书不辍,写作不辍,将自己的文化创造汇入中华文明长河之中,成了中华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承传者与弘扬者。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传统精神一直把为文和为人合二为一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把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统一起来作为最高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比如说曾国藩,在平定洪、杨战事最紧迫之时,还在军中校订明末大儒王船山的遗著《船山遗书》。中国古人对“文”有一种高度的信仰,所谓“内圣外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是说,可以为文一套,为人又是另一套,这个不行,不是圣人之道。而在当下,很多人已经没有了古人对文的这种信仰,过度物质化、欲望化,缺乏理想与精神,缺乏自律与尊严。
所以,我一直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你的诗歌与散文创作。你有中国优秀传统文人对文化的信仰与追求。你五十岁开始写战争诗,那时已是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又打过仗,仕途一片光明。当此之际,大部分人的选择都会是一心一意奔仕途上,生怕有什么事情分了心,减了分,妨碍了仕途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初始阶段是文人、仕人身份兼而有之,但仕途走到一定程度,就把文人身份丢了,一心一意当好官。我想,除了心力精力不允许之外,更多的是对“文”这个东西的信仰不够。反观你的创作经历,起步为文之时,正是为官一帆风顺之时。而且,五十岁才开始写诗,创作前景一般不会被看好了。但是,你总是让人一再吃惊,写诗横空出世,风头正健时又戛然而止,另起炉灶重开张,把散文又写得风生水起。最令人感佩的是退休后,65岁开始强攻5000年中国古代战争史,闭门谢客,笔耕不止,费时5年,在70岁完成五卷本《战争史笔记》。用我当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个人打赢了一场战争”。这其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执着、顽强,也充分表明,你对“文”这个东西有着非常深的信仰,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种牟取名与利的工具。有时我想,优秀传统总会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并且常常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endprint
朱增泉:我一直赞成毛主席说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所以我一入伍就开始自学,通过长期自学,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但我参战前从未想过要当什么诗人,参战给我提供了契机,使我突发性地写起诗来。官兵们上了前线,直面生死考验,情绪处于亢奋状态。我到前沿阵地去,发现猫耳洞里、堑壕壁上、炮阵地上,到处都有战士们用小石子镶嵌的,用小刀刻写的战斗誓言和诗句,宣泄他们的战斗激情。于是在前线办了一张战地诗歌报《橄榄风》。有一阵子,我连续工作了几天几夜,很疲乏,那天下午我叫司机开车出去走一走。车子顺着盘龙江河谷向西开到一处山坡下,我下车向山上爬去,后面跟着一名保卫干事、一名摄影干事。爬上山脊向南一望,哇,把我惊呆了。战区都是喀斯特地貌,南面耸立着一大片圆形山包,山包上长满绿色植被,就像一大片头戴钢盔的士兵已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我心里涌起一股激情,当夜写下了今生第一首小诗《山脉,我的父亲》,我在诗的序言中说:“人们都说,大地是母亲;我说,山脉是父亲。我踏着山脊去约会死神。”我写诗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通过去前线采访的记者、作家,把我登在小报上的诗歌带回后方,有些报纸杂志进行了转载,引起了人们注意。既然大家承认我写的这些分行文字是诗,我就“一发不可收”地写了起来。一直写到2005年,我把诗停了。集中精力开始写作五卷本的《战争史笔记》,146万字,写了五年才完工。在出版座谈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称赞说,这部书是史学的也是文学的,是军人的也是诗人的。铁凝主席概括的这两句话很精辟,我感谢她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何镇邦说:“《战争史笔记》是老朱的代表作。”他是从作品的分量和产生的影响来评价的。我接受并珍惜他们对《战争史笔记》的评价。我为这部书的确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动笔时我已65岁,写完时已70岁,没有一点毅力是拿不下来的。
二
朱向前:我有一个直觉判断,即好作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天赋型,比如莫言。一类是生活型,比如路遥。还有一类是学养型,比如钱钟书。这三类作家各有优长,创作出来的作品的面貌也迥然不同。同时,特长即特短,优势与欠缺并存。以某一类胜出的作家多,而具有复合型的作家少。当然,能把三者集于一身,基本上是百年难得一遇了。
据我观察,你的创作有点偏复合型,天赋和学养都占一点,但最突出的还是生活——军旅生活,而且是从士兵到将军数十年扎扎实实的军旅的生活磨炼和生命体验,当然,还有心胸、气度、眼界的开拓与提升。要说学养,你属于终生自学型,与钱钟书的学院式不可同日而语,但你是活学活用,经世致用的,学习与生活、与工作、与生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你的军旅生涯都渗透在文字当中,这其中透露出来的骨力、精神和气象是一般军旅作家没有的。这个东西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凭一时之热血或才气能生造出来的,而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个是骨子里的东西,别人学不来。另一方面,你的精神世界又是主动与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化去靠近的,去融入的,这又与你终生学习的毅力分不开。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被改造,同时又没有迷失自己,并且一定程度上赋予中国传统精神以新的活力,写出的东西能被当代人理解并且喜欢。
总之,我认为,你不属于才华横溢的作家,但你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持久追索,强健了当代军旅文学的风骨,提升了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内蕴,真正写出了当代军旅文学的况味。你是当代中国军队建设与变革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一点使得你和所有靠临时采访、靠短期体验写作的“旁观者”作家们徹底区别开来了,从而比他们把当代军旅文学的况味写得更真切,更入木三分。“况味”这个东西可不简单,真正能把它写深写透,写得醇厚浓郁,写得独具一格,写到一定高度,当代军旅作家中恐怕也不过是个位数。这就是你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你对当代军旅文学的独特贡献。
朱增泉:你对我的赞扬过誉了。的确,对我而言,军旅生涯不仅是影响而且是决定了我的整个人生,这种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不可磨灭的。我的爱国情怀,民族情结,使命感、责任感,直至生死观,都是军旅生涯铸就的。我把一生交给了军队,军队给了我一切。雷达是著名文艺评论家。他说我有“天生的历史感”,使用的是文学语言。我哪里有什么“天生的历史感”,都是通过看书看来的。我对历史题材有偏好,这倒是真的。历史都是人创造的,历史也都是被人破坏的。通过历史看人和通过人物看历史,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切入点不同。我有时想把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写一下,必然要写到这段历史相关事件中的人物表现,这是通过历史看人;如果我想写某一位或某几位历史人物,就必然要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剖析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是通过人物看历史。两种写法是相通的,好比一个深宅大院,从前门进去看个究竟,或从后门进去看个究竟,两头都走得通,这算不算通常所说的“融会贯通”呢?
我总结的第二条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的诗句,我借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慨。我坚持业余写作这么多年,确实不容易,感慨良多。我写历史题材、政治题材的东西比较多,思考的问题大多和我们中华民族兴衰存亡有关,与人民群众的疾苦有关。我作为一名老军人,这是肩负的使命所使然。从总体上说,我的散文随笔比较厚重、大气,有点历史底蕴,语言比较简洁,有我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但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就这次出版的四本散文随笔而言,每一本书中都有几篇好文章;但有不少篇目自己也并不满意。孰优孰劣,都交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同时,我是一个现实主义派,是写实派,写诗、写散文随笔都是这样。我坚信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我的诗歌都来源于生活。写散文随笔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这更不用说了。我写历史散文,对史料的引用是很严谨的。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差错,那是由于自己没有把史料完全查清、吃透,有时是一知半解,有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时是粗心大意。
朱向前:我还接着说“况味”,我认为况味是个比较微妙的东西。它现实可感,有温度,有颜色,有质感,但是又必须落实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上面。我想,这些比较具体的东西就是文学本身的东西。首先是人物。你的散文随笔当中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不仅形象立得住,更重要的是你对他们的深入而独到的分析。中国有句老话,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别看《三国演义》中的每个人物着墨不多,但都经得起琢磨,越琢磨越觉得不简单。所以,没有点人生阅历和精神底蕴,还真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人物。你的战争人物形象系统包括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和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朱可夫等,像这样一些被历代作家反复书写过的人物,你是如何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与观察的?endprint
朱增泉:我开始写人物散文,是写自己接触过的人,真实,但缺乏深度。后来注意从多角度切入去写一个人,避免概念化、平面化,既写他的正面,也写他的侧面,甚至反面,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真实,有血有肉,所以比较有深度。我写帝王将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物卷中的《汉初三杰悲情录》。汉初三杰是指张良、韩信和萧何,写刘邦同这三位西汉开国功臣间的微妙关系,我自己觉得把这四个人都写活了。历史卷中有一篇《秦皇驰道》,我高度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秦始皇一向是挨骂的,过去人们往往把秦王朝的速亡都归罪于秦始皇的“残暴”,尤其是“焚书坑儒”。我把《史记》中关于“焚书坑儒”的记录翻出来细细琢磨了一番,弄清了它的前因后果,我认为“焚书坑儒”这件事不仅有秦始皇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简单粗暴,也有一些“术士”欺骗秦始皇惹出的事端,也有李斯出的歪点子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也有儒生们文人相轻互相攻讦的劣根性在作怪。中国大一统局面的体制化结构,如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等,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奠定的基石,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几块基石谁都搬不动,否定不了。当然,历史本来就是任人评说的,有不同观点很正常。但是,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维护民族自尊,维护民族团结,这些底线谁都不能突破,突破这些底线就是谬论。
朱向前:“况味”之二,在于你在作品中注入的深沉思考。这种思考不是才子式的,也不是官员式的,而是结合了你的人生阅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与领悟,这种深沉思考是一般人难以抵达的。因此,这些思想就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精神价值,可以说是军旅文学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我甚至还注意到,你写的游记,也并非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带有很深的问题意识,通常都是通过古代问题来思考当代问题,增加了厚重感和忧患意识。这是你所有作品中的一个鲜明特色。
朱增泉:我的国内游记大部分是写大西北的,这同我调入原国防科工委工作有关。我们的马兰核试验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都在大西北,每当有大型试验任务我都去,分管试验中的政治工作。每次试验任务结束后,我都会留下多待几天,走一些地方,熟悉大西北,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要了解中国历史,尤其了解中国古代战争史,不了解大西北不行。汉武帝抗匈奴、通西域,中央政权与匈奴、西夏、吐谷浑争夺河西走廊,明清两代与北元残余势力(西蒙古、东蒙古)的反复交战,这些历史陈迹大多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这片广阔地域内。我以浓厚的兴趣一次次、一處处去寻访,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军事知识,每次回来都能写出一点东西。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更激发了我热爱这片辽阔疆域的情怀。文章的厚重和开阔,都来源于此。古人认为写文章的基本素质要求就是两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如果我不去大西北走那么多地方,我这些文章根本写不出来。
三
朱向前:我发现你在对“文”的求索道路上有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文无定法”,不定于一体。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你最初写诗,后转为散文,再到《战争史笔记》。在我看来,《战争史笔记》有很浓的历史研究味道。也就是说,在晚年,你实际上从散文又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历史研究,当然是比较散文化的历史研究。
所以,我认为,你求“文”是与求“道”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道”也比较复杂,有为兵之道,有为将之道,有为帅之道,还有战争之道,有强军之道,有为政之道,有历史之道。在你的散文创作中,我能看出你这方面下的巨大功夫,以及你上下求索、目极八荒的雄心壮志。军史专家糜振玉曾指出,《战争史笔记》题材鲜明,是一部散文化的战争史。能得到军史权威的肯定,也很难得。而且在这条路上,你一直把“文”与“道”结合得很好,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到了一定年龄,人生阅历与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便选择一种最合适的文体进行表达,以达到“文以载道”的效果最大化。这种做法是很明智的,也是你能取得今天成就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朱增泉:为什么我创作的文体经过几次重大的转变?我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我自己一向以“文无定法”为信条,对文体的“规范”历来不重视。后来有了“大散文”一说,我对文章结构处理更随意了。严格说起来,我书中的有些“随笔”,并不像纯文学随笔,那样的随笔汪曾祺写得最好,他的随笔有一种不经意间信手拈来的深厚功力。他的短篇小说中也经常出现大段随笔式文字,但细抠起来,一句都动不得,甚至一个字都动不得。我的“随笔”只是在文体结构上“随意而为”的意思。原因之二,我在诗歌创作后期,我已发现自己的诗歌中叙述成分太多,尤其是长诗,而诗歌是排斥叙述的,写散文可能更适合我。所以从1990年以后,我逐步转向散文随笔创作。原因之三,我2004年退出现役,从2005年开始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写作《战争史笔记》,没有时间写诗了。用散文笔调来写《战争史笔记》,是我有意为之,这也许是这部书的价值之一吧。糜振玉是军事科学院老副院长,军事学术权威,我的《战争史笔记》能得到他的肯定也不容易。我在长期读书自学中体会到,凡历史,读起来都是比较枯燥的。我想为年轻读者们写一部读得进、有吸引力的历史读物。我语言中的“诗意”,那是因为我毕竟是位诗人嘛。我是写什么学什么,通过写作这些文章,学到了不少知识。我说过,到中国历史长廊中去走过一趟和没有走过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仅丰富了知识,也提高了人生境界。
朱向前:在你的散文创作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部分,那就是《观战笔记》系列。这个系列是你对现代战争深入观察的结果。比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9·11”恐怖袭击,这三场战争的三位主角:萨达姆、卡扎菲和本·拉登,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低烈度战争,你也分别做了深刻的阐述。老实说,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很多人研究历史下功夫很深,但一观察当代问题就丧失了判断能力。这一点,让人们看到你的勇气、责任感,与活跃、灵敏的思维力,毫无暮气,充满朝气,十分难得。
而且在眼界、对策、预判、前瞻等等诸多方面,你是把这一批散文写出了我军高级将领的高度,有着居高声自远的效果,这是一般作家所不可比拟的。你写这一批散文就在这些现代战争发生后不久,做到了实时共振,及时发声。这很考验一个人的胆量与眼光。现在看来,这一批散文所表达的思想也不过时,很有时代意义和警示作用。书中对美军信息化战争作战理念、作战样式和作战手段的概要介绍,对二十一世纪美国战略思维及其战略走向的分析和预判,对二十一世纪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及必将面临美国战略遏制的分析和预判,正在“不出所料”地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endprint
朱增泉:这是你对这批现代战争散文价值的新发现。战争卷中的文章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写伊拉克战争的,第二部分是写中东、北非风波的。我把写北非、中东风波的文章也归纳进“新一代战争”,理由已在《自序》讲清楚了。写伊拉克战争的文章,曾单独出版过一本《观战笔记》。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潘凯雄先生约我再赶写一些评述中东、北非风波的文章,和《观战笔记》一书合在一起,为我重新出了一本《朱增泉现代战争散文》。其实你说的前瞻性和预判能力,是我对世界局势走向分析的结果。从宏观层面作战略性分析判断,不像对某些突发性事件的预测那样难以捉摸,它是有迹可循的。就像观察一条河流,只要找到它的源头,弄清它的流向,再根据季节变化,是可以预见它的水流大小变化的。在《伊拉克战争后的亚洲命运》一文中,我把亚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放到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上去对照分析,其发展趋势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篇文章是2004年写的,相隔10年之后,我又把它拿出来加个按语发表了一次,因为我重读时发现,文章中对亚洲发展趋向以及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都在我这篇文章的预料中。
朱向前:我与你相识已久,今天能借机为题当面求教,获益匪浅,也很高兴。我觉得时间将证明,你是在当代军旅文坛上立得住的、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人物。你自己如何评价?
朱增泉:对于写作,我只是一位“票友”,从未产生过不切实际的奢望,一切交给读者和评论家去评说吧。我还是回到这四卷散文随笔集,这是我对自己的业余写作做的一个总结。以后是否还能写些什么,要看生命活力恢复和保持得如何了。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很关注。今天你和我这一席对谈,你围绕“况味”这一命题,略过细枝末节,从总体质量上阐发我的诗歌散文创作对军旅文学的“独特貢献”,这比一般评论文章从单一向度或从技巧层面分析我诗歌散文作品的得失高了一个层次。“况味”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东西,你眼光独具,说明你对我的诗歌散文读进骨子里去了。
朱向前:你的创作和研究一再让我们吃惊,也一再让我们感动。前不久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你的新著《红楼梦诗词全钞》。这几乎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老来读红楼,你通过对其诗、词、曲、赋的解读,深幽、绵密、细腻地体验到了蕴含其中丰富、复杂的人生况味。尤其再配以你拙朴而灵动、大气而潇洒的朱氏行草,更平添雅韵高致,渐入人书俱老之佳境,也充分展示了你旺盛的生命活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