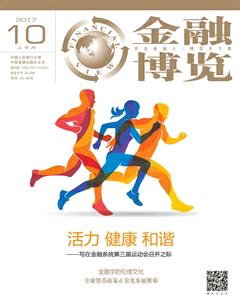利率是如何决定的?
徐高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种资产的回报率,以及资本市场里投资者的投资业绩。因此,我们面对的一个价值万金的问题是:利率是如何决定的?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的货币收放来影响宏观经济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环节——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的广义货币派生。在第一个环节中,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大的金融机构(如大型商业银行)投放货币。这种直接由央行投放出来的货币叫做基础货币,决定了金融市场(更具体地说是货币市场)中流动性的多寡。
商业银行持有基础货币是有成本的(需要向中央银行支付利息),因此,商业银行有动力将自己持有的基础货币再放贷出去,获得收益。这两者之间的利息差就是商业银行的利润。商业银行向外的放贷行为形成了又一轮的货币扩张,创造出了可为实体经济使用的广义货币(如M2)。
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顺畅的——央行这个水龙头里一出水,实体经济这个水池就能感受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顺畅的情况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此时央行只能将金融市场的利率设定在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相一致的水平上。否则,经济将会在通胀或通缩的方向上不断自我加速,最终失去稳定。
为了看清这一点,假设在央行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名义利率明显低于实体经济名义投资回报率(名义投资回报率等于真实投资回报率加上预期通胀率)。这时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会发现,从金融市场借钱来投资项目是有利可图的,于是会在金融市场中寻求融资(向银行要贷款、发行债券等)。这会在金融市场中产生较大资金需求,给名义利率带来上行压力。如果央行执意要维持低利率,就只能通过更多的货币供给来对冲资金需求上升的压力。于是,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会加大,形成更高的通胀率和通胀预期。而这反过来会让名义投资回报率变得更高,进一步推升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如此循环下去,货币供给、通胀水平会不断走高,最终让经济金融体系失稳。
反过来,名义利率明显高于名义投资回报率的状态也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会发现投资项目的回报率还覆盖不了资金成本,因而会减少融资,令金融市场中的资金需求下降,给利率带来下行压力。央行如果要维持高利率,就得减少货币供给。但这又会造成通胀的走低,进一步打压融资需求。这一过程持续下去,金融与实体中的货币量会越来越少,最终形成严重的通货紧缩,让实体经济陷入衰退。
所以,在货币政策传导顺畅的状况下,央行必须将名义利率设定在与实体经济名义投资回报率相契合的水平上。这便是央行设定利率时面临的约束。而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显然不是让经济失稳。目前,世界主要中央银行都有双重目标,一方面要保持通胀的稳定,另一方面要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这样的目标和约束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太高的自由度。
当然,即使是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能瞬时完成传导。从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到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上升、广义货币的派生总要有个时间。此外,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也会自然增长。因此,央行的货币投放并不总是带来通胀的上升——增量货币可能为经济增长所吸收,也可能还暂时未传导到通胀上去。但从较长期来看,实体经济状况和费雪效应对央行货币操作的约束是不能忽视的。从长期来看,决定利率的是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在通胀稳定的状况下,利率最终由实体经济的真实投资回报率所决定。
阻塞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可能阻塞。此时,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与金融市场的名义利率会脱钩,流动性效应在利率的决定中起主导作用。在次贷危机之后,这一现象变得尤为普遍。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阻塞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碰到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这通常会发生在实体经济陷入严重通缩的时候。通缩会让实体经济的名义投资回报率变得很低。但名义利率总是存在着0这个下限,不可能无限降低。于是,当实体经济名义投资回报率降得很低之后,通常的货币宽松就无法再刺激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和经济活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不再顺畅。此时央行需要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量化宽松(QE)等手段来直接压低长期利率和风险溢价,以便刺激实体经济。同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阻塞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对传导路径的行政干扰。
不过需要注意,传导机制受阻会让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并伴随实体经济的低迷或是危机。政府会采用措施来设法打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因此,传导受阻的状况不是常态。
决定利率的关键因素
简而言之,阻塞货币政策传导的政策扰动势必难以持续,因而只能在短期内有明显效果。所以,除非是在流动性陷阱这种极端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中长期是通畅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名义利率虽的确是由央行所决定,但央行决定利率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内生的,受到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约束。实体经济的名义投资回报率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名义利率水平。考虑到通胀在央行的调控下一般会保持稳定,所以决定利率的关键因素是实体经济的真实投资回报率。
那么,实体经济的真实投资回报率又是如何决定的呢?投资来自社会中的储蓄。由于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会持续递减,储蓄的多寡就决定了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也是储蓄回报率,因而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中的储蓄行为。如果储蓄者是消费者,这就形成了一种自动调节储蓄的市场化机制。在消费者看来,储蓄是通过牺牲当前的消费来获得未来的消费。因此,消费者每时每刻都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权衡。如果储蓄回报率看来太低了,那么消费者就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这样,投资会下降,投资回报率会因而上升。反过来,如果消费者认为储蓄回报率较高,比较有吸引力,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于是,投资就会增加,令投资回报率下降。有这种调节机制存在,投资回报率在长期来看会保持稳定,因而也就保证了利率水平不会向上或向下持续运动。
事实上,这种储蓄的自发调节是市场经济自我平衡的重要机制。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意味着资本开始过剩。此时减少储蓄、减少投资,有利于降低资本过剩的状况。反过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则表明资本相对不足,此时储蓄的上升有助于快速弥补资本的缺口。从这个角度来说,利率实际上是引导资源在消费与储蓄之间(同时也是消费与投资之间)做合理配置的价格信号。适中的利率对应着平衡的经济结构。
全球消费不足与低利率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比较容易理解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的低利率环境。
后危机时代,全球投资回报率与储蓄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破裂。在储蓄的自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候,产出资本比率与储蓄率之间应存在正相关关系(产出资本比率与资本回报率正相关,可作为资本回报率的跟踪指标)。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差不多30年里,全球经济数据中确实可见这种关系——储蓄率随投资回报率的升降而增减。但在次贷危机后,全球产出资本比率虽大幅下滑,全球储蓄率却持续处在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并未随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走低。以投资回报率来衡量,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储蓄率太高了,存在储蓄过剩的现象。换言之,全球的储蓄者并未因为储蓄回报率的下降而明显降低储蓄,从而导致全球利率持续处于低位。
全球的储蓄过剩压低了全球资本回报率,让不少国家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只能依靠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不能消除储蓄过剩这一经济结构的失衡,因而无法让全球经济走出后危机时代的低利率环境。
全球经济要根本性地走出低利率,需要进行经济结构向消费转型,把更多收入转化成为消费而非储蓄,从而消除全球经济的过剩储蓄。而这需要对收入分配做有利于居民部门的重大调整才能实现。(作者为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济学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