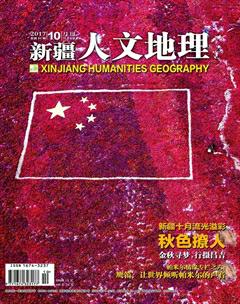托乎拉苏草原牧歌
宋红霞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走进了草原腹地,毫无顾忌地四肢伸展了躺在草原上,风儿在我的耳边窃窃私语,细润潮湿了我的眼睛。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走进了牧民人家,哈萨克族妈妈起得比太阳还早,手挤的鲜牛奶,羊粪烧开的奶茶,草原上袅袅的炊烟迷乱了我的心灵。
第一次领略如此不同的草原,宽广大气、雄浑壮美,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美丽的传说更像登努勒台古道一般绵延悠长。
这就是托乎拉苏草原,诗一般的梦幻,画一般的仙境!

通道与仙泉
已至初秋,在哈萨克族朋友巴合提江的带领下,我们驾车从阿恰尔电站西行,沿着阿恰尔河前往托乎拉苏草原。这个季节的阿恰尔河,水量充沛、碧波盈盈,源自天山的雪水透亮清澈,在巨石上飞溅起朵朵浪花,欢笑声不绝于耳。河道两旁河柳茂密,胡杨舒展,五彩斑斓的野花点缀其中,故事与野花一起生长。
托乎拉苏,哈萨克语是“直线翻越”或“一直往前走,翻过大山就到”的意思。相传是一年盛夏,一伙维吾尔商人途经这片草原欲往精河,向在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询问捷径,牧民便指着北边的“库色木契克”说:托乎拉阿索乌(意思是“直往前走”,翻过大山即到)。于是,这片大草原便以其音变“托乎拉苏”流传至今。从伊犁至精河县大河沿子镇,走此通道距离仅为180公里。
20多公里的柏油路面结束后,便进入了崎岖颠簸的山道。山道很窄,依山形成。道路两边的风景也有所不同,山势明显陡峭了许多,高大的松树像撑天巨伞,茂密的爬地松匍匐在山坡上,草地铺展蔓延到河道边。就在我对眼前的风景目不暇接之时,巴合提江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位置,大声招呼我们下车,把我们带到山边一处泉眼的位置。
这处泉水几乎要被山上滚落下来的块石掩盖了,被过往的牧民清理后,用一根很粗的钢管通向外界。阳光下的喷泉,透亮清澈而闪烁着神秘的光泽。巴合提江告诉我们说,这处泉眼是牧民心里的仙泉,在哈萨克族牧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牧民每次进山的时候,喝上三口泉水,山神就会保佑牧民平安、一切皆顺;出山的时候,也要喝上三口山泉水,告诉山神要出山了,感谢山神的庇护。
我蹲下身来,双手合拢,足足地喝了三大口山泉水。这山泉水特别清冽甘甜,润泽到了心里,“古道崎岖难通行,两天两夜辗转场。一眼仙泉涌山间,连掬三口保平安。清透甘甜润心间,碎石抱泉永不歇。百里古道佑苍生,阿恰尔山显雄奇”。
前行的道路越来越颠簸,弯道也越来越多,我们的车仿佛在巨浪中颠簸,小心翼翼地缓慢行驶着。行进了一个小时后,巴合提江告诉我们,前面就是天山支脉科尔古琴山了,马上就到托乎拉苏草原了。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托乎拉苏通道,歷史上也称为登努勒台古道。托乎拉苏通道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路况崎岖,秋冬大雪封山更难行走。但在明末清初,通达伊犁主要依靠这条古道。乾隆二十七年,经伊犁将军阿桂奏请朝廷重修果子沟旧道后,才逐渐荒废。
尘土飞扬中,我向后张望,想努力地多储存搜索一些有关古道的记忆和印象,却见古道随着山势的升高和弯道的增多,逐渐消失在身后。而古道却是真真切切地穿过了岁月的河流,穿越了历史的烟尘,让人心驰神往,魂牵梦萦。
我的草原之夜
眼前的山势虽然越来越高 ,却平坦了许多,天地顿然开阔明朗,无边无际的托乎拉苏大草原仿佛一副巨大的油画铺展在天地之间,成群的牛羊、零星的骆驼散落在草原上。远处的科尔古琴山连绵起伏、沟壑纵横、松林叠翠,如同蜿蜒盘旋的苍虬,挽手相连,幽谧而深邃。

当年雨水充沛,但因为已经入秋的原因,草原上有些被牛羊过度啃吃的地段,草色已经转黄,但黄的璀璨,黄的诱人。那草原的深处,依然是满眼的绿色,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星星点点的紫色小花点缀其中。一只孤独而桀骜的苍鹰在草原的上空缓慢地飞翔,目空着一切。天空是一尘不染的蓝,零星的几朵云,或停驻,或流动,只为了陪衬天空。远远望去,四野茫茫、无边无际,色彩黄绿相间,金色的光带在草原上掠来飘去。
草原的夜在我们目不暇接之际,悄无声息地来到。火红的晚霞给远处的山峦披上了彩衣,云朵也变得火焰一般鲜红,草原变得更加安静和空旷,我的内心也出奇的平静。
我们今晚要住在草原上,住在哈萨克族牧民的传统毡房里。
巴拉提江指着前方说,前方不远就是他父母的家。我很好奇,我目之所及的前方怎么看不到一处毡房呢?巴拉提江说:“你们都看不到,但我能看到呢。”
夜色中,草原深处出现了几处光亮,那是牧民家里温暖的灯光,夏牧场草原上的牧民现在可以依靠太阳能取电。当我们到达住处时,已是满天的繁星,夜空的星星低垂,特别的亮。巴拉提江父母家的夏牧场就在这块草原上,两处哈萨克族的传统毡房,一栋用蓝色和白色苯板搭建的简易房屋。毡房前停放着一辆越野车和一辆皮卡车。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天气好的时候,牛羊就在圈起来的这块草原上憩息。不远处,有一处几家牧民联合修建的圈舍,遇到暴雨恶劣天气时,牛羊就会转到圈舍中。
知道我们要来,巴拉提江父母早早就准备好了一切。把我们安排到了最大的一间毡房坐下,长条形的木条桌上摆满了哈萨克族风味的酸奶疙瘩、酥油、冰糖、馕饼,满满的三大盘煮羊肉冒着热气端了上来。毡房的骨架用红柳枝和花纹艳丽的彩带捆绑编织成的,高三四米,上部为穹形,下部为圆柱形,环形的毡墙,地上铺着红黑相间的花毡,蓝色丝绸镶嵌着白色花边的幔帐,四周的挂壁上还挂着许多哈萨克族手工刺绣艺术品。直对着门的毡墙上,挂着四条完整修长、细柔丰厚、光润美观的狼皮和狐狸皮,一条皮柄马鞭挂在居中的位置。巴拉提江告诉我,这张狼皮付出了六七只羊的代价。去年秋季,巴拉提江家的羊每天晚上都被狼叼走,他的父亲就设计了铁夹,联合起周围的牧民,才把狼套住。狐狸皮是去年牧民在冬窝子放羊时捡到的,去年山上的雪下得特别大,个别年幼体弱的狐狸没有扛过冬天。悬挂于中间的皮柄马鞭更是精美的工艺品,手柄用牛角打制而成,油润光滑,镶嵌了几粒红色和蓝色的宝石,鞭部用牛皮编织而成,握在手里,柔软而有劲道。
羊肉用山里最纯净的山泉水烹煮,只放了盐,吃到嘴里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味道。同行的朋友们,这时已经卸下了所有的疲劳,端起了酒杯,大口吃着肉,大碗喝着酒,爽朗的欢声笑语不断。我不胜酒力,巴拉提江笑着给我说道:“奶茶可以多喝一些,草原上的奶茶喝上44碗也不会觉得够。”44碗,该是几大壶?纯牛奶,放了盐的白开水,用砖茶烧制的黑浓茶水,再舀一勺子色泽金黄的酥油,搅拌几下,一碗浓香的奶茶就在巴拉提江的手里兑好了,香浓无比。
这个草原之夜,热闹无比的推杯换盏中,我按照巴拉提江叮嘱的程序自己倒奶茶喝,已经数不清了到底喝了多少碗……
精灵塔尔米
天刚有少许的亮色,我便悄悄地起身,从包里取出洗漱用品,走出了毡房。草原的清晨别有一番景致,我怎么能错过呢?
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空气里充斥着满满的青草味道和山泉的清冽。推开栅栏,漫无目的在草原上行走。此时的我,被一种极其细微的声音吸引。那是自草原皮肤上所发出的,牧草舒络筋骨的声音;也是被风吹袭时,草尖与游云相互拥舞的声音。此时草原,是一尘不染的翠绿,天空是没有一丝雾霾的蔚蓝,天地浑然一体。两条牧羊犬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戏耍打闹,有时紧贴着脸颊,有时把对方推到草地上,用舌头亲吻着对方的脊梁。三四头黄红色皮肤的牛儿摔着尾巴,时而低头吃草,时而纠缠着耳鬓厮磨,好一副温馨浪漫的画面。河谷高低起伏,一条小小的溪流无声地流淌着。
目之所及的前方,是完全被松树覆盖的科尔古琴山。我目测了一下距离,好像不太远。鼓足了勇气,刚行进了几步,就被从后面追上来的加尔森阻止了。七岁的加尔森板着面孔,瞪着乌溜乌溜的黑眼珠挡在我的前面,对我说:“山里有老虎、豹子,还有野猪,不能去!”这和前一天夜里巴拉提江对我们的提示是一样的,我确信了是真的。

加尔森是朋友巴拉提江最小弟弟的儿子,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家庭实行幼子继承制,就是父母最后部分遗产由幼子继承。也就是说,这块草原将由加尔森的爸爸继承。按习惯,儿子的第一个孩子要送回父母身边当父母的“亲生子”。加尔森在还没有上学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和在草原上放牧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我和这个草原上的孩子一见如故。他嘴里咬着一根青草,在河谷和草原上一会奔跑,一会仰卧,一会翻滚,做出各种顽皮的表情和动作让我给他拍照。他是草原的儿子,自然的精灵,他对着我的耳边大声说:“草原的风是绿色的,风来了,草原就绿了。”
过了一会,太阳出来了,金色的光芒播撒在草原之上,但地势低洼的河谷处是太阳无法照射到的地方,却还是毫无遮拦的绿色。此时的草原,在光影的作用下,就是一副色彩饱满的油画。加尔森在光影里奔跑,忽明忽暗。
因为那天还要赶往五媳妇沟,我拉着加尔森不舍地返回毡房住地了。推开栅栏时,巴拉提江的妈妈正娴熟有力地打开毡房顶部的天窗。哈萨克族毡房的顶部开有天窗,盖有活动的毡子,系一根长绳,方便拉取,用以通风。不远的草地上,一个简易的铁皮炉子立在那里,旁边的两个尿素袋里装着干的牛粪和羊粪。老妈妈用一个旧迹斑斑的瓷盆,将牛粪和羊粪各一半地盛满,双手捧着送到铁炉里。过了一会,袅袅的炊烟在草原上空漂浮起来。炉面上紧紧凑凑地放着四个式样不同的铁壶,个个干净锃亮。炊烟升起来之后,老妈妈才一手提着壶,蹲在附近的草地上洗脸。老妈妈七十多岁的样子,面部轮廓饱满,刻满皱纹的脸,透着黑红色健康的光泽,长裙外面罩着一件土黄色的马甲。洗过脸之后,老妈妈片刻也不停留,就进到毡房去切肉了。哈萨克族女人辛苦忙碌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美好的时光总嫌短暂。早饭后,我们和巴拉提江的爸爸妈妈告别后准备出发,却找不到加尔森的身影。
我绕开人群,放眼寻找,只见加尔森瘦小的身影飞快地跑到最大的一顶毡房里。过了一会,加尔森两只小拳头攥得紧紧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让我摊开手掌,一把金黄饱满的塔尔米在我的手心散落。塔尔米、肉类和奶制品一直是哈萨克族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食品,而作为主食的,只有塔尔米一种。现在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塔尔米的种植越来越少。但是,哈萨克族群众仍对塔尔米情有独钟,哈萨克族牧民就在山坡草地上,找一块平缓的地方,略加开垦,撒上種子,待秋季时就可收割,经筛选、洗净、煮熟,再凉晒、烘干、脱皮,才可食用。新加工出的塔尔米,可直接放在茶水里食用,也可在生牛奶中煮食,吃起来非常绵软、香甜。对这个草原上的孩子来说,塔尔米也是一种宝贵的零食。临别时,塔尔米更是一种宝贵的纪念。我的心里又酸又软,不由泪眼婆娑,匆忙低下头来掩饰。我翻遍了随身的包包,翻出了两块巧克力和一只我随身使用的青花瓷笔套的中性笔,默默塞到了加尔森的手里。希望下次相见时,加尔森还能记得给他拍了很多照片的我。
坐到车里时,我已经泪如泉涌,不敢回头。
这是一次匆匆的行走,但却如宝石一般镶嵌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成为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珍贵的尘土,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生长出金蔷薇的肥沃的尘土,散发着馥郁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