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青铜器的出土与研究概述
李 娜,艾 虹(.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00;.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
中山国青铜器的出土与研究概述
李 娜1,艾 虹2
(1.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位于河北省中南部,为当时重要的诸侯国。1956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发现了青铜器,随后在六七十年代又有大量青铜器被发现,古代的中山国开始进入文物研究者的视野,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逐渐展开,并不断深入。出土的青铜器分布范围广,数量多,种类丰富。专家就中山国青铜器的铭文、纹饰、铸造工艺、文化内涵等多个领域展开研究,取得了阶段性丰硕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山国历史、经济、文化以及族属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
中山国;青铜器;考古发现;研究现状;综述
中山为白狄别种所建,原称鲜虞,是由鲜虞部落联盟发展而来。至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始见于《左传》,此后,经过长期发展,中山国逐渐强大,并于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史籍对中山的记述匮乏,因此中山国曾被赋予“神秘”色彩。自1974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和灵寿故城相继发现后,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和研究热潮。随着中山国考古遗存的不断发现和发掘,大量制作精美、特色鲜明的中山国青铜器相继出土,成为先秦北方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对象。
一、中山国青铜器的发现与出土
早在1956年春,原平山县三区三汲村农业社在村西北打井时发现积石积炭墓,并出土四件铜车马器和多件玉器[1],但由于当时此类墓葬在河北并不多见,因此未能及时准确地对墓葬和随葬品性质做出判断。对比近年来中山国墓葬相关材料,基本可以肯定当时的打井作业面应属于一处战国时期中山国中小型墓葬区,而这四件素面铜车马器则是最早发掘所得的有确切记录的中山国铜器。
进入60年代后,中山国青铜器的发现逐渐增多,也引起了学者较多的关注,部分材料也及时发表,其中以行唐县李家庄战国墓所出青铜器最为突出。
1962年3月,原行唐县屹嗒头公社李家庄村村民在村西北角断崖处取土时发现铜器和人骨,后经确认为一座竖穴土洞墓,计出土文物16件,其中13件青铜器。郑绍宗在分析墓葬地望和铜器特征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其“可能属于战国初期中山国的遗物”[2],这一观点为日后进一步鉴定本地区中山国文化遗存提供了参照。此后,至1974年中山国故都灵寿故城及王陵被发现确认之前,在中山国故地又发现有多批中山国青铜器,除比较零散的发现和文物征集外,重要的还有以下几处:
1966年1月和12月,先后在行唐县疙瘩头公社庙上村和杨家庄公社黄龙岗发现两座墓葬M1和M2,分别出土青铜器11件和6件[3]。
1970年10月,唐县北店头公社北城子村村西窑场先后发现东西并列的两座墓葬,出土两批铜器,其中M1出土铜器11件,M2出土铜器66件并有部分铜铆钉[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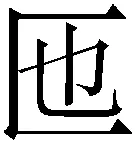
1971年,满城采石场西侧发掘一座石棺墓,出土6件青铜礼器和1件铜勺①。
1972年,在行唐县西石邱出土青铜器7件[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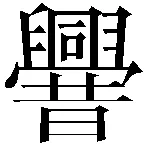
除中山灵寿故城和王陵区外,70年代以后中山国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主要有:
各项发掘简报和系统介绍中山国灵寿故城及王陵的大型发掘报告相继发表、出版,使发掘材料能够及时公布于众,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和重要前提。
二、青铜器铭文研究
中山国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尤其是中山三器的发现,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自70年代末开始,关于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一枝独秀,并得到持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
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一文中,首次公布了M1和M6的情况,发表了M1所出《兆域图》铜版、铜方壶、铜圆壶和铁足大鼎的铭文,并作了初步释读[17]。与此同时,学者围绕《兆域图》和中山三器铭文展开了广泛讨论,相继发表了多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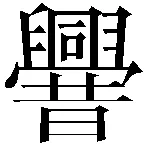
经过诸家研究考释,《兆域图》与中山三器铭文得以基本通释,学者开始针对铭文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或补释,将研究开展得更为细致和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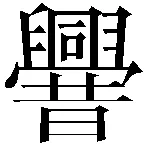

除集中研究考释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外,学者对其他中山国有铭青铜器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在中山国刀币文字研究方面,现有陈应祺《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42]和高英民《战国中山国金贝的出土——兼述“成白”刀面文诸问题》[43]两篇文章,对于认识中山国刀币文字具有一定意义。
在众多中山国铭文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以中山国文字或铭文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如林宏明和王颖先后以《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为题,对战国时期中山国文字进行整理研究。林宏明指出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字形与风格在时代上与东周早期不同,在地域上具有鲜明的晋国特征,并总结归纳了中山国铭文的异形规律,此后又出版《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44],将博士论文的研究开展得更为深入;王颖的研究则以对中山国文字构型特点见长,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45]。
韩国留学生也对中山国青铜器铭文进行了考察研究,如姜允玉的博士论文《中山王铜器铭文的语文学研究》[46]和闵胜俊的博士论文《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美学研究》[47],分别侧重于对铭文的语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中山国青铜器的铭文内涵。
总体来看,对于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其中又以对中山三器铭文研究最为突出,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和深入,从集中于铭文考释,发展到全面探讨铭文的构形、音韵、美学等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三、青铜器器物研究
对青铜器器物的介绍和研究是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而开展的,同时又因考古材料的积累而不断深入。学者在发掘简报、报告的基础上对中山国青铜器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现有研究基本可以分为整体性关注和个体性考察两个层次。
(一)整体性关注
中山王陵青铜器的出土,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快便出版了《河北出土文物——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专刊,选刊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中的精品[48];而随后出版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则收录了中山王陵墓出土的成组器物[49];此后,在系统总结我国青铜器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九卷也收入了大量中山国青铜器,并附有详细出土地点及器物尺寸、形制等信息,是研究中山国青铜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杜廴西松所作前言《东周时代齐、鲁、燕中山国青铜器研究》一文对中山国青铜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简要梳理[50]。随着中山国青铜器的大量出土,对中山国青铜器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
李学勤一直密切关注中山国考古工作,除对中山国墓葬与铭文的研究外,还对中山青铜文化作了探讨,其《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一文已将视角扩大到对中山国墓葬文化内涵的探讨上,对各墓葬出土铜器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指出“在战国前期中山已接受很多华夏文化的影响,然而仍在较大程度上保有北方民族的特色”[51]。此后,他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更多地介绍了中山国墓葬与铜器出土状况,并再一次强调“中山的华化应视为各民族文化交会融合的潮流的组成部分,其结果是为列国的统一奠定基础”[52]。另外,作者还有一些研究中山国青铜器的文章被收入《新出土青铜器研究》[53]一书中,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朱凤瀚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详细梳理了战国中山王墓和中小型墓出土的青铜器,对遗址和青铜器进行了年代讨论,分析了与周边诸侯国出土青铜器的异同,并指出战国早期中山国青铜器在器型上与燕国有较多相同处,是受燕的影响或是由于地域原因而与燕有共同的北方青铜文化因素,至战国中期以后,中山青铜容器与中原诸国已无大的差异,表明中山与周、三晋地区文化的融合加快,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54]。
李玉杰在《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一书中,认为中山国青铜礼器的特点为“既表现出与中原华夏民族相融合的风格,又具有北方青铜文明的特点”[55]。
综合来看,很多学者在对中山国青铜器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都注意到了中山国青铜器在文化面貌上的特征与转变。在这一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山国青铜器特征存在时代上的变化,战国早期更多地具有北方文化属性,保留着较多的本民族特性,至战国中期以后则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最终丧失了自身的文化传统。
此外,曹迎春还曾专门撰文探讨中山国青铜器的北方民族特性[56],并在研究青铜器文化属性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山国的民族特色[57],对加深中山国青铜器自身民族文化特性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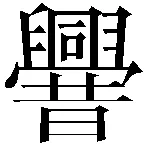
另外,何光岳主编的《北狄源流史》[61]、杜廴西松的《古代青铜器》[62]等书也都对中山国青铜器有所涉及。
(二)个体性考察
对中山国青铜器的个体性考察,是指对出土的某件、某几件或某类中山国青铜器进行的研究,除上文所述对中山三器及其铭文的研究外,其他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也比较零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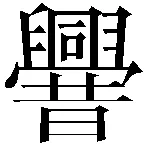
另外,天平和王晋撰文专门讨论了中山国山字形器,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山国的山川祭祀制度[69],对于研究山字形器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山国思想文化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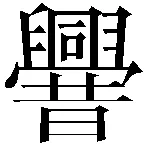
四、青铜器纹饰研究
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是传统金石学的重要内容,既能作为青铜器器物研究的一个方面,也可以开展专题性研究。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山国青铜器不断出土,为中山国青铜器纹饰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近年来,学者围绕中山国青铜器纹饰展开了较多讨论,并呈现了开展专题性研究的倾向。
前文部分成果已对中山国青铜器纹饰有所涉及,如曹迎春的《从青铜器看中山国的北方民族特色》一文便对中山国青铜器纹饰中的狩猎纹饰和动物纹饰进行了详细解析;郄瑞环的《魏国与中山国比较研究》则以比较研究的方式对中山国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进行了考察;而一些对中山国青铜器进行个体性考察研究的文章,也多对器物纹饰有所论述。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中山国青铜器纹饰的考察也更加细化。张金茹在《鲜虞中山国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一文,在分述中山国酒器、食器和水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山国的装饰艺术,对动物纹饰的应用、造型及青铜器的镶嵌工艺均进行了初步探讨[74];伍立峰的硕士论文《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认为大部分中山王墓出土的器物都以生动的动物形象为重要特点,同时指出中山国装饰艺术具有综合创新的特征,并分析了铸造技术发展对青铜器器物造型的影响[75],此后作者又专门撰文探讨了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形成的背景和原因[76];贾莉在硕士论文《鲜虞中山研究》中,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中山国青铜器纹饰与其他中原地区诸侯国进行对比,探讨了彼此间的异同,认为中山国与周边中原诸国青铜器文化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现象[77]。
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具体器物的纹饰进行专门讨论,如陈伟的《对战国中山国两件狩猎纹铜器的再认识》一文,对战国中期中山鲜虞贵族墓出土的刻线祭祀狩猎纹铜鉴(M8101:4)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的铜盖豆(M8101:2)纹饰进行了详细考察,进一步深化了对两件器物纹饰及青铜器制造工艺的认识[78];李健和刘云在《对一件战国燕式铜豆器表装饰工艺的再探讨》一文中,将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燕式青铜豆与各地出土的与之相似器物进行对比,对中山国出土类似铜器的纹饰也有所介绍和分析[79];曹迎春在《中山国经济研究》一书中,也对中山国青铜器纹饰特点进行过论述[80]。
总体来看,对中山国青铜器的纹饰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视,在中山国青铜研究成果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并逐渐出现了以纹饰研究为主体的学术成果,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
五、余论
纵观研究历程,中山国青铜器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已涉及铭文、纹饰、铸造工艺、文化内涵等多个领域,从不同角度对中山国青铜器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在各项研究当中,以中山王器铭文的考释工作开展最早、所获成就最大,并带动了对中山国文字研究的全面开展,深入到全面探讨文字的构形、美学、音韵等各个方面;对青铜器器物的研究也得到了不断发展,无论是对中山国青铜的整体性关注,还是个体性考察,均有相关成果出现,但对具体器类的研究尚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和可能;关于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以纹饰为切入点,对中山国青铜文化进行探讨,成为近一二十年的一项研究热点。
总之,结合考古发掘材料深入开展对中山国青铜器的相关研究,是研究中山国历史和先秦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状况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发掘河北古代文明的关键所在。相信在广大一线考古工作者和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对中山国青铜器及中山国历史的研究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绩。以上仅是对中山国青铜器出土与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没能对所有成果详尽阐释,未尽之处将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完善。
注 释:
① 参见1972年7月16日光明日报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的通讯《满城唐县发现战国时期青铜器》。
② 参见张克忠的《〈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补释》,未刊稿。
[1] 康保柱.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发现战国墓[J].考古通讯,1958,(6):49-50.
[2] 郑绍宗.行唐县李家庄村发现战国铜器[J].文物,1963,(4):55.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行唐县庙上村、黄龙岗出土的战国青铜器[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4] 郑绍宗.唐县南伏城及北城子出土周代青铜器[J].文物春秋,1991,(1):14-19.
[5] 唐云明,王玉文.河北平山县访驾庄发现战国前期青铜器[J].文物,1978,(2):96.
[6] 王巧莲.行唐县西石邱出土的战国青铜器[J].文物春秋,1995,(3):75-77.
[7] 崔宏.战国中山国墓葬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5.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J].文物,1985,(6):16-21.
[11] 文启明.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J].文物,1986,(6):20-24.
[12] 王丽敏.河北曲阳县出土战国青铜器[J].文物,2000,(11):60-61.
[13] 李文龙.河北顺平县坛山战国墓[J].文物春秋,2002,(4):43-45.
[14] 夏素颖,韩双军.河北平山县黄泥村战国墓[J].文物春秋,2004,(2):45-47.
[1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县文物保管所.唐县淑闾东周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2,(1):41-45.
[16] 杨书明,杨勇.灵寿县青廉村战国青铜器窖藏[J].文物春秋,2008,(4):64-66.
[1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31.
[18] 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J].文物,1979,(1):42-52.
[19] 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79,(2):147-170.
[20] 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附论墓主人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1):39-50.
[21] 于豪亮.中山三器铭文考释[J].考古学报,1979,(2):171-184.
[23] 张政火良.中山国胤嗣妾子次虫壶释文[A].古文字研究(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 赵诚.《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A].古文字研究(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79.
[26] 杜廴西松.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今译[J].文献,1980,(4):152-156.
[27] 蔡哲茂.平山三器铭文集释(上)[J].书目季刊,1986,20(3):53-84.
[28] 蔡哲茂.平山三器铭文集释(下)[J].书目季刊,1987,20(4):40-81.
[29] 蔡哲茂.平山三器铭文集释再补证[J].书目季刊,1987,21(1):168.
[30] 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81-85.
[31] 何琳仪.中山王器考释拾遗[J].史学集刊,1984,(3):5-10.
[32] 吴振武.释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器物铭文中的“钅瓜”和“私库”[J].史学集刊,1982,(3):68-69.
[33] 朱德熙.中山王器的祀字[J].文物,1987,(11):56.
[34] 何直刚.中山三铭与中山史考辨[J].文物春秋,1992,(2):22-23.
[35] 刘钊.战国中三王墓出土古文字资料考释[A].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C].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37] 李敏.战国中山国铭文异体字研究——以平山三器为代表[J].现代语文,2016,(5):142-143.
[38] 杜廴西松.“五年复吴”释[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87.
[39] 胡顺利.中山王鼎铭“五年复吴”的史实考释辨[J].中国史研究,1984,(3):165-167.

[41] 徐海斌.中山王器铭文补释三则[J].文物春秋,2008,(5):28-30.
[42] 陈应祺.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J].中国钱币,1984,(3):14-27.
[43] 高应民.战国中山国金贝的出土——兼述“成白”刀面文诸问题[J].中国钱币,1985,(4):36-37.
[44] 林宏明.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M].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
[45] 王颖.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46] [韩]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的语文学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01.
[47] [韩]闵胜俊.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美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1.
[4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出土文物——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
[49]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50]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纂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51] 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J].文物,1979,(2):37-41.
[52]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3] 李学勤.新出土青铜器研究增订版[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54]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5] 李玉洁.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6] 曹迎春.中山国青铜器的北方民族特色浅析[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57] 曹迎春.从青铜器看中山国的北方民族特色[J].晋中学院学报,2008,(5):79-81.
[58] 史石.中山国青铜艺术的特色[J].河北学刊,1982,(3):78-80.
[59] 苏荣誉.战国中山王墓青铜器群铸造工艺研究[A].苏荣誉.磨戟——苏荣誉自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0] 郄瑞环.魏国与中山国比较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61] 何光岳.北狄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62] 杜廴西松.古代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63] 胡小满.中山国古都出土乐器简论[J].中国音乐,2007,(4):70-75.
[64] 邢倩倩.先秦时期河北音乐历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0.
[65] 高英民.中山国自铸货币初探[J].河北学刊,1985,(2):87-91.
[66] 陈应祺,李恩佳.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J].农业考古,1986,(2):117-161.
[67] 陈少华.酽酽酒香间的雄风与礼制:战国中山国出土的青铜酒具[J].收藏家,2016,(11):49-57.
[69] 天平,王晋.论山字形器与中山国的山川祭祀制度[J].世界宗教研究,1992,(4):127-137.
[70] 巫鸿.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J].文物,1979,(5):46-50.
[71] 刘来成.战国时期中山王兆域图铜版释析[J].文物春秋,1992,(增刊):25-34.
[72] 张丽敏.错铜鸟兽纹铜壶赏析[J].文物春秋,1997,(2):76.
[73] 杨洁.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鉴赏[J].文物世界,2014,(6):72-74.
[74] 张金茹.鲜虞中山国青铜器的造型艺术[J].文物春秋,2002,(5):43-46.
[75] 伍立峰.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D].苏州:苏州大学,2005.
[76] 伍立峰、曹舒秀.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形成的背景[J].社会科学论坛,2013,(3):144-148.
[77] 贾莉.鲜虞中山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78] 陈伟.对战国中山国两件狩猎纹铜器的再认识[J].文物春秋,2001,(3):12-20.
[79] 李健,刘云.对一件战国燕式铜豆器表装饰工艺的再探讨[J].文物春秋,2013,(1):56-59.
[80] 曹迎春.中山国经济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
ASummaryofStudiesontheUnearthedBronzesofZhongshanKingdom
LI Na1, AI Hong2
(1.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2.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Zhongshan Kingdom, located in the central south of Hebei provinc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an important vassal state. In 1956, bronzes were found in Sanji village, Pingsh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Shortly after, a large number of bronzes were found in 1960s and 1970s. The ancient Zhongshan kingdom began to enter the vision of cultural relic researcher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cultural studies were gradually carried out, and deepened. Unearthed bronzes are featured with a wide distribution, a great number and a large variety. Expert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such research fields as inscriptions, ornamentation, casting proces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Zhongshan Kingdom’s bronze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materials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history, economy, culture and ethnicity of Zhongshan Kingdom.
Zhongshan Kingdom; bronzes; archeology discovery; summary
K231
A
2095-2910(2017)03-0056-06
[责任编辑尤书才]
2017-07-18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国中山国青铜器研究”,编号:No.HB15YY046。
李 娜(1982-),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艾 虹(1989-),男,河北昌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在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