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狼
陈忠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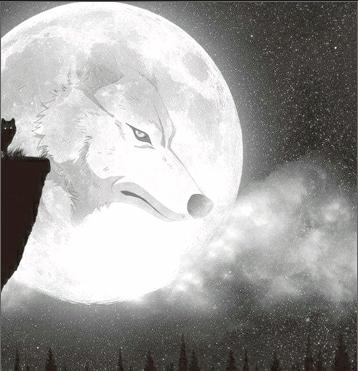

几个根系都扎在乡村的朋友遇到一起,很随意也更自然地慨叹着生活发生的急促到不敢想象的变化,由此而不由自主地感慨童年时期乡村生活的艰难,有人说到一块糖疙瘩留下的难忘的记忆;有人说到他直到进县城寄宿读中学时,晚上睡觉脱裤子时才发现别人穿着贴身衬裤,回家哭闹着要母亲赶制一条;有的人说他和一位女同学同坐一条长凳同趴一张课桌整一个学年,竟然发现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不敢正眼看对方一眼,往往是伪装看书用眼角的余光偷瞄一眼,如此等等。这些旧时生活经历的细节,几乎是一人道来人人呼应,都有过同样的或类似的经历。其实不难理解,那时候关中乡村乡民的生活情况大同小异,如上三种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我都经历过也发生过,那时候寻常存在的生活世象,今天竟有恍若隔世之感,却又如此鲜活,如在昨天发生。
这种老朋友老同学老乡党的聚合,没有任何主题话语,纯粹闲聊,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一种再轻松不过的气氛,再加上几杯酒下肚,情绪愈加亢奋,往往发生几个人同时说话各说各的人生际遇以及感慨。我往往在这种情况里省下口舌,享受听的乐趣,却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便是有人说到了狼。几个人都争抢着说到自己幼年遭遇狼的险事和趣事,我也加入了说狼的旧话之中。朋友中竟有人插话说,你能写文章,把你这些狼的故事写出来,挺有意思。我曾动过此念,之后又觉得意思不大,便拖下来。前几日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说狼的短片,业已沉寂的写狼的兴趣又发生了。
自有生活能力的幼稚时期,我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最早产生的恐惧来自两种东西,一是狼,另一个是鬼。印象里对狼的恐惧肯定早于鬼,先说狼,暂且搁置鬼的故事。
小时候闹性子耍脾气,父母顺口一句恐吓的话,狼来了。尤其是晚上,玩得兴奋不安生睡觉,或是因什么不高兴的事使性子,父母没招了就请出狼来吓唬我。狼是什么样子无法想象,恐惧的效应却在心里形成了。我对狼的近距离感知,发生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那年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劳动分红需得等到年底,父母平时只顾在农业社出工干活,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产都归集体了,自然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了。家里总不能缺盐,醋可以由母亲酿造,也难免头疼脑热去看病买药,还有我和家兄的学费,都得花钱。父亲想到了养猪,猪养肥杀了卖肉,或是把肥猪卖给屠户,都会赚一点利钱。父亲在后院垒了猪圈,春天买回一只小猪,放進猪圈。那个猪圈的上方,横着搭了几根木棍,上边又架着一束一束从坡坎上砍下来的满身长刺儿的野酸枣棵子,是为防狼跳进猪圈咬小猪的。在猪圈的外墙上,用当地出产的一种白土化成浆水画了几个圆圈,据说狼怕钻圈。其实,村子里凡养猪的人家,猪圈四周和上边都是这种防狼的措施。然而,不妙的是,把小猪放进猪圈仅仅半天一夜的第二天早晨,父亲便在猪圈外边的地面上发现了狼的蹄印。尽管小猪安然幸免,父亲仍断然采取措施,白天把小猪关进猪圈,晚上把小猪放出来安置到屋子里,在后门左侧的木梯下的墙拐角,铺了一层黄土,又撒了一撮稻草,小猪便卧在那里过夜。
我那时在城里读初中,寄宿学校,周六晚上才回家一次。有天晚上睡到半夜,我被敲击后门的响声惊醒。父亲却依旧打着鼾声。我摇醒父亲说谁在敲门。父亲随口不在意地说:“是狼。”我不由得啊的一声,睡意全吓跑了。父亲便告诉我,自打把小猪安置到后门门内的墙角,夜里时不时就有狼来守在后门口,初发生门被撞响的头两次,他手抓一根木棍,拉开后门门闩时,狼便窜上后门外的白鹿原坡上了。他曾在月光下看见慌急逃窜的狼的身影,佯装追赶几步,吓一下狼,多少能安生几晚。过不了十天半月,狼又来了,又把后门板弄得咣咣当当响,他不仅懒得招理,而且照睡不醒。父亲告诉我,狼能够在很远的原坡上闻到猪的气味,总想吃猪。父亲还告诉我,狼是用屁股碰撞后门板,狼是铜头铁尻子(屁股)豆腐腰,打狼要打腰。说罢,又睡着了。
我却睡意全无,似乎心还在慌跳着。后门板停住了响声,大约是狼听见了父亲说话的声音。当父亲睡着不久,后门板又响起来,我更加害怕了,从我睡觉的后屋的炕,到后门不过几步,狼就在后门外用尻子碰撞后门,门板响几声,卧在后门内的猪就发出却也不甚惊慌的一两声哼哼。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象着狼的发着绿光的眼睛,龇着长牙的大嘴,越想越怕越睡不着。我又摇醒父亲。他披衣下炕,懒得开后门,只听他用脚把后门板蹬得山响,就回屋睡下了。后门再未发出响声,狼吓跑了。我缓了好久才睡着。
到这年冬天放寒假时,这头猪已长成一头大肥猪了,正在加精料追肥,不久就该卖掉或宰杀了。我几乎每天晚上半夜时分都能听到狼用尻子碰撞后门板的响声,竟然也不再发生惊吓睡不着的事了。有一晚,又被狼碰撞后门板的声响惊醒,我竟然想和狼有一个短距离接触的冒险举动,捞起父亲常备的那根木棍,走到后门口,本想拉开后门敲那只恶作剧的狼一棍子,但到后门前却胆怯了,万一我在拉开后门板的一瞬间,那馋急了的狼朝我扑来怎么办?我便学着父亲的做法,用脚猛蹬后门板,狼逃走了。这是我与狼的最短距离的接触,之间仅隔着两扇门板。过了几天,杀了肥猪,再也听不到半夜狼用尻子碰撞后门板的响声了,我竟觉得有点寂寞,似乎缺失了什么。
早在一年前的冬天,还经历过一回狼的故事,不是发生在通常的乡野,却是发生在省会城市西安。我刚刚考上初中,新建的校舍尚未完工,便把新招的四个班级的学生临时安排在一所停歇的教堂里。教堂在西安城东门外的东关北边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倒也清净,是一方听讲写字的好地方。教堂的后门外,是一块很大的场地。有人在这里养了一群羊,用很简陋的围栏围住羊群,养羊人自己食宿在废弃的也很破旧的砖窑里。教堂的后门外设置男女厕所,我和同学一天几次出走后门去方便,不久也就看出过去的砖厂场,现在的“牧场”上的生活景象,大约在太阳出来许久,养羊人才赶羊出场(据说羊吃不得有露水的草)到野外去放牧。太阳落山时,他又把吃饱了牧草的羊拦回“牧场”,圈进围栏里。入学时看见的小半大羊,眼看着到冬天就长成大羊了。
临近寒假,正是关中地区最寒冷的数九季节。我在某日早晨进入教室开始早读,听班里同学说,昨晚“牧场”上的羊被狼咬死了两只。我架不住好奇,和一个同学跑出教堂后门,头一眼就看见,放羊汉字正在持刀剥着羊皮,鲜红的肉体,且已开膛,内脏就堆在脚旁边的一只木盆里,正在剥离这一只羊的羊皮。我闻到一股血腥味,却也没问羊的主人,想来昨天夜里发生狼咬死羊的惨事是无疑的了。
这是1955年的冬天,西安城东门外的东关北边一条小巷里发生的狼咬死羊的事。顺便简介一下那时的西安古城的格局。西安古城有一圈虽则破旧却基本完整的明代修筑的城墙,墙顶上可以对开汽车,足见其雄厚。西安城中心有钟楼鼓楼作为标志,以此展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也就有了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道大城门。四道城门外仍然延续着城市的格局,分别为东关西关南关北关,比之四道城门内的四条大街的规模自然小而短得多了。我在1955年看到的东关的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是庄稼地,这里那里散落着村庄,却不与东关里的城市人混居。就在东关的北面的小巷里,庄严肃静的教堂后门外,竟然有狼光顾,且咬死了两只即将出栏的肥羊,约略可以想到50多年前古城西安的一斑。我曾猜想,说不准那野狼完全可以窜进东门,在东大街乃至钟楼鼓楼下转悠觅食……在我却是看到了弱肉强食的直观现场,竟然是在城市范围内的教堂后院。
我第一次看见狼,是在两年后的一天早晨。我上初中三年级时,转学到离家较近的一所中学,约20华里,依旧继续着背馍寄宿的生活。已成规律的生活秩序,是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背着母亲蒸好的馍上学,绝大部分的农村学生都是这样求学读书的,不仅不以为只啃干馍喝白开水的生活艰苦,而且对新中国给予的上中学的机会心怀感恩。记不得那个周日下午因何故未能返校,周一天不明便起身背馍赶路,那时没有公交车,更不敢奢望自行车,只有步行,却也习以为常。因为天尚未明,父亲便陪我赶路,主要担心是怕遇见狼,那时候拦路打劫的凶事几乎闻所未闻。
暑末秋初的灞河川道的黎明时分,弥漫着一层白色的水雾。路上不见行人。过了一个马家村,也未遇见一个早起的村人。出马家村要翻一道流沙沟,很深,仅有一步宽的小道,这是传说中多有野狼出没的地方,往往使人有阴森的心理压迫。有父亲相陪,我只顾走路,没有任何恐惧,下沟再上沟丝毫也不觉得累,只怕迟到,尤其是陌生的新学校的开学第一天。不觉间翻上流沙沟对面的平地,天色有亮光了。父亲突然惊叫一声,狼!我吓得当即收住脚步,便看见离我们不过十来步远的谷子地头,有两只狼,灰黄色。两只狼在谷子地头的流沙沟边上嬉戏,这只跳起来扑向那只,那只歪头躲过,纵身跃起又扑向这只。狼肯定看见了父亲和我,却不逃走,依然戏耍着。人说虎不失威,我直接看到了的狼也不失威。父親似乎不甘于就此走掉,顺手在地上捡起两块石头,接连朝狼扔去。那两只玩得正开心的狼并不惊慌,却也终止了戏闹,缓缓慢跑着朝北边去了,给人以悻悻的感觉。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在乡野间和狼的遭遇,距离很近。有父亲在身边,短暂的惊怕很快过去,我又真实体验了父亲存在的意义。再说,那两只戏耍着的狼,没有任何凶猛残忍的外相,和我见惯了的戏耍的狗几乎没有差别。这是1958年9月初大跃进正热火的年月的一次奇遇,这年我16岁。
这时候,我尚无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的资格,每逢学校放假,寒假时到坡上拾柴火,暑假也是到坡上割草,可以挣工分。这里所说的坡,就是地理上白鹿原的北坡,起伏有急有缓,形成一条连着一条的大沟浅峪;舒缓的坡地上被先人们开垦为田地,种植小麦;陡峭的坡坎和沟峪里只能生长荆棘和野草,间有杂树。我和伙伴拾柴割草的时候,常常能发现狼拉下的新鲜粪便。狼的粪便很容易辨认,常常挟裹着白色的羊毛和黑色的猪毛,任何其他动物不会拉出这种粪便来。可以想到,就在昨夜,狼从这里走过,不由得心里发紧,偶尔还会看到被狼撕扯破烂的小孩的衣裤,那是不幸早夭的孩子因为埋得浅,被狼刨出来了,却不见残骨,我常被吓得不敢多看一眼。后来的许多年间,时不时会听到村人中间的传闻,临近那个村子什么人家的猪或羊被狼咬死了,或叼走了,甚至偶尔传闻吓人的惨事,什么村什么人家的小孩被狼伤害了。这样积久的传闻,即使无意,也在加深着对狼的印象,凶残。
大约到了“文革”发生的第二年,我所工作和生活的西安东郊地区,也和西安其他地区一样激烈着造反夺权的风潮,几乎是村村社社无宁日。与这里那里不断发生的武斗相映成趣的是,有两只狼似乎也被疯狂的社会气氛感染了,到处为非作歹,前日咬死了坡上某人家的猪,昨天夜里又叼走了河川一户人家的羊,还有威胁行人的危险事相继发生,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我那时候正在一所民办中学任教,造反伊始便停课闹革命了,学生时来时不来,教师也获得了来去自由。我因被划到“保皇”系列,受到小小的批判,虽然成了什么组织也不参加的逍遥派,却不敢任性,坚守在学校养那只正待产的老母猪(农业中学自力更生办校)。这时几乎心如死灰,却也没有了任何欲望的烦恼,业余爱好文学创作的兴趣早都消亡了,能否继续做一名教师都不敢太乐观。尽管如此,却仍然不敢马虎对老母猪的保护,到坡地上挖来酸枣刺棵子,几乎把猪圈上边纵横交错架满了,料定那两只癫狂的狼也只能徒叹奈何。我真的在猪圈外边的土地上不仅发现了狼的蹄印,还发现了狼拉的粪便,完全可以想见在猪圈外踅摸着又不能得逞施暴的狼猴急的样子,可惜这里没有我家的后门板供它用尻子碰撞的撒野行为,我自安然睡觉。
这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早晨起来便看到地上落了一层不薄亦不太厚的雪,原也不足为奇。我正洗脸的当儿,突然听到学校背后传来几声响亮的枪声,扔下毛巾便跑到院子里,心里想着武斗虽不新鲜,却还没有动用过枪炮,是不是今日破禁了?跑到院子里往后看去,白鹿原北坡上茫茫一层白雪,蓝天下的白雪地上,有三四个人在缓慢行走,可以辨认出是穿着绿色服装的军人,手里提着枪。起初以为驻军借着难得的雪地演练,随之遇到一位路过学校的熟人说,解放军为民除害,打死了那两只呈疯狂状态作恶多端的狼。我当下便有欢呼的欲望,表现出来却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这下好嘞”的话。
我的家乡有一所军事性质的高校,就在白鹿原北坡一个很大的深洼里。据说是经过反复论证,这是一方最可隐蔽的好地方,便把军校设置在这里。军校有警卫连,常常做许多爱民的善事,在当地群众中口碑甚好。他们肯定听到乡民被那两只癫狂的狼危害的议论,便决定为民除害。难得这一场雪,再狡猾的狼也无法消除行走留下的蹄印。战士便循着狼的蹄印,在白鹿原北坡的沟梁坡坎之间追踪发现了两只狼,先打死一只,再追着逃脱的另一只,又打死了。我听到的那几声枪响,就是射击逃到学校背后坡沟里的那只狼时发生的。
眼看着战士们从坡坎上走下来,从学校门前的公路上经过。我站在路边等着,看见两个战士用步枪抬着一只狼,另两个战士跟在左右,侍候着换肩。那只狼的皮毛上染着血,刚刚结束它癫狂的生命。狼头耷拉着蹭着地皮,舌头伸到长嘴外边。我不自觉地留心看了看狼的皮毛的颜色,灰黄色,只是比我十年前上学路上碰到的那两只狼的灰色偏重一点,感觉却相去甚远,那两只狼在熹微的晨光里嬉闹,尽情撒着欢,眼下看到的却是被枪击致死的一具狼尸。
这是我的家乡灞河川道白鹿原坡地最后的两只狼,死在解放军战士的枪口下。四十多年过去,这方有原有坡有河有川的颇为适宜野生兽类生存的地方,却再也没有发现过狼的行踪。
在濒临灭绝的动物名单中,似乎还没有列入狼,可见狼的生命力之强。然而,就我眼见的关中平原地区,自不必说,单是渭北高原乃至毛乌素沙漠,十余年间已经变得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形成网状体系,火车奔驰汽车穿梭,狼们便失去了任性撒野随性作恶的自由空间,迁徙到更僻远也更阔大的荒野地带去了。可以想见狼的数量在减少,比不得20世纪50年代随处都有狼的蹄印的现象了,却远远不到濒临灭绝的危急状态。我又想到,有些濒临灭绝的动物,除了生存环境恶化等因素外,很重要一条是这些动物自身所具备的商品价值,被那些生财无道挣钱无门的人盯住,或捕捉或猎杀,偷换几张钞票。譬如老虎,虎皮虎骨乃至虎血,都是任人随意张口要价的昂贵之物。狼的皮毛不值几个钱,狼的骨头亦无保健的药用功能,内脏无疑属于废物。即使作为动物的一个品种,狼在动物园里,其形象也缺失观赏趣味,甚至连狐狸的毛色也不及。狼是以凶残而造成深远影响的。如果不是它对人类和家畜为害太过太烈,一般情况下,人是不会和狼计较的,也懒得费劲劳神去捕杀它。同样可以对比的是狐狸,不在乎它天性就喜欢偷鸡,可见人的宽容;人之所以捕杀狐狸,诱因全在它那一身珍贵的皮毛,狐皮做褥不仅色彩漂亮,而且特别暖和,尤其是它的尾毛,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的绝佳用料。狼与狐狸是连一点优势都比不出的,且不说虎。
时不时地从媒体上得知老虎生存的危机,便引发担心;获知仅剩几只的朱鹮,经持续多年的精心救助和保護,已经繁衍到一千余只的颇为壮观的族群,完全脱离灭绝的危情,我甚为欣慰,那鸟儿实在太漂亮了;无论狼是否会灭绝,我却怎么也操不上心来。平心而论,我和狼没有构成成见的因由,尽管它曾经用尻子撞碰过我家的后门门板,却不过是猴急的无奈的举动罢了,没有对家养的猪造成伤害;尽管上学的路上遇见过两只狼,因为身边站着如山的父亲,我也没有受到威胁,倒是看到戏闹着的狼的可爱的一面。在我生存的白鹿原下灞河川道,四十年不见狼的声息和踪迹,似乎也没有听到过一声惋惜或遗憾。
我相信狼不会绝种,少几只就少几只吧;也希望狼不要灭绝,它毕竟是野生动物之一种,是造化赋予世界的一种生命形态,无论其可恶或可爱与否。
(选自《记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