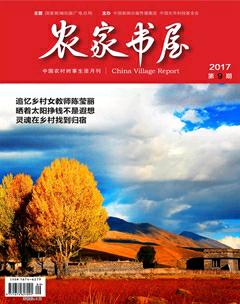城市的混凝土与记忆中的故乡大地
叶然
官墙里,在作者笔下只是沉睡在都市里的一条繁华落尽的旧巷子,当旧巷子装满了来自四海八方贫下阶层的人,它便成了城中村,东方的“贫民窟”。这里生的很粗糙,可是这里又活得很热闹。是的,它虽被称“官墙里”,却与官僚毫无关系。
《官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只是一本随笔文集。这个随笔写的很随意,主题却是鲜明的:当一个人走出了乡土,又该走向哪里?一个人的乡村和城市,何处又是自己的归宿?
自从城镇化大刀阔斧的开始,在城市,也在乡村。不论是城市里那些土著,还是穷尽了前半生才从乡村大地里走出的,现已摇身一变成为专家、学者等的上等人、中等人,都開始对已逝的乡土心心念念,也为留住乡土做各种事情。一时间,“谁夺走了我的故乡”“谁剥夺了我于城市生活的权利”等,有关乡土和城市生存权的讨伐便到处开了花。
当孩提时经历过的地方,其模样竟然随着城镇化不复存在,记忆中的美好于现实中逐渐崩塌时,我们便要伸出援助之手进行“挽救”了。有着农业社会背景的中国人,是有着浓厚的怀旧情结的,尤其对孩童时期的经历,再眷恋不过,这也通常被人称为是一种情怀的体现。而有着这种感受的人群,尤其在中原和西部黄土高原最为明显。大地是有生命力的,它给生长在泥土里的人统统烙上了印记。不论走到哪里,这种烙印是怎么也抹去不得。
所以,我们都是一只脚踩在城市的混凝土上,另一只脚留恋在记忆中的故乡大地上的一群人。我们不想失去正在生活的城市,亦不想丢失记忆里的乡村。
的确,在这最贫穷的村落里,有最淳朴的人,最淳朴的人依然在用最原始的农具耕种土地,有挑水的扁担,更有最能代表乡村的破旧的房子……
但是,又有其前后矛盾之所在:嫌弃它,却又赞美它。或许,乡建之所以难以进行和备受争议便是在此的:乡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乡里的人想要消灭它,过上翻新的生活,城里的人想要挽留它,过上田园的旅人生活。
但终究乡村不只是城里人的。对于乡建,我们终究还是要摆脱掉对留住乡土和乡愁的呻吟。过分的护佑,对住在乡里的人们来说,等同于剥夺了他们向往富贵生活的权利。
没有他们的村和城,这村和城的建设不可说是成功的。所以,给乡村和城市定义一个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是谁夺了谁的城,谁抢了谁的村,便是永远无法说清楚了。
作者书写了每一个乡里人和乡里事,也包括“城中村”里的人。在作者的描述中,他始终都在强调彼此融合的乡建方式。正如他所言的,如果引入到乡村的产业,不论是在精神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上,如果不接地气、没有普适性,那么这只能是一种排村民的、想当然的乡村建设。村民眼里没有田园诗,田园诗只在走出乡土,对故乡进退两难的人那里。
当然,作者对乡土也是有着十分浓重的情怀的。作者笔下的官墙里虽正常存在,但它始终是被城市边缘掉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被认作了“城中村”。它生在城市,却不属于城市,就是官墙里的宿命,亦是生长在官墙里的人的宿命。有着这种特质的城市,均不可称为成功。因为生长在里面的人都是被排斥的一个群体。
我想,生活在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害怕有一天会被“赶出”城市,而又不知道以哪种方式回到来时的地方。那么,这时,对于一座城市的诉求便是,自己能够不被“赶”走、有安全感的城市。但往往最有可能被“赶”走的,便是生在城市最底层的“城中村”“贫民窟”的这一个群体。
一座城市,或许它并不是一座经济发达、街容繁华的城市,但它一定是一座包容性的城市。不论它有多重的压力,它都应该尊重城市里每一个讨生的人。一座尊重城市里每一个个体的城市是城市最合理的存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