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京味”作家的文才与心史
吴志菲
从一位没读过几年书的小小交通员,成为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他经历的坎坷波折不是一篇短短的文字所能容纳的。他说,人一定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自己所能贡献的,惟有写作是一个认真的选择
小八路、日本劳工、新四军战士、解放军文工团员、见习记者、创作员、建筑工人、“右派”、作家,这样一些名称放在一起,似乎多数之间都不是很搭调。若说这些名称分别指代某个人的一段人生,这个名称排列写照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生脉络,那么许多人会想:这种戏剧性人生想必只在矛盾迭起的小说中才能得见吧?
但是,这的确不是某位作家独具匠心的笔下虚构出来的戏剧人生,而是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传奇人生。迈着一双大脚,邓友梅曾走过战争年代那峥嵘岁月,走过狂热年代那苦难深渊,也走过劫后余生那辉煌大道。如今虽已是高龄之年,邓友梅却还坚实地“走”在他的路上,而且他的足下总在生“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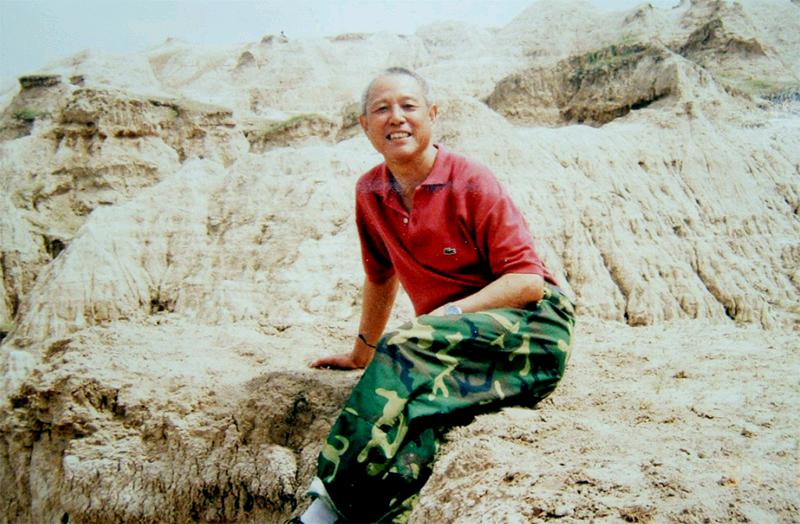
只上过4年学却领一代“京味小说”之风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舍先生因写作“京味小说”而成就经典。约半个世纪后,邓友梅继之成为又一位重量级的“京味小说”作家,与同时期的陆文夫并称为当代两位以写南北城市小说而著称的名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人们刚从“文革”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反思苦难的“伤痕”文学应时而生,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在铺天盖地的“伤痕”之中,邓友梅于1979年发表作品《话说陶然亭》,立即以一种迥然不同的奇异姿态震惊文坛。此后,邓友梅又发表了《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邵氏兄弟》《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一组具有浓郁老北京民俗风情的京味文化小说。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品,“邓友梅”这个名字在当代文学史怎么也无法绕开。
尽管邓友梅从解放后便来到北京,但他祖籍是山东,出生于天津。2005年夏天,一家电视台给邓友梅录专题片时,邓友梅和摄制组一行人特意赴天津找寻童年的记忆。在天津昆纬路小学,邓友梅上了4年学,这也是他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最高“学历”。遗憾的是,现在昆纬路小学的景致完全变化了,邓友梅在那儿已经找不到过去的一点影子。
只上过4年小学的“鲁籍津生”邓友梅又怎么写出了那么多惟妙惟肖的“京味”小说呢?有句话说,“罗马不是一天砌的”,邓友梅对于老北京人物风土的熟悉实在是几十年精心积累的成果。
解放后,邓友梅随部队来到北京,最初的工作便是和一些旗人知识分子打交道,了解他们的各方情况,安排他们的工作及生活。在清朝政权尚存时,旗人有一种特权:子承父职,生来有一份钱粮;而且旗人子弟只能习武学文,从军当官,不准经商、务农、学手艺。于是,旗人后代根本不必为生计操心,斗蛐蛐遛鸟,驯狗架鹰,玩的名堂多之又多。大清政权倒台后,许多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旗人沦落到无法糊口的地步。可是,在深入地接触了那些老旗人后,邓友梅才知道,旗人在吃喝玩乐上的“闲功夫”不可小看。
邓友梅曾访问过一位王爷的后代,那位老旗人坦率地说除了玩以外自己什么也不会做。但是,他却有一个绝活——听戏时只要演员在台上唱一口,他立马就知道学的是哪一派。后来,这位老旗人被安排到了戏曲改革工作组,“工作内容便是听戏,听完后指出哪些不足、应怎么改进,写出来,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当时,邓友梅知道有一位在工地伙房烧火的老旗人的故事。据说,这位烧火师傅小时候经常跟着他那喜爱哼曲的父亲吹笛玩儿,“北京市成立昆曲剧院找不到笛师时,这位老旗人一试吹,一吹惊人,一下子被评定为一级乐师”。在邓友梅所接触的那些老旗人后来都各尽其才,成为新中国的劳动者。据他所知,那些人里面能编能写的为曲艺、京剧写词编剧,对吃喝有考究的到有关单位作“品尝员”或物价调查员,能写会画的更可参加书协画院,最差的也安排到某些部门做文书刻蜡版,得到了发挥特长的机会。
从这些活生生的人与事上面,邓友梅仿佛看到古都的兴衰,他细细品味着发生在天子脚下的那些人生故事。他知道,若从普通人的视角写出老北京的画面,也许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这种长期的、自觉的观察与思考,积淀下了邓友梅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文革”后,决意写出自己特色的邓友梅开始发掘老北京风土人情这座“宝库”。
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必有其一份韵味独特的方言,方言无疑是地域文化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友梅试图用北京口语来写北京人的生活。邓友梅在生活中发现,同是北京人,上了年纪的人与年轻人语言不同;同是北京郊区,通县与门头沟又不同;就是北京城内,东西南北也不一样。过去老北京有“东贵西富,南贫北贱”之说,不同阶层所使用的方言自然有区别。为了写出老北京的气韵,邓友梅曾经花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吃过晚饭到天桥去听评书。
那时,北京南城天桥的茶馆是听书人的好去处,老有说书人在那儿说《聊斋》、《七侠五义》等传统书目,就是连着听三个月也不会重样。邓友梅去茶馆听书之前,他先要把故事看一遍,了解故事情节,然后自己想着应该怎么去讲,并在家里自己讲一遍。这样一个程序后,再去茶馆听说书人讲,找到自己的差距。而且,他也不光听说书人如何用北京话表述生活,还搜罗周围坐着的那些听客们嘴里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地道的北京话,不是知识分子在学校里能学来的”,邓友梅说那段茶馆听书的经历,对他写小说起了很大作用。
确实,写作者虔诚地伏下身子,与现实生活越近,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更能吸引人。20世紀80年代末,邓友梅在创作中篇小说《烟壶》时,曾经到河北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他不但在车间里仔细观察每一道工序,还与王习三促膝谈心几昼夜,并因此与王习三成为好友。回到北京后,八月的京城气温高达38摄氏度,酷热难耐。然而,被创作的热情激发的邓友梅顾不得炎热,每天4点多钟起床就开始写作,一连两个月不停地写,以致胳膊、脖子和大腿上都长满痱子。小说发表后,连“末代皇弟”溥杰先生也惊叹邓友梅“近著烟壶稗史,洛阳纸贵”,评论家们更是把“京味小说”作家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了邓友梅的头上。endprint
一条小消息“唤”醒了他的思乡梦
1983年1月的一天,邓友梅翻看《人民日报》时看到一张小照片,上面是几个农民在集市上挑选布料和针织品,下面的文字说明是:“山东省平原县去年农业又获丰收,人均集体分配达到280元……”当“山东省平原县”几个字跳入眼帘,邓友梅的手微微颤动起来,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沸腾了,他使劲眨眨眼睛——没错,正是山东省平原县,久违的故乡!视线仿佛被那条小新闻粘住,邓友梅一遍又一遍地“贪婪”捕捉那上面每一点信息。
邓友梅从1945年入伍,后随部队南下,以后近40年没有回过故乡平原。对他来说,故乡是痛苦的记忆,打着屈辱与辛酸的烙印。
平原县王凤楼镇邓庄是邓友梅的祖辈劳作生息的地方,他的祖父是闻名于乡里的木匠,但手艺好也抵不住时局艰辛,一家人没过上一天温饱的日子。祖父生了5个儿子,饿死了两个,卖了一个。邓友梅的父亲十来岁给人放牛,冬天去放羊时仍然光着脚,两脚冻僵后就伸在新拉的动物粪便中取暖。稍大些,他便随乡人闯关东到了东北。在沈阳拉车时他结识了一位东北军军官,给这位东北军军官拉包车。东北军进关时,他随着也进了关,到了天津,在铁路上谋到一份差事,总算有了一个开枝散叶的“窝”。
邓友梅出生于天津的海河边,5岁开始上私塾。“七七事变”后,邓友梅随父母回山东老家避难。一年后全家重新回到天津,已到入学年龄的邓友梅进入昆纬路小学上学。
后来,邓友梅全家搬离天津,缘于一次他父亲的血性爆发。面对日本工头蓄意挑衅,气愤不已的邓友梅父亲照着日本工头的鼻子就是几拳,把日本工头疼得直叫唤。得罪了日本人,不但差事保不住,天津也不能呆了,父母决定这次彻底搬回老家。邓友梅已上到四年级,却不得不告别心爱的学校。
老家也来了日本人,他们在每个村庄都设了据点,村民们每日进出村子都要被搜身检查。日本人虽然猖狂,但八路军的势力也时常活跃在村子里。“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光啊我的好老乡”,在村里动员参加八路军的会上,邓友梅学会了这首歌。1943年,在这首歌的鼓舞下,邓友梅报名参加八路军。因为年纪小,他被安排在八路军渤海军区的交通站当小交通员。
和老电影里的小交通员一样,那时邓友梅经常爬上草垛或屋顶为八路军望风,或者为八路军当向导、送情报,有时还混入据点与卧底人联络。那时,日本鬼子对成年人进出村庄搜查很严,但对小孩子不太防范。有时,孩子们你追我跑就能混过去。有一次,八路军的两个伤员被俘,上级命令邓友梅混进据点。他就以看亲属的名义混进了据点,借提药箱子的机会见到了两个伤员,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为此,邓友梅还受到了一次正式的表扬。
1943年底,因八路军实行精简,年龄太小的邓友梅被部队精简回家,“复员费”是40斤小米、几尺粗布。为躲避日伪军的搜捕,他不得不回到天津打零工谋生。有一天,已是几天没吃饭的他正在街上游荡,忽然看见一家工厂招工,凡有人报名便可到院子后头领一碗豆腐脑两个烧饼。不明底细的他也凑过去报名,生怕人家嫌小不要他,他还跟招工的说了几句好话。在招工表上签字并按上手印后,邓友梅领到了那份饭食。晚上,所有工人一起被装进一辆闷罐火车。一路上邓友梅惴惴不安,不知火车会开到哪儿去,火车一直开到青岛附近的一个小站。不久后的一天凌晨,工人们又被强行押上了一条装运矾土矿石的轮船。这时候,邓友梅才知道自己会被送到日本当劳工。
在海上航行了7天,船才到了日本的下关,邓友梅被送到山口县德山曹达工厂做火药,那时日本壮年男人几乎都被送到前线参战,工厂里干活的都是妇女。男劳力则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抓来的。邓友梅虽然那时还未成年,但仍然每天要从事高强度的劳动,而且手脚稍慢便会招致一顿拳打脚踢。
在异国他乡饱受欺辱,邓友梅做梦都想回国,想参加队伍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1945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邓友梅和一批劳工被遣送回国。逃出日本人的控制后,邓友梅就找到部队,第二次参加了革命队伍,任鲁中军区敌工科通讯员。
自此,邓友梅近40年没有再回到故乡。然而,月是故乡明!邓友梅怎么不想念故乡,在梦中他已回过故乡无数次了。于是,他每每看到来自故乡的新闻,自然情绪如海波般汹涌起伏。“人均集体分配达280元”,这可是平原人从来沒有过的富裕。邓友梅记得,他的小时候有一年闹灾荒,村里一位独身的“老财”躺在炕上饿死了。村人帮他料理后事时,发现箱子里还藏着两口袋粮食,竟不舍得吃。人们叹他太吝啬,可一位长辈说:“他是村里的头面,说话说上句,拉屎占上风,汉奸队来拉夫都对他高抬一手,为啥?不就是比别人多两袋粮食吗?粮食吃了,就不是他了!”两袋粮食就能够活活“压”死一个人,这在过去的平原,或者在旧中国也并不是天方夜谭。
当然,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处于飞速发展中,“人均集体分配达280元”其实并不算特别具有典型意义。没去过平原、不知道平原的读者可能随便扫一眼就过去了。可是,邓友梅却因这条小消息而激动落泪了。好不容易放下报纸,邓友梅却抵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拿起笔,挥挥洒洒一篇《说说故乡平原》,尽情释放自己心中的的兴奋。他在文中写道:“平原头一次被当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来,登在报纸上,向整个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泪,怎能不失眠啊!”
这条新闻勾起了邓友梅以往只埋在心底的思乡情,他决意要回故乡看看。1983年4月,邓友梅回到了故乡平原。在县城里,他能认出的只有火车站那座日本人修的水楼子。走在大街小巷,若不是耳边萦绕着的乡音,邓友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脚下踩着的是故乡的土地。在回邓庄的车上,邓友梅看到沿途村庄里堆着的小山一样的棉花垛,看到一排排的新房,也注意到了普通村民脚上的新皮鞋。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印象包裹着他,令他目不暇接,分外欣喜。
在后来的日子里,邓友梅又先后几次回到了故乡,并写下了《再说故乡平原》《平原行》《今日故乡平原》等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对故乡的那份眷恋和牵挂。故乡的变化日新月异,邓友梅欣喜着,也常常为故乡发展尽己之力。endprint
生活终会回报热爱她的人
在生活中,邓友梅爱好广泛,喜爱钓鱼,每天打太极拳,爱听评书,会唱京剧,还研究烟壶,收藏烟壶、拐棍。除了这些传统的东西,邓友梅对新事物也不拒绝。在中国作家群中,邓友梅是较早使用电脑的作家之一。北京作家大换笔那一年,邓友梅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了。平时,邓友梅也爱上网看新闻,并通过E—mail传递邮件。“写稿件不用抄写了。”这是他最大的感慨。
“网络语言我看不懂,没看网络作家的作品,什么‘雷啊,‘顶啊,不明白。以前发表文章要经过几道关,现在只要写了,就可以自由发表,不要说‘百花齐放,这真是‘千花齐放啊。”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邓友梅说自己现在对网络上的有些东西还不是太懂,还要学习,至今没有开博客。在邓友梅看来,写作公布于社会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当然,现在网络文学创作还是一个过渡时期,会逐渐上到理想的境界。”
數年前,邓友梅的“将军肚”日渐凸起,经向有关专家咨询后,邓友梅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节食降糖、控制体重的饮食计划。以少食优选为原则,即少吃或不吃主食,多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蔬菜、豆制品及少量瘦肉,因为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完全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养生不如养性”,邓友梅认为生活规律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特别对脑力劳动者尤为重要。他早上6点钟起床锻炼,8点钟左右开始工作,晚饭后进行1小时散步,晚上10~11点上床休息。邓友梅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他编创了一套力度适中、动作连贯、姿态优雅的“邓氏太极”,引得不少人向他讨教学习。
“进一步山高路险,退一步海阔天空。此话说来容易,做来难。”邓友梅热衷钓鱼活动,曾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副主席。他技艺超群,有一回一杆竟钓上两条大鲤鱼,每条三四斤重。他认为垂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我精神疗法。“钓翁之意不在鱼”,凡垂钓者,不管钓多钓少,总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每提一次竿,都能获得快乐的享受。
虽然前半生里曾经历苦难无数,但已是耄耋之年的邓友梅身体仍可说硬朗。“淡泊明志,豁达高远”,这是他所推崇的生活信条。他常说人的一生必定经受很多挫折,不能总把自己放在真理的位置上,指责别人的不是,那样永远也跳不出怨恨伤感的怪圈。
“多宽容,少计较,你首先微笑,生活也就会向你微笑了。”睿智如邓友梅,尽管人生的路有时关卡重重,但是只要脚踏实地,一颗心不死,就能突破万难,就能足下有路。正有谓,生活给你关上了一扇门,生活也会给你打开另一扇门。邓友梅迭荡起伏的人生,如同一部戏剧,如同一首诗……
责任编辑 余玮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