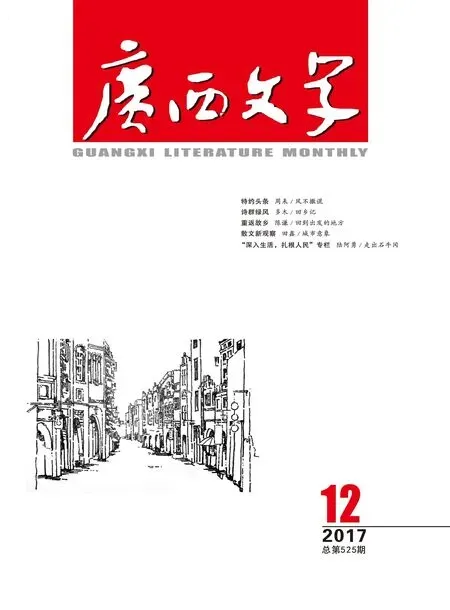回到出发的地方
陈 谦/著
这是2016年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坐在位于南宁柳沙半岛的“我在咖啡图书馆”二楼的小厅里,面对一屋子的新朋旧友,开讲自己的文学之路。这是由立足于家乡广西的中国著名文学理论期刊《南方文坛》主办的我的新书《无穷镜》读者分享会。主办方精心设计的大幅活动招贴上,“从广西南宁到美国硅谷”的醒目字样标示出它又不仅只是关于一本新书的分享活动。从一楼入口处到楼上的活动厅里,一路有鲜花和笑语,桌面和书架上堆放着我这些年来在国内陆续出版过的书。
这里的一切,与外面那个我称作故乡的城市一样令人感到陌生,却又有着温馨的熟悉——坐在左右支持着我的家乡的文学友人——著名文学评论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著名作家、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先生,广西师范学院教授、文艺评论家陈祖君先生,《广西文学》副主编、小说家李约热先生,广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志峰博士——他们多年来一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师友;更有人群中我那些发小和好友亲朋。坐在他们中间回望来路,就像与熟人在家门口拉家常般轻松愉悦。然而,我发现哪怕是在故乡,自己同样绕不开那个在异乡被人们反复问过的问题:作为一个理工生,一个1989年春天从南宁出发的助理工程师,又在美国硅谷芯片业界沉浮过十多年的设计工程师,你是怎么获得写作的技能、最终成为一个作家的?
我望向人群,有瞬间的走神。很久以来,我不时会想起当年坐在病重的父亲床边,说起自己开始学习写小说的时刻。守护着面临生命危机的父亲,陪他回忆往事,怀念故人,却在远望自己遥不可及而父亲已无法陪同抵达的未来时,我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悲从中来,想不出一点办法安慰他,竟说起了文学。我告诉父亲,自己正在海外新兴的中文网络上发表散文随笔,分享自己在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心得体会,获得了读者积极的回响,令人兴奋。父亲安静地听着,疲倦的病容里不时泛出笑意。他缓缓点头,说:如果你真的对文学有兴趣,那你要学写小说。我说我正在写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那不是因为要安慰父亲,而是觉得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时刻,这样的未来能让我们暂时忘掉当下的绝境,有所盼望。我当然没提及自己面临的写作困难,自己如何编不圆一个简单的故事,又如何缺乏一个小说作者应具备的虚构能力。虽然父亲没能读到我的小说,但每每回首往事,令人有所安慰的是,父亲在离开时至少知道,我在写作上的努力,对避免沦入他最担心的“浑浑噩噩”的人生有所帮助。

在《南方文坛》主办的陈谦作品分享会上(从左至右张萍、陈谦、张燕玲、东西)
我已接受了父母在我写作道路上的缺席,只在这特别的时间、独特的场合,面对着眼前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才深切地意识到他们的缺席如此令人遗憾。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出版后,时在旧金山湾区26台任华语节目制片的舒建华兄曾安排制作了一辑对我的访谈。当我走出镁光灯圈,迎上来祝贺的建华兄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会让你的父母骄傲的!” ——建华兄不愧是责编了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的文化人,以此完美地安抚了我内心深切的叹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自己的文学启蒙来自父母的直接影响,虽然他们的初衷并不是想要培养一个作家。在我儿时面对文化的蛮荒时,父亲努力引领我走进古典文学的过程,母亲为了让年少的我不至无聊而订下的那些文艺刊物,在寒暑假里为我从她任教的学院的图书馆里借来的各种文学书籍,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门,启发了我对文学最初的兴趣。而在此时,在故乡面对着那些熟悉的面孔,我意识到了另一个遗憾——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刘柳全的缺席。这些年里,我总是机械地告诉好奇的人们自己从小喜欢写作,却一直没机会说过,这“喜欢”与刘柳全老师的直接关联。
我是在2008年的春天里偶然听到刘老师去世的消息的。成年之后,一路狂奔,越跑越远,平时想起刘老师的时候并不多,总以为他就在那里,等我将来什么时候闲下来了,就能随时拜访,更不曾将“永别”这样的字眼跟他联系在一起。
2008年早春,我小学到高中时代一路同班的好友阿康,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有了偕先生和儿女,与妹妹一家结伴从美国返乡探亲访友的计划。她们姐妹俩打算在南宁邀请老同学和中小学时代关系亲近的师长们来参加大派对——我们自幼在南宁西郊学院的围墙里长大,从幼儿园到高中读的都是学院的子弟学校,召集众人的难度并不那么大。后来听说那个派对很成功,筵开数桌,宾主尽欢,嗨到最高点,此乃后话。
我因走动较勤,平时与老同学联系多些,于是受阿康所托,在春天里就开始帮她联系老同学。我先找到好友蓝兰。蓝兰不仅生长在学院里,成年后还一直在学院里工作,只要找到她,别的同学就能像地里的萝卜一样被成串拔出。热心的蓝兰在电话里爽快地应下,让我报个名单。
当报出“刘柳全”三个字时——我们私下对老师都直呼其名,这倒很像美国人。蓝兰在那边很快地说:“他已经走了!”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清,叫起来:“你讲什么?”“他死了”——蓝兰的口气里带上了明显的不耐烦。“啊?!是怎么回事?什么病?”——刘老师从来都是吸烟很厉害,早年因生活困难,吸的又都是劣质生烟,心肺有问题不奇怪,前些年也曾听说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做了搭桥手术,恢复得不错,平日也很注意保养,深居简出的,而且一双儿女都已成人,生活环境大为改善,日子刚有了滋味,怎么会这样?
蓝兰在那头不吭气。我仍不罢休:“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就走了?”——我清楚地记得前段还看到过刘老师和妻子的近照,他笑得那么开心。蓝兰的口气就冷了:“我不知道。我只是走过,看到布告栏上有讣告,说哪天开追悼会。就这样。”

刘柳全老师及夫人
放下电话,我呆了一阵。从百叶窗叶片的缝隙间看出去,是早春阳光下茸茸的新绿。刘柳全走了。句号。就这样了吗?布告栏?讣告?——都贴在老地方吗?——小时候不时在院行政楼对面的布告栏里看到那样的东西,大多是认识的长辈,每每看到,总是很害怕,又很担心。最早对死亡的认识,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给阿康打去电话,两人一阵唏嘘。为蓝兰那不耐烦的口气,我还跟阿康说了几句,觉得这太不像她了。后来蓝兰告诉我的另一个坏消息更令人震惊:她那高大壮实的父亲正是在那段时间因医疗事故在昆明突然去世。有关死亡的话题,是她当时最不愿触及的。
我从带在身边的旧物里,翻出一本封面上印着“广西林学院”字样的学生登记册。那是母亲早年在广西林学院教书时的收藏。对在“文革”后期开始在学业上认真起来的我,它是新鲜玩意儿。我看到自己留在扉页上的字迹:“记录下我——一个普通女孩子的中学时期那永难忘怀的学习生活!它将使我永远感到无比值得眷恋!——随着记录的增多,我是怎样一步步地迈步向前!……” 多亏当年白纸黑字记下,要不我不会相信自己曾这么幼稚、矫情过。
这本登记册里清楚地列着刘柳全老师是我高一、高二两年的语文老师——我是“文革”后最后一届只念了两年高中的一代,真是生得逢时——没有被送去下乡,却又学制最短,得以在十六岁时进入大学。
高一第一学期的学业期评栏里,与其他学科一串的优绩相比,“82分”的语文总评如此刺眼,特别对在语文科目里一贯表现突出的我而言。我记得很清楚,这次语文期评走低是因受到平时作文成绩的影响。
在刘柳全老师接手当我的语文老师前,我初三的语文老师是林老师。林老师是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当年因照顾夫妻关系而从郊县中学调进学院附中。与我们习惯的那些严肃到沉闷的老师不同,林老师的性格很外向。他镶有两颗耀眼的金牙,一咧嘴笑,满口灿灿生光,很有喜感。他的衣着也与那个时代人们朴素得寒碜的风格不同,走上讲台时总是皮鞋锃亮。他说带点壮音的普通话,在儿化音上总有点犹豫,就咬得特别用劲儿,领读那些内容夸张而煽情的课文时,语气激昂,声情并茂,将课堂气氛烘托得很好。他总是强调,他最喜欢的是抒情散文,当年的课本一翻,这类文字到处都是,“啊!!——”“呀!!——”“吧!!——”他领着我们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我和小伙伴们都热血沸腾,像打了鸡血般兴奋。到了初三,作文训练的分量明显重了,我们学着在记叙文里频频堆砌感叹词,后来发展到论说文里也放,果然“啊”越多作文的得分越高。我自开始识字、练习造句起,就在努力模仿报刊腔,总以为文字越华丽越激昂就越好,跟林老师的品位一拍即合。我的作文成绩在越来越多的感叹号引领下节节高升,直冲到了九十八分的历史新高。这下我乐坏了,后来无论是在批判文章还是论说文章里也会无端地插上几个“啊!”“呀!”,它们都能夺来高分,百试不爽,令人忘形。
我在以为已练得无往而不胜的绝技时,成了刘柳全老师的学生。没想到,高一第一次的作文发下来,就给直接刷到七十几分。我一下就懵了。再仔细看下来,到处是被画掉的感叹句和形容词,那可都是我过去拿高分的法宝。被宠坏了的我仗着从早些年“反潮流”中练得的冲劲儿,揣着作文本直接就去找刘老师“抗议”。
刘老师坐在办公桌前,卷着烟卷听我抱怨完,不紧不慢地说,他的学生的作文要拿到八十分是很难的,七十几分已经很不错了。我争辩说自己的作文过去可没拿过九十分以下的,怎么会你一来,就跌到七十几分?刘老师点燃手卷喇叭烟,边吸边说:每个老师的评分标准不同,习惯就好了。我又争辩了几句,见他没有给我加分的意思,只好灰溜溜地走人。
我对刘老师好奇起来。很快就了解到,刘老师是广东潮汕人,“文革”前从广东考上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时在邕宁县明阳镇的广西劳动大学教书。1972年广西劳动大学与广西农学院合并。在这之前两年学院开始办附中,因缺乏师资,他被从大学部借调来教语文。说是“借调”,却从此被留在附中教书直到退休。他还曾兼教过我们的历史课。刘老师中等身材,浓眉大眼大鼻子,南人北相,说一口在广西地区非常突出的标准普通话。夏天里总是穿件泛黄的半旧木薯蚕丝的短袖,下身是洗得泛白的黑色绵绸裤,裁剪不大合身,看上去有点短,带着一种紧张感。春秋天里则一身半旧阴丹士林中山装、足蹬褪色解放鞋,朴素得寒酸。听家里同是从劳动大学过来的同学说,刘老师的妻子是他在劳大时娶的明阳农村姑娘。在那个年代里,农村户口要转入城市比登天还难,而农村里女儿一出嫁就得离家,而儿女户口按政策是随娘,所以刘老师的一双幼小儿女也是农村户口,娘仨都没有食品和布票配给,要花高价买粮买布,以刘老师一人的薪水要养这么多张口,还要接济在乡下的父母,妻子的身体又不好,生活很困难。同学又说,刘老师早年在大学曾跟女同学谈过恋爱,可因刘老师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相好的大学女同学顶不住家庭的压力,最后跟他吹了。同学还说,刘老师的妻子非常悲观,老想自杀,说自己若死了,两个孩子就有救了,能随爹拿到城市户口,不用一辈子当黑人黑户。这些闲话听了让人心情沉重,感觉到老师的不易,上课便用心起来。

作者高中时代照片

与父亲在南宁人民公园
我们上高中时,全国高考已恢复,学习的目的性变得清晰起来,语文课也不再是只学写歌颂性或大批判文章,而是按新的教学大纲的要求,从记叙文、论说文、应用文,一个个文体循序渐进地学。刘老师在讲解各文体的技术性关键点时,反复强调一定要甩掉“假、大、空”。而在讲解挑出的精读课文时,他在鲁迅的文章上花的功夫总是特别多,从文章背景到文字细节,反复讲解,后来我想,很多时候他是因为自己沉醉其中。我因之前读过家里的《鲁迅选集》,对他提到的文章有所了解,经常能答对提问,学习兴趣大增。在讲解和布置作文练习时,他总强调要写出真情实感,不要喊口号,并会举反例作对比,启发我们的感受。那些不必要的抒情助动词,夸张的形容词在我的作文里越来越少。虽然我的作文再没上过九十分,可刘老师经常会将我的作业作为范文在讲评课里念给同学们听。他从不会告诉大家作者是谁,可同学们总能从我得意张扬的表情里读出答案。刘老师还不时将我的作文拿到他代课的高年级班上去念。我在文中的一些幼稚夸张的表达有时会让同学们哄笑,但更多的时候听到的还是大家的赞扬和羡慕,特别是高年级同学的衷心夸赞,让别无他长、好胜心又挺强的我感到自豪。我变得总在盼望作文课的到来,一拿到作文题目,便在第一时间里开始构思、动笔,之后就期待它在下一次讲评课中被刘老师大声念出。自我价值由此获得的确认,潜在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我中年后渴望从平淡的生活海洋中出逃时,它成了我的一只救生圈。
我的弱项在写作论说文时显现。虽然我也铆足了劲儿向班上论说文写得出色的男生阿声他们学习,跟着他们研读《红旗》杂志,推敲《人民日报》社论,可写出的论说文不是绵软无力,就是逻辑性不够强,夹叙夹议的比例也不太协调。在讲评课上,阿声他们的作文不时取代了我的,成了范文。我没有由此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反倒有了患得患失之心,不时在课堂上给同学挑刺,总想证明自己才是最好的。刘老师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到了1977年底,南宁市教育局宣布要举行“文革”后第一届全市中学生作文竞赛,参赛代表由全市各中学推荐,到市里集中参赛。刘老师将我约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推荐我作为高一年级的代表去参赛。我一听就坚决不肯,找了各种理由推却,就是没说出最大的私心其实是“脸面”。我心中的小算盘“啪啪”地拨着:自己平时在班上对自己的作文那么高调张扬,此番去了若不能获奖,怎么有脸面对全班同学?大家不会笑话我吗?刘老师当然不管我心里的那些小九九,就像当初不肯为我改分数一样不松口,坚持要我去参赛。我拗不过,竟在教师办公室里哭了起来,又将平时有所羡慕的同学的名字提出来,让刘老师考虑让他们替代我。刘老师摆摆手,说这事就这么决定了,最重要的理由是你的笔头快——我平时的作文基本不打草稿,是直接写到作文本上的,再在上面涂改,这从那乱七八糟的页面就可看出。在这点上,刘老师跟我过去的语文老师都不同,他并不要求作业的整洁,也许我的快笔头是这么练出来的。我那时到底不过是中学生,心里再不情愿,可老师的脸一拉,也只能自认倒霉,硬着头皮上了。
作文竞赛在南宁四中举行。那是一个阴冷的午后,我们坐着学院的车子到达时,南宁各中学的参赛代表已进教室。我们这些平日里生活在郊区,自幼就读于学院子弟学校的人,对市里的中学生活是很好奇的。我在走廊上急走,东张西望,紧张里带着兴奋。刚在高一年级的赛场里坐下,就听到了铃声,主赛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高一年级组的作文题目:可爱的南宁。我愣了一下。“最可爱的人”之类的文章,从小课文里可没少读,无非是从崇高的精神、纯洁的品格之类入手,不吝溢美,写到最最最。可南宁是一座城市,我平日里只有过年过节,或要随母亲到广西医学院看病时,才有机会进城逛逛,连市民的语言也不会讲,南宁的形象实在有点空洞。但刘老师是对的,我的急才来了,在脑子发空时,从林老师那里学来的高举高打的本领也帮上了忙,灵感突发,直接破题,从“看到《可爱的南宁》这个题目,脑海里流过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开始,写到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再写到毛主席冬泳邕江时说的“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二十度也冷”对奋勇向前的南宁人民的激励,最后再上八度,到毛主席逝世时我和同学们立下的“继承遗志的钢铁誓言”……虽然没上什么助动词,但感叹号可没少用,最后连自己也激动起来,真是下笔如有神,待交卷的铃声响起时,竟有意犹未尽之感。
从教室里出来,走在人流中,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觉得对付过去了,感觉还不坏。第二天回学校上课,刘老师也没有专门过问比赛的细节。因对自己获奖并没把握,我心下甚至希望大家快点忘了这事。
获奖的消息最早是从我们前楼的王佩璋叔叔那里听到的。王叔叔是南京人,为了与抗战时在桂林避难时结识的中学女同学的爱情,大学毕业后要求到广西工作,分配到广西大学电力系教书,家安在妻子工作的广西农学院的教工宿舍里。王叔叔知识渊博,兴趣非常广泛,平日宿舍里高音喇叭一播完新闻,就总有好些叔叔伯伯在一起谈论交流,话题从中国到世界,从眼下到历史,我很爱跟着旁听。王叔叔通常是这个圈子的主侃,他在我们小孩子随着广播骂蒋光头时,会正色说,他少时在南京的植树活动中见过蒋中正,穿着呢子军装,马靴长呢袍,可威风了,很帅的。我觉得很不可理解,还问那蒋介石不是光头吗?王叔叔肯定地说蒋是光头,但很威风英俊,这不矛盾的。看着他那毋庸置疑的表情,我不敢再多问,留下很深的印象。王叔叔一家住在我们前楼的一层,哪怕是在“文革”期间,平时我们出出入入,也总会看到他在自家窗前的书桌上伏案读写的身影。他的业务能力超强,“文革”后大专院校恢复职称评定,他作为广西第一批获破格晋升高级职称的数名学者之一,上了《广西日报》头版头条。王叔叔后来在广西大学电力系当了多年系主任,桃李满天下。已在两年多前因病去世的王叔叔,也是在我年少时关注并激励过我的人。
那个早晨,王叔叔快步走上我家住的二楼,来到我家门口。他先是确认我的学名——平时大家都只叫我的小名,所以他也不肯定。然后说那真是我获得了南宁市中学生作文竞赛高一年级第一名。我和母亲听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王叔叔肯定地告诉我们,他是从邻居那儿看到的获奖名单。王叔叔的邻居时任南宁六中校长,比我们郊外的人早些获得了消息。
那天一早到学校,我便从刘老师那儿正式获得了通知。刘老师还告诉我,因为我还在数学竞赛里获了优胜奖,市教育局通知说,要安排我在颁奖大会上作为获奖代表作大会发言。因为是市里的决定,这没法推了。
春节过后,颁奖大会在南宁市中心的朝阳灯光球场举行。作为“文革”后学风渐盛时代的第一次全市学业竞赛,颁奖会的气氛热烈,场面隆重,红旗、标语和锣鼓齐全,高音喇叭里口号和乐曲激昂。母亲特地让打着两条小辫的我穿上黑底白红小花点的新衣裳。面对球场里坐得满满的几千名南宁市各校师生,我用自己生硬的普通话读了事先写好的稿子。为了写出值得让人学习的先进事迹,平日里贪玩懒散的我在讲稿中摇身一变,成了书山勤寻路、攻关不畏难的女学霸,夜夜苦读不肯眠。我还虚构了面临学习困难时的思想斗争,最后如何以英雄烈士为榜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持前行,这种励志的故事获得了很好的回响。在接下来那段时间里,我还被邀到市里的电台录音,接受记者采访,继续宣传自己也开始相信的“事迹”,让我的母亲都有些反感起来,她大概觉得自己都不认识那个文字中的女儿了。刘老师在这期间却是宽容的。他没有鼓励,也没有批评,只是默默地传达市里的各种活动通知。因为学院里没有连接市里的有线广播系统,我没听到自己在电台节目里的自我吹嘘,后来还是家住城里的体育老师来告诉我他听到了我的声音。
那段时间里,颁奖活动的照片满满地贴在朝阳灯光球场临街的大橱窗里。在那个百废待兴、青少年重新坐到书桌前渴望学习知识的年代,南宁市中心最热闹的朝阳广场上,来来去去的人们都会关注到它。我的获奖作文被收入市里编印的小册子里,作为范文在全市中学生中传阅。可惜那本小册子早已不知所终。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年学着报章媒体上先进人物们的腔调,将自己的成绩归功于党的培养,感谢了毛主席通过教室挂像两边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天天教导我;为了让细节更丰满,我甚至还找到一些父亲教育我的小故事,却并没有对将我送到这个小小舞台上的刘老师表达特别的感谢。
热闹一时的日子很快过去。生活归于平静。跟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也投入到备战高考中。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选择报考文科专业,在越来越紧张的高考准备中,刘老师在我的生活里渐渐退远。
高中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我只在最早的一两年的寒暑假里,曾和一些同学一起去看望过高中时代的老师们,当然不会错过我们的老班主任刘柳全老师。那时,刘老师一家四口仍挤在大学部男生宿舍楼的一间屋里,灰扑扑的老旧家什,窗前放着一张书桌,窗外是桉树高阔的树影。刘老师神情轻松,卷着喇叭烟卷,和我们闲聊,听我们讲各自的大学新生活。他说起自己如今的学生,感叹地说,再没遇到记叙文写得过我的,也没有遇到论说文写得过阿声的,而论综合成绩的稳定,也没超过阿康的。作为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我们听了,都有种说不出的高兴。他是第一次直接地表扬了我们。

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阔大,我们在寒暑假里也越来越忙,同学们约在一起不再容易。再去看刘老师时,感觉他也已沉浸在新的生活里。他后来升任学校的教务主任,肩上有越来越多的责任,关注的是更多的师生了。接下来听到有关刘老师的消息总是好的——搬了新家;妻子的户口也早落实了,还在学院里安排了工作;一双儿女也已成人,儿子到南京读了大学,毕业后工作了,非常孝顺,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后来又知道他退休了。在别的老师那儿看到他的照片,脸上的笑容简直可说是灿烂。我也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出书,偶尔也想,等下次再回南宁时,应该去看看刘老师了,他是真正会在乎我写了什么的人。可这想法一直就只停留在念头里,总以为前面有大把机会,没想到,这一等再等,等到的却是刘老师离世的消息。
这些年来,我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他们一路扶助我前行,成为我的知音和良师益友。没有他们,我不会有今天的收获。而有些曾经为我的来路清扫过杂草,铺垫过基石的人,比如我的父母,比如刘柳全老师,这些在我年少对我有过期许的人们,他们没有等到看我交出的作业。
感谢《广西文学》让我以这样的形式重返故乡。故乡是你年少的时候爱过你,对你有过期许的人所居住的地方——我对齐邦媛教授的这些话,深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