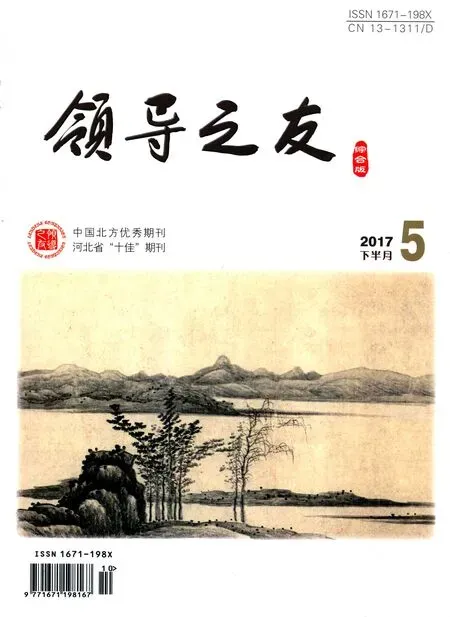陶渊明与重阳节
王东梅
陶渊明和重阳节,是一个人物与一个节日紧密融合的典范。
陶氏之所以成为重阳的节日偶像,取决于他的诗文和其他的史料、笔记。他有专写重阳的《九日闲居》诗,其序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其诗云:“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有菊无酒,如何不抱憾?
南朝《宋书·本传》说,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堪与《九日闲居》诗互为印证。他坐在菊花丛中浮想联翩,想到人生的短暂、自己喜欢的九月九习俗、饮菊花酒的好处,抱怨一般人士的虚度节令,自己节日无酒、只能“空服”菊花的尴尬,酒具蒙尘、酒坛空泛的羞耻等等。但他还是从秋菊冒寒繁荣的品性中,学到了许多,对自己辞官归隐的人生选择无怨无悔。
南朝檀道鸾笔记《续晋阳秋》有一则记载,续了上述正史的内容:“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官府中给役小吏)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笔记与正史描绘的陶潜的节日机遇,正好相反:一是“无人送酒”,一是“白衣送酒”。或许,这是陶氏不同年份重阳节的不同遭际。
这两者后来都成了典故。唐代王绩《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诗最后两句曰:“香气徒盈把,无人送酒来。”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开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这里的“无人送酒”可以有两种理解:我坐在香气盈把的菊丛,久久等待,却像陶渊明一样没有人送酒过来;或者,我不像陶渊明那样幸运,我久坐菊丛,香气徒然盈把,却无白衣人送酒过来。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醉花荫》“东篱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暗用陶渊明“无人送酒”典,身边“无人”,只好独自把酒,是在抱怨丈夫节日不归。
清代蒲松龄有一首叹息自己命运漂泊的《重阳》诗:“中秋恨是在天涯,客里凄凉负月华。今日重阳又虚度,渊明无酒对黄花。”自比无酒过重阳的陶渊明。
连邻国日本,也流传陶渊明的“白衣送酒”典故。《古今和歌集》纪友则有首《人在菊花处待人来》的和歌曰:“在此赏花人,待人人落后。篱边白菊花,误作白衣袖。”把白菊花误认作白衣人,诗境颇有异趣。
重阳是菊花的节日,曹丕曾赞曰:“九月九日,草木遍枯,而菊芬然独秀。”陶渊明爱菊,爱重阳节,关于菊的诗歌,更负盛名的是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饮酒》篇。自此,陶渊明与菊、与酒、与重阳连在了一起,菊花甚至获得了“篱菊”“篱花”之名。
唐代刘长卿《九日题蔡国公主楼》有“篱菊仍吐新,庭槐尚旧荫”句。清代曹寅则有”九日篱花犹寂寞,六朝粉本渐模糊”的《寄姜绮季客江右》诗。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亦有哀诗曰:“哀此东篱菊,当年共护持。今秋花上露,只湿一人衣。”
陶渊明的人生轨迹、人格力量,他的清高、淡泊名利、勤劳执着、土地情结、亲民和蔼、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陶渊明美好的菊诗、重阳诗、传记,使菊的意象、酒的意象,连同他自己也成了一种意象,叠合在了重阳节的身上。他这个人和他的名字,成了重阳节的代表、象征、符号,他自己成了一个节日的品牌。后人如宋代黄庚《九日怀舍弟》诗中,曾径直表述道:“重阳陶令节。”人物与节日名合成一词了。
人们把一个历史名人与一个节日联系起来,有助于增加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亦有助于对这个人物的纪念。就像屈原进入端午节一样,重阳节俗里就少不了陶渊明的面影,重阳节也因为有了陶渊明而变得丰富厚重起来:爬山登高、吃重阳糕(与”高”谐音)、崇拜高人陶渊明。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是清高、潇洒的理想人格的象征符号。作为重阳节偶像的陶渊明,正表现了这种文化符号的深厚意蕴。
(责编 / 刘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