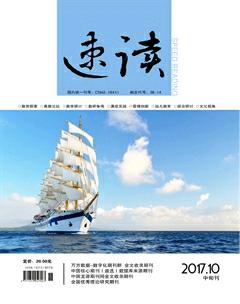合同解除异议制度辨析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及商事活动的活跃,合同的解除权及对其的异议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违约方能否主动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异议期限如何定性以及超过法定的异议期限后,法院或仲裁机构是否需要进行实质审查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笔者通过代理案件的经验,拟从解除权的行使主体、利益衡量及异议期的性质进行辨析,促进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合同解除权;异议权;异议期
《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按照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主张解除合同的,应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如存异议,可采用司法手段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上述规定创设了我国合同解除异议制度。为规范其适用,2009年最高院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对该制度的具体适用问题进行了解释。但是,合同解除异议制度备受批判。“形同虚设”、“诱发机会解约”、“利益失衡”等字眼铺面而来。司法实践中,亦呈现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争锋相对。笔者试图对合同解除权的主体、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利益衡量、合同解除异议期的性质等方面进行辨析,以期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在司法实践中的统一适用及制度完善提供有益的建议。
一、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适用困境
目前,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适用困境是:如果超过《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法定三个月异议期限,法院亦或仲裁机构需要对合同进行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即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的违约一方主动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于三个月异议期限届满后,法院是否仅根据超过异议期限及发出通知的形式无瑕疵而认定合同已经解除?如果采取实质审查,势必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虚置高阁,如果采取形式审查,如何规避机会解约的风险?最高院研究室在对上述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中答复: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但并未说明如超过三个月异议期限后如何处理。2011年的民事适用法律问答中,上海高院的意见较明确,认为:在适用第24条规定时,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首先具备合同法第96条关于合同解除的条件,即应当具备合同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的前提;其次应以法律规定的合法方式通知对方。若满足上述条件,另一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或法定三个月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则合同解除成立。若一方当事人并不满足解除合同的条件的,则不应适用最高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因为最高院的意见并不明确,且出现大量截然相反的案例,导致合同解除异议制度出现适用困境。
二、合同解除异议制度辨析
(一)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是否局限于守约方?从理论上,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提出的有效率违约理论为违约方提出解除合同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即违约一方从违约中获得的利益大于其向非违约一方做出履行的期待利益;或者当履约的成本远远超过各方所获得利益时,违约比履行更有效。以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代替继续履行合同,对于遭遇突发情形(不属于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致使履行成本过高的违约方而言,是最经济亦最有效的方式,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从法律条文上,《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反向说明,特定条件下违约方可以享有合同解除权。从司法实践上,最高院公报于2006年第6期刊登的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二审判决书中支持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其裁判明确指出,“当违约一方采取继续履行的方式所需的物力和财力远超其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即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之条件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应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但应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以确保守约方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综上,违约方在特定条件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不仅限于守约方。
(二)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利益衡量
任何法律的形成过程都是各种利益权衡和考量的过程。“公平”和“效率”多数情况下不能兼得,只能在确定利益追求后寻求一个合理的中间地带。对于合同解除异议制度亦不例外。此制度的设计以及目前出现的困境,均源于利益衡量标准不同。从利益衡量的角度重新审视上述的“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问题,不难发现:这两者的冲突主要是实体的权利来源更为重要,还是稳定的法律秩序更为重要。实质审查强调实质公平,解除权的行使必须享有实体上的合法的合同解除权。形式审查则侧重于形式公平,主要审查通知的程序和有无超过异议期限,以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笔者认为,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本没有对错,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亦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形式公平更为可取。一方面,它兼顾公平与效率,有效防止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加快司法进程,使更多的人体会到司法的公正。而一味的追求实质公平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交易秩序不稳定。故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衡量,笔者赞成,如合同解除的异议提出时已超过三个月的异议期限,法院应仅做形式审查据以认定合同解除的效力,不宜再进行实质审查。这种做法亦更符合《合同法》96条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逻辑衔接。如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审查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时,无论是否超过三个月都要对其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第24条便形同虚设。只要解除合同的一方不具备合同的解除权,无论对方是否于异议期限内提出异议,均不影响合同是否解除的认定。如此,享有异议权的一方只要确定对方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便不必急于大费周章地提起诉讼或仲裁,取而代之的行动为静观其变。这样便使得第24条处于尴尬境地,亦使得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处于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故超过法定的异议期限后,对合同解除权进行形式审查是法条的应有之义,也利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
(三)合同解除异议期的性质
从合同解除异议期性质入手,亦可以窥探出形式审查之义。该异议期应属于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诉讼时效的适用前提是存在一种请求权,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便丧失胜诉权的一种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可以中止、中断或延长。除斥期间一般仅适用于形成权,指法律规定的某种民事实体权利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则该民事权利的消灭法定权利的固定存续期间,权利人在固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即发生实体权利消灭的效果。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合同解除异议期设置目的为催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确定合同是否解除的法律状态以维护交易安全。加之合同的解除权为形成权,故可将合同解除异议期理解为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形。据此,异议期限届满后,权利人的异议权利即消灭,法院或仲裁機构只需对合同的解除权进行形式审查即可。
三、完善建议
尽管笔者论述了超过法定异议期限后,对合同解除权进行形式审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无可非议的是,对其进行形式审查确实存在权利滥用、机会解约、特定条件下增加非违约方的诉讼成本等问题。那么应如何进行完善呢?
首先,建议适当延长《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关于法定“三个月”异议期限的规定。其一,一般情况下,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后,为防止另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往往采取拖延战术,与对方进行你来我往的谈判。故此期限不应设定太短。其二,法律规定一方以发函的方式解除合同,却要求另一方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提出异议,从权利对等角度,亦应适当延长异议期限,使得异议权人可以有效采取措施。笔者建议将此异议期限延长至一年。
其次,完善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的衔接工作。大量的司法判例印证,合同的解除并不意味着合同项下违约责任的消灭。如因违约方提出解除合同,致使合同解除的,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要求违约方向非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以保证非违约方(异议权人)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现实既得利益。
再次,当条件成就时,出台规范合同解除通知的形式、送达方式的细则。只有这样,方可避免程序上不符合规定的合同解除的通知发生法律效力,降低机会解约的机率。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合同解除探微[J].江淮论坛,2011,6.
[2](美)理查德·波斯纳, 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68.
[3]陈思静.合同解除的异议权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3,5.
[4]汪东丽,袁洋.合同解除异议制度废除论[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6.
[5]郭超.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法理辨析与裁判规则——对赵某诉何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评析[J].天津法学,2017,2.
作者简介:
李莹莹(1987.12—),女,汉,河南省郑州市,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工作单位: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