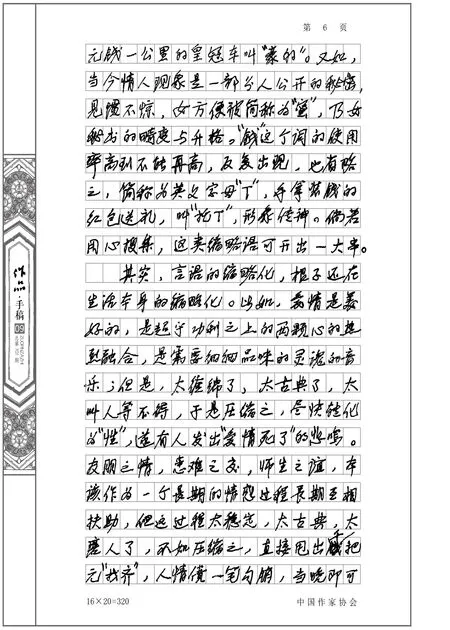90后文学新粤军的两驾马车:路、索耳比较论
——90后小说观察之三
文 /徐 威
文 /徐 威
徐 威
男,江西龙南人,1991年生,广东省作协会员,中山大学中文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现居惠州。在《作品》 《诗刊》 《中国诗歌》 《诗选刊》 《星星·诗歌理论》 《当代作家评论》 《当代文坛》 《创作与评论》等发表小说、诗歌、评论若干,著有诗集《夜行者》。
路魆:在臆想中言说
幻觉与臆想,原本就是毫无逻辑可言的。所以,在我看来,路魆笔下的幻觉中,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路魆在作品中所构建的荒谬而有着强大隐喻的“独立世界”——《拯救我的叔叔卫无》中神秘而诡异的监狱、《圆神》中的工厂、《林中的利马》里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别墅、《围炉取冷》中孤岛般的医院、《窃声》中的王家园小区……它们都自成一体、远离人世。然而,我恰恰认为,这种远离实质上正是一种隐晦的人世观照——这些世界指向的正是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比如,在孤岛般的医院中,“我”与其他医生分区而居,难以相见,因为“区域是不能乱跨的,因为有人曾经试过乱跨区域,被革职,最后被人发现死于野外。恐怖的禁忌是我们心里长久以来的法度。”这实质上正是我们现代人孤独、牢笼、隔离等精神状况的一种隐喻。又如《圆神》中的工厂,“我创造的圆神工业,是一个现代化的地狱,那些无休止、无缘由的劳作,就是孟婆汤,只要动手劳作了,就是自我遗忘、自我赎罪。忘忧之地,艺术的天堂。”[3]所以,路魆笔下的世界,不是具象而是抽象的,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路魆在幻觉与臆想中书写荒谬,在荒谬中袒露人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魆的小说虽不呈现现实生活,却同样有着尖锐的批判力量。
现在我的小说的特殊性已经得到公认了。然而,如果有人直接问我:“你写的究竟是什么具体的故事?你是怎么写出来的?”面对这样的问题,由于内心深恐产生误会,我只能回答说:“不知道。”从通俗的意义上来说,我的确不知道。并且,我是一个有意地让自己处于“不知道”的状况中来写作的人。由于信仰原始之力的伟大,我必须将其放在虔诚的、认为的蒙昧氛围中去发挥,以使自身挣脱陈腐常规的羁绊,让强大的理性化为无处不在的、暗示性的激励和怂恿。[4]
二、索耳:隐晦与多重指向
索耳,本名何星辉,1992年出生于广东湛江。索耳在高中时期就已开始创作,2013年以索耳为笔名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在《作品》《山花》《长江文艺》《芙蓉》《青年作家》《当代小说》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近二十篇,其中《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南方侦探》还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今年夏天,索耳从武汉大学毕业,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坦白说,阅读并试图解读索耳的小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我在阅读他最初发表的作品之时,心中就闪现出了许多的困惑与不解——《卡拉马佐夫线》中,这个标题到底是何意、与小说文本有何联系,至今我仍看不清楚、想不明白。这种隐晦特征,在他之后的小说创作中也一直延续着。我们很难如同以臆想、幻觉、死亡等为关键词归纳路魆的写作主题一样,用三两个关键词汇去总结索耳的小说创作。显然,这是他有意为之。在创作谈《我所追求的是异质之美和审美共存》中,索耳说道:“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有一种无可定形的状态,同时和主流文学审美保持距离”、“ 我觉得多一点不确定性不是坏事”[8]。这样一种文学观,使得索耳的小说文本具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确认,哪一种解读才是索耳创作的真正意图。甚至于,我还暗自怀疑,有些作品索耳自己本人也并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纵观索耳的小说作品,可以发现一条较为清晰的分界线——《卡拉马佐夫线》《铸刀师的遗产》《调音师的依米酱奈》等是其练笔之作,初见索耳在小说叙事上的尝试,然而文本的力量始终有限;《蜂港之午》《杀观众》中其笔法逐渐走向圆润,可看作其过渡期;至《前排的幽灵》《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南方侦探》《在红蟹涌的下半昼》,小说文本的内容与结构愈加协调,相互支撑,使得文字隐含的力量愈加强大。与此同时,《显像》《白琴树苑》则显示出索耳在叙事上的“异质”与“新变”。
《前排的幽灵》带有一种神秘的气息,其指向的是记忆、勇气与救赎这样深刻的文学主题。在老詹多次的梦境与殷姑对其独特的拯救治疗中,老詹记忆深处的恐惧被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在那个疯狂而残酷的特殊年代,站在前排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打死的一幕,对老詹的一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之后,老詹再也无法站在前排,看电影始终选择坐在最后几排,看球赛也认为坐在前排有生命危险。在小说中,老詹的朋友瓦沈建是这一记忆的挖掘者,他或是暗示(如假装无意地告知老詹“我”的父亲是被人打死的,这令老詹沉默数秒,最终仍不敢面对,只能转移话题),或者直言(直接告知老詹:“你是幽灵”,而他的任务就是拯救正在消亡的幽灵),或是震喝(“你不喜欢坐在前面,是因为对前排的位置有一种恐惧感,你害怕坐在前排,因为你以前坐在上面,你曾经是最前排的观众。你看到了一些让你恐惧的东西……你亲眼看到了你父亲活活被殴打的场面”)。现在与过往、真实与梦境的相互交错,使得小说在结构与内容上相互支撑,生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
如果说在《前排的幽灵》中,我们还能看到索耳在叙事结构与叙事意图上有意为之的痕迹的话,那么,在《在红蟹涌的下半昼》里,这种隐晦与多重指向则潜藏于流畅自然的日常书写中。这篇小说的情节极为简单——一对年轻夫妇,在电视上看到红蟹涌的风光广告,并于第二日前往红蟹涌度假。这是极为流畅的日常生活书写。然而,小说却饱含隐喻色彩,直指现代人的生育焦虑。两人在生小孩问题上的争执、“我”所梦见的蟹脚雨、把宠物猫寄养在朋友处、打捞不到海鲜却每日坚持出海的渔民、倒塌的东岸海湾大桥、妻子的对烟瘾的压制与放纵、一言不发的古怪导游被我们推下海、岛上漫天遍地的红蟹令我们落荒而逃、到家之后再去接回猫(“我们唯一的孩子”)……这些日常化的现实与不合逻辑的超现实杂糅在一起,最终聚集在一点:生育焦虑。一方面,是父母在催生,妻子也开始动摇,想要生小孩却又含糊其辞;另一方面,是将宠物猫当成唯一孩子的我们对于不生育生活的一种满足。这对年轻夫妇的矛盾与困惑、孤独与恐惧,在简单的日常叙事中若隐若现,令人印象深刻。
在《显像》与《白琴树苑》中,索耳的叙事探索值得一提。在《显像》中,索耳将《照相馆》《多少》《他山之石》《酷刑》《世上最好吃》《乙酸异丙酯》《审片人》《陌生的游戏》《上将和马》《一次刺剪》十个毫无关联的独立故事,组合成一篇小说。在《显像》这一大标题之下,试图呈现出人的存在之荒谬与艰难。《白琴树苑》亦是多个故事相组合的叙事方式,只不过,故事与故事之间还略有关联。小说每一节的叙事对象与叙事口吻都在变幻,索耳试图在偶然之中勾勒出那无形的必然命运来。这种写法,在《蜂港之午》中索耳曾使用过。
三、并驾齐驱的“两辆马车”
然而,这两个90后作家的叙事风格与美学特征又是如此相异。路魆的小说是反理性、反经验、反逻辑的,而索耳的小说则是理性、经验与逻辑的;路魆的小说作品弥漫着一股阴冷之气,时常令人头皮发麻,索耳的小说则如冒头的冰山一角,在看似普通中隐藏着巨大的力量;路魆的小说时常构建一片独立于现实的荒谬世界,而索尔的小说则紧紧扎根于我们的现实世界;路魆的小说源自于个体的感性体验,而索耳的创作则遵循着一套理性而学术的文学观念,这些观念来自于中外数十个国家的作家作品。
最后,我需要说明的是——从现阶段的90后小说创作来看,路魆与索耳可谓是广东本土90后作家中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如今,这两驾马车都已经上路,朝气蓬勃,锐意无限。当然,这并不是一条容易通行的道路,他们可能会遇到荆棘、坑洼甚至悬崖。然而,我始终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
愿他们继续奔驰下去。
注释:
[1] 路魆:《拯救我的叔叔卫无》 《青年作家》,2016年第9期。
[2]路魆:《幻痛的射击者》 《文艺报》,2017年5月3日。
[3]路魆:《圆神》 《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
[4]残雪:《一种特殊的小说》,见《残雪文学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5]路魆:《幻痛的射击者》 《文艺报》,2017年5月3日。
[6]路魆:《幻痛的射击者》 《文艺报》,2017年5月3日。
[7]路魆:《死与蜜》 《天涯》,2016年第1期。
[8]索耳:《我所追求的是异质之美和审美共存》 《文艺报》,2017年7月3日。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