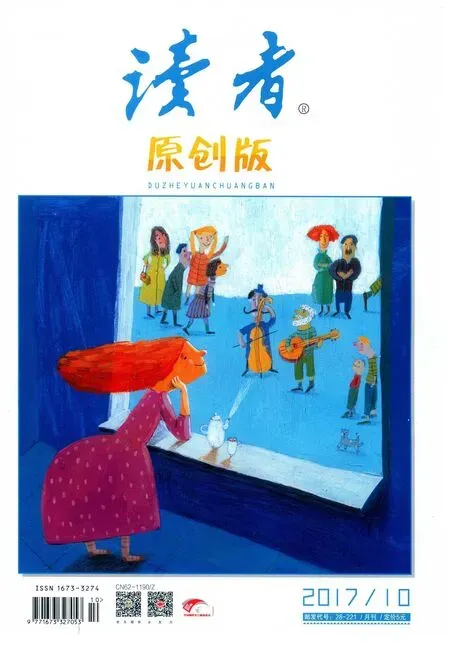张杨:我比从前更像自己
文|本刊特约记者 陈 敏
张杨:我比从前更像自己
文|本刊特约记者 陈 敏

▌导演张扬
《皮绳上的魂》8月18日全国公映,而它的姊妹篇《冈仁波齐》刚刚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
这完全出乎张杨的意料,他本以为这种文艺片知己寥寥。
尽管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爱情麻辣烫》获得了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而后凭借1999年的《洗澡》和2005年的《向日葵》,两次获得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1年的《昨天》和2007年的《落叶归根》也都口碑不俗……但那些毕竟都过去10余年了。
26年前,他24岁,第一次进藏,带着一台Walkman(随身音乐播放器)流浪了三个月。“那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它让我变野了,在城市中再也待不下去了。”途中他不断追问,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电影和真实生命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黄沙扑面迷眼。没有一条路是笔直的,他在艺术和商业之间也曾摇摆,也曾彷徨。
如今,张杨带回了两部西藏题材的影片。在北京繁华的通盈中心大厅,他戴皮帽,留长发,肤色黝黑,像个地道的康巴汉子,稳稳当当地站在一众打扮时尚的人群中。
尽量逼近真实
在拍摄《冈仁波齐》时,张杨带着十几个人的摄影团队,跟着朝圣者一路风餐露宿,跋涉2000公里,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拍了近一年,最终剪成不到两个小时的“纪录片”电影。演员是张杨从西藏的普拉村选择的几户村民,包含屠夫、孕妇、老人和小孩。他们也曾被同路的朝圣者质疑:这究竟是在朝圣,还是在拍电影?
张杨回答:“都是。”这种即兴的拍摄手法,也让他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表达上的自由。
途中,他们遇到一个小伙子骑车摔死了,张杨问当地人会怎么处理。他们说会为他念经祈祷,到了拉萨点一盏酥油灯。但最后,张杨把这段剪掉了,觉得偏戏剧化。在朝圣的路上,有新生,也有衰亡,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他想拍的就是藏族人民普通的生活,这需要摒弃电影拍摄技巧。
拍完后,他首先放给藏族人看,他们都觉得真实,他才认可。
“我认为绝对的真实是没有的,只希望能拍出尽量逼近真实的片子。”
16年前,张杨执导的电影《昨天》被称为当时最勇敢的电影,由演员贾宏声和其家人主演。片中,贾宏声30岁,戒毒成功,出院后过着安定的生活。片外,这个消瘦的男子重回大众视野,但依旧跟自己较劲,缺乏应酬的热情,骂走商业片的导演,孤独到底。43岁时,他从自家的窗口跳下,完成了他一直想要的飞翔。
张杨感叹:“其实,我特别理解宏声,他和世界的那种隔阂,我也有。他的偏执里有我们这群人的痛苦。20世纪90年代,我们都喜欢代表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导演戈达尔、德国的法斯宾德、美国的马丁·斯科塞斯……从小说、音乐、戏剧到电影,我们都渴望摆脱上一代人的乡土气。”
“跟自己死磕”的演员贾宏声,磕长头的虔诚的藏族人,张杨理解这种纯粹,也营造出真实的诗歌和远方。如此才能令人落泪,心生震撼。
我们也逼问自己一把:“我们的‘冈仁波齐’在哪里?该用怎样的方式‘朝圣’?”
从西部公路走到内心深处
新电影《皮绳上的魂》,是张杨在《冈仁波齐》拍到第八个月的时候,新建了一个150人的团队,抽出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它改编自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一个作家去小说里寻找他创造的人物—这个立意十年前就打动了张杨。
导演张杨也曾在寻找中迷失过。
处女作《爱情麻辣烫》让他一举成名,《昨天》《洗澡》先后上映,投资方开始找上门来,周围的朋友聊的也都是市场和票房,他难免焦躁,变得顾虑重重。2010年,他尝试拍了商业片《无人驾驶》,预估票房为六七千万,实际却只有2000多万;2012年拍了《飞越老人院》,他怨自己“没能坚持把它的黑色、荒诞和个性做到极致”,最终也是票房惨淡。
那段时期,努力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的张导,日渐陷入对自我的深度怀疑之中。
在北京焦灼了一段时间,2012年年底,他搬到了大理名为“归墅”的住所,面朝洱海,欣赏倏忽万变的海光天色,看看片,读读书,闲时骑着哈雷出去,载一车花回来。就这样,他一边发呆,一边思考。
发呆发够了,张杨筹划进藏拍戏。面对投资人,他开门见山,说下部电影可能是个赔钱的买卖,但是投进去很值得,因为“它会真正具有艺术的价值,赢得别人的尊重”。
在导演手记里,张杨记录了和扎西达娃聊剧本的情形:“七年前,我希望扎西达娃能加强剧本的冲突和戏剧性,强化商业性。而现在,我希望减少戏剧性和商业性,要空灵一些,简洁一些,让整部电影充满冷酷的诗意。”
当剧本做出颠覆性的改变,张杨不清楚有多少观众能看懂。
采访的当天就有观影活动。

▌《皮绳上的魂》电影海报
电影讲述了猎人塔贝杀鹿后获得天珠,后被雷电击中而亡,但活佛使他复生,让他将圣物天珠护送至莲花生大师掌纹地,以此赎罪,并降服心魔。这一路,他遇上了甘洌的爱情,遭到仇家追杀,因目睹生死轮回而在清晨的湖边俯首大哭。塔贝一度迷失方向,而去掌纹地的地图却神秘地刻在了他的后背上—距离在脚下,道路就在自身。
然而,这还只是一个时空。作家格丹创造了塔贝这个角色,却丢失了他的结局。带上狗,背上包,他决定去剧中找寻。
从西部公路走到内心深处,虚拟和真实层层交缠,每个人物都在他所处的时空爱恨杀离,导演在多时空里展示出数代人之间的追逐……
张杨曾自比作家格丹。广袤的森林、沙漠,独特的丹霞地貌,神秘的掌纹地,其中90%以上的无人区取景地都是张杨自己一步步跑出来的,而他寻找的不仅是电影语言的可能性,更是电影对真实生命的洞彻。
贾宏声说自己出生于伦敦,是列侬的儿子,现在也有人说张杨就是个康巴汉子。他从大理或者西藏回北京时,戴着牛皮帽子,穿着绑带的皮靴,不声不响地往座位里一缩,大家过了半晌儿才认出是他。
朋友说他变了,媒体说他头发留长了,但张杨自己说,上大学时他就留长发。那时,他和同学在中央戏剧学院组建了Hospital(医院)乐队,下了课就把大音响搬到窗台上放摇滚乐,让周边的中学生都“入了坑”。

▌《皮绳上的魂》剧照
眼前的这个男人没有了当年甩发打鼓的荷尔蒙,他语速很慢,声音低沉,表情也像电影的慢镜头,偶尔抹一把脸,好集中精神认真答题。
当谈到他的穿着时,他说:“甭管我穿什么,其实我骨子里一直挺摇滚的。摇滚的核心就是自由,是以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像自己了。”
不再摇摆的张杨,把头发留回了当初那位摇滚青年的长度。
拍电影不是为了票房,重要的是你在表达什么
▌《读者·原创版》:《冈仁波齐》是文艺片市场的一匹黑马,你对《皮绳上的魂》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
张杨:没有什么信心,黑马可能是特例。但能发片就好开心,票房不好我也开心。越艺术越小众,这是电影规律。艺术往往更具实验性和极端性,不会向大众妥协。导演也清楚,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但也不需要所有人都理解,只希望有一部分三观相合、知识结构相近的人懂得。影片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
▌《读者·原创版》:这是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片子,同时拍难吗?
张杨:不难,因为我脑子是特别清楚的。《冈仁波齐》比较即兴,也是我的修行。我们曾遇到一群朝圣者,他们计划围着冈仁波齐转1000圈,已经转了两年,600多圈了。虽然面目漆黑,衣衫破烂,但他们的眼神里充满虔诚。
《皮绳上的魂》的剧本2007年就写完了,2014年才拍出来,因为投资、环境等各种客观条件不成熟。好在十年前读的扎西达娃,现在看也一点儿不过时,他的小说很先锋。
▌《读者·原创版》:《皮绳上的魂》重点要表达什么?
张杨:个体在自己的困惑中如何寻找和救赎。就像格丹小时候逃避了小女孩递过来的天珠,长大后成了作家,寻找主人公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寻找自我。最后他接过天珠,直面自己的使命,继续走下去。而他创造的主人公塔贝,则映射了作家的另一面,就是想赎罪。两个人最后相遇,作家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就是指找到了自己的责任。
▌《读者·原创版》:你1997年就拿到导演奖,这20年对于“导演的责任”的理解有变化吗?
张杨:基本没有。电影对我来说还是一种个人表达,希望更多地跟我的生命和生活有一些内在的联系,不会纯粹为了娱乐或者某个概念去拍电影。越个人,就会离大众和市场越遥远,但这两部电影,我都是在往个人表达极致的方向走。拍电影不是为了票房,重点在你要表达什么。
▌《读者·原创版》:这种表达会受到限制吗?
张杨:限制是多种多样的。你过去可以说是审查制度,后来你发现资本和商业也都是限制,创作还是一样难。但重点还是,你内心的自由度有多大?你是否彻底放开去表达?最起码,我觉得自己获得了对电影认识的一种自由,不会让资本构成限制。
比如我用手机拍一个几分钟的短片,也是一种表达。我把《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两部片子放到一起拍,花了3000万就拍完了,这就是一种自由。钱多了就不自由了。
▌《读者·原创版》:现在你拍的电影和过去相比,表达上有什么变化呢?
张杨:我拍电影是有底线的,不会突破自己的底线。像《洗澡》《昨天》,虽然每个阶段表达的重点不同,但我当时都挺喜欢的,不然不会去做。
《飞越老人院》关注的是老人面对死亡的态度。这个浮躁的市场,缺少跟普通人的生活对接的电影。
到《无人驾驶》,我开始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摇摆。它有点儿拧巴,自己有点儿不满意。当时就觉得必须刹车,再这样拍下去可能会把自己拍丢了。
相对来说,这两部西藏题材的电影,是我在思考之后,徘徊之后,比较坚定地想要去做的。它们都侧重“精神”层面,是我愿意聊聊的。我深知会做得很艰难,尤其在必谈票房的今天。但这次创作很自由,很自我,没有什么障碍,让我重新坚定了电影的本质。
也许观众能从看完电影的那一刻重新面对生命。
无解,年轻人只能自己去经历
▌《读者·原创版》:前几年你搬到大理,思考自己要往哪里走。能跟年轻人分享一下你的解决途径吗?
张杨:无解。你很难教育别人,以过来人的身份说什么都是无用的,年轻人就得自己经历。导演也没有别的能力,只能拍个电影让你看看,或许对你有影响,或许改变不了任何人。或许看的时候,你的心会突然软一下,共鸣一下,但走出电影院,回到生活中,一切照旧。
▌《读者·原创版》:那“逃离北上广”搬到大理或者丽江呢?你说人生总要有自在的、接近内心深处的、不由自主的刹那。
张杨:那倒无所谓。在哪里都可以获得自由,只是我个人很喜欢大理闲适和散漫的生活。在北京就是聊电影聊得太多了。
城市是我的一部分,在路上是我的另一种生活状态。西藏、云南我都很喜欢,那里的那种开阔的视野是城市无法给予的。当你站在旷野之上,内心就会有一种震撼。路上的风景永远都在变幻,大理每天的云彩和星空都不一样,怎么看都不会厌烦。
在路上,你才能感受到世界如此之大,永远有和你的生命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发生,陌生的景色和新鲜的人们,让你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小格局。
▌《读者·原创版》:有人说你的新作是在过度消费西藏。
张杨:关于西藏的电影很少,所以不存在过度消费。西藏本身就有很好的故事,有人文环境、历史风俗、宗教传说,但呈现在电影里的非常少,九牛一毛。我反倒觉得拍摄西藏的电影越多越好,这样可以让观众更多地了解西藏。
▌《读者·原创版》:对拍电影这件事情还有野心吗?
张杨:我就想拍几部自己内心真正认同的好电影,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有鲜明的独特性。与这个密切相关的,是导演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也是电影绝对不能躲开的东西。当然导演也在发展,一点一滴地建立他的世界观。对我来说,如果这个东西缺失了,那拍电影的意义就不大,无非就是你做了一个叫作导演的工作。
不过,创作永远都有焦虑。在焦虑和困惑之中不断思考,才能拍出好电影。
这两年来,我觉得自己更艺术了,更坚持了。我在用最笨但最真的方式表达着自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