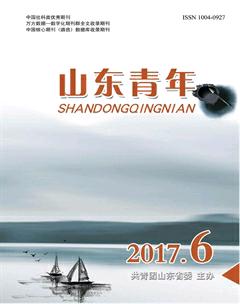行政行为界定及理论重构概述
唐啸��
摘要:传统理论对行政行为的界定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于何种行为属于行政行为难成定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演变,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作为新型行政管理方式不断涌现。传统行政行为的理论界定已无法涵盖新时代下行政主体依法作出的职权行为。不同[1]学者提出不同行政行为重构理论,重构理论主要集中解决三个问题:何为传统行政行为?其理论缺陷为何?重构行政行为的具体方式及依据为何?通过总结归纳当前学界关于这几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对行政行为重构理论进行大致了解,从而有助于判断何种行为属于行政行为。
关键词:行政行为;行政私法化;行政行为扩大说;行政行为缩减说
行政行为的理论是行政法学的重要理论,什么是行政行为是进行行政法学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和开展其他行政理论研究的基础,众所周知,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现象的法学学科”,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的、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法律规范系统”[1]。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贯穿于行政法的各个方面,与行政主体、行政受案范围、行政法律关系等行政法学研究对象密切相关。明确行政行为的概念,正确合理地界定行政行为的具体内涵,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行政行为这一核心范畴一直存在各种争议,特别是其概念内涵的界定为各学者争相讨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等新型行政管理手段是否能作为行政行为看待,若能其则可划入行政法领域调整,也即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何界定行政行为关系到理论与实践的衔接,不同的行政行为的定义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实务中自当区别待之。
一、行政行为理论界定
对行政行为的界定,各国和各学者都有其不同的理论主张。“行政行为的概念因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制度的需要而衍生”[2],法国、德国、日本对行政行为的概念作了不同的理解。行政法上,对行政行为存在三种不同的识别标准,及行为机关标准、行为性质标准和行为作用标准,行为机关标准是以行政行为的主体为识别标准,行政行为应为行政机关所为的行为,行为性质标准则以某一行为的行政性质作为划分行政行为与非行政行为的标准,行政作用标准在法国的行政法研究中居于通说地位,是指行政机关用以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的法律行为,以及私人由于法律或行政机关授权执行公务时所采取的某些行为。德国对于行政行为的定义规定在《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中指的是:“行政机关为规范公法领域的个别情况采取的具有直接对外效力的处分、决定或其他官方措施:一般处分是一类行政行为,它针对依一般特征确定或确定范围的人,或涉及物的公法性质或公众对该物的使用。”[3]与德国对行政行为的理解趋于一致的日本在行政法研究中将行政行为理解为“行政机关就具体事项所为公法上的单方行为,即将立法行为、公法契约、合同行为等排除于行政行为之外”[4]日本采用了對行政行为作限缩解释的方式,与此相反,我国台湾地区采纳了日本早期的通说观点,在《行政程序法》中将行政行为作为行政处分的上位概念理解,所谓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就公法上具体事项所为之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5]
我国对于行政行为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理论:其一,在我国行政法学初建时期,通说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6],该说认为行政行为是公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法律行为,会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随着自由福利国家理论的发展,国家放松管制,行政私法化理论的出现,政法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诸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计划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的出现,以往对行政行为的界定不再能涵盖所有的行政行为,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其二,主体要素说,该说认为行政行为是法律上被赋予权力的机关的一切行为。该学说既将行政机关运用职权所作的行政法律行为包含在内,也将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所作的行政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以及行政私法行为都一并纳入到行政行为的理论之中,却又将受行政委托机关、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一律排除在行政行为理论之外,此种学说明显的不适合行政行为的科学界定,目前很少有人坚持这种观点。其三,法律效果说,从法律效果界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也即某一行为若是行政行为,它必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一定的法律上的效果,不包括没有法律效果的准行政行为。其四,具体行为说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针对具体事项或事实,对外部采取的能产生直接法律效果使具体事实规则化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最广义说和最狭义说,前者认为行政行为是一切与国家行政管理有关的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行为,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后者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具体的人和事采取具体措施的行为,相当于具体行政行为。
二、传统理论之异议
通说将行政行为的定义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也即行政行为一般应符合主体要素、职权要素和法律要素,既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但这一定义为各学者所诟病[7],其认为:
1.通说导致学理和司法实践背离。行政行为的界定理应要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提供指导,又要涵盖行政主体所有的行政活动方式,既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又要以开放的姿态预测未来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许多行为被理论界定为行政行为类型但却被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例如行政立法行为,行政立法行为为抽象行政行为,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虽然取消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说法,但在行政诉讼范围的规定中明确了“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另外,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将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国家赔偿对象,那就意味着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赔偿请求人可以以行政赔偿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的行为种类,但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行政事实行为。这进一步证明了行政行为成立理论与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相悖的现象。
2.某些公权力行为地位不明。对于行政事实行为和准行政行为的行政法属性被通说所质疑和否定。行政事实行为是不依赖于行为人的意图而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种类,由于其缺少意思表示这一要素而与行政行为相区别。准行政行为也是因为欠缺某个要素而被对数学者确定为“介于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法律行为之间的行为种类”。但行政事实行为与准行政行为界限不清,相互混淆,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讲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准法律行为混为一谈。行政合同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内部行为等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在行政法学中都处于不确定状态。
3.行政行为体系混乱。由于对行政行为概念进行不同的界定,导致了对行政行为的不同分类,对分类的科学性程度标志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成熟程度,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分类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将行政行为划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单方行政行为和双方行政行为、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是学界所公认法划分方法,但如果将行政行为划分为单方行政行为或双方行政行为,那么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都是单方行政行为,此种划分只是对一类行政行为的再划分。
三、行政行为概念重构主张
针对行政行为的重构问题,我国行政法学界主要出现了两大阵营。一为行政行为扩大说,一為行政行为缩减说。行政行为扩大说认为在我国现行行政行为的司法实践背景下,鉴于行政诉讼法的新修订,已将行政事实行为、行政协议等纳入到行政行为之中,并取消了“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中的规定,改用行政行为,为保证法学上的概念与司法实践中的概念所承载的价值的同一性,有必要对行政行为进行重新确定,并作为通用的概念予以推广,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有利于与执法者与守法者所接受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保持一致,实现法律的正确运用,从而实现行政法治的统一,此其一,其二该说认为对行政行为进行扩大解释,有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广义上的行政行为是人权保障的强化、服务行政的出现的结果,其强调的是人权保障的首要价值。其三,基于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和法律文化背景不允许建立狭义的行政行为理论。我国没有与德国相似的独立的行政法院,很难保证行政行为的司法最终性,亦没有类似德国的行使司法审查权的宪法法院,建立狭义的行政行为理论只会使众多行政行为脱离司法审查,有悖于司法最终性原则,不利于人权的保障,还有就是因为我国公民并没有良好的法律文化,在我国道德重于法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遵守远不及德国,专业性的狭义行政行为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基于这些理由,行政行为扩大说主张将阶段性行政行为、服务性行政行为,例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预备性行为等纳入到行政行为的范围之中。
行政行为缩减理论主张将新型行为手段与行政行为并列对待,保持传统行政行为概念的特定内涵,缩减通说的外延,使之成为其他类型行政活动方式的同位概念,并以行政诉讼制度为背景,界定行政行为的概念及其内涵,其认为不同方式的行政活动有着不同的司法控制规则,根据国家的立法政策,新型的行政手段可以逐步与行政行为一道并列融入行政诉讼之中。
行政行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够被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行政指导、行政命令等新型行政行为是否能被纳入到行政行为的范畴,关系到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构行政行为有利于加深对行政行为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杨海坤,蔡翔,《行政行为概念的考证分析和科学重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3]柳砚涛,《行政法中的私法适用研究》[C],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2005.
[4]章志远,《行政行为概念之科学界定》[J],浙江社会科学,2003.
[5]孔林军,《论我给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改造——以行政合同司法救济为切入点》[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
[6]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7]陈越峰,《中国行政法(释义)学的本土生成——以“行政行为”概念为中心的考察》[J],清华法学,2015(1).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