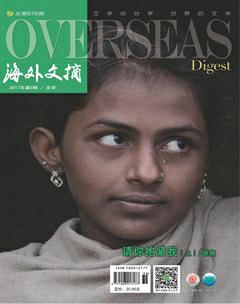“怨”诗说
林继宗

不平,有了“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上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诗歌作用之一。《汉书·艺文志》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诗·大序》则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倾向或侧重。司马迁或许是最早倾向“怨”诗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说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甚至有的以身殉诗文,如屈原赋《离骚》。《离骚》正是中国“怨”诗的代表作。司马迁归纳说,《周易》、《离骚》、《诗三百篇》等“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郁结就哀怨,诗歌大抵是“有所郁结”的不得志人士或伤心的失意者“发奋”的呼喊或叹息了。
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诗歌里,往往劳者、饥者与怨者的怨恨之歌才真正反映出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听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长歌当哭”成了人们熟知的常用语。国外“怨”诗之说也颇盛行。著名诗人海涅肯定地设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格里巴尔泽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豪斯门说诗是一种分泌,不管是自然的分泌还是病态的分泌。
不平则鸣,鸣的常是“怨”诗。当然,如韩愈所说,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和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但他更倾向后者。他比前人更明确地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念。《全宋文》说:“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后人干脆归纳为七字诀:“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
韩愈推崇穷书生的诗作。司马迁、钟嵘只说穷愁使人作诗、作好诗,王微只说文词不怨就不好,韩愈除了肯定司马迁的话,还说快乐人也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诗。韩愈的事实依据是:“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19世纪西洋不少诗人认为:最甜美的诗歌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忧郁是诗歌里最合理合法的情调”,“忧伤宜于诗”。
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
暗示,含蓄以及早熟
中国“怨”诗富于暗示与含蓄,也是早熟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精美的诗歌语言含示难以凑泊、不可明言的境界与“怨”情。不说出来的怨情比说出来的怨情更富于诗意。“解识无声弦指妙”,“此时无声胜有声”。诗人领引你到语言的涯际穷边,于是便有了神妙深秘的静默:“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崇敬钱钟书先生,这位著名的学者型作家,已有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他虽然在多个领域具有高深的造诣,却一直非常谦逊。他在日本讲学时延引了意大利一句嘲笑人的惯语以自嘲,说自己“发明了雨伞”。据说在意大利有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他凑巧拿着一方布和一根棒,于是急中生智,用棒撑起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很顶用。他在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公之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连棒带布赶到专利局报告并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让他看个仔细。钱先生自嘲道:“我今天仿佛就是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他的谦逊与幽默,博得了满堂敬意与热烈的掌声。
我由钱钟书先生的诗歌理论想到了黄潮龙文友的诗歌。自然,黄潮龙文友的诗歌绝不只有 “怨”诗 ,他的诗路是很广阔的,品种也较多。他从十几岁开始学习诗歌创作,至今已经出版好几部诗歌集,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绿月亮》,写得有形象,有意境,有情趣,有韵味。《绿月亮》也获得了诗歌界普遍的好评,并被评为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提名奖。
乡土诗歌以自然、质朴的方式表现了浓郁的家园情结。乡土诗让读者对农村和生活其中的人有更深的了解和关怀,但又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常常会导致创作与接受者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乡土诗在创作逃避和传播障碍的原因之一。《黄潮龙诗选》大致可以分为节令、名胜、特区、抒情、乡土几部分。本文主要从黄潮龙的乡土诗(集中在《诗选》第五辑:乡土芬芳),讲述其诗歌作品的语境和情怀。
黄潮龙是潮汕地区的抒情诗人,面对全球化语境,仍坚守着乡土的那份本真,将饱蘸情感的笔触深入到乡土家园,这种对乡土文化精神的掘取无疑增加了他诗歌创作的空间。他的乡土诗,抓住了诗歌创作根性的东西,面向土地,面向故乡,用朴素的情怀,写风物、抒命运、咏文化,将生存幸福和隐痛写得独特而深刻。“如果假我一个春季/我会在回家的路上成熟/追逐着歌吟第一声春的礼赞(《回乡》)”。黄潮龙对自己的故土的依恋不离不弃,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他每时每刻的诗歌呼吸,体味到其责任和良知。这些作品让人想起与榕江平原生命的牵连,闻到潮汕文化的气味,是回忆、寻找、呼唤,也是深省、反思、整合,是一种特有的人文精神和关怀。在诗歌语境上,也为读者留下了又一思考与探索的空间。
疼痛感是诗歌中最永恒的力量,但疼痛感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情感的流露,只有这样才具征服力。面对相对宁静却又滞后的故乡,黄潮龙有着自觉的现代诗歌观念,诗人的情绪没有被世俗观念所撕裂,而是呈现出一种饱满而自足的情绪和心态。“风从老寨的屋顶跌落下来/流经老墙上一道道蛇行的罅隙/我听见水珠从凤尾竹叶上滚动的声音/被风轻轻托起……/那场雨真的下了很久/带上贫穷与富裕/带上惆怅与希望/在不远处飘来的/80年代的音乐声里/缠绵(《老寨》)”。
黄潮龙文友写乡土的诗歌中,很大一部分充满疼痛感。生长在幸福,谁会注意到季节的变换/榕江平原,为冷酷的希望而颤动/为艰苦岁月的日子流泪……一个婴儿看着这混沌的世界,在犹豫/不知是否愿意这样成长下去/内心的独白有谁对话/东方正红,一颗星明明灭灭/充满着未知(《榕江,是大地的脐眼流出来的吗》);“在灶浦和京岗之间/有条江河/我在用生命的悲喜/向你泅渡/这是怎样一种/艰难的生存方式/榕江,母亲河/我虔诚地膜拜着/缓缓走向你,从此融化在/你宽阔柔情的摇篮里(《站在京岗渡口瞭望榕江》)”。
当然,黄潮龙文友诗歌的乡土特色远不仅仅是其对故乡的描述,而是表达了故土既是起源又是最终归宿的乡土认同。比如《乡愁》:“昏睡了这大街小巷/只有月亮与心醒着/醒着的月泛出漫天的心事/让心泅渡/夜于是徘徊,月也徘徊//乡愁是环村的小溪/时时将故乡紧抱/乡愁是一只盲鸟/飞不出一堵沉沉的黑墙/夜很苦恼/何处有洗涤积物的晨风。”诗人没有直接抒写多么思念家乡,而是从一个游子文人的角度出发,以小街、月亮、小溪、晨風等物象,用昏睡、醒着、泅渡、徘徊、苦恼等元素来修饰,这些纯美的画面、刻骨的乡情、诗意的过渡和递进本身,就具有概括和新意,简洁而又有感染力,透出生机勃发的新意,体现了他对当下农民处境的深切同情以及自身悲悯的人文情怀,真切而自然,是一个游子追寻生命之根时自然而然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恩之情。
品读黄潮龙文友的乡土诗,使我有一种久违的温柔敦厚之感,这是他的诗歌给予读者厚爱的最大回报,“那场雨一定下了很久/让人忘记了开始和结束”(《回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