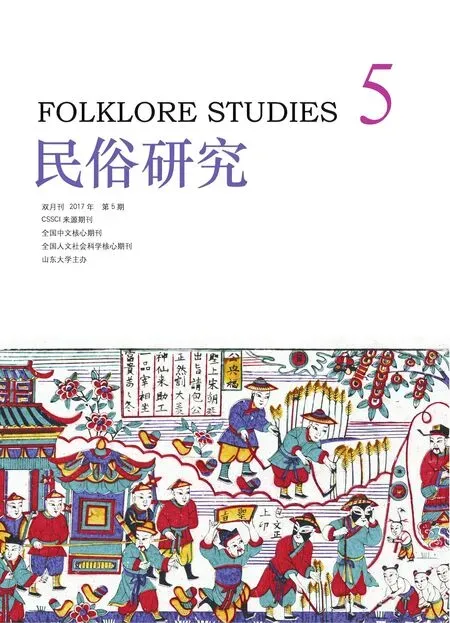地方的多重感知:一种生态博物馆的路径
尹 凯
地方的多重感知:一种生态博物馆的路径
尹 凯
在现代性与在地性的影响下,“地方”或“地方感”的相关议题日益成为不同学科重要的知识生长点。在遗产与博物馆学领域,作为一种塑造“地方感”的文化工具,生态博物馆在项目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遭遇到了认知社区或乡村的困境。地方的感知并非唯一,而是极具主观性和场景性。乡村个体、乡村集体、地方政府、生态博物馆都有一套解释地方的逻辑视野,这种多元性的地方感知是理解地方、治理地方的关键所在。
地方;地方感;生态博物馆;乡村集体;地方政府
一、提出问题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一个重要的多学科概念,指的是一种理解个体与群体如何定义自我,及其与自然、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复杂过程。作为一种学术议题与社会思潮,“地方”与地方感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和深化,这种“在地性”的关怀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迁徙与离散等议题密不可分。地方感话语的产生,一方面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脱嵌或脱域(disembeddment)机制*[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解释“同质化运动”*Ursula Heise,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Oxford: Oxford Universtiy Press, 2008, p.51.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美]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王志弘译,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2页。密不可分;同时也可视为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纠缠在认同政治中的体现。*Sharon Macdonald, “Museums, National, Post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 Museum and Society, vol. 1, no. 1(2003), pp.1-16. Sharon Macdonald,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17-19.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王海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的论述也是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尝试。关于“地方与无地方性”*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议题,艺术领域走得更远,“有根性”的本土化阐释不再是逃避资本主义市场的有效路径,而是已经被纳入到一般性的“国际文化”中。正如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所说,“地区性对于现代的全球资本来说的确绝对是最根本的信息,绝对根本。”*[美]弗雷德·迈尔斯:《表述文化:土著丙烯画的话语生产》,[美]乔治·马尔库斯、[美]弗雷德·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梁永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9页。聚焦于地方感议题的论文集《制造地方感:多学科视角》*Ian Convery, Gerard Corsane and Peter Davis(eds.), Making Sense of Plac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2.囊括了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博物馆学、遗产研究等诸多领域,为我们理解人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多学科的国际视角。
关于地方感的概念与研究维度,不同学科着眼于自身的问题意识,答案不尽相同。*关于地方感的理论梳理详见:钱俊希、钱丽芸、朱竑:《“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人文地理》2011年第6期;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华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期;唐文跃:《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旅游学刊》2007年第11期;王姗姗,宗秀蔡:《地方感与生态身份认同——梭罗生态观新读》,《都洋湖学刊》2012年第2期;黄逸民:《全球与地方的二元辩证——全球化时代地方的流动性与复苏》,《都洋湖学刊》2013年第6期。从遗产与博物馆领域来说,地方感的产生也是一个渐变的演化过程。一方面,当下遗产概念的地方性建构不仅与全球化的反思有关,而且与遗产自身观念的流变有密切的关系。从70年代强调普世性文明图式的世界遗产,到90年代以来对文化遗产在地性价值的凸显,文化遗产研究经历了从全球到地方,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发展。*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另一方面,以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新博物馆学运动同样将具有“社会”意味的社区、乡村或遗址作为传统博物馆反思的实验室,借生态博物馆路径来体认地方认同与地方情感。此观点集中体现在彼特·戴维斯(Peter Davis)的《生态博物馆:地方感》*Peter Davis, Ecomuseum: A Sense of Place. London and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中。彼特·戴维斯巧妙地实现了生态博物馆与地方的嫁接,不仅将生态博物馆作为处理“地方感”的文化工具,而且将其与当下社会最为棘手的困境联系起来,成功开拓了生态博物馆的思考与实践范畴。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地方感知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层级性:个体从生存空间(existential space)的感知来体验地方的文化与结构;乡村集体从工具空间(instrumental space)的维度来取舍地方的历史与范畴;地方政府从认知空间(cognitive space)的维度来想象同质性的地方传统与意义;生态博物馆项目组则从建筑空间(architectural space)或计划空间(planning space)的形式架构来制造地方意象。简而言之,由静止的物理场景、活动和意义等基本要素所组成的地方*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47.,在不同的空间视野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
在2012-2016年间,笔者参与多项生态博物馆项目*笔者参与的生态博物馆项目如下:“山西省平顺县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总体规划”(2012年),“松阳生态(乡村)博物馆群总体规划”(2015年),“松阳·吴弄生态博物馆建设规划”(2015年),“松阳·酉田生态博物馆建设规划”(2015年)。,在此过程中深感作为一种文化工具,生态博物馆所形塑的地方仅仅是多重地方感的一种。地方在地理学意义上是一个空间位置和地理景观的概念,它在能动性上的“无力”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意义集聚的竞技场。被表述的地方在认识论层面成为各方观念接触的场所,同时暗含着有关“何为地方”的争论。据此,笔者将从局内人的个体和乡村集体、地方政府、生态博物馆等四个层面来分析地方感知的多重场景与阐释。
二、局内人:一种个体化的地方感
人们通过自身的态度、经验、意向、经历透镜来审视周边环境,所有的地方和景观体验首先是个体层面的,这种内在于空间结构内部的视野来自于作为文化群体成员的具体与真切的体验经历。作为地方象征的村落、民居、田地、道路构成了局内人的一种无意识的地方印象,这种局内人的观点暗含了村民个体的过去经历和村落精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地方感知呢?这种出于生活空间考量的地方认知有何价值?从目的论角度来看,这种零散的、带有主观意识的地方感知对项目建设帮忙微乎其微,但如果将其放置在地方感的不同表述中,它的价值会通过比较研究而得以凸显。
2015年7月,笔者借松阳生态(乡村)生态博物馆群总体规划项目的契机对浙江省松阳县酉田村进行建设前期的田野调查,其中,“村民如何看待自己村落”的一系列问题是遗产调查的关键。常年居住在酉田村的大部分村民在被问到“你觉得你们村有什么特点”这样的问题时,他们一般的反应是先笑笑,然后回答“我们村没什么特点”。不过,一些村民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回答,比如“有许多老房子”*被访人:包国标;访谈人:买岸笛;访谈时间:2015年7月5日;访谈地点:松阳县酉田村3号民居。,“29号民居的故事”*被访人:叶连汉;访谈人:尹凯;访谈时间:2015年7月3日;访谈地点:松阳县酉田村村委会(酉田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村子有医药世家”*被访人:叶宝华;访谈人:买岸笛;访谈时间:2015年7月4日;访谈地点:松阳县酉田村28号民居。。这种地方感知的无意识性反映的并非是局内人对地理空间认知和理解的缺乏,而是这种地方感已经内化在日常生活实践中。
7月5日,项目组在入户访谈过程中进入24号民居,家里的大人都不在,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小女孩在看电视。访谈时间的充足和言语沟通的方便让笔者得以充分地就村落认知问题进行深入访谈。当被问到酉田村在她心中的印象时,她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在晒谷场玩耍的场景,童年的记忆慢慢浮现,而且这些儿时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她对于地方的认知。与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村落认知不同,她认为酉田村的特色是“树多”*被访人:叶晓雯;访谈人:尹凯;访谈时间:2015年7月5日;访谈地点:松阳县酉田村24号民居。,这一独特的回答引起了笔者极大兴趣。随后,她为我们画出她心目中的“村落结构图”。


左面的一幅图是叶晓雯在自我感知基础上“绘制”的酉田村落结构图,通过这幅图我们能够看到几个酉田村要素:自己家(24号民居)、邻居家、学校、水井、空地、草地、祠堂、池塘以及与之相关的乡间小路。通过这幅图我们能够分析叶晓雯地方感知的认识原点——“家”。叶晓雯绘制她心目中的酉田村时,正是从“家”开始,以此来确定方位与位置。文森特·文茨纳斯(Vincent Vycinas)认为,“即使我们背井离乡多年,家却定义和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Vincent Vycinas, Earth and Go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artin Heidegger. The Hague: Marinus Nijhoff, 1961, p.84.的确,家不仅仅是我们居住的房屋,而且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参照点,它形塑了我们认知与理解外在事物的方式。
与此同时,这幅图交代了她在酉田村的三种日常生活:第一,草地空间构筑了她关于儿时的记忆,她所认识与理解的草地面积远远与现实的规模不成比例,这种比例上的夸大代表的是一种感知上的重要性,地理空间承载的是童年的记忆。她所标出的“空地”依然是一个来自过去记忆的想象,因为现在酉田村在这块空地上早已种满了茶树。由此可见,来自个体生命的生活空间表述往往充满着主观性的色彩。第二,学校以及从家到学校的道路标识的比较完善,酉田村的五心小学是她小时候上学的地方,从家到学校的道路更是走过无数次。虽然现在五心小学已经成为村委会(酉田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驻地,但是空间命名与内涵的变化并未带来相应的感知上的转变,相反,来自记忆深处的体验与经历定义了这一空间。第三,进村与出村的道路也值得特别注意,原因在于叶晓雯绘制的这幅图中仅仅标出了这条道路沿途经过的祠堂与池塘,最近出现的摄影亭、牛栏、观景廊、旺美家庭农场等新事物尚未被纳入到她所感知的村落整体中。
个体对村落结构的认知体现着个人与村落的联结,或者说个体生命历程与村落空间的重合。叶晓雯对酉田村的认知并未包括酉田村的田地、新村等空间格局,这些与其个人体验无关的现象尚未被纳入到她对地方感知的图式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每一个酉田村民都绘制一幅酉田结构图的话,那么这些基于个人体验的结构图式应该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同样的地理空间,不同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体验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地方感。
如果我们将叶晓雯所认知的村落结构图与右边住建部编制的酉田村落结构图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个体心目中的“村落整体”其实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规范的。政府部门基于测量、统计、绘图、标识、比例、分类等手段所做出的酉田村落结构图是一种科学认知的产物。如果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的话,那么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关于原始人与欧洲人是如何认识澳大利亚西北部景观的论述*Amos Rapoport, “Australian Aborigines and the Definition of Place”, in W. Mitchell(ed.),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nd Practice. Los Angeles: Proceedings of the 3rd EDRA Conference, 1972, pp.3-3-1 to 3-3-14.极具启发。局内人的地方感表述来自于一种无意识的生活经验,被纳入到理解框架的地方要素皆具有重要性和象征性;政府部门的地方感表述则来自于一种科学性、功能性和实用性的现代逻辑,整体得到最大化阐发。
三、集体的策略:村支书眼中的地方
正如上文所说那样,从个体视野或生活世界来看,被表述的“地方”是充满生命力的,具有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意义与体验。局内人的个体化感知无一例外地囊括了地方景观、活动与功能、意义与象征三个内在互动的地方要素。虽然个体表述的叠加并非集体感知,但是共享的文化体系(意义和象征)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集体认知地方的共识。照此推断,地方在村落集体层面的表述应该更加接近地方认同的核心区域,即地方感、地方精神(spirit of place)、地方天赋(genius of place)。*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48.笔者不禁疑惑整体性的村落是比个体感知更准确的表达吗?集体的地方认知究竟是通过何种渠道,以及如何被表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这诸多疑虑进行分析。
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依然是乡村社会的主要代言人,任何带有官方性质的活动与项目总少不了与村支书打交道,“遭遇村支书”也是人类学乡村研究的永恒话题。作为村落空间内具有双重气质的人*[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8-182页。,村支书对村落的认识与理解无疑带有整体的综合倾向,如果说个体的地方表述具有主观意识性,那么村支书的地方表述则是集体意识的写照。早在2012年,笔者在山西结识了白杨坡的村支书岳安龙,在松阳项目中,接连认识了酉田村的村支书叶连汉和吴弄村的新老村支书何跃平和叶增标,笔者将通过分析村支书的行动策略来认识村落整体意义上的地方感是如何表达的。
2015年11月1日-2日,第三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乡土文化保护和乡村博物馆建设”的分论坛现场,来自白杨坡的岳书记以“民俗文化和乡土记忆”为题作了发言。在介绍白杨坡的基本面貌时,岳书记谈到:“白杨坡村区位环境是山连山,层层山林紧紧相连,梯田缠绕在山腰间,抬头望望天,太阳占去了半个天。这里属有三分耕地、七分是山,吃饭靠天,出门靠肩担,千百年来,白杨坡村农耕、纺织、文化记忆一直生生不息,传承至今。如今家家户户都还养驴,作为自家耕地、打场、磨粮使用。种地用的肥料仍使用驴肥、羊肥、牛肥,种出来的粮食绿色无公害、环保,这里种植棉花,历史悠久,家家户户仍在纺织棉花,家织土布,加工土布床单、土布鞋。”*岳安龙:《民俗文化和乡土记忆:以山西省平顺县白杨坡为例》,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第三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之分论坛六:乡土文化保护和乡村博物馆建设》,北京,2015年11月。
岳书记这些关于“白杨坡”的认知实际上是在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的恬然淡泊景象跃然于纸上。2015年10月,笔者再次重访白杨坡时并未见到岳书记所描绘的村落图景,棉花种植、手工纺线与织布都早已不在,全村仅有两头驴,羊和牛在村落里早已不见,更不用说家畜肥料。岳书记关于目前白杨坡的真实表述值得商榷,村民活动与意义体系基本上是村落过去图景的想象。岳书记为什么不描述当下白杨坡的现状,而是以过去的记忆来表述呢?这种表述背后的发生学机制是什么呢?
关于这一现象,笔者暂时采取“存而不论”的策略,接着回到浙江省松阳县,因为类似的地方表述也出现在这里。作为浙西南家族聚居形态的典型代表村落,吴弄村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资源一度成为乡政府所在地。吴弄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落,因此新建的民居很多,构成了地理空间上的“吴弄新村”,与依据宗族血统和道统理念而先后建造的古民居群——“吴弄旧村”一起共同构成了整体上的吴弄村。在吴弄村开完村民代表座谈会后,项目组要求老支书带我们去吴弄村走走。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我们穿梭在“吴弄旧村”连绵成片的古民居之间,周边古道、古树、古井、溪流、竹园、农田与村落和谐共生,融为一体。在笔者的田野笔记中曾这样写道:
在老书记的陪同下,我们对吴弄村的整体进行了初步了解,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何为村落,他们是如何在他者面前定义自我,定义地方感。在介绍吴弄村,或者带我们展示村里的遗产资源时,老支书和新支书无一例外地将吴弄村的地理范畴、心理认同、村落认知定义为传统民居保护很好的吴弄旧村,吴弄新村根本不在他们所说的吴弄村整体认知范围内。*资料来自于尹凯:《松阳·吴弄生态博物馆建设规划调研日记》,2015年7月2日。
在走访杨家堂、靖居口、金村等浙江传统村落时,村支书为我们展示的村落整体感知是以古民居为主的传统建筑,日常生活世界被这种独特的地方感知所切割。岳书记采取时间维度上的错置来表述白杨坡,何书记则采取空间维度上的切割来理解吴弄村,前者将过去的村落图景作为一种对外表述的模型,后者将部分的村落图景作为对外展示的村落典范。在他们的集体性策略中,现代的地理景观、日常生活和村落精神统统被忽视,那些带有历史意味的、来自过去的陈旧之物反而成为村落的代表性符号与象征。
这种策略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为什么集体性的村落感知会出现这种关于地方的错觉,甚至是曲解呢?原因可能在于与个体性地方感知来自直接体验不同,共识性或集体性的地方表述的生成机制和发生学原理在外部,而非村落内部。也就是,共识性或集体性的地方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众媒体或外界社会的影响,它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和操纵性。*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61.换句话说,村落在面对外界社会表达自我的时候,不自觉陷入到一种供需关系的消费结构中。村落固有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会伴随“外部需要”而被挑选、生产与强化。
中国传统村落曾经存在过相对封闭的状态,那个时候的村落集体感知来自内在的发生学机制,共识性地方感知是深深根植于地方的。随着旅游文化与大众媒体的兴起,村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信仰层面上从地方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并被纳入到整体的社会场景中。整体村落与现代性都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两种文化体系,村支书的地方表述在面对两者接触与碰撞时采取的是一种“互补性分化”*[英]格雷戈里·贝特森:《纳文——围绕一个新几内亚部落的仪式所展开的民族志实验》,李霞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6-163页。的策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被表述为臣服与支配、展示与欣赏的关系,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整体性结构框架。
四、概念的隐喻:地方政府的感知错觉
如果说个体化的地方感来自于主观的体验,集体性的地方感出于一种分化的策略,那么抽象性的地方感则是一种想象的建构。当从认知空间或抽象空间来感知地方时,地方往往呈现出同质性、中立性和无经验性的面向,具体的生活世界被一种人为或社会的建构所取代。此时,地方感知的主体不是村民个体,不是村支书,而是地方政府。笔者将继续采取地方感知主体层层递进的分析路径,审视地方政府是如何认识与理解地方的,并讨论这些表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松阳县是浙西南地区建制最早的县,历史上曾经是浙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11年,松阳县第九次党代会确定了“全面推进‘两区建设’,全力打造‘田园松阳’”的战略任务。自此“处州粮仓”、“松阳熟,处州足”、“桃花源”、“金瓯玉盘”、“田园松阳”、“绿色崛起、科学跨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化名县”等概念和口号开始频繁成为松阳县的代名词。这些概念的提出对于松阳县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分析。在此,笔者还是回到松阳生态(乡村)博物馆群建设的过程中,从项目组与地方政府的接触与互动中评价地方政府是如何表述县域地方的。
2015年7月6日,松阳生态(乡村)博物馆群建设暨松阳县政府座谈会在松阳县召开,时任松阳县县长王峻在此次会议中提出:
松阳没有大文化,没有历史文化名人。松阳的特色在于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形态,我们的农业在浙江省GDP占第一位。所以我们松阳县的农耕生产、生活是特色。自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们在讨论松阳县生态文明之路怎么走时提出了一个概念,我暂时叫它为“全县域的农耕文明博物馆。*资料来自于尹凯整理:《松阳生态(乡村)博物馆群建设暨松阳县政府座谈会》,浙江松阳,2015年7月6日。
王县长的讲话确定了松阳县地方表述的特色,即“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具体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村落相对封闭等一系列要素。显然,现在的松阳县域内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农耕文明村落。首先,从生计方式来看,作为松阳县山地生活形态的代表,酉田村一度被认为是松阳县农耕文明的代表,但是通过走访,项目组发现酉田村并非如此的简单与同质。当下酉田村的主要生计方式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规划方案》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最初,酉田村的先民们以种植水稻为生,从播种耕耘到收割加工,辛苦劳作,不舍昼夜。随后,酉田的村民们不满足于稻谷带来的微薄收入,开始尝试养蚕、养蜂。从1997年开始,外地老板开始在山中引进种植翠冠梨,因获利较大而逐渐在全村推广。从2004年左右,酉田村开始种植茶叶。因为经济收益比稻谷高,茶叶已经成为村中绝大多数村民赖以为生的产业。现在,村民根据村中实际情况而选择以高山水果和茶叶种植为本村的重要产业。*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松阳·酉田生态博物馆建设规划方案》,2015年12月。
笔者的观察也证实了酉田村正在发生的变化,很多稻作农业的农具早已远离民居的核心空间,被任意地堆砌在民居二楼,任由其落满灰尘,慢慢腐烂。其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农耕文明几乎不存在商品化现象,生活形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形态,但是,现在的松阳县茶产业、水果产业则是有系统的产业链条和商业氛围。第三,农耕文明所谓的保守与封闭村落结构也早已瓦解,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范围上来讲,松阳县的村落并非是封闭的。通过访谈,我们发现酉田村的茶叶会出现在温州、杭州,翠冠梨会出现在县城、嘉兴、杭州等地方。
为什么王县长所谓的农耕文明一说如此经不起推敲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摘录当时所做的田野笔记直观呈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要不就是松阳县的50个传统村落中有的村落还保留了水稻种植技术与传统,这些村落还没有进行深入了解,情况不得而知。但是根据我的推测,这种可能性极小。要不就是王县长口中的“农耕文明”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即农业产值在浙江省GDP产值中占第一位所造成的错觉。要不就是以田园松阳为代表的田园、桃源、古民居、传统等一系列词汇造成了一种想当然的先入为主的理解偏差。*资料来自于尹凯:《松阳生态(乡村)博物馆群建设规划调研日记》,2015年7月7日。
农业产值与农耕文明并非一个概念,单纯以数字来定义地方是非常危险的。抛开松阳县种类丰富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风水文化、产业文化等资源不谈,笔者将重点论述地方政府关于地方表述的错觉是如何形成的。
与主观体验和分化策略不同,地方政府对地方的概念表述落入到抽象空间的陷阱里。抽象空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逻辑关系,空间与地方的描述可以脱离经验观察与实地研究。爱德华·瑞夫(Edward Relph)认为这是一种人为想象的自由创造,同时也是象征思维成果的直接反映。*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26.在抽象空间里,具体的经验感知被全部泯除,用麦克西·杰曼(Max Jammer)的话来说,“地方被认为是一种连续的、均质的、同质的、有限的或无限的空间。”*Max Jammer, Concept of Space: The History of Theories of Space in Physics. New York: Dove Publications, 1993, p.7.以农耕文明这一抽象系统来统合县域内的不同文化资源是一种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制造差异的策略,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种地方感知与建构是必要的。但是就生态博物馆与地方感知之间的关系来看,地方政府对地方表述的错觉容易将生态博物馆带入到一个僵化的模式中,使其丧失固有的开放魅力与再生产的可能性。
五、生态博物馆:一种他者的地方表述
与上述几种地方表述的逻辑略有不同,生态博物馆采取的是一种“计划空间”的认知模式,它是一种创造地方的有意识行为。无论是农村规划还是城市建设,再造地方的尝试与二维空间的功能有关,而非空间的活动体验。与主观的个体性感知以及科学的实用性感知不同,基于生态博物馆项目的地方感知与秩序再造涉及到空间范围内土地使用的效力。*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23.比较研究能够发现生态博物馆所秉持的地方感究竟是什么。个体性的地方感是局内人的一种主观体验,集体性的地方感是面对他者而分化的一种策略,抽象性的地方感是一种基于同质性的想象错觉,而计划性的地方感是一种重新建构地方认同和地方现实的有意识尝试。作为当代“地方运动”(place movement)的一种形式,生态博物馆旨在通过对现有地方景观、村民活动、意义体系的有意识创造,来重建有关村落生活空间场景中的地方特殊性与重要性。
生态博物馆的“法国模式”*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3年,第46-59页。在处理县域范围上具有非常有效的操作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态博物馆从县域范畴来进行地方表述是相对无力的。地理范围越大,地方要素越多,相应的特色总结与提炼也越困难,内部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地方表述无法形成共识。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在建设过程中,并未明确提炼安吉县域的整体性地方概念。也就是说,“品牌”或“名片”虽然提升了一个地方的可辨识度,但是往往会带来一种简化地方的风险。正如上文所述,无论王县长如何定位松阳县的特色,都会存在误解和偏差,比如松阳县西南部的生态保育主题与三都乡的山区生活形态、四都乡的休闲景观就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以县域为单位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不适宜提炼“地方主题”,开放性的系统结构既能够为具体的生态博物馆运营提供空间与活力,又能够为将来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留有余地。
具体到以村落为主体的“小地方”,生态博物馆关于地方表述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说,生态博物馆在表述以村落为单位的地方时,独特的“他者眼光”提供了有效的洞察力。我们并非在强调他者的地方感知比局内人的地方体验更加深入,而是说生态博物馆的整体性理论框架更为系统地整合与感知了地方。吴弄村的一些老人普遍认为吴弄村的特色在于“三叶产业”(烟叶、茶叶、桑叶),但是从生态博物馆的立场来看,这仅仅是吴弄村地方感知的组成部分之一,水利、古民居、祠堂、教育、新区等一系列要素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地方感。因此,生态博物馆的优势恰巧在于它的外来者眼光,深入的田野调查能够无限接近地方的内在核心——地方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作为整体的地方感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的想象性表述不同,生态博物馆表述地方的手段是极为有效的。通过对切实地理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把握,生态博物馆试图在现实的地方场景中“捕获”现实。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盲目分化”的缺陷,不至于让地方落入到供需关系的结构模式中。正如生态博物馆的村落整体展示和体验体系所发生的自我流变与认识转型一样,生态博物馆对地方的表述日益走出所谓的“好古主义”倾向,而逐渐正视村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过程性。
毫无疑问,生态博物馆的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究其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外来理念的地方表述。也就是说,村民、村支书、地方政府扮演的是一种“局内人”和“自我”的角色,而生态博物馆则处于一种“局外人”和“他者”的立场。那么,这种来自“他山之石”的地方表述是否合理有效呢?它对地方秩序和地方意象的理解与建构是否具有合法性呢?这需要通过分析生态博物馆的属性以及生态博物馆介入地方的路径来回答。生态博物馆在保护与理解地方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每一个生态博物馆都寻求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创造一种联系。生态博物馆的特殊属性提供了其介入地方的有效路径:
生态博物馆覆盖一定的地域范围,由选定的文化景观要素构成,阐明了事物是在原初场景中的形态、位置以及如何发生。试图解释概念、位置与过程,试图保护、储存与重构,试图动员参观者,并使其方便接触文化遗产。建立在文化与旅游互动的基础上,关心现存的状况,需要地方政府、协会、组织、公司、个人共同努力,依靠主动的志愿服务,旨在制造一个旅游者能够进入的小有名气的地区。吸引地方居民参与,创造地方认同的感知,吸引各个层次的学校与教育部门,保持与时俱进。新近的要素与特色及时纳入到短期或长期的发展规划中,旨在整体展示——兼顾一般与特殊,与地方艺术家、手工艺人、作家、行动家和音乐家保持合作。通过学术层次的研究传播,提升研究风尚,旨在阐明技术与个体、自然与文化、过去与现在、昨天与今天之间的联系。*Peter Davis, Ecomuseum: A Sense of Place. London and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19-220.
生态博物馆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对地方的表述并非是口头上或言语上的,而是一个“有所为”的行动计划。从上述生态博物馆的评量指标可以看出来,生态博物馆对地方的行动是一个整体而综合的复杂体系,如何统合各方关系来构建地方意象成为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博物馆不仅提供了感知地方的理论路径,而且还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统合了不同层次的地方感知,成为认识地方、理解地方的最佳策略。
作为浪漫主义与原始主义诗学表征的地方、地方感、在地性话语虽然是一种平衡与对抗“现代性对空间侵蚀”的努力,但是我们在建构地方的时候,仍需谨慎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地方主义的建构一般逃避不了田园乡愁的乌托邦式想象;其次,过度强调地方自治会生成交流与互动的抗拒之情;第三,过度强调地方精神与情感会造成地方感的迷思;第四,过分沉迷于地方社会的过去意识,会造成对当下的感知不足。除此之外,着眼于空间场所的地方感对于地方文化的把握是不够的,还应考虑地方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Pan Shouyong, “Local Histories and New Museological Approaches in China”, in John Gledhill(ed.), World Anthropologies in Practice: Situated Perspectives,Global Knowledge. Oxford: Bloomsbury, 2016, pp.117-130.,时刻关注地方历史,甚至是民族国家历史在地方上的发现与发明。“地方感”与“历史感”的共同体认不仅是生态博物馆介入地方的前提,也是其他“地方运动”理解地方、感知地方的关键。
[责任编辑 刁统菊]
尹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在站博士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100)。
本文受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