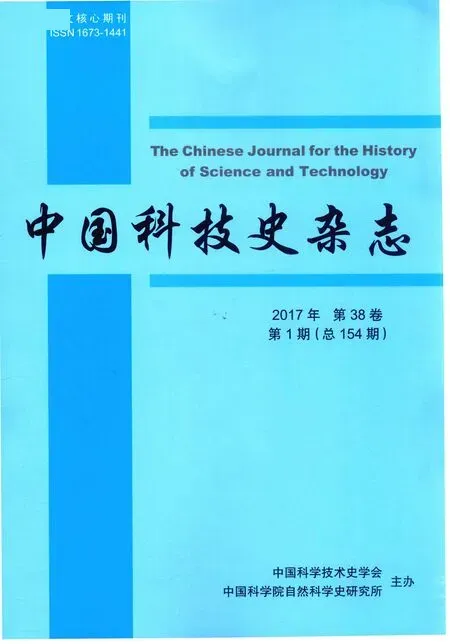民国时期的中华矿学社
范铁权 王 昕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保定 071000)
民国时期的中华矿学社
范铁权 王 昕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保定 071000)
中华矿学社是民国时期专事矿业的学术团体之一,成立于1928年。此时恰值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百废待兴之际,对于矿产的调查与研究迫在眉睫。该社秉承“联络同志,研究矿学,调查矿产,共谋中国矿业之发展”的宗旨,开展了大量活动,如发行《矿业周报》、召开常会、举办讨论会、开展矿业调查等,积极报道中国矿业消息,介绍矿学知识和开采技术。围绕中国矿业发展,中华矿学社社员阐发了其具体主张,包括倡议健全组织机构和法规、矿权国有、节制利用、改良矿工待遇等方面。中华矿学社的成立及其发展对近代中国矿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华矿学社 王德森 矿业
中华矿学社是民国时期专事矿业研究的社团组织,由王德森等人于1928年3月在南京发起成立。该社围绕中国矿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兼为农矿部提供矿业咨询。中华矿学社的成立及其发展对近代中国矿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无对中华矿学社的专门研究。本文通过对现存资料的梳理、解读,对中华矿学社作整体考察。
1 成立背景
中华矿学社的诞生,与当时中国的矿业现状密切相关。政府对矿业的关注以及有识矿人的倡议是其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
近代中国,受开采秩序混乱、技术落后、交通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矿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颁布《中华民国矿业条例》,规定矿藏为国有,允许政府、个人、外商和中外合资办矿。各军阀官僚亦积极投身实业建设,如袁世凯在启新洋灰公司等多家工矿业中拥有股权,冯国璋也拥有直隶夹山、遵化和兴隆沟三处金矿[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矿业之发展,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矿产开采秩序,强化国家监督取缔制度,为中国矿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末民初,赴欧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逐渐增多,其中不乏专攻机械工程、采矿、冶金等科者,如宾步程、谌湛溪、周则岳等。这些人归国后,大多投身工程教育事业或厂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工矿业的发展。1914年,宾步程出任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后为湖南大学之一部分)校长,他担任这一职务长达10年,为矿界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谌湛溪1909年回国后,先是奉命到各省考察矿源,后担任湖南益阳板溪锑矿总工程师、长沙华昌公司总工程师、河北唐山煤矿局局长,井陉煤矿局局长兼工程师及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等职务。1925 年,北洋大学将采矿、冶金两学门合并为采矿冶金学门。1929 年,北洋大学各学门均改称为学系,采矿冶金学门即改为矿冶工程学系[2],也为矿界输送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据统计,截至1935年,北洋大学矿冶工程学系毕业31班,共310人。按当时供职情况分,各级行政机关职员25人,大学教授14人,大学助教5人,大学职员4人,中等学校教职员33人,矿业冶炼工程单位任职者106人(任矿师或工程师者76人,矿业技师2人,冶炼工程6人,任矿局经理、总办或局长者22人),铁路公路重要职员者15人,市政部门、水利部门和公私企业单位任职者40人,留学5人,已故14人,其他15人,状况不详者34人([2],20页)。众多矿业人才的涌现,为中国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的矿业精英们意识到,制约矿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实是,民族矿业规模小、力量弱,往往遭受由列强控制的大矿业的摧残,因此“何以不团结精神,联合力量,一致向环境奋斗,而决志把一切敌人消灭呢?”“我们专习矿术者,趁此训政开始,注重建设时候应当联络起来,共谋矿业的发展。”[3]在这一背景下,各种以发展中国矿业为宗旨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如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矿学研究会等。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于1913年诞生于上海,以“联合全国矿业共图发展”为宗旨;矿学研究会于1916年由宾步程等人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出版刊物《矿业杂志》,从发行之日起,便受到众多矿人青睐。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矿学研究会的家具、印章、文件等均遭散失,许多会员也因矿业衰败纷纷转入其他行业,以致《矿业杂志》不能继续出版,于1924年10月停刊,矿学研究会亦趋于停顿。1928年3月25日原矿学研究会的部分会员黎锦曜、王德森等人在南京组织成立中华矿学社,并通过《中华矿学社章程》,同年4月呈准立案。
中华矿学社名称与矿学研究会不同,但精神原属一贯,以“联络同志,研究矿学,调查矿产,共谋中国矿业之发展”为宗旨,发行《矿业周报》。成立之初,中华矿学社租用南京大纱帽巷副10号房屋4间为社址,1928年6月迁至螺丝湾锏银巷14号,同年11月借用管家桥倪姓地皮自建房屋6间为社址。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学社之房屋不敷使用,又购得西家大塘荒地二亩四分余自建房屋,并于1935年迁入。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矿学社趋于停顿,《矿业周报》亦于1937年8月停刊。直至1944年4月12日,中华矿学社才再次被批准立案,社址位于湖南耒阳[4]。中华矿学社虽欲竭力恢复运转,但终因元气大伤,逐渐走向消亡。
2 中华矿学社概况
中华矿学社组织机构严密,学社设常务干事、编辑干事、会计干事和各地干事。常务干事负责学社具体事务,如有临时重要事件发生,由常务干事及编辑干事召集联席会议处理;编辑干事负责《矿业周报》的编辑与整理,并交由常务干事;各地干事负责学社与各地的通讯与联系。常务干事不仅负责编辑人员的聘请、《矿业周报》的出版,且负责联系各地方、矿厂的通信员,召集社员出席年会。常务干事每年改选1/3,于每年的11月30日抽签退出1人,再根据章程第七条之规定,提出3人以上为候选人,在选举票上载明。“选举票按照章程于是年12月10日分寄各社员,限于次年二月底以前寄回,以得票最多者当选。前项抽签退出之常务干事得为候选人。”[5]学社每月开常会一次(后改为半年召开一次),选举常务干事及各地干事,并讨论相关事宜。在学社召开的第一次常会上,公推王德森、黄伯逵、范柏年为常务干事,刘眉芝、熊锦耀、谭焕达为编辑干事,王德森兼庶务会计,范柏年兼理文牍事宜。会上,根据刘眉芝提议在各地推选干事:“暂推周苕青为驻汉干事,蒋石灵为驻皖干事,史维新为驻赣干事,各地干事服务细则,由常务干事起草,交常会通过。”[6]此后在历届常会上,都将推定各地干事作为一项重要社务。
中华矿学社社员,分普通社员、永久社员、赞助社员3类。社章规定,普通社员经介绍人介绍入社,每年交常年金、常年捐;“一度缴纳常年金二十五元者”[7]为永久社员,并以后永不缴纳;对学社提供过资金援助者,可为赞助社员。创社之初,学社对于社员入社的要求相对比较严格。社章规定:“凡曾受矿术教育三年以上,或曾在矿场炼厂服体力或脑力之勤务五年以上者,得由社员二人以上介绍入社。”又规定:“凡被介绍入社者由常务干事将其履历及介绍人通知各社员,自发通知之日起,如在四个月以内,各社员对其无疑义时,即为本社社员。”社员入社缴纳入社金二元,常年金二元[5]。社员入社后,若一年半未缴纳社金,即停寄周报,“两年未缈者,即不将姓名编入社员录”[7]。之后,学社逐渐放宽了入社的限制,“凡是赞成学社的主张、实际在矿场炼厂工作的矿人”[5]皆可加入。中华矿学社的社员构成大都与矿业相关,既有矿界的普通工人,也涉及煤矿的工程师、行政人员等。据1931年统计,在229个社员中服务于各地矿场者128人,服务于各矿政机关内41人,服务于本社者3人,服务于其他矿业团体者5人,经营商业者3人,服务于矿业以外机关者30人,暂时赋闲者19人[8]。
中华矿学社的经费来源主要有3项:第一项为《矿业周报》收入,包括广告费和订报费;第二项为学社收入,包括会费、常年捐、代办技术盈余、房租;第三项为上届结存、存折息金等。中华矿学社在成立之初遵循社章规定,一般不接受机关法人或非社员的捐助,但“前承农矿部司长胡博渊先生,科长彭耕先生,中兴煤矿总矿师张景光先生之捐助,应即登报鸣谢案”[9]。因缺少稳定的经费支持,租地费用、干事津贴以及报刊的印刷出版等费用令学社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地干事经纷纷建言献策,最终确立了两种方案。
其一,捐款。黄伯逵在第二次常会提议:
(甲)一次捐,不论多少,只捐一次;
(乙)常年捐,分二种,(1)认定每年捐洋若干,一次或分次缴纳,不附条件(2)认定每年捐洋若干,一次或分次缴纳,但以有相当收入为条件;
(丙)按月捐分二种:(1)按月纳捐,数目自由认定,不附条件(2)按月纳捐:“每月得薪在五十元以内者不捐,五十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二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五。”[10]
其二,中华矿学社代办各种有关矿业技术之事务,帮助各公司、企业改进技术,“如当事人愿将盈余充作经费,本社代收之作为报酬”[5]。此项规定使得学社获得了一定的经费支持。据统计:“五年之间,收入约2.1万余元,支出约2万元,截止本年五月三十一日为止,尚存银元1800余元。”[11]
1933年,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中华矿学社原有房屋不敷其用,遂决定另购地皮自建固定场所,学社再遇经济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学社推出定期广告、推销合订本方案,在《矿业周报》上刊登企业广告,“进行半载,广告应征者有北平地质调查所及中福煤矿公司,开滦矿务局则按每月增加广告费”[12],其他企业亦纷纷在该报上刊登有关矿业之消息,广告费一度成为中华矿学社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开展活动
自成立以来,中华矿学社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以下分而述之。
3.1 发行《矿业周报》
《矿业周报》前身为《矿业杂志》,1917年3月在长沙创刊,以“贡献于一般社会而改良之期,维护祖国固有之命脉”[13]为宗旨。原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主编黎锦曜。《矿业杂志》设有论说、学术、译述、调查、记录、杂俎、矿产时价等栏目,内容涵盖矿业政策、矿产调查、矿业开采、矿业机械介绍、矿石鉴定、冶炼等。杂志从发行之日起,便受到众多矿人的青睐。但受政局、经费等因素制约,《矿业杂志》于1923年10月停刊,共出版5卷69期。
中华矿学社成立后,学社发行《矿业周报》,原因为“碻信吾国矿业应有一传达最近消息之周报,遂决然创为之”[14]。《矿业周报》由常务干事负责办理,编辑人员及各地方、各矿厂通信员由常务干事在社员中聘任。中华矿学社的第一次常会上,就筹备《矿业周报》出版达成了如下决议:“(甲)四月十五日以前,由编辑干事集齐第一期创刊号稿件,交常务干事复印,以后每七日,按期交稿;(乙)由常务干事负责筹款出版。”[6]1928年4月,《矿业周报》在南京正式问世,刊物设有社务记录、新闻、矿业消息、市况、专件、矿产时价、矿场通讯等栏目。抗战全面爆发后,《矿业周报》于1937年8月停刊,共出442期。
作为中华矿学社之喉舌,《矿业周报》以报道中国矿界之消息为职责,为政府及国内外有志于此的同仁了解中国矿业搭建了平台。自发行以来,该报报道了大量有关中国矿业的消息,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以对中国矿业的现状及其面临问题的报道最为丰富。国内外有关铁、锰、锑、锡、铅、锌等矿藏的开采、产量、经营、运输、贸易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也屡屡见诸该刊。该刊于各地、各矿派干事通讯员,及时搜集各省日报及其它刊物的信息。学社还随时派员前赴各矿开展矿产调查与地质调查,调查报告刊登在《矿业周报》上。关于矿业生产之支柱——矿工亦是该报关注的重点,中华矿学社希冀通过对矿工生活的如实报道,督促政府改善矿工的待遇,谋求矿政的廉洁:
本报出版以来,为文以吊矿人之死于地中者屡矣。前期方吊烟台煤矿之死者,此帝国主义主义铁蹄下之矿人也,本期又吊北票煤矿之三百余人。夫北票官商合办之矿也,然则死于帝国主义者,死于官,死于商,动辄得死,矿人之死,诚轻于鸿毛矣。呜呼!!!民命微贱,矿人由烈,谁实恤之,天青日白。[15]
《矿业周报》以传达矿界第一消息为职责,发行一年便深受民众青睐,有报道提及:“订购本报者,较一岁时增加百分之十八,而社员与交换之发行数,均有增加。”[14]“非社员而订阅本报者亦加多,本报汇订之第一二三集之销路亦加多,是中华矿学社之意思传达日广,而吾国矿界消息之交换亦日繁也。”[16]由此可见,该刊充分发挥出其联结纽带的作用,藉此团结了一大批矿界同人,亦使矿业观念在民众心中逐渐生根发芽。
3.2 召开常会
尽管时局动荡,条件艰苦,但中华矿学社坚持每年召开常务会议,其内容大致分为四部分:1.事务,包括推定各地干事及通讯员、改选常务干事、派社员赴各地调查矿产;2.周报,包括周报编辑的任命、周报的发行状况以及周报合订本的状况;3.收支,主要报告周报的发行费用、广告费收入以及该社的收支情况;4.社员,主要报告该社的社员人数与基本情况,如新入社之社员的介绍以及死亡社员之人数、社员姓名地址录等情况。
中华矿学社成立之初,每月开常会一次,1928年4—6月间共召开了三次常会。在第三次常会上,常务干事提出:“近来社员日增,多散居各地,在京者甚少,以后每月常会,应否变更办理案?”[17]经与会者决议,常会改为每半年举行一次,社务情形、出纳状况由常务干事按月报告各社员。如有临时重要事件发生,由常务干事及编辑干事联席会议处理。采用新章程后,中华矿学社每半年召开一次常会,共召开了18届常会。中华矿学社历届常会大体情况见表1。

表1 中华矿学社历届年会情况一览*表1根据《矿业周报》历年“社务报告”统计制成。

续表1
随着各项社务的不断开展以及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华矿学社亦逐渐步入正轨。在该社的第一次常会上,补选王德森、黄逢源、范柏年为常务干事,即第一届常务干事,此后的历届干事均由选举产生;常务干事每年改选1/3。历届常务干事选举情况见表2。

表2 历届常务干事选举情况一览*表2根据《矿业周报》历年“社务报告”统计制成。
中华矿学社定期召开常务会议,是该社得以维持10年之久的重要因素之一。召开常务会议不仅处理了该社的社务,如干事的选举任命、周报的发行状况等,亦使得矿界同人齐聚一起,交流各地矿产情况,互通有无,从而对我国各地的矿业概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3.3 举办讨论会
中华矿学社还曾举办讨论会,讨论中国矿业问题。1929年4月22日,该社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场地举办第一次讨论会,张福铨、谌湛溪、杨国劲、张光嗣、刘眉芝等20余人参加,黄伯逵主持。在讨论会上,社员刘眉芝提出,我国矿业应由政府用国家资本来经营,还是奖励人民投资?并提出“实业建国与国家资本”的题目供与会社员讨论。谌湛溪、杨柳溪、张福铨、李琦伯、范伯年、熊锦耀等先后发言,“历三时之久”[18]。4月29日,中华矿学社召开了第二次讨论会,会上继续围绕上次议题展开讨论。首先,谌湛溪“申言应如何运用国家资本谋中国之实业独立(自产自销)而达到实业建国的目的”[18],社员们亦纷纷发表看法。主席提议各社员以书面形式详述个人意见,在《矿业周报》上发表。讨论会最后,谌湛溪提出下次讨论会之主题为“中国锰矿业”,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不难看出,这些议题在当时亟为迫切,颇具现实性。与会者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3.4 实地调查
中华矿学社积极组织社员进行实地调查。1928年11—12月从农矿部领到200洋元,于次年1月派王德森赴山西平定阳泉及河南中原公司调查煤铁矿产。1929年3—5月共领到300洋元,即于5月派王德森赴江西丰城、进贤一带调查煤矿[19]。除此之外,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孟宪民,由学社派往湖南、广西调查地质矿产;任湖北建设厅技师多年的王德森,亦奉命调查鄂西矿业。孙越崎赴陕西调查延长石油矿及韩城煤田;范柏年调查湖南永兴煤田;董伦、赵天从奉命调查胶济路沿线矿业,等等。以上社员之调查进程及其调查报告在《矿业周报》上予以登载。
王德森对山西阳泉调查阳泉保晋公司第二矿厂进行调查,报告详述煤层、煤质、煤量、采煤方法、选煤、运煤、地面设备等方面。他还调查了工人的待遇:“平定各矿刨煤均用包工法,由领岔者招领工人六七名至四十名不等,大概视煤层之好坏而定。……大概每日除吃饭照油之外每名能得三角上下。领岔者得十五元上下。打石工人亦系包工制,每打进青石一尺给洋八元,沙石六元,白滓五元八角,黑滓五元一角。”[20]《矿业周报》1929年第50期登载了王德森赴江西丰城煤田的调查报告,内容包括煤田位置、地形、地质,以及煤田所包含各矿的基本情况。经勘察得知,该地“煤层共有九层,而可供开采者仅二层……兹假定本区内,可采之煤层面积占一半,即六百万里,煤层平均厚度六尺,则可采之煤应占三万六千万吨”[21]。煤量之丰,由此可见一斑。但该处煤田大部分矿厂均系土法开采,自然通风,开采状况不佳,“故所产之煤除供烧锅外,无多出售” “盖丰城附近,从未有一较新式之矿,所取煤层只合家用”([21],15页)。王德森的此次调查,以其专业的采矿知识,调查清楚了该煤矿的产煤量,得出该矿煤炭“只合家用”“无多出售”的结论。刘文曜在调查四川彭县白水河煤矿后提出了专业的开采建议,该地“山势雄厚,煤层尚多,以外面露头考之,似在六七层以上。若在山麓顶开一直井,可透任何煤层。再从井底打一平巷,出山脚,则各层所采之煤,均可由直井堕下,运输甚为便利,水亦将顺势下流,无需排水设备。于采掘成本,可减至极低。惟矿处山中,运输至为困难,宜架高线路至宝兴场,方可解决。”[22]这些工作为当地政府制定合理的开采计划和相应的矿业保护法规提供了参考。
3.5 参与抗日救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形势危急。汪精卫于1931年12月10日通电全国,发起国民救国会议,希望各团体代表参加。中华矿学社对此深表赞同,积极复电,并通知学社社员及各常务干事推选代表参加。学社亦向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发布通电,号召大家自救,电文中频频出现“倭奴横逆,人天共愤,合群御侮,急在眉睫,窃念外交急迫,国事日非”[23]等语。进而,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文章登载于《矿业周报》上,反映了中华矿学社坚决抗日的鲜明立场。如《本社为铁锰对日输出宣言》一文痛批日军对我国同胞的杀戮,建议禁止对日输出铁和锰:“飞机、军舰、重炮、坦克车、枪弹,这些残杀我国同胞的利器,含了我国供给多少万吨的铁和锰!东北三省的土地,已死同胞们的血,成为供给日帝国主义者制造军器的代价。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铁锰对日输出,并不因领土丧失同胞牺牲而受阻止。本社从矿人的立场说:要救国,要民族独立生存,最低限度,从今日起,不能有一吨铁砂及锰砂输给日本帝国主义者。”[24]《对日经济绝交与原料之供给》《日帝国主义操纵北方煤田之大阴谋》《评日人对东三省之矿业》等反日文章也陆续见诸报端,显示了该社抗日救国的决心。
4 主张
作为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的平台,《矿业周报》登载了数量可观的文章,探讨中国矿业之发展。其主张之荦荦大者,可分述于次:
4.1 倡议健全组织机构和法规
矿业之发展关乎国家命脉,其发展迫在眉睫。如何发展中国矿业?中华矿学社的广大社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署名“孑”的社员撰文主张“设中央矿务局以办国营矿业,废止一切征收矿税机关,矿税直接交农矿部,违者严惩之,至没收其全部财产”[25],从而使整个调查、设计、统计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刘眉芝提出,国营矿业应技术化,“而不宜稍染官场气习。求国营矿业之进展者,由宜注意及此”[26]。无规矩不成方圆,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有鉴于此,中华矿学社社员主张工矿必须及时改革,具体来说:“一、颁布整理工矿条例,一切国有省有地方公有各矿,由中央设立整理工矿委员会整理之。二、聘任富于经验学识之矿冶专家为整理委员逐矿调查,详细计划,责成当事者,切实奉行,并随时派员查察,不遵照者,严惩之。三、规定各项表册,限期填报,严予勾稽。四、组织矿厂职工委员会,准其共同监察。五、事务工程,概用专门人才,使全体技能化。”[27]该社主张“未归私营之矿,概归公营”[28],允许民间私营之矿,但应予以整顿,归农矿部监管,并征收适当的税率,一般开采期为10年。
4.2 矿权国有
近代中国受列强侵略已久,一些矿藏的勘探、开采等权力长期为外人控制。中华矿学社的社员多为矿界精英,对此有着深切的认识。为使政府当局以及各界人士认识到矿权国有的重要性,该社亦作了详细陈述:“首先,凡浩大事业,据财政学道理,应由国家经营,已成商矿,其退出之外股,人民无力补充,自当乞援于国家资本,且与各国废约、矿权收回后,各矿区理应为国家所有;第二,时值裁兵之时,运用国家资本,可以安置数十万所裁之兵,使其消纳于开垦辟矿之途;第三,又时值反日运动高涨之时,如能运用国家资本大规模开发江浙皖赣一带之煤,借水路运输之便,减轻成本,可以达到抵制日煤之功效。”[29]
广大社员借助《矿业周报》将矿权国有的主张传达给各界民众,唤起民众对矿权国有重要性的认识。谌湛溪在《矿业周报》的创刊号上曾言:“欲振实业于产业私有制度下,是与大道背驰也,是奋强弩之末也。”[30]署名“孺子”的社员在《日本经济侵略下之我国钢铁业》一文中提出,矿权国有分收回、整理、扩充三步进行[31]。署名为“轶”的社员撰文申明:“中国经营钢铁事业,现只有汉阳铁厂与本溪湖铁厂,其资本又多为日本所占有。为国家谋公共利益计,开采铁矿之权,当属之国有。”[32]“萍”在其文章中指出:“利用我贱价之铁砂、制造彼昂价之钢铁、厚利归人,损失在我……倘政府毅然宣布铁矿国有、急起直追,组设钢铁厂,自采自炼,操纵自如。日钢涨价,与我何有。”[33]“如柴”在文章中主张锰矿国有,在他看来中国产锰之省皆与日本有密切关系:
其侵略之法:非华人为之傀儡,代取矿权,即华人为之债奴,供其绞榨。于是全国之所出,即日人所入:地在中国,而利在日本:不啻日本借中国之地置其锰!夫钢铁者立国之基础,锰者炼钢之要素。中国之铁量不丰,日人已掠其十之久二;锰量其薄,日人则几掠其全额。国且不立矣,何发展推广之足云?[34]
在“孑”看来,钨矿也需要收归国有:“吾国之钨,能以最低产费,供给全世界而有余,故如统归于一机关以调节产额及输出,实能全世界钨业,钨产于赣粤湘三省连界之廿余县中,他省如河北湖北尚有零星产地,故欲统一钨业,非国营不可为功。”[35]中华矿学社社员主张将铁、锰、钨等矿权收归国有,以为立国基础。1927年1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与日本沆瀣一气,在上海签订借款合同,导致公司的多项权力为日人所控制,逐渐沦为单一对日供矿机构。矿界人士对此痛心不已,极力呼吁将矿权收归国有。1927年3月,武汉政府交通部成立了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负责该公司一切整理事宜。在舆论压力下,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1927年6月11日第三次会议议决接管汉冶萍厂矿,“全部实行整理”[36],于同年12月命技佐黄伯逵驰赴大冶铁矿,调查工人及一切情形。但大冶厂矿对黄伯逵态度冷淡,日方更是强烈抗议,并以武力相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交通部发出命令撤回黄伯逵,对“接管”事宜一拖再拖。1928年3月底,中华矿学社就矿产国有问题呈文农矿部,之后又与农矿部矿业司长胡博渊、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就此事反复沟通,晓以利害,敦促政府将矿权收归国有。
4.3 节制利用
矿藏为大自然赠予之产物,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资源。该社主张节制利用矿藏资源。社员“孑姜”撰文指出:
吾国铁矿蕴藏非丰,而建设需用钢铁至多,人口四倍于美,若岁用钢铁照美人所用数计,已知可估之矿量,约足支十年,故非关正用,盖藏不能浪启。不制钢铁而采矿砂出售,雇主只一倭邻,事之专者易为制,理至显也。然则铁矿将不开乎?曰,不然。是在统筹全国建设者,先计钢之需要,再及制铁,方及采矿可也。[37]
锰藏开采也应统计所需,再及开采,“制钢必始于自给,钢之计定,方及制铁以应制钢之需,而采铁矿采锰随之,如不由此道而采铁锰矿,自耗天产以壮他人,是循出生而入死之路也”[38]。《矿业周报》1929年73号的“编辑者言”一栏中,署名“立薛”的社员也提出,应“先计钢之需要,再及制铁,方及采矿。盖自采自用,则他人无如我何”[39]。这一主张与矿产国营实为一体共生,此举可防止我国矿产流入别国,从而有力地保护我国矿产资源。
4.4 呼吁改善矿工待遇
许多矿场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无视矿工诉求,矿工工作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生活待遇差,矿工罢工事件多有发生。中华矿学社对各地矿场开展调查,在《矿业周报》上大量登载各地矿工的生活状况,以期通过舆论压力引起当局者以及矿厂负责人对矿工生活的关注。如在260号中载,湖南、常宁、西宁墟钨矿工人每日工资约为0.4元[40];在北平门头沟煤矿,矿工最小的14岁,最长者50余岁,且“下窑的道路极陡,空身上下,尚觉吃力,何况背上更有六七十斤的煤块的负担?牛马生活,亦胜此多多,所以矿工没有一个不是面目青绿,神情呆滞,骤视之,已非人间的动物了”[41]。众多矿区实行包工制,如“平定各矿刨煤均用包工法,由领岔者招领工人六七名至四十名不等,大概每日除吃饭照油之外每名能得三角上下,领岔者(包工头)得十五元上下”[20]。包工头与普通工人工资差异之大,令人诧异。基于此,中华矿学社呼吁废除包工制,提高矿工工资待遇,改善工人的生活。黄伯逵撰文表达了要求废除包工制的决心:
开滦工人呻吟于包工制之下已迭志本报,工会亦曾一再要求,无如矿方员司与包工者勾结甚深,狼狈为奸,力谋保留,开工会一俟组织健全,将再提出取消包工制之要求,不达目的不止云。[42]
1932年,中华矿学社函邀全国各矿业团体,发起组织全国矿人公会,以“联合全国矿人,发展吾国矿案,改进矿人生活,共谋国利民福”为宗旨。启事及章程草案刊登在《矿业周报》第174号上,得到各矿业团体的积极响应。该社提出改善矿工生活的主张,符合矿工之心声,这些舆论迫使一些矿场改善了矿工待遇。
5 结语
作为民国时期专事于矿业的社团,中华矿学社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学社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成绩斐然。学社创办的《矿业周报》刊载了大量的矿业信息,促进了矿业的信息交流,通过报刊,促进了矿界同人的交流,对推进中国矿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矿学社组织社员进行实地调查,探查中国矿产储量及分布,唤起了国人对于矿权重要性的认识,为各地矿业发展提供了诸多专业意见;
其二,与政府关系密切。学社的许多社员在国民政府各部门中任职,如王野白曾是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的“三块王牌”之一,曾任萍乡煤矿整理局整理专员、资源委员会湘南矿务局局长等职;谌湛溪曾任农矿部行政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参与了多项矿业制度法规的制定。正是得益于这一关系网络,中华矿学社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大多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学社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也往往能引起政府的重视。
其三,在中华矿学社的影响下,许多关心中国矿业的机构、组织蓬勃兴起,促发了政府和更多的有识之士持续关注中国矿业,从而推动了中国矿业之发展。
可以说,作为民间社团组织,中华矿学社在经费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开展了大量活动,并就中国矿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其史绩和地位应予以客观而充分的评价。
1 史全生. 近代中国转型与社会思潮[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43.
2 张明, 潜伟. 北洋大学矿冶学科的创建、建设与启示[J].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11,(6): 17.
3 发刊词[J]. 矿业周报, 1929,(1—24): 20.
4 蔡鸿源, 徐友春. 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M]. 安徽: 黄山书社, 2012. 84.
5 中华矿学社章程草案[J]. 矿业周报, 1929,(1—24): 427.
6 本社第一次常会记[J]. 矿业周报, 1929,(1—24): 42—43.
7 中华矿学社会金细则[J]. 矿业周报, 1930,(92).
8 社务记录[J]. 矿业周报, 1931,(144): 9—11.
9 第六次干事联席会议[J]. 矿业周报, 1929,(1—24): 423—424.
10 本社第二次常会记[J]. 矿业周报, 1929,(1—24): 92.
11 陆. 五年来之中华矿学社[J]. 矿业周报, 1933,(241): 4—9.
12 本社新屋建筑经过及账目[J]. 矿业周报, 1935,(354): 14—17.
13 达夫. 发刊词[J]. 矿业杂志, 1917,1(1): 1.
14 孑姜. 敬告读本报者与吾国矿界[J]. 矿业周报, 1929,(72): 2.
15 厂. 矿人之死轻于鸿毛[J]. 矿业周报, 1929,(25—48): 168.
16 本报之未来[J]. 矿业周报, 1929,(96): 2.
17 本社第三次常会记录[J]. 矿业周报, 1929,(1—24): 143—144.
18 社务记录: 举行两次讨论会[J]. 矿业周报, 1929,(1—24): 76.
19 社务报告[J]. 矿业周报, 1929,(25—48): 407—410.
20 王德森. 阳泉保晋公司第二矿厂调查[J]. 矿业周报, 1929,(25—48): 168—172.
21 王德森. 江西丰城煤田调查报告[J]. 矿业周报, 1929,(50): 8.
22 刘文曜. 四川彭县白水河煤矿调查报告[J]. 矿业周报, 1937,(420): 9—13.
23 蒋. 本社参加国民救国会议之删电[J]. 矿业周报, 1931,(170): 2.
24 本社为铁锰对日输出宣言[J]. 矿业周报, 1933,(224): 2—4.
25 孑. 矿官与矿业[J]. 矿业周报, 1929,(1—24): 174—175.
26 芝. 国营矿业宜技术化[J]. 矿业周报, 1929,(53): 4.
27 整理工矿[J]. 矿业周报, 1929,(1—24): 145—146.
28 厂. 矿法问题[J]. 矿业周报, 1929,(25—48): 219.
29 专件. 本社向五次全会的请愿[J]. 矿业周报, 1929,(1—24): 192—195.
30 諶湛溪. 创设国业委员会说帖[J]. 矿业周报, 1929,(1—24): 26—28.
31 孺子. 日本经济侵略下之我国钢铁业[J]. 矿业周报, 1929,(1—24): 115—116.
32 矿业与建设[J]. 矿业周报, 1929,(1—24): 23—24.
33 萍. 日钢涨价[J]. 矿业周报, 1929,(1—24): 211—212.
34 如柴. 锰矿国有[J]. 矿业周报, 1929,(1—24): 282—283.
35 孑. 钨业国营[J]. 矿业周报, 1929,(68): 2.
36 胡政, 张后铨. 汉冶萍公司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389.
37 孑姜. 先冶后采[J]. 矿业周报, 1929,(64): 2.
38 孑芝. 出生入死[J]. 矿业周报, 1929,(74): 2.
39 立薛. 钢铁独立自给[J]. 矿业周报, 1929,(73): 2.
40 冼荣熙. 赣南钨矿视察记[J]. 矿业周报, 1933,(260): 7—16.
41 北平门头沟煤矿矿工生活状况[J]. 矿业周报, 1933,(262): 4—5.
42 伯逵. 开滦包工制有取消倾向[J]. 矿业周报, 1932,(174): 4.
ChineseMiningSocietyintheRepublicofChinaEra
FAN Tiequan WANG Xin
(DepartmentofHistory,HebeiUniversity,Baoding071000,China)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minerals were crucial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 new found country. Established in 1928, Chinese Mining Society was one of the specialized academic groups in mining indust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By the principal of “Connecting comrades, studying mineralogy, investigating minerals, and striv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ining industry”, the society carried out a number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publishingMiningWeekly, Convening regular meetings and symposium, lunching mining surveys,etc., to report mining news and introduce mineralogy knowledge and mining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ning industry, the society members explicated some concrete proposition, such as advoc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s, nationalizing the ownership of the minerals, limitedly utilizing the mineral resources, ameliorating miner’s treatmen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ning Societ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modern Chinese mining industr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Mining Society, Wang Desen, minerals
2016- 11- 04;
:2017- 02- 11
范铁权,男,1974年生,河北滦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王昕,女,1993年生,山西晋中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Email:fantiequan@163.com。
N092
A
1673- 1441(2017)01- 0025- 12
——《外国语学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