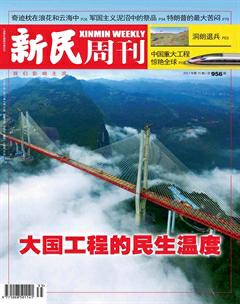花式嘲讽评论者指南
万川
本雅明曾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构成的书,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头马笔下塑造的迷宫正是对本雅明“引文”理论的一次实践。
“评论从来就是模仿。”
在此书的第247页,我再次陡然感受到街角处迎面撞上来的嘲讽气息,先是一慌,然后释然:“还好我不是一个评论家,我只是一个微小的读者,嗯。”我花了三个并不连续的晚上读完全书,然后第一个冒出来的疑问是:“大头马是男的女的?”我拿着问题去问朋友,得到的答案是:这不重要。我转头想了想,是啊,的确不重要。
大头马的这本小说,着实技巧华丽,语言这玩意儿在他手上像转笔那样自在随意。为什么大头马是男是女不重要呢?套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就是:他死了。大头马在《一块丽兹饭店那么大的沉香》中说:“但凡上过文学理论的课,应该都能够明白这个小把戏是什么。”侥幸有几节文论课没睡着,使得我此刻能够稍稍揣测一下这个小把戏。这个小把戏,就是罗兰·巴特说的“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说,文本概念的诞生宣告了作者的死亡。这种死亡并非指作者不存在了,而是作者隐蔽了。在大头马的这本小说里,从《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到《评论指南》一共八篇,每一篇他都用不同的语言将自己遮蔽起来,就像推理小说中提到的反侦查秘诀一样:把一棵树藏在森林里。大头马把自己隐藏在诸多作家的语言森林中,包括马尔克斯、塞林格、索尔·贝娄、赫胥黎等。而这一“隐藏”方式又指向了一个更庞大的迷宫——一座博尔赫斯式的花园。本雅明曾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构成的书,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头马笔下塑造的迷宫正是对本雅明“引文”理論的一次实践,只不过他的引文是诸多过往写作者的声音。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大头马营造的这一语言迷宫,并非像本雅明那样出于某种写作上的雄心壮志,更多的反而可能是一种游戏心态(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大头马创造了一个《盗梦空间》般的多维的、复杂的叙述空间。同时在这一空间中,又安插了“如何写小说”这一命题,使得小说与现实的边界越发地模糊起来。这一“小把戏”安德烈·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也玩过,并称之为“纹心”。在大头马笔下,一会儿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一会儿是写两个人爱情故事的作者,一会儿又是写作者的作者,仿佛在八门金锁阵中生门入景门出,来来回回,闲庭信步;又如古装电影拍摄现场,“Action!”“卡!”循环往复,导演端坐一旁,隐隐有穿越之感。
从结构上来看,这本小说真的是八个短篇组成的吗?并不是。其实每篇文本都切实关联着另一文本,或隐或现,用老话说就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各种语言上的小把戏,就像这棵树上的果实,在枝丫间相互交错,撑起整个文本里巨大的叙事空间。正如大头马在文本中说的那样:“你可以把这些短篇视为一个长篇的若干碎片,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而这一切都将评论者引入早已挖好的文本陷阱。
除了用语言的森林来设置障碍、用多维的叙事来模糊空间、用戏谑的口吻来诱导方向,大头马在最后一章《评论指南》中更是一本正经地创立“评论学”这一冷门学科,煞有介事地介绍学科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理论方法。大头马头头是道,说得有鼻子有眼,过于真实,以至于你能隐约察觉到它其实并不真实。而这恰是对评论的一种反讽。就像文本中男主说的那样:“光背定式没用。”
这种嘲讽很难说是善意的还是不善意的,因为这仅仅是一场文本游戏。只不过你面对的是一个博览闲书、智商感人、转笔娴熟,同时又极具演员天赋的“顽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聆听嘲讽,并赞美、享受着迷宫的精致。而在这一刻,你将必须从评论者沦为一位卑微的读者。endprint
——小学中低段音乐妙趣课堂活动设计策略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