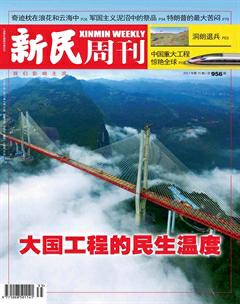二十二,让我们的眼泪和热血,拥有相同的温度
孔冰欣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影片中的老人们半生风波恶、半生逐水流,但她们仍能微笑,仍能呈现一派“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淡然。她们正是“活着”本身最好的代言人,苦水往回倒,总得向前看。
《二十二》公映了,可是句号并没画上,留下了一串省略号。
“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只要命长,穷不讲了。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看,没有吃(就)慢慢来。”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今年的这一天,由郭柯执导、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正式在全国公映。
《二十二》延续了“前作”《三十二》的思想脉络,仍旧讲述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的故事。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至少有20萬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而郭柯在2012年刚接触“慰安妇”题材时,中国内地仅余32位幸存者,当时拍成的片子,便定名为《三十二》。2014年,郭柯再次深入“慰安妇”世界,却发现只有22位老人在世了,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叫作《二十二》。
就在影片上映前的8月12日,海南老人黄有良在陵水家中离世,享年90岁——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三十二、二十二……这个数字,最终会变成零。
当我们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影片中的老人们半生风波恶、半生逐水流,但她们仍能微笑,仍能呈现一派“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淡然。她们正是“活着”本身最好的代言人,苦水往回倒,总得向前看。
可是,作为观众的我们,不该忘记历史;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克制
《二十二》通篇可以说都很克制。
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林爱兰,如今瘦弱的身躯深深陷在了椅子里,腿也抬不起来。她日复一日用干枯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啊,收养的儿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
毛银梅老人则是韩裔“慰安妇”,原名朴车顺。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如今说得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
此类题材的纪录片很难把握——若不够悲凉,或控诉乏力;倘过于激昂,又恐打破老人晚年生活的平静。郭柯选择了更为克制的视角:大段的日常生活镜头,看不见历史的“腥风血雨、凄风苦雨”,听不见撕心裂肺的哭喊咆哮——这样处理,被一些爱之深、责之切的议论评价为“起意值得尊敬!内容清汤寡水,主线、逻辑、气韵朦朦胧胧”。
片中,毛银梅老人把“拿个杯子”听错成“拿被子”,一边嘟囔着“拿不动啊”,尔后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院里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林爱兰老人的房间里挂着一把把的菜刀、水果刀、镰刀;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曾被有些媒体解读为:老人惨被日军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依旧被仇恨笼罩,家里的刀统统是用来砍“鬼子”的。
实际上,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逼仄的小房间里,蚂蚁、老鼠是“访客”。之所以挂那么多刀,“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颤巍巍的林爱兰认真地告诉导演。
机器默默转着,海南的炎夏、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镜头切换,随时光流逝。
这是一群很真的老人,在摄制组的眼里,她们还是一群很可爱的老人。
郭柯说,第一次去看“慰安妇”韦绍兰老人的时候,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给了她500元零用钱。当时我们是四个人去看她,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她让我坐在她身边,从衣服里掏出来四个红包,说你们四个是一起来的,要过年了,你们拿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我打开时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
摄制组也喜欢毛银梅老人院里的栀子花,老人就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毛银梅拍拍对方的身子,让他微微蹲下,然后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衣服的口袋上,站到一边“嘿嘿”笑。
拍摄林爱兰时的小插曲颇令人忍俊不禁: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着急得不行,告诉摄制组村民阿憨把奖章偷走了,而阿憨否认了指控。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以及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是假的。总之,觉得自己“闹乌龙”的林爱兰羞涩地笑了,如同少女,还不好意思似的躲着镜头。
这群“慰安妇”,就好像中国大地随处可见的那种老祖母,她们会美滋滋地做午饭,在锅里搅动,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会半坐在床上全神贯注地看86版《西游记》,开心地笑;会温情脉脉地唱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桔梗谣》……
最猝不及防的,是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的讲述。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其购置药物、营养品。
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看,本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流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
隐痛endprint
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其实,观众和导演的感觉大体差不多罢。这些“地母”一般包容沧海的老人们,也给我们,好好上了一堂关于人生的课程。
伤口仍然隐隐作疼,相互熟悉交心后,那些潜藏在岁月里的隐痛会慢慢浮露出来。不是不苦,不是不哭,只不过,若想更放松地活下去,就不能常常撕开、舔舐疤痕。
毛银梅将“慰安妇”身份瞒了50余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不为人知的往事。
林爱兰说到母亲,开始抑制不住地抽泣。她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妈妈被日本人抓住,绑起来扔进了河里;不久,她本人即堕入了噩梦般的“地狱”。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了,她“没有讲实话”。“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
某天,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老人倚在炕上发呆。摄制组见状,留下两个“关键人物”,清场完毕,等待老人自愿倾诉。许久,老人小声问,门都关好了吗?
门关好了。于是,李爱连哭着回忆,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当年18岁的姑娘拼命吃,胃里火辣辣,嘴没停。后来,落下了胃病——这段蘸着血泪的回忆,终究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
经历最传奇的,是韦绍兰老人。她1944年被日军掳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离返家,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妻子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韦绍兰试过喝药自杀,被抢救。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泪往心里流”。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还是被生了下来,长大,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即便女方愿意,她们家里人也不愿意。从小到大,他常被指指点点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这个“日本人”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嚷嚷“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对未来没什么期待,只希望临死之际“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
倘使昔年的心魔孽障尚能勘破,那么若干“慰安妇”幸存者的亲人更像是穿肠刺骨的劫。比如有位拒绝拍摄的老人理由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子女不再赡养我了。”比如还有老人哭诉,每回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就会被儿子“搜刮”走。比如海南另有位“慰安妇”在破屋里卧床不起——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就在旁边,是摄制组人员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推着她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任何戰争/革命中,或许死去最多的,是男人;但是受伤最深的,是女人。
记录
2013年底,《三十二》陆续在国内外电影节中展映,获得不少好评。
郭柯因此片获得很多鼓励,却认为自己任重道远。2014年起,他又开始不断走访国内“慰安妇”幸存老人,带领摄制组历时4年,横跨国内5个省份29个地区,完成了纪录片《二十二》。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公映许可证。2017年7月,影片在国内部分城市点映,总计有32099名热心民众众筹观看该片。
去年4月,郭柯将《三十二》的原版拷贝及海报捐赠给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他表示:“这里是《三十二》的最好归宿,希望将来全世界更多关注历史,关注‘慰安妇题材的朋友能看到纪录片,看到这些老人当时的心境和生活。”去年世界“慰安妇”纪念日(8月14日),郭柯又将《二十二》的原版拷贝捐赠给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二十二》公映了,可是句号并没画上,留下了一串省略号。
纪录片不比商业片,经济效益一般达不到什么高度。郭柯也无意通过镜头渲染悲情,更不会消费幸存者,只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他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他的态度将是今后发展的基础。
郭柯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几十个,以便多寻找一些出口。而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记得,在某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影,之后感慨:“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纪录片,没有一味指责,反能促使我们自己回想、沉思,这些老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看过《二十二》的日本导演和民众,说得最多的是“谢谢”。
郭柯希望,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如果一部片子全是愤怒、责备、说教,你让人看啥?老人能活到现在,说明了一切。”
告别亦无可避免。《二十二》以葬礼开场,以葬礼结束。“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了。”郭柯说。
然而,在“慰安妇”幸存者生命的倒计时,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同时,让那些被历史绑架的人,和主动肩负起历史的人,一起站到台前。这样“竭尽所能”的电影出现在院线,是一种胜利。
当众筹成功,张歆艺资助,冯小刚微博“吆喝”;当主流媒体、公号网络甘当“自来水”,甚至还有朋友宁愿出钱邀人观影;当观众被《三十二》《二十二》感染,发弹幕力挺罗善学“你是中国人”、“你是我们的同胞”;当影片票房破亿,网上纪念品义卖数小时内被抢空……
这,又是一种胜利。
永恒的“人性文明”,指引人类螺旋式上升。让我们的眼泪,和我们的热血,拥有相同的温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