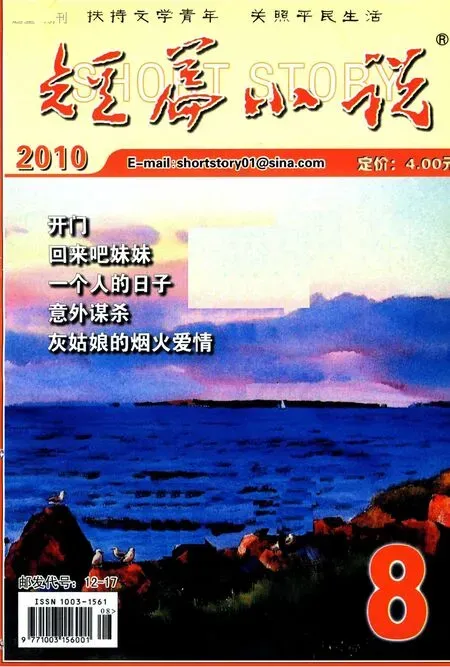孤单
◎叶凉初
孤单
◎叶凉初
叶凉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业余写作十年,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有多个短篇小说发表在《雨花》《青春》《作品》等杂志,是多家中文网站的签约作家。

老江的葬礼上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之所以说他特别,首先是因为他的衣着打扮,然后,他在这个阴沉沉的冬日午后居然戴了一副墨镜,头上那顶压得低低的皮帽子也颇引人注目。这个男人身材高大,一袭藏青色长身羊绒大衣,应该已经有点年纪,他笔直地站着,面容悲慽,不说话,有一种威严感。
老江如愿埋在他厮守了一辈子的后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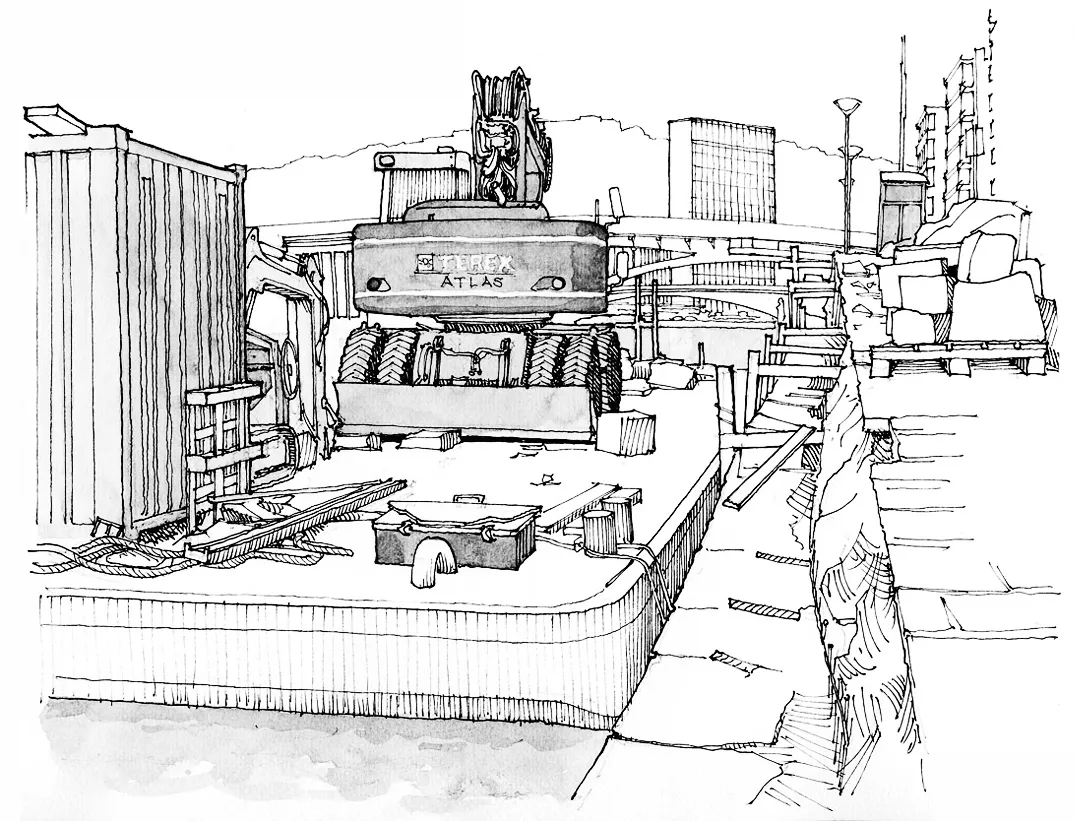
像许多江南小村一样,星湾村背山面水,风景秀丽,后山上夹种着各种果树与茶树,一年四季里瓜果飘香,能在此安葬,是老江的心愿。大家遗憾的是,老江走得太早了,他才刚过六十,这才刚刚到了人生的收获期。
最不能接受现实的是老江的女儿江小娅。三个月前的国庆节,她回家时,老江还在前面的湖里捕了鱼,在后山上摘了橘子,为她忙得像一只幸福的陀螺,可三天前她被电话叫回来时,面对的是父亲冰冷的尸体。邻居告诉小娅,父亲死在后山上,他在山上修剪树枝,不慎从树上掉了下来,是他们家的大黄狗下山来找人的。等大家上去找到老江,他已经气绝。不过,老江看上去安详平和。奇怪的是,他穿着的竟不是平日做农活的衣服,相反是一身崭新的中山装,一双黑色布鞋也是簇新的,更奇怪的是,连接近鞋底的白色沿边也干干净净,没有沾上一丝泥土。
江小娅已经晕厥过去一次,村里的赤脚医生江梅在给她挂水,她神色憔悴地坐在一把吚呀作响的破竹椅子上。突然,她呆滞的目光有了焦点,她抬起头来,四下里寻找,很快失望地低下了头。那个戴墨镜的男人不知道何时已经消失了,他没有和大伙一样留下来吃饭,他走得很快,显然,他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陌生的,除了老江。可是,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干的人,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是的,江小娅认为他应该是父亲生前的朋友。父亲一生的最巅峰不过是做过村里的临时会计,而刚刚离开的那个男人,显然不属于星湾村、星湾镇,他应该来自更遥远时尚的大地方。
老江的手机就放在江小娅的手边,如果她想解开这个谜,也许手机是最好的办法,但这会儿她没有那个精神,她整个人都陷于一种麻木中,痛苦和悲伤似乎也不确切,应该是一种绝望吧,对父亲千呼万唤也不见回音的绝望,这个屋子再也不会出现父亲的身影的绝望。她突然发现,一向井井有条的院子有些芜杂和荒凉,这不是这几天的忙乱造成的,而是更长时间里的缺乏打理。可是在父亲,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是多么细致整洁的一个人,连劈柴都堆得一溜齐的人,却把整个院子都荒芜了。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独自躺在冰冷的后山上,后山的风,越过湖面,寒凉刺骨。江小娅的心就像被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揪住,无法动弹。她以为父亲就像家门前的湖泊、家后面的山陵一样坚实永恒地存在,可是不,他绝决突然地消失了,甚至没有给她这个唯一的女儿留下一句话。
次日早上,本是江小娅一家回城的日子,她起了个大早,去了后山。按老规矩,一个人最后离开的地方,才是他的灵魂长久停留的地方,江小娅想单独和父亲去告别,或许,他的灵魂还在那儿,等着她。小娅小的时候顽劣如男儿,爬树下湖都是家常便饭,她爬上过后山最高的树,清楚地看到湖对面的风景,她难以想象,父亲居然会从一棵树上掉下来,就此离开。
冬日的后山是荒凉的,因此视野要比别的季节好,只有一丛丛茶树,仍然隐忍地绿着,仿佛在为不远处的春天养精蓄锐。父亲最后爬的那棵黄楝树,已经掉光了叶子,像一个瘦而高的老人,孤单地站在那儿,低头认罪似的。黄楝树是后山野生的,春天里,父亲摘了嫩叶,腌制或者生炒了吃,味道极鲜美。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穷,就走村串巷去卖这腌过的黄楝头,三分钱一筷子,一竹篮子的黄楝头可以卖两块钱,那是一笔巨款。江小娅因此知道黄楝树是一种珍贵的树种,生长极缓慢,每到春天,奉献一茬美味的嫩叶。
要从13岁离开星湾村上中学那时算起,江小娅待在外面的时间比星湾多得多。对于星湾,特别是近年来的星湾,她是陌生的,更有一种故乡的感觉。比如这个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的初冬,星湾村几乎没什么人,除了几个晒太阳的老人,路上看不到年轻人。入夜,整个村子里安静得死气沉沉,没有灯火,没有说话声,偶尔传来的狗吠,只是加深了夜的安静。这是一个空了的村子,江小娅觉得陌生。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每家至少有三五口人,三代、四代同堂的屡见不鲜。
从后山顶上往村子的方向看,顺坡而下的房子显得寥落、陈旧、低矮,散落在冬日的枯木之间,这些老房子,大多是新世纪初,甚至是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盖的两层楼,还有就是那些作为古村落象征保留下来的更老的房子,鸿书台、耕乐堂,怕是有百多年的历史了,偶尔有外面的游客满怀好奇心来探访它们,镇上已经在逐步修缮,以期可以发展旅游业。房子前面是村道,村道早已不是小娅小时候的那种泥土路,宽敞的柏油马路连接到每家每户,村首依水而建的停车场也十分宽大,放在城里是极奢侈的了。
一切都变得更好,除了人少。哪怕是后山的收获季节,村里的年轻人也不会回来帮忙,宁可自家的果子烂在山上,老人们见了心疼,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村里大约有七八位这样固执的老人吧,他们或者无处可去,或者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向往,总之他们守在这里,与日月、湖山、果树、老屋,以及寂寞相伴。老江算是一个。
老江其实是有地方可去的,作为独生女儿,小娅也责无旁贷。自五年前母亲进城帮她带孩子之后,她担心父亲独居,多次想叫他一起去城里,无奈父亲每次去都如同蜻蜓点水,住不了两夜就要往星湾赶,用母亲的话说,怕星湾一夜之间搬走了。
小娅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她想父亲这样两面走走也很好。偶尔星湾有了稀奇新鲜的吃食,父亲就颠簸百十里地送进城里来,也能和家人小聚一下。有一次,父亲进城时,小娅无意间听到他和母亲的谈话。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父亲问。
家,这里不是你的家么?母亲说。那时母亲在城里已有两三年,很适应了。
我说星湾的家。
那可说不定,轩仔还那么小,这里洗衣做饭带孩子都离不了人,指不定要十几年呢!
那时,我们都七老八十了。父亲叹息道。
等你过了六十六岁,就进城来,你一个人在村里,我们也不放心。母亲说。
六十六岁,在星湾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纪。如果母亲或者父亲到了这个年纪,做女儿的要为他们大办寿宴,做一生中最隆重的生日。
过了六十六岁我也不来城里,我在这里浑身难受,吸气儿都不顺,空气里尽是汽油味。父亲不高兴地说。
江小娅听了心酸,为了自己的舒服,她从父亲身边抢走了母亲,因为她需要母亲为她打理小家,她甚至还想,父亲刚刚六十,身体健朗,一个人在乡下自由自在的,应该也很不错。没想到,父亲那么强烈地盼着母亲回去。有几次,父亲多待了两天,乡下的邻居会打电话来催他回去。父亲多半会说,是牌搭子啦,现在乡下人少,凑一桌麻将也很困难,所以大伙想他早点回去。那时,小娅会不自觉地看母亲一眼,母亲是最恨父亲玩麻将的,但现在,母亲丝毫不在意这个,只叮嘱他一个人也要吃好饭,天冷记得添衣。
父亲颇识得几个字,在他这个年纪,算是村里的文化人。所以江小娅很早就教会父亲用微信聊天,也常常和父亲用微信联络,一开始,他很欢喜,看到什么稀奇事都爱拍照传给她,时间长了,小娅能及时回复的也越来越少,父亲也不大发了。父女间的微信更多的用来发送一日日长大的外孙的照片,江小娅每次都记得,把母亲一起拍进去,她想,父亲是想念母亲的,自己的舒适是因为父亲的付出。
下山比上山快许多,一条小路是那种走的人多了就成为的路,杂树丛生中,蜿蜒而下。小娅想象着父亲每天早上上山干活,整理果树茶树,傍晚时分下山,中午就在山顶吃一点简单的饭食,随身带着一把粗糙的大茶壶。这条路,他不知道走过多少遍。
村首的停车场上,母亲、老公和儿子都已经在车上等着她了。相比小娅,母亲憔悴得更厉害,她半闭着眼睛坐在车里,几天前还风韵犹存,这会已经完全是个老太太了。有几个老人来送行,家族里赶来老江葬礼的年轻人本来就不多,昨天下午早已进城了,忙着挣钱,谁也耽误不起。时间只属于老年人,他们站在寒风与冬阳之间,瑟缩着身子,不说话。时间只属于老年人?小娅觉得有点变味,不是常说,年轻人才有大把的时间么?
车子开出星湾村,折上省道,箭一般地往城里去了。江小娅想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父亲走了,仿佛她和星湾的最后一点联系也断了。从此,星湾就是江南的一个普通村落,与她没有什么关系。即使这么想着,也没有太多的疼痛感。
父亲的手机很新,估计用得不多又小心翼翼,并且保持着充足的电量。一开屏,是轩仔的笑脸,上次回来时,小娅帮他设置的。
通讯录里的第一个人叫叶雨明,江小娅不认识,虽然她三天前打过这个电话,但对于他是怎样一个人,毫无印象。突然,电光石火间,小娅想到了昨天父亲葬礼上的那个人,那个戴着墨镜,穿着大衣,格格不入的男人。她本能地确定,这个人就是叶雨明,至于他为什么会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小娅还是毫无头绪。
等过两天有时间,一定要向这位叶叔叔道个谢。小娅心里想。
父亲和这位叶雨明的通话、微信很频繁,甚至超过了和她这个做女儿的,他们一定是极好的朋友,至于他们如何相识相交的,小娅真的有一丝好奇。她心中,父亲是内向沉默,或者说略略有些清高的人,不大会主动结交朋友,更何况保持这么频繁的联系。
微信里大部分的记录都是平常的往来,好像叶雨明来星湾的次数比较多,比如春天时他会问,“茶叶可采没有”“桃子熟了么”“我下午到”之类。最早的微信始于前年的春天,也就是说,满打满算,两个人相识不过两年。叶雨明是杭州人,有一个儿子在国外已经成家了。由此江小娅推算,虽然他看起来年轻,也是父亲那个岁数的人了。或者也因为孩子都不在身边,更有共同语言吧。
江小娅想起自己给叶雨明打的那个电话。她说,叶先生,很冒昧,我不认识您,但我知道您是我父亲江炳明的朋友,我父亲不幸去世了,我想,朋友一场,我得告诉您这个消息。电话那头的叶雨明明显吃了一惊,然后用他浑厚低沉的声音问,什么时候的事?
江小娅很后悔昨天的葬礼上没有打起精神来好好招待一下这位父亲的朋友,他悄悄地来了又走了,饭也没有吃,这让缓过气来的她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江小娅没有想到,叶雨明能依约出来见她,他们约在市中心一家普通的咖啡连锁店见面。江小娅刚刚坐下,只觉得面前一道身影,正是叶雨明。他依然穿着上次的长身羊绒大衣,只是没有戴墨镜,坐下来时,顺手将皮帽子放在左手边。小娅忙站起来,叫了声叶叔叔好。
叶雨明朝她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
江小娅这回看清了,虽然叶雨明和父亲是气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但他的确是父亲的同龄人。
叶雨明问她:“老江的事,都妥当了?乡下规矩多,难为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话让小娅一阵心酸,又一阵温暖,想起自己这一阵子的忙碌,照顾病倒了的母亲、年幼的孩子,父亲的离开,真像天空塌陷了一角。她像一个小兵,猝不及防地被推到了前沿阵地,手忙脚乱。
江小娅点了点头,又问:“叶叔叔是怎么认识我父亲的?”
叶雨明看了看周围,掏出一支烟,对江小娅说:“我们认识有两年了,应该是前年的春天吧,我去星湾采风,遇到你父亲的,那时,他还健康。”
“是的,我父亲身体一直不错,所以,我很难相信一棵树的高度能把他摔没了,他也是在山上长大的,身手利落,怎么也不至于。”泪水涌出来,江小娅也没有擦。
在叶雨明的袅袅烟圈里,江小娅听到了一个她全然不知道的,发生在星湾的故事。
三年前的早春,叶雨明从杭州开车到了星湾,退休之前,他是一个文史专家,一生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他是奔着星湾那些上百年的老房子来的。看完了老房子,他在湖边钓鱼,就在这时,遇到了老江。老江在湖边的地里种菜。四野茫茫,山静水籁,两个年纪相仿的男人很自然地聊了起来。叶雨明没有想到,这个乡野间的农夫不仅有细腻的感情,也有很好的表达。他说,他小的时候,家里有祖母、父母、兄弟姐妹,一家七八口人,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六十年过去,过着过着,就过成了一个人,纵如是,他也不敢轻易离开家,离开星湾。女儿以为是他难以适应城里的生活,事实上,是他无法割舍这里的一切,在城里,他觉得自己像是流水上的浮萍,甚至没有活着的感觉。身体滋润,灵魂枯萎。叶雨明听到这八个字时吓了一跳,他眼前的老江,瘦黑的面孔,眼神柔和略显木讷,除了面部轮廓间清晰可见年轻时的英俊之外,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可他说灵魂枯萎。
叶雨明说,人在六十岁时应该活开了,应该为自己而活。
老江说,辛苦了一辈子,为老的,为小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父母走了,女儿进城了,连老伴也在女儿那发挥余热去了,他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
老江的话,让叶雨明无言以答,他想到自己,自儿子去了美国,孤家寡人的自己不也常常有类似的感觉么?只是他会开车,衣食无忧,至少在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可以四处旅行,如果有一天,对旅行都厌倦了,叶雨明也没有想好,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反正他不会去美国,就像老江不肯去城里一样。
这种类似于同病相怜的感觉让他们相谈甚欢,天色将晚时,两个人一前一后回了老江的家。
老江的家在叶雨明这个一生住宅条件严峻的杭州人眼里,不啻是一个世外桃源。首先它临湖,是湖景房,最东侧的房间里,能清楚地听到湖水拍岸的声音。老江的房子其实有两处,他现在住的是一幢2000年左右建造的二层小楼。十多年的风雨侵蚀,墙门已经斑驳,但整个外墙都贴着马赛克,见证着昔日的时髦。另一处房子在隔着一个后院的山坡上,是一处百年老宅。它原本不是江家的,是老江有了闲钱后,独具慧眼把它买下来的,据说当时才花了八千块钱。门口立着文物保护的牌子,应该是这幢房子的后门,光滑的条石门槛很高,砖制门楼,边上写着“此处未开发,止步”。继续往里走,一条约七八米长荒草蔓延的小径之后,这一重门楼巍峨隆重,完整精致的砖雕门楼,有乾隆年间的题字。里面是一重院落,朝着东南,状似一把直尺,虽然破败,却有浓重的往日气息,陈旧完整的雕花长窗,井沿光滑的老井,只是屋里屋外都堆满了杂物,叶雨明觉得,老江过的是极奢侈又极荒凉的日子。关于老房子,现在政府给老江两个选择,要么他自己出钱修缮,将来有旅游的收入也全部归他,要么,由政府出资修缮,将来的收入也与政府分成。在叶雨明来到星湾之前,老江还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所以,老江很自然地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和这个来自大城市的有见识的新朋友商量。
叶雨明选择前者,老江听了,沉默一会,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就是重修的钱不是个小数目,他手头上没有,也不能和女儿开口要。叶雨明说,他可以想办法。说了又马上后悔了,这不明摆着叫老江不要和政府合作而和他叶雨明个人合作嘛。
幸好,老江好像没有想到这一层,他先是感动,表示,如果叶雨明能借这笔钱给他,他一定会如期还上,后山的茶叶、果树,一年里至少也有几万块钱的收入,老江再三强调。
晚饭很简单,天井里一个塑料盆里养着老江头一天晚上打来的鱼,院子里到处都是蓬勃生长的马兰头,胡乱掐一把就能炒一盘。饭是在土灶头上做的。这种灶头叶雨明并不陌生,以前的乡下人家,都是这种大灶头,几乎占据半间屋子,并列着两口大锅,中间稍上方处有一口小锅,是专门用来放水的,小锅下面并不用柴烧,只借着两口大锅的余热加温,小锅里的水常年温热,但不会烧开,一般用在早上洗脸刷牙。早春天气,乍暖还寒,叶雨明守着红彤彤的灶膛,暖和得睡意朦胧,只想打个舒服的盹,可是,老江在那边说,开饭了。
让叶雨明惊喜的是,老江端上来一碟腌制的黄楝头。这种神奇的树叶,一放到舌尖就满口生津,一种奇异的美味迂回曲折而来,迅速布满整个口腔。不知道为什么,黄楝头奇异的味道,让一种久远岁月里隐藏着的记忆凶猛地扑面而来,狠狠地逼出了叶雨明的眼泪。幸而屋内灯光昏暗,叶雨明一仰脖子,将眼泪和着老酒一并吞下。是的,他记得,这种童年里的味道,连同那高低起伏的叫卖声,心一下子软弱得不行。
晚饭后,天色完全黑透了,两个人在厨房里抽烟。老江点着叶雨明的软中华,姿势生硬,不知所措。他是个从不抽烟的人,这一点和叶雨明不同,叶雨明是个离了香烟就没有安全感的人。
老江很快在楼上为叶雨明收拾出床铺来,一张干净的单人床,粉色条纹的床单和被子是成套的,上面罩着一顶蓝色的尼龙帐子,这床铺看上去有点滑稽,充满不和谐感。老江自己也意识到了,讪讪笑着说:“叶兄弟你将就着吧,颜色不搭,但东西都是干净的,晒过太阳的。”是的,那被子有一种棉布在阳光中暴晒过后的特别馨香。
叶雨明出来一般都在正规的酒店住,连农家乐都很少光顾,连他自己都奇怪,竟然在初识的老江家过一夜。这一夜不能说睡得特别好,但也勉强过得去。乡间的夜实在太静了,静得耳朵嗡嗡作响。叶雨明很不习惯,再说,年纪大了,睡眠本来就少,天刚一透点亮,鸟雀们就使劲地叫唤。叶雨明起床时,发现老江不在家里,也许是出去买早点了,一想也不对,这村子里只剩下七八个老人,谁来卖早点。按原计划,离开星湾后,叶雨明将继续北上,走访古村落。
叶雨明踱步到阳台时,看到了湖泊中有人撑着一条小船,正在使劲地朝自己挥手,定睛一看,正是老江,他在收网,如此说来,昨天他睡下之后,老江又去湖里张了网?不知道今早的收获如何。
叶雨明顾不上刷牙洗脸,拿上外套直奔湖边,老江的船也靠岸了。老江满脸喜色,提着一个红色水桶在摇晃的小船上稳稳立着,一个箭步跳上岸来。
“没有什么好货色,全是杂鱼,但杂鱼有杂鱼的好。”老江说着,把水桶拎到叶雨明面前。
“天哪,好多鱼!”叶雨明欢欣地喊道。大半桶水,大约有几十头各色的鱼脑袋挤着,看得叶雨明心里痒痒的。
“叶兄弟,等我把鱼杀了,轻盐腌了,你带上,回家正好蒸了吃,鲜得很。”老江说着,在湖边的埠头上坐下来,他杀鱼不用刀,用大拇指剔去鱼鳞,然后往鱼头下方轻轻一挤,鱼的内脏都挤出来,动作麻利,不消一会,一堆杀好的鱼齐整地码在那儿。
比起晚饭,早饭更简单,老江煮了六个水鸡蛋,一人三个,吃完他们分道扬镳。老江说,叶兄弟你六月再来,那时有枇杷和杨梅了,到时我微信你。
呵对了,老江居然会熟练地用微信,这让叶雨明吃惊又高兴,马上加为好友。离开的时候,叶雨明带着老江送的一瓶腌黄楝头和一包腌杂鱼。下次来,带你去捕夜鱼,再带你去看后山的黄楝树,整个后山,我还没有发现第二棵呢,老江说。
老江说的,叶雨明都很期待,他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回到老家度个愉快的暑假,和小伙伴相约下次相见,并为此设想了许多计划。认识老江,真好,他想。
听说老江待会要去镇上的茶厂,叶雨明无论如何要送他,老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把满当当的一担茶叶塞到后备箱里,那是已经老了的茶叶,成不了昂贵的碧螺春,只好轧碎了做红茶。然后,老江小心翼翼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叶雨明的车子一向很洁净,但老江拘谨的样子让他有点恨自己的洁癖了。浩荡春风吹动着老江的旧衣裳,车驶过,有几个老人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叶雨明的车子,在他们惊异的目光中,叶雨明感觉到老江不动声色的笑容。
六月的星湾是最美丽的,后山上五彩缤纷,黄的是枇杷,红的是杨梅、桃子,采摘过的茶树在阳光下绿油油的,期待下一茬丰收。星湾后山一带的碧螺春是品质最好的,因为茶树都夹种在果树中间,茶叶带有隐约果香,山野气息浓厚。上次来时,看到老江用一架笨重的木梯,这回叶雨明带了一架轻巧可折叠的不锈钢梯子,果然,老江见了,爱得不行,他坦白说,扛着木梯上山下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他们摘了一天的枇杷,用小竹筐装好,每筐六斤左右,放了满满一屋子,老江说,有村民来统一收购,价钱便宜一点,也可以自己出去卖,但麻烦,还要承担变质的风险,所以他选择前者。傍晚时,他们用电话敲定了老江一个远房的侄子,明天一早来拉枇杷。晚饭时分,两人就如释重负地喝了一点米酒,酒也是老江自己酿的,又就着月光在院子里坐着喝了一壶茶,然后,老江说,出发!
叶雨明觉得自己的心跳频率都改变了,他提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几乎雀跃地跟在老江后面。老江背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有手电筒和一个简洁版的类似电唱机一样的东西。叶雨明在小型的广场舞上见过,大妈们用它来放音乐。老江也一样,他买了许多戏曲的唱片,还有流行歌曲,夜晚,独自在湖上张网时,放歌,歌声里弥漫着湖水的清润,飘出去很远,将寂寞一扫而空。
看到老江的“船”,叶雨明心里一怯,走不动了。那个拴在石埠头的塑料壳子是船么?它在河水里微微荡着,看上去那么小,那么窄,轻飘得没有分量。
老江看出了叶雨明的心思,他几乎是嬉皮笑脸地挑衅道:“怎么样?上不上?”
“我以为,至少是条木船。”叶雨明说。
“以前有过木船,可外人都知道这村子里现在没人了,小偷格外多,不要说是解个缆绳就能走的船,就是那些锁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都被多次光顾。只有这塑料壳子不值钱,是公园里淘汰下来的旧东西,用着正好。”老江说完,人已稳稳落在船梢处,示意叶雨明上船。
叶雨明将手中的竹篙递给老江,老江会意,将竹篙往船外沿的河水里猛力一插,如定海神针般将船夹住,叶雨明得以平稳上船,但他不敢站着,一屁股坐在船舱的横梁上,重心放低,很快找到了感觉,老江拔出竹篙,轻轻一点,小船箭一般出了港口,向湖泊冲去。
老江用的是丝网,张在离湖岸几十米湖水中,湖里其实养着鱼,但丝网力道很小,网住的也不过是些个头很小的野鱼,所以养鱼人家也不太计较。很快,两道丝网放完,老江有自己的记号,他说凌晨时分他会来收网。然后,他将竹篙往湖水里一插,用一截麻绳系住了船。湖上有风,但不大,对于这么大面积的湖水来说,轻轻晃荡的湖面可以说是风平浪静。老江放了一段戏曲,是越剧《红楼梦》的《宝黛初见》。
“想你老婆了!”叶雨明一边递烟给他,一边笑着说。
“这会还真不想。老婆在,绝不会让我出来张网的,你想,一个人,一条船,还喝了酒,又是在夜里,这不是不要命么。”老江笑嘻嘻地说,叶雨明觉得这会儿的老江真可爱,他平实的语气里总透着点幽默。
“你离婚多久了?离婚也没找到更好的,后悔了吧。”老江杀了回马枪。可是叶雨明不以为忤。他的生活中,极少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机会回应。
“很多年了,应该是儿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我算算,十多年了。刚刚解放那儿吧,觉得天是蓝的,水是甜的,我是有翅膀的,根本想不到要重新回到婚姻的笼子里去,现在年纪大了,突然发现合适的人很少了。找个年纪相仿的吧,说心里话,不是很愿意,女人在我们这把岁数,虽然也是花,却是棉花。找个年轻的,又缺乏勇气,不知道人家是冲着什么来的。总之左右为难。”叶雨明说的句句是掏心窝子的话。
“棉花?哈哈哈,可我们俩现在连朵棉花都没有。”老江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湖面上回响。
那天晚上,两个花甲老人在湖面上待了很久,直到叶雨明发现口袋里已经没烟了,才由老江把船撑回来,怕有十点钟了,村子静得像不存在,两个人在月光下走着,月光透过树枝的间隙洒在青石路面上,留下细碎斑驳的影子,在微风下摇摆不停,叶雨明竟有些顽皮地踩在每一片树叶的影子上,跳跃着前进。偶尔,老江手里的竹篙和石板轻轻摩擦,发出“咔”一声响,老江立即警醒地提高一点,怕惊扰了这安静。
山村有种奇异的魅力,虽然是深夜,虽然是陌生的地方,虽然如此的安静,但不叫人害怕,相反,整个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静了下来。
这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叶雨明来星湾的次数起码有十二次,星湾成了他自驾游中去得最多的地方。老江因为农闲没事可做要去镇上打工时,叶雨明坚决反对,为了让老江有事可做,叶雨明在第二年的春天叫老江养了一批鸡鸭,说好十月间他带回杭州去送朋友。老江兴兴头头地答应了,每隔一两天就在微信上向叶雨明报告它们的成长,每天喂的食物,赶着他们去后山吃草的照片,直到有一天,微信突然中断了。
叶雨明对老江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电话中老江的声音也郁郁不欢,但他说没有什么事。叶雨明赶到星湾时,老江已经将养到半大的几十只鸡鸭都卖了。
江小娅面前的咖啡已经凉透,卡布奇诺丰富的泡沫凝在杯壁上,让人失去食欲。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积了一堆长短不一的烟头。
那批未及长大就消失的鸡鸭,江小娅在去年夏天回星湾时见过,她和母亲都批评父亲养它们,因为家里突然鸡飞狗跳,臭气熏天,江小娅一直以为是因为自己和母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父亲才处理掉了。她记得父亲说过,卖给附近的养鸡场了。有次,小娅的儿子在院子里折了一棵细弱的树苗,老江十分心疼,小娅很意外,因为这样的树苗满山都是,老江粗着嗓子说,这是黄楝树苗,野生的,好不容易才找来。想来,那是给眼前的这位叶叔叔留下的。
“是的,后来,老江又帮我找了一棵,放在苗圃场养了几个月,才让我带回杭州。可是,不久也死了,因为七楼阳台的阳光雨露实在太有限了。”叶雨明遗憾地说。
“叶叔叔,您和我爸为了养鸡的事吵架了么,他才卖了它们?”小娅好奇地问。
“没有,只是,发生了比吵架更严重的事。老江只能这么做。”叶雨明燃起一根新的香烟,他知道在一个年轻女子面前抽那么多烟很不礼貌,可是不抽,他不知道如何继续这话题。
“怎么了?”小娅突然像被针戳了一下。
“因为老江生病了。小娅,这事我本不该说,但我知道你对老江的离开心存疑惑,而且,星湾现在是一个空心村,甚至不是一个太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有别的想法,会更让你痛苦。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老江得了肝癌,是晚期,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想了很多路途,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明白么?”叶雨明坐直身子,看着江小娅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江小娅呆呆的,血色一丝丝从她姣好的面孔上退下去,泪水一点点涌上来,惨白的嘴唇哆嗦着,她伸出双手,慢慢将脸埋进去,瘦弱地肩膀剧烈抽动着。叶雨明掐熄烟头,将面孔转向窗外。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