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一家合伙股份公司……
陈晓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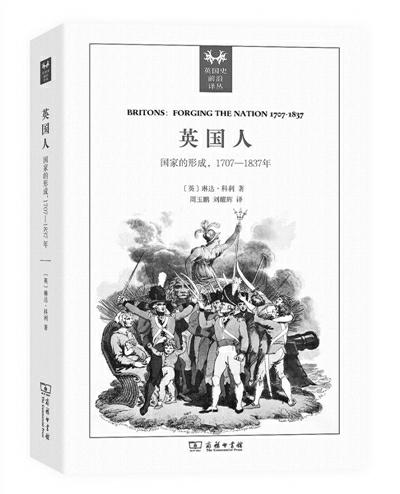
陈晓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琳达·科利的大作《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中译本终于出版了。
该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思想的高度和撰写的难度。因为,作者探讨了一个很难精确界定的东西——英国性。所有人都知道,但凡涉及国民性一类的问题,都很难处理,要么大而无当,要么云里雾里,要么以偏概全,要么无病呻吟,似乎说清了什么,却又往往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最关键的是,即便有一些精当的分析,也很难服众,成为学界或者社会的某种共识。
不过,琳达·科利却通过另一种视角探讨了这个十分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历史的视角,这再一次显示了历史学的优势。她一步一步地描述了今天所说的英伦三岛的四个部分如何凝聚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正因其视角的独特,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1992年初版后,不到20年竟然已经再版五次,这在同类学术著作中,应该说是相当罕见的。当然,这或许也与当代英国人的某种无名焦虑有关,当前英国的脱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焦虑的反映。那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如何界定?我们的未来向何处去?
“投资民族国家”
关于国家的形成,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投资民族国家(investing in the nation)。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而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国家的再版。这个新型的国家,其实质就是现在人们常常称呼的“民族国家”。而且,在英国这块土地上,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有着浓浓的商业气氛,因此,法国人轻蔑地将其称为“小店主的国家”,不是没有道理。
这一点,从当时英国众多的爱国协会的活动就可以看出来。这些爱国协会的使命都是公共性的,它们有意对外,并意在改革国家政府。一些商人建立的俱乐部的目标也非常商业化,那就是要赚钱:“为了我们的国家,通过讲理和举例来阻止消费法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并反过来,鼓励消费英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122页)而一旦某些协会具有将爱国热情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动力,协会的存在及运作方式就会发生改变:“由此,英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仁爱相结合,会在整个王国传播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教导这些年轻人敬畏上帝,同时教导他们的手和手指为国家、为真实而重要的美德而战,我们就可以期待,这种行为能令上天垂青这个国家”。(125页)
的确,各种爱国协会都增加了商人与政府高官相识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商业活动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海外贸易需要皇家海军的支持。哈弗沙姆勋爵的话十分直白,“阁下的舰队和贸易之间关系密切,它们互相影响、不可分离;你的贸易是你海员的母亲和护士;你的海员是你舰队的生命,而你的舰队是你贸易的安全和保障,这两者一起,又是英国财富、力量、安全和荣耀之所在”。(97页)所以,为皇家海军贡献自己的力量,既是一种热心为公的姿态,也能确保其获得应有的回报。
显然,投资爱国主义(希望这样的用词不至于让人们产生某种误会,但英国人的确将爱国主义也作为一种投资看待),其物质的回报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保护其成员的利益的,尤其是商业的利益。但这样的一种关系也表明,在这个社会,乃至任何一个社会,积极的爱国主义,很容易汇聚成要求更广泛的公民权和政治变革的洪流,因为人们要确保自己的投资不至于随时被喜怒无常的统治者卷走。
而自由和获得认可的急迫心情,是人们在朦胧中构建一个新型国家的潜在欲求,正如书中所说,对于很多小人物而言,加入各种爱国团体是获得某种影响力的路径,作为个体,过去他们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这样一种方式的存在,也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更符合商人需求和喜好的国家。或许,下面的这段话表达了当时资产阶级爱国者的心声:“你们是自由民的儿子,尽管贫穷,但你们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儿子;记住,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131页)真是精妙!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这不仅是对自身价值观念的评估,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人相信,个人成功和国家利益永远相辅相成。
“金融军事帝国机器”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在1707年由于合并法案,并由汉诺威王室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基础都非常狭隘,几乎是完全依靠军事力量才得以延续的。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的政治被一部分辉格寡头控制,被统治的人们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然而,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几乎是人为制造的民族,由一小部分土地贵族统治,富有侵略性的盎格鲁寡头,能够吸引比他们自身基础宽泛得多的民众来支持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世界上第一部“金融军事帝国机器”。(菲利普·哈灵,《现代英国国家》,第32页)
各种类型的从事贸易的人总是支持这个国家机器的最显著的人群,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巨大的数量。在18世纪的英国,五个家庭中可能就有一个依靠贸易为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与贸易有关的人比一般的英国人更需要政府。国内的贸易商,即便是小贩,也十分依赖一个好的社会秩序以保证商业和信贷能够安全便利地流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要求国家的海军在危险的航线上保卫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当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爱国者,尽管如此,在紧急时刻,这些人都有最强烈的理由支持政府,并对国家忠诚。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国家给他们带来收益。
英帝国的实力有赖于贸易,保护这项贸易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新型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股份公司,股东们来此投资就是要想盈利。那么,公司如果要想盈利,就必须有清晰投资方向和盈利目标。这个目标,很快就确定了,那就是打击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法国。一旦确定了主要的敌手,其他一切都围绕这一中心点运作,事情就好办多了。
帝国斜阳与身份认同
因此,英国学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光荣革命”最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不是宪法决议,例如《权利法案》或者意识形态的辩论,而是决定同法国开战。有了共同作战的对象,有了共同的敌人,一个新型国家民众的凝聚就不是问题了。之后,英国与法国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次战争,直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所以,一些史学家将其称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英国的政治家也许会就怎样最好地击败法国进行争论,但共同点是,他们一致认为英国自由的法律、独立、经济的繁荣以及殖民地的扩张,都取决于对法战争的胜利。不难看出,英国历史的运作自有其诡异的规律。这个以新教为旗帜,以牟利为基础的新型股份公司—民族国家,正是在与自己的敌手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且,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逐步地完善了这一新型国家的构建。
琳达·科利的著作止于1837年,真是一个好年份!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英帝国和大不列颠都处于一个即将达到顶峰的阶段,工业革命的任务即将全面完成,议会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帝国的扩张无往不胜,英国人在自我认知方面,也处于一个心情自我膨胀的最佳时期。然而,顶峰之后,即是帝国斜阳。二战后,无论是英帝国还是英国本身,都开始了向下的位移。这是一个痛苦而无可奈何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由形成的合伙股份公司性质的大不列颠,本身的认同开始受到了挑战。
“股份公司”合伙盈利之时,红利滚滚而来,面对“搭车者”,身份问题的主要麻烦是甄别你是不是英国人。日子不好过,潜藏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了。正如潘兴明所说,时至今日,英国国家的身份认同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存在着一个“去英国化”的趋向。在英国,对英国国家身份的认同在四个地区并不一致。英格兰最为坚定,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诉求日益强烈,北爱尔兰刚刚实现和平不久,国家认同问题尚未成为当地居民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北爱尔兰走上与苏格兰、威尔士两地的相同道路只是时间问题。而原先曾是英国一部分的爱尔兰更是在上世纪20年代就宣告独立,与英国分道扬镳。
于是,以自由和新教为旗帜的“股份公司”,随着新教氛围的淡漠和“自由”的无处不在,似乎要在“自由”的旗帜下逐步地萎缩下去了。琳达·科利的大作受到了英国社会如此广泛和热烈的欢迎,人们不难想象到其中的奥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公司,在迅猛发展和扩张之时,是否应该守住某些底线?如果要,那么,这些底线是什么?科利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或许也没有人能给出权威的答案。我们只能重复一句套话:让历史告诉未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