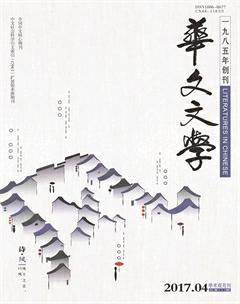当代武侠小说侠隐结局的人类学考察
李巍
摘要:当代中国武侠小说中大侠的命运结局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在归隐与死亡的宿命中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齐一化。然而这种独特的归隐宿命并不常见于更早期文本中的侠客,他们不仅可以建功立业追随王权,也可以功成名就娶妻生子。归隐或死亡的宿命归结于江湖世界的独立本体化。而身处其中的大侠也由草莽一跃而成为权力肩负者。身处独立江湖的侠客拥有了早期神话和史诗中神祗和英雄的特征及其使命,大侠必须以武功为手段行使他们安定江湖世界的伟大职责,最后以死亡或归隐的方式完成这一职责。
关键词:江湖;归隐;死亡;大侠;神性;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116-08
熟知武侠者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想必不会陌生。语出《神雕侠侣》郭靖之口。郭靖算得上人们阅赏武侠文本时较为典型的大侠形象,不仅武功卓绝,且具备超越古侠的“为国为民”情怀。武艺超群、为国为民,这些所谓超越之态俨然已成当下武侠之常态,若无这些也难称大侠。当古侠被注入奇技神功和兼济天下的道德担当之后,古侠也正式蜕变为今之大侠,原本出路多元的古侠也走上了唯有死亡和归隐才能获得终极解脱的宿命。
一、当代武侠赋予“侠之大者”的归隐特权
当代武侠文本的收尾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它们结局惊人一致,不做归隐之途必是刀下亡魂。鉴于武侠小说数量众多,这里仅以金庸武侠小说为范本做个简单考察,如,《神雕侠侣》中杨过达到武功的制高点时携小龙女归隐;《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在反元起义的大潮中归隐;《碧血剑》中袁承志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归隐;《侠客行》中石破天回到小时候居住的荒山;就连《鹿鼎记》中的流氓韦小宝也带着七个老婆归隐。若不是归隐就必然是死亡,如《天龙八部》的乔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有论者指出武侠小说的四条共性模式,“一、冷兵器时代拯危济溺的尚武精神。二、独来独往的个人冒险、英雄人格。三、神化气功为基础的超人武功的描写。四、武隐模式的隐逸宿命论。”①武侠向来被视为为中国独有,流露着特有的中国品格。“于刀光剑影中渗透着中国的文化精神,此乃武侠小说的特殊魅力所在”。②“在所有的中国文学样式中,只有武侠小说顽强保留着自己的中国特性。”③
因此关于侠隐结局的出现,前人的不少阐释都局限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鲜有超脱的人类学或跨文化视野。如有论者认为“现实中的游侠结局,往往并不美好。一般的侠,或者被朝廷诛杀,或者在帮会火并中丧生,或者變节而失去自我”。因此“这就促使人们对侠的结局重新定位思考。反思的结果是创造了‘文化之侠最突出的完满形式——侠隐。”④也有人会以张良的人生轨迹来为此辩解,张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名动天下然后功成身退堪称美好人生之楷模,游宦怎么看都颇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而游仙也跟“逍遥游”的境界颇多类似之处。显然功成名就后的“隐”是中国传统文化关照下比较完满的人生。虽然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对侠隐的影响不容置疑,也显而易见。可是这个文化传统自古就有一以贯之,但侠隐并不特别显见于当代之前的武侠文本。虽然古代不少文本也体现了所谓“归隐”,但与当代武侠文本的归隐相比可谓差之千里。顶多算是“消失”或“另寻新路”,以唐传奇为例,虬髯客虽黯然退去,但结局是成为扶馀国主,这是跑到异域开疆拓土去了。再如,聂隐娘结尾于“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与其说她归隐还不如说她“消失”。这并不能确保她后续无复有侠义行为。相比之下,归隐是大侠携长剑美女隐遁山林,从此再不过问江湖,犹如半死状态。两者有本质不同。
除了“归隐”一途,早期侠客还能堂而皇之走上仕途,尤以明清侠义小说为甚。大侠可投奔官府建功立业,甚至升官发财。不仅如此,早期侠客也不如当今侠客之潇洒快意,甚至甘为朝廷之鹰犬高官之走夫。如《三侠五义》。鲁迅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⑤再如,《施公案》中黄天霸之于施仕伦,《彭公案》中马玉龙之于彭朋。侠客们心甘情愿在官老爷周围转悠,为其鞍前马后,最后凯旋回朝封官荫子。即使《封神演义》的仙侠们,最后不也在助力武王伐纣之后荣登封神榜。此种侠客在当今文本亦有所见,然而多以反派面目示人,如《碧血剑》中两个武功高强的反派——安剑清和玉真子,皆是效力朝廷之流,一个卖力于明朝锦衣卫,一个投降于满清皇太极。此种例子举不胜数。而众人更为亲近和熟悉的侠客,乃是不附朝廷只属门派,甚至无门无派纯粹浪迹天涯的逍遥剑客。归隐一般是他们的特权。况且就神化气功这条来讲,就并非古侠必备之技能,内功也是当代武侠文本的最新演化产品。再者,个人冒险与英雄人格也有待商榷,古侠之行径很多出于个人私利,如为私交、为功名等,甚少怀揣天下苍生,且多与政治目的相关联,如荆轲的刺秦王、虬髯客的争夺天下、聂隐娘的政治暗杀等等。最有名的莫过于水浒英雄的招安冲动与趋于正统的努力。此外,在早期文人歌咏侠客的诗歌中也体现了侠客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如张籍《少年行》有“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诗句,曹植《白马篇》的“幽并游侠儿”也是急于建功立业。纵然不去建功立业,侠客也可能会有一个不做归隐的完美结局,《儿女英雄传》里的女侠十三妹不就跟张金凤一起嫁给了安骥,从此两女共侍一夫,收尾于童话般的结局。《绿牡丹全传》(又名《宏碧缘》)中骆宏勋和花碧莲也是以妻妾大团圆招安受旌表为结局。因此,所谓武侠的共性模式其边界应以当代武侠小说为准。
由于武侠“中华独有”,人们对它的审视向来抱持“古已有之”的态度,最后难免落入以儒道为据的传统老路。追索文化传统的努力面对侠隐、武功等突如其来的武侠新特点时显得力不从心,其乏力之处正在于视野的局限,弗莱早就提醒“把文学全然看成个人的事业,这样便掩盖了许多批评的事实。”⑥把武侠全然禁锢在中国,同样会掩盖很多批评的事实。以原型角度观之,作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内容朴素、情节都高度程式化,“最容易观察到原型”,显然更适合以人类学视角切入。人类学视角势必将武侠置于人类广阔的整体文化视域之中,溯源武侠在上古时代的神话模型与巫术对应,对古今中外各类“侠”进行比较考察。若以此视角稍作引申便能轻易发现,当代侠客具备的“为国为民”“以死救世”胸怀,让他们更接近于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和神祇。如果仅以此种“大侠精神”为基点并放眼四海,不难发现,郭靖、乔峰、令狐冲与其说像荆轲、展昭、聂隐娘,还不如说更像吉尔伽美什、贝奥武甫、甚至是美国队长(美国的漫画英雄)。显然侠客在当代武侠文本中经历了由侠到“侠之大者”的转变,并以归隐作为其特殊标志。那么尝试以英雄来审视当代侠客,探究“侠之大者”的生成,必将有助于侠隐之谜的解开。
二、独立江湖——“侠之大者”的诞生之地
古今中外的英雄敢标举“为国为民”“拯救苍生”的大纛,展昭等侠客却只能充当官员的保镖、打手或践行水浒好汉的“替天行道”理念,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英雄对“天下”独立负责,传统侠客不过是替人卖命尔。那么探究当代武侠小说是否为大侠开拓出一片独立于皇权的“天下”将变得至关重要,因为英雄和神祇之所以能够坦荡肩负“拯救”世界的职责,正在于他是那个世界的王者,而不是一个二流保镖角色。显然在当代武侠小说中这样的“天下”是存在的,它表现为江湖的本质性蜕变,或曰江湖世界本体化。江湖不再依附王权或世俗,侠客的活动场域顿时无限扩大。当梳理中国武侠文本之际,可发现这一关键转捩点出现在民国新派武侠崛起之际,江湖如涅槃重生焕然一新,由地理名称蜕变成一个桃花源式的独立世界。从此江湖侠客的命运变成整齐化一的归隐和死亡。
若非要勾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起点,可以说是滥觞于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它“是中国侠文化史上第一部以演叙武林门户之争的长篇武侠小说。以昆仑、崆峒派剑侠争夺水路码头为冲突,其中穿插反清复明的线索”。“向恺然在中国侠文化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二,向氏之前的武侠小说以官府为中心,他把小说中心转向民间。”⑦“在武侠小说类型的演变中,《江湖奇侠传》的最大贡献是将其立足点重新转移到“江湖”上来。”⑧在此之前没有独立江湖存在是大家的共识,但江湖的独立并非一蹴而就,尽管在此之前江湖依然是王治之地,但某种分化的端倪早已显现,“到了唐宋的豪侠小说中,剑客才真正职业化,而且与‘世人拉开绝大距离,俨然成了‘第二社会。”⑨但“唐人小说中的‘江湖还只是远离朝廷或官场的闾巷民间,尚未有更具体的描写;宋元话本中的‘江湖则已跟抢劫、黑话、蒙汗药和人肉馒头联系在一起。”⑩可见,古代的江湖不过是民间闾巷的另一个代名词罢了,它的本体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当今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已逐渐走出历史,演变成为一个带有象征色彩的文学世界。{11}这个“‘江湖世界不存在金钱匮乏或饿肚子之类形而下的问题,侠客可以一心一意打抱不平替天行道。”{12}
《江湖奇侠传》之后,特别是梁羽生和金庸之后,江湖向着更加独立的方向讯跑。不过现代武侠与当代武侠之间尚有区别,两者之间存在渐进的转变关系。民国武侠带有传统武侠烙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侠客的保镖、打手功能和“替天行道”动机大量保留,如《奇侠精忠传》中杨遇春等侠客帮助官府平叛苗族起义,《四海群龙记》中豪侠的杀富济贫等等。而且此一时期武侠創作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愤世嫉俗,有的借此消遣,有的则纯粹从商业市场入手”。{13}然而随着武侠小说的商业化,对连载刊物销量的关切导致武侠小说原型层面(通俗化程式化)的内容剧增,文人借侠客以浇块垒的武侠文本日渐式微。到了当代,港台武侠的创作基本上唯市场销量马首是瞻,因此更多的打斗炫技、更厉害的侠客人物顺势出场,大侠(主角)也臻于完美,不仅体现在道德上也体现在能力上。侠客不再依附他人,不会因鸡毛蒜皮的琐事影响行侠仗义,也不会轻易被敌人打败。对市场需求的满足愈发依赖江湖的独立,侠客需要更自由的空间来来展示担当与抱负,而不是畏畏缩缩听命于王命调遣。世俗王权由中流砥柱变为点缀修饰的背景。如金庸武侠的三分历史七分想象。江湖的事开始由江湖说了算,江湖的事开始由江湖的规矩办,江湖规矩超越王权之法。更有甚者,连这种背景也抛弃了,江湖更加纯粹,如古龙“设置的小说环境几乎没有确切的历史年代,也无可查的历史人物”。{14}江湖独立后侠客最显著的变化是侠客权力化。在世俗世界,保家卫国安邦兴土的责任在士在官在天子。侠客的侠义行径无非是对世俗王权的补充。如《水浒传》的“替天行道”,皆是在世俗王权不能有效维护正义之时才发挥作用。唐传奇里的聂隐娘是政治途径无法解决问题时出现的。可以说江湖不独立,侠客便天生带着草莽气息,不讲尊卑称兄道弟,权力等级在他们的世界崩塌为一池废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参见《韩非子.五蠹》)侠必犯禁,侠乃乱源,它天生是等级秩序的对立面,不仅不是权力中心,甚至必然“闾巷”出生,与庙堂相对。而在独立的江湖中,侠客从权力对立面一跃而成为权力承载者。在独立江湖,最大的话语权最高的指挥者舍大侠其谁呢,不过名称有别罢了,教主、盟主、宗主、帮主又或者掌门皆可。江湖还演变成具有完整生态体系的武侠世界,它由门派组成,门派不再是政府打压的结党私会而是名门正派,最大的门派代表最正统的权力(在金庸武侠中通常由少林承担,因为少林武功天下第一),门派的强与弱,江湖地位的高与底,根本上取决于功夫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有大侠或者大侠的多寡。
不难想象等级制度如此明朗的江湖,大侠(帮主、掌门、教主或盟主等等称呼)非常明显地对应着世俗世界的权力阶层。大侠犹如部落的英雄、祭司一般左右着江湖的世界秩序,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武侠世界中的万万生灵。百姓安居乐业的重任由帝王转移到大侠手中,江湖之乱不仅祸害武林,也势必殃及无辜小民。江湖世界的命运完全由门派或帮派掌握,即便是不参与任何门派的独立侠客也必然拥有在江湖一呼百应的威信。他们对于江湖的掌控一目了然,除非他隐居世外,完全不过问世事。
江湖独立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民间草莽即刻变为庙堂之上。在独立江湖层面上,侠客完全拥有了神话之神祇、史诗之英雄的对等地位。不再是处庙堂之远的江湖小民,对苍生大事无动于衷。从此之后,大侠便像神话中的神祇或史诗中的英雄,承载起一个独立世界的安定或守护职责,由一个游侠转变为“侠之大者”,肩负起为国为民的重责。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完全颠覆了之前因道义、复仇或私交而行动的小侠,游走到了江湖世界的舞台中央。
三、“侠之大者”与英雄、神祇共同的
职责和神性
除了大侠“为国为民”的道义担当让大侠与英雄相近外,当代武侠小说正邪对立的二元叙事以及大侠抗击邪恶拯救江湖的人生路径,都跟上古英雄史诗和神话传说的主题并无二致。其实按照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的分析来看,世界文学本就是一个整体。弗莱按照人物行动能力的高低,把文学分为神话、浪漫英雄传奇、高模仿、低模仿、讽刺五个循环阶段。该循环模式尽管遭人诟病,不过它所提示的英雄传奇与神话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却是值得注意的。神话不仅是原型批评的起始,也是一切文学原型的发端。中国武侠本就跟神话以及英雄传奇密切关联,把武侠的源头追溯到神话时代也不乏其人,这不仅因为“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15}而且“神话和传说中的古朴道义,崇高的报复,坦荡的心胸,壮烈的自我牺牲精神,深刻的复仇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在追求理想、正义的奋斗中的不计成败的坚毅姿态,都作为中华民族狭义精神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培养、滋润了中国武侠文学的成长。”{16}
如弗莱的循环模式所揭示的那样。武侠小说不仅可以看做神话的续接和变形,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直接是英雄传奇的一種。所以有人直接把武侠小说归结到“英雄侠义小说”这个类型中(如陈颖的《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毕竟侠客们“具有英雄所应具有的一切:力量、奇技、坚韧、善良、顽强、凶猛等等,同时也常常获得英雄所获得的崇高荣誉。”{17}除此之外,大侠与自然的关系与西方英雄传奇颇为类似。西方文学“浪漫故事的主人公(英雄)进入这样一种世界里:日常的自然规律多少被搁置一旁,对我们常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超凡的勇气和忍耐力,对浪漫英雄来说却是自然的。”{18}中国武侠小说中侠客的能力参差不齐,有武功高强能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也有武功不那么玄乎,但以一敌十的本领还是没问题的。更有一种仙侠,飞沙走石、撒豆成兵、御剑飞行无所不能,接近神仙。总之他们都处在高模仿以上而低于神话的阶段。侠客或英雄不像神那样完全脱离世界的规律,也不像普通人那样对世界无能为力,在他们身上多少还是有些自然规律“被搁置一旁”了,典型如轻功对重力原则的搁置。中国之武侠小说正好对应到西方浪漫英雄传奇。
不过以上分析只适用于在独立江湖行走的侠客,他们与早期神话英雄、史诗英雄可谓血肉相连,都身兼保卫邦国族群的神圣大任,这是责任也是权力。早期在官老爷身边转悠的侠客可以有正义感,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他们不必承担英雄和神祇的职责,这种责任是属于官老爷的,如包拯、施世纶等。仗剑天涯路遇不平之事,出不出手、救或不救全凭个人,纵然救得一时救不得一世,救得一人救不得一国。江湖独立后情况猛然大变,杀得了一人就能救得了天下。这一切当然归功于江湖的独立,但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武功。神祇英雄之所以能成为神祇英雄在于他们有特殊的能力或神性,他们有能力肩负保卫族群的重大责任。没有神性光环,所谓英雄不过一介凡人尔。武功在江湖世界必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武功是大侠权力和神性的最明显外化和根基,是行使保卫职责的最重要手段,“武功相当于原始人的巫术,是人类试图借助自身一些特殊的行为动作,来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去应对强大的异己力量。巫术,是力图用特定的仪式行为去获得神的帮助,战胜异己、自然或其他人群”。{19}所以它类似神祇的仙术道法,英雄的奇技伟力、祭司巫师的巫术。
武功如此重要,然而在早期武侠文本中侠客武艺不佳乃至对武功一窍不通也是事实,早期的侠主要强调侠之精神,有没有武功倒是其次,“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城,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参见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这说明“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方是真侠客,有没有高超武功并不重要。“古侠并不一定会技击,‘凡侠客必定武功高超,那是小说家制造的‘神话。游侠结私交、立声名,解缓急,赴厄难,重要的是‘古道热肠。而不是‘匹夫之勇。”{20}这说明武功在独立江湖世界的出场是其职责和神性的必然要求。
武功让大侠们飞檐走壁,体格精壮,以一敌十。甚至是涉水浴火,返老还童,更夸张的是能起死回生,老而成妖。这些能力正是神性的体现。武功具备神性特征还在于它俨然已经超出“技击”、“搏斗”的范畴,明显具备一种神性职责或杜撰一词表之——巫术职责。祭司使用巫术,其目的是祈求用某种仪式对部落的生存产生有利影响,如降雨、捕猎成功、部落平安等等,祭司一般不会滥用巫术。大侠同样不会滥用武功,武功的出场意味着与恶人搏斗,目的是为了肃清江湖败类,还江湖世界以安宁。如同先民依靠巫术来维系对自然世界的干预,保证自然顺从己意,在武侠世界正邪对立的基本设定中,江湖的稳定也只能依赖于大侠高超的武功,这正是大侠武功神性的真正作用,一旦其武功不足以保证江湖稳定或者他自己蜕变成邪恶势力,那么江湖的平衡被打破,这就势必要开启一轮类似针对国王或巫师的更新仪式。
维护江湖稳定的终极手段是武功,祸乱江湖的终极武器也必是武功,大侠武功的高低关系整个江湖,影响整个武林。典型之处是武侠小说对武功秘籍的神性渲染,如葵花宝典、九阳神功之类。邪恶侠客练成了绝世神功(如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将有统一江湖的实力,正义侠客练成绝世神功(如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才可拯救天下。通常两者会来一个大对决,然后正义侠客大获全胜。对决既显现了神性转移的仪式,也表明了神性维护江湖稳定的巨大作用。如同原始社会中旧国王、旧祭司被新国王、新祭司所取代,人的替代本身只是表象,祭司所代表的神性及职责并没有增多或减少,只是从一个躯体转到另一个躯体。同样一个大侠对另一个大侠的战胜也是表象,武功的神性本质和职责依然没变。武功高强的坏人一日不死,江湖便一日不得安宁。试想身居反派之位的东方不败(笑傲江湖)、逍遥侯(萧十一郎)、雄霸(风云)等若不是有着惊世骇俗的高强武功,哪有这么许多江湖的血雨腥风。而那些武功令人望尘莫及却并没有祸乱江湖的绝顶高手,只因他们不是死亡便是归隐,如金蛇郎君(碧血剑)、中神通王重阳(射雕英雄传)、少林扫地僧(天龙八部)、独孤求败(神雕侠侣)等等。
四、“侠之大者”的英雄职责
要求其神性的死亡更新
当代武侠文本中的大侠之所以获得与英雄等同的地位和职责,不仅在于他是独立江湖的权力者,也在于他具备神性(武功)光环,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否意味着权力者必然具备神性,对此有诸多人类学和历史学上的证明,只不过展现神性的手段不同罢了。通过简单考察,得以了解任何时代的权力始终与神性纠缠不清,在巫术和原始宗教时代,祭司酋长的权力神性体现在他通过巫术与万物神灵进行交往。文明时代的帝王贵胄,其神性要么体现为他们是神或神的一部分,如中国的天子,上天之子,仅从名字上就能辨认出神性的存在;要么体现在他们得到神的授权,如无论中外,古时的人们都认可君权神授观念。如果脱离神性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必然遭到质疑。任何权力的合法性必然都建基在神性之上。
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权力,权力的代表依次有,神(各种神,早期一般是动物神,如各种图腾)、祭司、部落英雄、国王、上帝、官僚(如中国的官僚阶层)等等。这些人正是文学最喜爱表现的对象。他们在文学上的对应时代,依次是神话、史诗、英雄传奇、清官戏等等。这些现实中亦是文本中的权力代表无疑都有神性特征。没有神性,权力便没有合法之基信服之力,也难怪历代创业君主,特别是草根帝王在坐稳江山之际都要编撰关于自己的神奇轶事,以此来证明自己天命神受。由此可见,大侠的神性和职责,让他不仅接连到神与英雄,更是直接打通与早期原始社会中巫师、祭司以及图腾神的关系。他们都承载着对应世界的保卫职责,他们权力的合法性都需要神性保证。但神性既带来权力,也蕴含与生俱来的风险,若权力者的神性不能保障部族的繁荣稳定,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也将不远了。如根据《金枝》丰富的记载可知,每当遇到天灾人祸,人们一般都会拿国王或酋长进行祭祀以求得神性更新。只不过这种祭祀仪式到了后来只是变成了一种徒有形式的仪式,成了泰勒所描述的“文化遗留物”,人们已然忘却其原初的意义和使命。
即使职责履行得不错,神性也必然内在地要求更新,这种更新的刚性需求建基在这样一对矛盾之中,神性是無限的,它是保证部落、家国、天下繁荣的基石。而现实中的权力承载者,只不过是凡夫俗子肉体凡胎,毕竟面临衰老和死亡。为了确保神性的永恒永在和效力不减,神性虽不灭却可以转移,可以由一个肉体转移到另一个肉体,当然是一个强壮的身体。因此,原始巫术先民决不允许神性承载者的自然死亡,神性的转移必须发生在其承载者还比较强健的状态下,否则这种神性必然受到老朽多病肉体的拖累而受损。这正是侠之大者在江湖的完整人生轨迹,从默默无闻到武功深不可测的至高巅峰,然后命运急转直下,不是步入死亡就是趋于归隐。不过在人类文明的不断演化过程中,这种必死于壮年的转移模式有所式微。
权力神性更新的最外在形态表现为崇拜——毁灭——再崇拜的过程。死亡正是毁灭环节最好的展示。从一些人类学中的资料中可以窥见原始人的权力更新到底有着怎样的仪式和步骤。弗雷泽在《金枝》开篇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意大利罗马的内米湖畔,人们随时可以折下一根树枝来挑战现有的“森林之王”,只要他能战胜现任祭祀并杀死他,就自然成为下一任“森林之王”。森林之王在被挑战杀死之前,人们虔敬地尊之为神,它是祭司也是王甚至是神,它是人们心中的权力。然而人们又可以随时去挑战这个“神”。在我们看来,“神”是被杀死了,然而在当地人看来,神没有被杀死,只是神性转移到了一个更为强壮有力的身躯中,这个身躯能保证神性更有效地发挥保护族群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神性更新的方式。根据《金枝》的丰富记载,人们可能因为发生灾变,可能因为神人衰老,甚至可能仅仅因为到了执政的时限,便处死现任国王或祭司。但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实用的目的,更新即将失效的神性,在先民看来,神性是确实的,神性转移也是必要的。也难怪巫术时代的先民们并不那么迫切地想做国王,即使坐上了也免不了整日担惊受怕。弗雷泽的一段描写精彩地道出这种承载权力的内心紧张。“他是一个祭司又是个谋杀者。他手持一柄出鞘的宝剑,不停地巡视着四周,像是在时刻堤防着敌人的袭击,而他要搜寻的那个人迟早总要杀死他并取代他的祭祀职位。这就是这儿圣殿的规定:一个祭司职位的候补者只有杀死祭司以后才能接替祭司的职位,直到他自己又被另外一个更强或更狡诈的人杀死为止。”{21}
大侠在独立江湖行走也会不断被人挑战,然后不断击败敌人,直到自己最后隐匿山林或战死敌手,否则这一过程将永不停止。寻找高手进行挑战然后夺取天下第一的称号在当代文学文本已是家常便饭,然而古侠若能复生定然会对这一举动表示匪夷所思。因为大侠背负了江湖世界的权力,负责维护江湖世界的安定繁荣。以原型角度来考察,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原型。荣格曾说“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22}权力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其有对应的神话形态和仪式形式也是理所应当的。
在各国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中都明显地体现出权力原型,很多神都会死而复生,如盛行于西亚的阿多尼斯、苏美尔的杜木兹、古埃及的奥西里斯等等,而且年复一年,很多史诗中的英雄们也是慷概赴死求得神性更新。权力原型的具体表现在不同时间点上总是有所不同的,正如弗莱所说它们是经过置换变形的,在不同的民族中被不同文化修改或扭曲。在中国比较明显的表现乃是贪官与清官的叙事模式。他们以文曲星、武曲星或青天大老爷的神性姿态降临,然后贪官总是被清官处罚,以此来体现权力神性的仪式更新。而到了现代,贪官与清官模式随着社会的前进,其影响力日渐衰微,但其新的表现形态却在武侠小说这一特殊的品种中异常活跃。
五、结语
侠隐流露着大侠无法与命运相抗衡的无奈。武功再高,若在江湖继续行走,注定也是命运戚戚。归隐是中国文化对权力原型负面特征的规避方式。但规避并非中国独有,各种文化中都有存在。甚至早在远古时期就在实践层面上展开,如寻找替代品,或把神性一分为二,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取代和战胜来完成仪式。如,某些部落领袖会找死囚当替罪羊,但这个人其实还是某种程度的自己。弗雷泽论述柬埔寨和暹罗人有找临时国王(一般是死囚)的习俗,临时国王虽只统治王国几天,但这几天内他确实拥有实权,死囚扮演的临时国王甚至可以和王妃们同寝。这种行为说明大家把这种代替看成是真实的,否则是无效的。几天后临时国王被处死,国王重回宝座。临时国王的出现在有些地方是周期固定的,在某些地方只是出于偶然需要,“临时国王是根据惯例,每年指定的。但在另外一些例子里,指定只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例如解救国王实际临头的灾难,把它转移给替身。从而让替身暂时代他为王。”{23}这些所谓紧急情况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国王职责的不到位,因而激起大家神性更新的渴望,临时国王才出来救场。不管怎样,文明兴起,规避开始,只不过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方式。
总之,没有独立江湖,武功也不会超出“技击”范畴而披上神性外衣,大侠们也无所谓安邦保土的职责,更不用担心自己的江湖地位(权力)被另一个不知何处而来的新侠客取代。如果江湖不独立,对于处庙堂之远的侠客而言,身在江湖就意味着远离权力远离纷争。江湖不仅不是是非之地,反而是侠客建功不成之后的终极退路。所以早期的侠客功成名就也好,生儿育女也罢,不过是底层人民的正当要求,又有谁会来要求他们承担一个完整世界的安定职责呢。只有当独立江湖诞生,大侠们才会岌岌有危机之感。
这种危机感与生俱来永远跟随,面对原型的心理势能,即使作者也有些无奈。如荣格所言,“它吞噬艺术家的个性,无情地奴役他去完成它的作品。”{24}虽然诸多作家都在试着去突破武侠小说的一些基本模式,但“侠文学漫长的历史和侠意象的原型意义,使读者对侠文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期待”,这种“阅读期待”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凡冠之以“侠”的文学,不能满足这种期待,读者的接受心理就会下意识地予以排斥。”{25}其实,侠隐的结局就已经显现人(当然是集体的人)在某种层面上的自由,它毕竟是一种主动姿态的规避,而不是无能为力的接受。
① 梁归智:《论武侠小说的基本模式》,《文艺争鸣》1989年第3期。
② 陳平原:《剑与侠——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1990年第1期。
③{17} 蔡翔:《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第9页。
④ 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⑤{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198页;第6页。
⑥{18} (加)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第4页。
⑦{14}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7页;第221页。
⑧⑨⑩{11}{12}{20}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第35页;第139页;第145页;第151页;第29页。
{13}{16}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第40页。
{19} 李欧:《在神话性中生存——当代武侠小说的深层内涵》,《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21}{23} (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上)》,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第289页。
{22}{24} (瑞)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第78页。
{25} 李欧:《论原型意象——侠的三个层面》,《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第4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Hero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surprisingly, meet with the same fate in that there is a unique aesthetic sameness in their turning into hermits and ending in death despite the fact that such unique hermitage and death are not normally seen with the heroes in the early texts as they are not only able to achieve success and follow the royalty but can also marry with kids after they achieve success, with hermitage or death attributable to the independent identification of the river-lake world, in which the heroes become the carriers of power from the bandits. When the knight-errants situated in the independent rivers and lak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qualities of the deities and heroes in the early myths, they have to perform the great duties of achieving peace in the rivers and lakes by dint of martial arts skills, completing such deeds either in death or in hermitage.
Keywords: Rivers and lakes, hermitage, death, daxia or knight-errants, sacredness,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