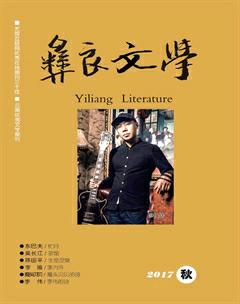生命涅槃
陈田平
我曾经问过自己,如果我不去启蒙读书,如智慧未启,我在老家的那一亩三分地上,成长、耕地、娶妻、生子、放牛,进行周而复始的本质轮回。
那也许是另外一种幸福,命运的轮子主导着宿命的因子,我的母亲还是坚持让我去上学,于是,我走过了我家门口的小河,翻过门口的大山,过童园、下寨、九里十三湾、坟场、马杠在新场中学上完初中,之后到县城上高中,在到昆明读大学,我离开了故乡, 抛弃了我的土地,羊群和牛。踏上了另外一条求学的路。
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后,乡下人面临着大城市人的复杂和贪婪,目睹了社会底层的辛酸苦辣,我收起我写诗的梦想,我努力地奋斗着,在丢了祖先给我本质之魂后。我总惦记在故乡行走的那些日子,苦难而单一,简单而幸福。有时觉得我的衣袍之地,我就像一个过客,记得一兄弟说的一样,他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背起背箩走进地里劈菜的那一瞬间,觉得人生是多么的幸福,有时,人在瞬间的幸福是可以终极的。
这些年,很少回故乡,她就只能是一个心中的一种特殊符号了,可我的父母还在哪里,我一直以为我装了我父亲的身体,窃取了我母亲的思想,我可以带着他们离开,其实,我是幼稚的,他们根本走不了,我却走了,我不知道离开故乡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灵魂。但我已经离开了,生活让我魂都没有了,整天混迹于一群丢了魂的形尸走肉中。
我一直努力找回我丢掉的魂。
其实,人生在世,如草木一秋,转眼间,半生已过,想想过去那些事情,虽历经苦难和磨难,生命重生过多次,有时想想,觉得挺不容易的,向死而生,我要找回我丢掉的魂,我知道,他就在我苦难的故乡,我的故乡在昭通彝良的山上,那里是一个贫穷的村子,生长苦难和幸福,记得小时候,家里穷,生活异常艰辛,姊妹多,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想吃肉得提前给爸爸妈妈申请,一个月能吃一次,可每次的肉及其少,我们兄妹几个吃完就没有了,我母亲就把碗底的油给我父亲拌饭吃,毕竟父亲是家里唯一的支柱,我不懂事的妹妹问我妈妈,妈妈,你怎么不吃肉,我母亲说道,妈妈不喜欢吃肉,妹妹信以为真,我看见妈妈把菜汤倒进装肉的碗里筭了喝了下去,我的父亲眼里布满血丝。
那是一段苦难的岁月,他成长我的童年,像那些草木一样的简单,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妈妈给我煮了一个鸡蛋,家里不管有多穷在儿女过生日的时候都得煮一个鸡蛋让过生日的儿女吃,我六岁的生日,我妈妈给我煮了鸡蛋,我最小的一个弟弟看见煮了鸡蛋一直在火炉边守着,像是自己过生日一样,可他只能看看,任其嘴里的清口水流淌,我和妈妈说多煮一个分弟弟吃一个,我妈妈说不行,煮一个分三弟,那另外的几个怎么办,家里就这两只母鸡在下蛋,好不容易积满10个那是要到集市上去卖了给家里买盐巴和灯油钱的,绝不能浪费。鸡蛋煮好了,我妈妈给剥皮的时候,想吃雞蛋想吃疯了的三弟起来开始抢夺母亲手里的鸡蛋,我妈妈怕他抢走鸡蛋就把鸡蛋给我,我刚拿着妈妈给我的鸡蛋的时候,我的三弟伸手过来就抓,三弟才两岁,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妈妈看着三弟要抢给我过生日的鸡蛋,过生日的鸡蛋是不能分别人吃的,必须一个的吃下去,她狠狠地给了她三儿子两个耳光,三弟被我妈妈打得嚎啕大哭,我在旁边吃鸡蛋,妈妈看着我吃完鸡蛋,她走过去抱着三弟,我看见妈妈眼里的泪水,我把最后一口咽完,我看见我的别的弟妹在捡地上的鸡蛋壳在嘴里舔着,添得很香,那是我人生中吃得最难忘的鸡蛋,参加工作后,我曾经有30天,几乎天天在吃鸡蛋,失去了以前的滋味。
生命像野草一样疯长着,那个时候的日子每天都是一样的,七岁开始上学,每天早上干完农活,跑步到学校听课,下午放学后继续干农活,生命就像是在跑圈圈,周而复始,在故乡,辛苦的故乡人,重复着简单而复杂的轮回,千百年不变。最苦的就是晚上要推磨,现在人估计连磨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见过,我和弟弟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要负责每天晚上推磨,磨玉米面第二天煮饭吃,我和我弟弟像两头小驴一样在黑夜中推磨,直到自己精疲力尽,呼呼大睡,多数时间我60多岁的奶奶也参加,奶奶主要负责添磨。
1992年,我考上了初中,家里弟弟妹妹全部开始上学,家里负担越来越重,我们一年只能买一次衣服,平时我们都不准穿鞋,除非是冬天,我们的脚上长了厚厚的茧子,一般的木刺都难以刺进去,裤子永远都打着补丁,除了过年那天,记忆犹新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不兴穿内裤,就穿一条寡裤子,任风霜穿透,记得有一次我被学校评了一个三好学生,我穿着一条没有橡皮筋的裤子,我在家找一根草绳系着去学校,我上台领奖的时候给大家敬礼的时候裤子离开草绳掉了下去,里面什么都没有,光着,台下面人声颤动,笑声不断,我在台上还以为是下面的同学在鼓掌,我正得意着给大家转动哈身体的时候我们校长赶紧把我的裤子提起来把我抱下演讲台,并告诉了我的父亲,当晚我父亲狠狠的揍我一顿,原因是我把裤子里面的橡皮筋拿出来做了弹弓。我睡觉后我妈妈连夜帮我补好了裤子,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学校的女生见我都在笑话我。
上初中后,我每周会回一次家,我每周回来都可以吃一顿肉,我在学校吃的就是现在猪吃的,我家离学校有半天的路程,记得,我们每个星期交两块钱的菜钱,家里背五斤半包谷面交在学校里,每天两顿饭,菜里没有半点油,偶尔有一顿油基本是漂汤油,里面的油珠珠都可以数清楚。我一般为了节约五毛钱吃早点,两毛钱一个的包子,我星期六放学后不吃饭直接回家,30里的路程,走不动了就开始数数,数我走过的九里十三湾有多少步,实在饿的不行了就用树枝刨地里的红薯充饥,到家里我的奶奶总是给我煮了好吃的,最好吃的就是猪脚杆坨坨了,我工作后得出的结论:那基本是我吃的终极价值,
艰难的初中生活,差点要了我的命,三年中我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我拖着几乎散架的躯体念完了初中,中考我考了200分的总分。
初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一年,这一年,我赶着牛放牧于故乡的山水间,我的身体开始恢复,开始从我军医外公家(我妈妈的姑妈)的厕所里偷他家用来擦屁股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来看,看了很多遍,我妈妈卖了家里的一头过年猪给我去县城报名让我复读,村里几乎所有人都劝我妈妈说:送他去读书还不如给他讨个媳妇,我的母亲还是坚持让我去复读,复读时我喜欢我们班一个叫红的女孩,我以为我努力读书考上中专就能娶她,可是中考她去了昭通读卫校,而我又因为年龄大了不能上中专,我又回家放牛,看故乡的蓝天,读不懂那些变换的云彩和那些岿然不动的大山,我又开始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故乡的天地间学会了手淫,我着迷一样的让那种怪异的液体射到那些远去的河水里,一种莫名的快感让我精神错乱,我像是丢了魂的人,我母亲看着日渐消瘦的身体,她送了一只我家的大公鸡给我的老师,让我去读了普通高中,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
读高中后,我的弟妹因为没有钱交学费无法在继续上学,他们辍学在家,我二弟独自一人来昆明打工,记得我收到他写给我的信的时候,我读得放声大哭,我的妹妹開始在县城打工挣钱给我读书,她每个月挣80元钱,她一分未用全部给我做我上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苦了我的妹妹。同时三弟也辍学在家,他还小,他想上学,他甚至求过我妈妈,可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给他上学了,我看见我三弟抹着眼泪说妈妈我不上了给大哥上,我看见我妈妈哭了,高中三年我的学习一直很好,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在读书,也许命运就是这样的不公平,他总是要这样的折磨我,我高三开始生病,病得很严重,吐了很多血,我当时以为我肯定活不成了,家里几乎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给我看病,我坚持上学,病魔折磨我的身体和心灵,我来来回回走在地狱里,活着只是一种存在,一种虚无飘渺的存在,我的妈妈为了照顾我累起一身的病,我看着自己这样,我放弃了读书的念头,那年高考,我未考上。
为了逃避,我离开了家参加修内昆铁路,在阴暗潮湿的隧道里我看懂了生死,我用瘦弱的身躯挣每一分钱,直到我的路费够了后我离开了工地,我到昆明打工,我没有告诉我的母亲及其家人,我难以从我高考的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我相信了命运。
昆明打工期间,我走在社会最底层,看惯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我开始拼命地看书,期间我读完了很多世界名著,当时最艰难的时候我和二弟饿得受不了就喝自来水充饥,昆明的自来水是最难喝的,氯气太重,连续两天喝自来水,走路都没有了力气,第三天老板给了我两百元生活费才买米煮饭。饥饿让人的意识处于一种饥荒状态,两年时间我读了太多的书,却一事无成,我依然决定回家参加高考,那年是2001年,我都23岁了,我悄悄回到老家,用打工挣的钱交了报考费,我昼伏夜出,怕别人看见我,通过两个月的复习我参加了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告诉我妈说我考上大学了,我妈妈眼泪都出来了。考上大学,又开始为我的大学学费发愁了,那么多的钱那里来,我妈妈每天天不亮就从家里背菜走十几里山路来县城卖,帮我赞学费,我们全村的邻居和亲戚不管多少都帮忙,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把学费筹齐,我数钱才发现那些全是零票,我数着眼睛都湿了。
非常不幸的是三弟就在我准备上学的时候他在砍猪草喂猪时手被机器扎了,两个拇指没有了,妈妈哭得最伤心,除了我的学费,家里没有一分钱了,我的学费已经打入学校账户没有办法取出来,车费又不能用,那时,我遇见了这个世界上的好人彝良县三角医院的宋医生,她出钱给我三弟做完手术,一直不要还钱,真是好人啊。
啃着故乡和亲人的骨头,我上了大学。
大学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间了,我像着魔一样地博览群书,努力的学习着,古的、中的、外的,黄的,情的、爱的,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我能找到的书,并完成了小说《原色》,以对故乡的眷念,这是2005年的事情,之后我就为了生计一直行走于云南各地,流浪他乡,即将完成的下一部书里写着对另外社会现象的痛诉。